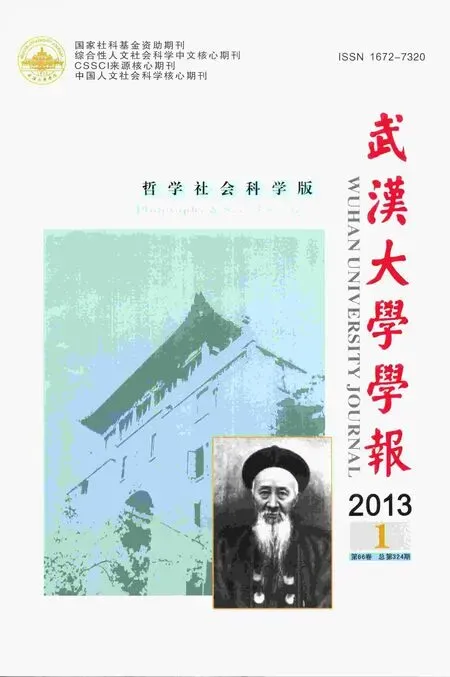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历史长卷与历史启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读后有感
2013-10-23李维武
李维武
正当人们对今天中国道德现状议论纷纷、忧心忡忡、揣测多多的时候,长期致力中国德育思想史研究的黄钊教授,为我们奉献了他潜心十年所完成的《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以下简称黄著)。这部近140万言的学术专著,以其强烈的历史感,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绚丽的历史长卷;又以其真切的现实感,为我们深入思考当今中国道德现状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正是在这种历史感与现实感交织之间,显示出黄著的学术性与思想性,也为读者进一步思考提供了空间。初读之后,深受教益,感想颇多,这里仅谈其中几点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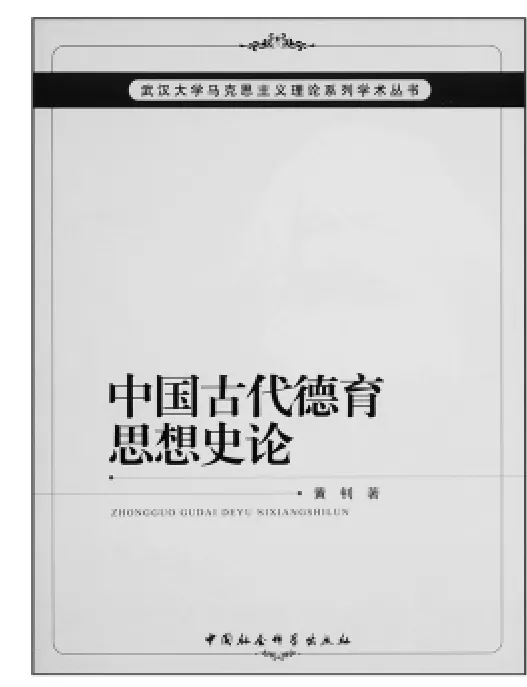
(一)考察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历史的通史眼光
黄钊教授的这部《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是一部中国古代德育思想通史著作。全书上起夏商时代中国德育观念的萌生,下至明清之际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德育新观念,对于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历史,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严肃的疏理和深入的反思,涉及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诸多人物、著述、学派、思潮,对其间的历史主线作了准确的揭示和把握,对其中的众多环节作了细致的阐明与诠释,既从总体上展示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流变历程,又从细节上描绘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精彩内容。这些都是黄著作为一部思想通史著作的优长之处。
当然,黄著作为一部优秀的思想通史著作更为值得肯定的优长之处,在于全书体现出了一种考察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历史的通史眼光。所谓思想史的通史眼光,不仅是指思想史家具有把握上下数千年思想历史的史识,而且更是指思想史家所具有的“通古今之变”的史观。这种“通古今之变”的史观,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即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和解读前人的思想历史,强调历史上的思想总是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而发展,不能把历史上的某种思想成果看做是凝固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东西;而这种思想的变化与发展,不仅是指在古代思想范围内的变化与发展,而且包含了由古代思想形态向近代思想形态的转化,由古代思想传统向现代思想传统的更新。因此,这种“通古今之变”的史观,最为关键的实是一个“变”字。一个优秀的思想史家,一部优秀的思想史著作,固然需要具有广博扎实的史识,但更为需要的则是这种“通古今之变”的史观,是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和解读前人的思想历史。在思想通史的写作中,只有具有了这样的史观,思想史家才能写作出真正优秀的思想通史著作。黄著之所以体现出一种考察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历史的通史眼光,究其原因,正在于此。
在黄著中,这种“通古今之变”的史观得到了自觉的领悟和把握,并将其贯穿于全书之中,融会于史论之间,通过考察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历史而鲜明地体现出来。对于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全部历史,黄著分为上中下三篇来加以论述:上篇论述先秦时期的德育思想,指出在这一时期中国德育学说从萌发到逐渐走向成熟,其思想成果对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德育思想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篇论述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德育思想,指出在这一时期中国德育思想随着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而有所发展、进步,在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社会批判思潮诸观念形态中得到不同的开展;下篇论述两宋至明清时期的德育思想,指出在这一时期随着封建专制的强化,以思想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亦相应得到加强,尤其是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思想体系的宋明道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其思想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由此而激发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以冲破宋明道学的禁锢作为自己的重大历史使命。由是观之,三篇之间自有一以贯之处,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历史作了一脉相承的展开;三篇之间又有转换区别处,即在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历史的一脉相承展开中实有一个“变”字贯穿于中。这样一来,黄著就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历史走向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和阐发。而只有经过这一深刻的解读和阐发,黄著才能说以通史眼光对于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历史主线有了准确的揭示和把握。
(二)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研究的古今通气
重视“古今通气”,强调通过对古代中国人思想的研究为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提供启迪和借鉴,是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先生所开创的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学科点的一个治学传统。黄钊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就读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在中国哲学史的学习上直接受教于萧、李、唐三先生,深受这一治学传统的熏陶感染,并将其自觉地贯穿于《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全书之中。用黄钊教授的话说,这叫做“吃透两头”,即深入探讨中国德育思想史的“古”与“今”两个方面,并使之贯通起来。
黄著在开篇的《导言》中,专门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研究的“古今通气”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阐发。黄著指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成果,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具有超阶级、超时代的特性,因而具有可继承性和借鉴性,不会因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对后人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今日中国人来说,不仅历史上进步思想家或进步阶级的德育成果具有可继承性和可借鉴性,而且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德育思想成果,也并非全是糟粕,其中仍然存在着可继承性和可借鉴性。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其意义不只是指向历史的,而且也是指向当代的。在黄著看来,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对当代的意义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有助于为社会主义德育提供历史借鉴;二是有助于今人陶冶情操、增强斗志、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三是有助于我们在现实斗争中明辨是非;四是有助于推进当代先进文化发展。这些理论上的阐发,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研究的“古今通气”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鲜明地显示出黄著的思想性。
在黄著中,这种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研究的“古今通气”,由于受篇幅和体例的限制,在表述上不可能充分展开,而多为点评式的论说。但正是这些点评式的论说,往往于三言两语之间,能够抓住关键,揭示本质,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构成了书中的思想亮点。
例如,黄著在论述《易传》的道德精神时,对这些精神所给予当代中国人的借鉴作用多有提示,指出:《易传》倡导的“自强不息”精神,对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不仅过去是我们民族抗御自然灾害、反对外敌入侵的力量源泉,而且今后也将是我国人民开拓进取、振兴中华的精神支柱;《易传》倡导的“居安思危”精神,不仅对于我们民族在历代应对灾难、防患难于未然的艰辛奋斗中产生过积极影响,即使在当今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有其重大的现实价值;《易传》倡导的“革故鼎新”精神,为我们民族突破守旧、大胆创新给予了积极的思想引导,至今仍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激励力量。
又如,黄著在论述西汉初思想家贾谊的民本思想时,对这些思想所给予后世治国安邦的启示作用多有肯定,指出:贾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民”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为思想道德教育成果,它不仅在当时对执政的西汉统治者有教育意义,而且在以后对历代统治阶级都有警示作用。
再如,黄著在论述东汉末思想家仲长统的社会批判思想时,强调了仲长统对民间迷信活动的批判在今天仍然有着启发作用,指出:在仲长统看来,那些巫婆、风水先生们,即所谓“图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贵富,而望其能致之于我,不亦惑乎!”这就说明,那些巫婆、风水先生们,完全是自欺欺人,我们不应受骗上当。这些见解,对于破除迷信,均有相当的说服力,即使到了今天,仍有可供借鉴的现实价值。
通过这些点评式的论说,黄著把中国德育思想史的“古”与“今”两个方面贯通起来,有效地实现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研究的“古今通气”。这样一来,黄著的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研究,就不再只是指向历史的,而且是同时指向当代的,从而赋予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以活力和生气,由历史的意义与价值转化出现时代的意义与价值。更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些三言两语的论说中,实表达了黄钊教授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思考,提示了当代中国道德建设需要注意、需要加强、需要下气力下工夫的地方,令人深思,促人警醒。关心今天中国道德现状的人们,如果能够对这些精彩的评论加以仔细的咀嚼,是可以从中获得宝贵的教益与启迪的。
(三)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研究的空间拓展
黄钊教授的这部《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一个很鲜明的优长之处,在于以很大的努力来拓展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研究的空间,从广度与深度上推进这一研究工作的开展。而要做到这些,就不仅需要从总体上揭示和把握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的主线,而且需要具体地阐明与诠释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的众多环节。换言之,只有在后一方面下了艰苦工夫,才能从广度与深度上切实推进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研究,拓展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研究的空间。在这方面,黄著着力甚大,用工甚勤,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下述几点尤显重要。
首先,对于中国历史上一些存在时间不长朝代中的德育思想,黄著没有加以忽略,而是予以了认真的发掘和论述。如二世而亡的秦王朝,以往在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没有位置,而黄著在第十一章《秦汉之际李斯、陆贾、贾谊的德育思想》中,以第一节《辅佐秦始皇推行法治的李斯的德育思想》,对秦代政治家李斯的德育思想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又如同样短命的隋王朝,以往也难以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地位,而黄著在第二十一章《隋至唐初儒道合流思潮中的德育思想》中,以第一节《重“化人之道”的王通的德育思想》,对隋代思想家王通的德育思想进行了专门的阐发。这样一来,黄著就从具体环节上丰富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的主线,使这一主线在脉络上更为清晰,在内容上更为完整。
其次,对于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的一些重要环节,黄著着重对其内涵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以两汉德育思想论,黄著共用五章篇幅进行了疏理与诠释:第十一章《秦汉之际李斯、陆贾、贾谊的德育思想》,第十二章《汉初黄老新道家的德育思想》,第十三章《汉代儒家学者的德育思想》,第十四章《东汉反神学思想家的德育思想》,第十五章《早期道教经典中的德育思想》。从这五章的题名上即可看出,黄著并没有把汉代德育思想开展局限在以儒家德育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范围内,而是力求从不同思潮入手揭示汉代德育思想开展的丰富内涵。在这五章之中,黄著又对一些以往思想史研究中涉及不多的汉代道家、道教文献,如《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指归》《老子想尔注》等,进行了细致的清理和阐发,将其中所包含的德育思想一一发掘出来。对于这些文献中的一些细节,如《老子河上公章句》和《老子想尔注》的作者问题,黄著进一步加以了考证,于旧说之外提出新见。通过这些层层展开、步步深入的具体论析,黄著使汉代德育思想开展原本丰富的内涵,得以从历史的遮蔽中充分显露出来,开始为今天的人们所认识和了解。
再次,除了重视对历史上重要思想家和思想著述进行探讨外,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有作为的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改革家的德育思想,黄著也同样予以了重视和阐释。如对于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黄著从职业道德的视角对其德育思想进行了阐发,认为孙思邈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发展的杰出贡献,在于全面论述乃至构建了我国古代医学道德理论,不仅对我国古代医学道德的开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古代整个职业道德的建设也起了奠基的作用。又如对于北宋著名改革家范仲淹,黄著从政治道德的视角对其德育思想予以了阐发,认为范仲淹在力主改革的同时倡导高尚的道德精神尤其值得推崇: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成为我国古代忧国忧民理念的千古绝唱;他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呼声,表达了他不畏人言、不怕打击、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是他作为改革家的道德精神的生动写照。黄著对这些人物德育思想的重视和阐释,使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的研究空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细心的读者如果能将黄著的这些论析,联系今天中国道德现状来加以思考,又必然会对如何看待和建设我们今天的职业道德和政治道德,获得一些新的体会与启迪。
当然,在肯定黄著这一优长的同时,也应当看到黄著在这方面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如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典籍中,就有大量关于德育思想的内容,只是这些内容在表述方式上,往往与一般的思想史著作不相同。中国古代历史学的特点,就在于通过对历史上人物活动及其事件的记录与评价,来为后世人们的行为提供规范、指示方向。古往今来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典籍中,实于历史记录之中蕴含着德育思想,具有教化功能。这一点,从先秦时期人们对《春秋》一书的评价中即可以清楚地看出。郭店楚简《六德》说:“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庄子·天下》亦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些文献都明确地谈到了《春秋》的德育思想与教化功能。而《孟子·滕文公下》则对《春秋》的德育思想与教化功能揭示得最为鲜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历史著述中讲名分、讲道德、讲教化,使中国人通过历史这面镜子,知道如何做人,知道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由此而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在这方面,黄著其实也有所注意和论及,如设专节论述了大史学家司马光的德育思想;但总的来看,还是感到相当薄弱,还是感到留下了很大的拓展空间。
正是这样,我们在祝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问世的同时,期待着黄钊教授在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研究中有更新的拓展和更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