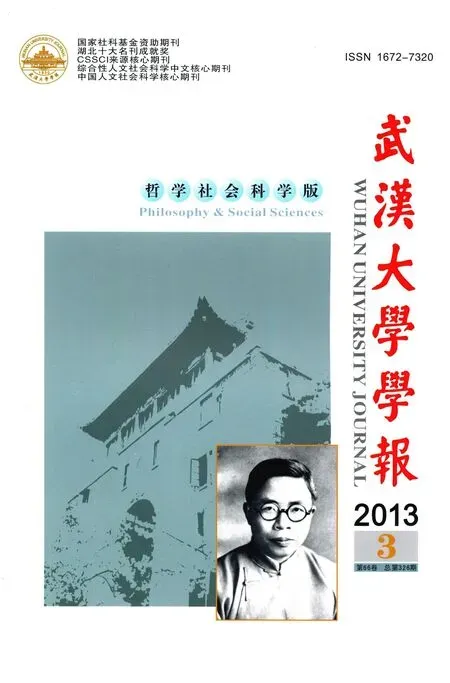民元时期的总统制到责任内阁制——政体理论在近代中国的文化重构
2013-03-18莫鹏
莫 鹏
政体是表现国家权力的一种形式,是实现国家权力的政治体制。辛亥首义后,为了巩固民主共和的胜利成果,革命党人对国家政体的制度设计作出了煞费苦心的安排。他们最初选择的是美国式的总统制,之后又变更为责任内阁制。从总统制到责任内阁制的变更,既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利益博弈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清楚地显示了传统一元权力观在民元时期对政体制度文化重构的轨迹。通过文化重构,政体的制度设计在观念和运作上发生变形,最终导向了既往的历史回复。
一、政体理论的原理及在近代中国的传入
政体理论是宪法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斯多德就曾对政体的概念作过经典的论述。在他看来,政体可以解释为:其一,“政体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的组织”①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29页。;其二,“‘政体’这个名词相同于‘公务团体’,而‘公务团体’就是每一城邦‘最高治权的执行者’”②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2~133页。;其三,“一个政体就是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③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82页。。因此,从亚里斯多德来看,政体是公职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亚里斯多德将政体分为正常与变态两大类:前者包括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后者包括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他认为,基于维护的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不同,正常政体与变态政体之间会发生相互转化。如君主政体蜕变为僭主政体,贵族政体蜕变为寡头政体,共和政体蜕变为平民政体。在亚里斯多德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所定义的政体概念主要是指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旨在表述政体是一种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制度性安排。需要指出的是,亚里斯多德尽管视政体为一种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制度性安排,并对政体职能作出了议事、行政和审判的划分,但他的政体概念始终没有涉及国家权力的分立与制衡问题①弗里德里希在研究亚里斯多德的宪政思想时明确指出,“没有提及对权力行使加以限制的必要”是亚里斯多德的宪法范式不具备现代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参见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三联书店1997年,第5页。。
亚里斯多德的政体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在后世的契约宪法观形成时期,他的思想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最终形成了系统的政体理论。需要阐明的是,这一时期洛克有关立法权与执行权的分权理论以及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政体,对政体理论的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述理论弥补了亚里斯多德的政体思想没有涉及权力分立与制衡的缺陷,使得政体理论的研究深入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探讨当中。此后,无论是谈及君主立宪制,还是总统制,或是责任内阁制,都不能绕开权力的分立与制衡这一原则。换而言之,任何政体的构建都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权力的分立与制衡遂成为政体理论不可或缺的内容。
自国家产生以来,中国就初步形成设官牧民的国家权力组织与分工的理论。这种理论表现为规定国家组织及国家机关职能权限等根本问题的一系列制度,散见于习惯法、礼、诏令等各种行为规范之中。如奴隶制三代就设有公卿相负责统率百官,总理日常国事,辅助王进行决策。秦王朝建立统一集权的中央王朝政权之后,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有关国家权力组织与运转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体系。如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唐代的三省六部制,明代的六部内阁制等等。正是以此为基础,历代王朝才顺利地实现了国家官僚机构的有序运转及国家权力的有效配置。然而,这些制度都是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皇权,所有的国家权力组织与分工都是在君主的绝对权威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国家根本不可能产生以权力分立与制衡为内涵的现代政体。出于维护长治久安的需要,中国尽管也曾形成过国家权力组织与分配的相关理论,但由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根本不具备产生政体理论的文化土壤。
政体理论移植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产物。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都是在近代通过法律移植由西方传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被卷入进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浪潮,清王朝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随之而来的是,传统的君主政体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最先是由一批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发出的。中法战争之后,以郑观应、陈炽等人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首先开始对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进行反思。他们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强盛并不在于船坚利炮,而在于先进的政治制度。于是,他们将国家富强与民族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对传统政治制度的变革,开始大规模地介绍西方议会制度,提倡君主立宪。这些思想对此后的维新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戊戌变法期间,以康有为等人为首的维新派提出了设议院、开国会、制宪法的主张,而其核心观点就是要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是,由于触及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戊戌变法并没有能够实践这种主张。从清末新政开始,随着统治危机的不断加剧,清王朝为了应对危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这种改革“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②严 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8页。,始终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可。直至《重大信条十九条》颁布,清王朝才匆忙宣布设置议会、实行君主立宪。但是,这一政治主张尚未来得及实施,清王朝就已经淹没在革命的洪流中了。
二、现代政体在民元时期的确立
西方政体理论是在清末传入中国的,但现代政体制度真正确立却是在民元时期。民元时期,围绕着各种势力集团的利益纷争,国家政体的选择经历了从总统制到责任内阁制的变更。
武昌首义打响反封建专制统治的第一枪后,仅仅一月之余,全国就有十余个省份宣布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而独立。尽管当时革命形势的风起云涌已经让清王朝政权岌岌可危,但真正迫使清帝逊位,进而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关键人物却是在袁世凯。武昌起义爆发后,迫于内外交困,清王朝不得不请袁世凯复出。袁世凯刚复出时只是统率海陆军并兼协理大臣,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成为受清王朝委托与革命党进行谈判的全权代表。这种身份的不断变化,使得袁世凯的社会威望急剧攀升。同时他又充分利用这种社会威望,一方面通过武装进攻不断给革命军施加压力,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又不断为清王朝制造危机,命令北洋新军暂停进攻革命军,企图胁迫清王朝接受和谈建议。最终,对于辛亥革命能否取得全国性的胜利,袁世凯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人物,在国内社会各阶层中无人能够取代。“以人才而论,新学界不乏坚卓环奇之士,然能操纵一切,在军事上、政治上之经验,威望素著,兼得外交上之信用者,无项城若。”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51~352页。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各种政治势力集团的普遍心声,社会各阶层已经把袁世凯当成了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的一个很重要的符号。要争取袁世凯赞成民主共和、推翻满清专制政权,革命党人能开出的最具诱惑力的条件莫过于大总统的职位。而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孙中山在此前的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到,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府,除效仿美国外,其他任何政体都不适用于中国。于是,各省都督府代表在汉口议决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确立总统制政体之时,也同时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选为临时大总统”②荆知仁:《中国立宪史》上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180页。。由此,总统制的国家政体得以确立。
通过政治妥协确立的总统制,为临时大总统配置了优势的权力。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大总统有统率全国之权、统率海陆军之权及任命文武官员之权,但制定官制官规及任命各部部长和外交专使须经参议院同意。同时,临时大总统行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之权以及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之权,也须经参议院同意。表面上看,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并没有特别之处,也要受到参议院的制约,但由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没有规定临时大总统的行为须受部长的限制,也未规定部长应对参议院负责,并且临时大总统的行为不受撤销审查,参议院几乎不可能制约临时大总统。
在总统制确立之初,临时大总统职位由孙中山暂代。但相比袁世凯,革命党人在军事上一败再败,在经济上一筹莫展,在社会威望上也远远不如。因此,对革命党人而言,在清帝逊位与当选总统执掌民国政权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推翻满清专制政权无疑是更优位的。武昌首义后,孙中山回国前曾与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在香港有过密谈。鉴于对袁世凯政治品格的怀疑,胡汉民曾建议孙中山应先到广东发展,等待时机成熟后再完成南北的统一。但是,孙中山认为作为革命领袖不能置身于事外,明确拒绝了胡汉民的建议。在他看来,“袁世凯诚不可信,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③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出版社1982年,第54页。。孙中山暂代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南京势同孤立,军队之隶编于陆军部者,虽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而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领,则素反对黄克强,不受命令,陆军部不能加以制裁。”④荆知仁:《中国立宪史》上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181~182页。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袁世凯不赞成共和,那么既无可用之兵又无可筹之饷的革命党人与之为敌,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为了实现推翻满清专制政权这一最高目标,革命党人不得不放弃临时大总统的职位。
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大总统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国家元首,放弃总统职位也就意味着放弃国家的中心权力。因此,革命党人在意识到必须要交出临时大总统职位的时候,开始计划以责任内阁制取代总统制,运用法律的手段限制袁世凯。出于这样的目的,革命党人通过《临时约法》精心设计了责任内阁制,试图将国家权力中心由总统手中转移到由总理及各部部长控制的内阁手中,利用参议院和内阁架空总统的权力,使总统成为礼仪元首。革命党人选择责任内阁制不是出于是否有利于国家权力有序运转和国家权力有效配置的考虑,而完全是为了限制袁世凯,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因此,《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为参议院配置了优势的权力。如《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列举的十二项参议院职权,没有一项受制于临时大总统。相反,临时大总统除了依照法律宣告戒严、接受外国使节以及颁发勋章等权力,其他权力的行使一律须经参议院的同意。这种权力失衡的政体设计显然违背了政体理论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则。
在政治集团的利益博弈下,民元时期先后建立起了总统制、责任内阁制的现代政体。从这一意义上看,由总统制到责任内阁制的政体变更,符合政体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制度安排的论断。但从更深层意义上看,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在观念和运作上发生变形,并没有体现西方政体理论应有的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宪政内涵。这与中国法律文化对政体理论的一元权力文化解读密切相关。
三、一元权力观的沉淀与支配
一元权力观的产生和存续受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和规定。传统的思维模式主要是以易经为代表的直观外推思维模式。这种模式按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的逻辑推导出“天道”派生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又分为阴阳两类。如天为阳、地为阴;君为阳,臣为阴。并且,规定阳尊阴卑,阴从属于阳。这就使得世界的统一性取代了世界的多样性,从而混淆了不同事物间的本质区别。传统的直观外推思维模式反映在国家权力的配置上就是一元权力观。运用传统直观思维方式来思考国家权力时,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要有一个至上而无约束的最高权力存在,以这个最高权力为原点自上而下地进行权力的分配①陈晓枫、易顶强:《略论传统直观思维范式下的近代中国宪政》,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4期。。它主要表现为君主上承天意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在此基础之上再由君主对国家权力进行逐级分配,形成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在这种政治权力结构中,君主虽然在理论上受制于“天道”,但由于“天道”的不可实证性,君主的权力实际上也就不受任何制约。
一元权力观的产生和发展还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中国深受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国家权力的配置上,首先强调君主是最高权力的主体,享有绝对的权威,其次才是在君主之下对百官的事权、职权的划分。可以说,整个国家权力都是围绕着君主进行组织、分配和运行的。元世祖所说的“中书省是朕左手,枢密院是朕右手,御史台是医朕两手的”②叶子奇:《草木子·杂制》,中华书局1959年,第31页。就是对此最形象的注解。浓厚的专制主义氛围为一元权力观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得这种价值观能够依附专制制度而存在。
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由督军妥协产生了临时政府,一元权力观原来所依附的制度体系已经消失殆尽,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元权力观也随之消亡。相反,中国由于数千年从未间断过的历史,早已在社会控制手段和方式上形成了稳定的传统。这种传统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凝结潜入中华民族的心理,从而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当旧的制度体系不再存续,这种传统就会通过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作用,依附于新的制度体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行法律制度的运行和法律效果的实现。“它通过将新的法律规范与旧的意识模式认同,使新制定的法律制度在整体的联系方面、以及社会实现的条件方面,受制于传统文化。”③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民元时期,国家政体的选择经历了从总统制到责任内阁制的变更。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从权力的构成来看,临时大总统的权力与美国宪法规定的总统权力相差不大。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总统制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之上,强调三权的分立与制衡,总统、国会、最高法院三个职能部门中任何一个职能部门的权力都不可能独大到不受制约。反观《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但在司法权的设置上只有“设立中央临时审判所”的只言片语,而且就其罗列的临时大总统和参议院的职权来看,也并没有为参议院制衡临时大总统提供有效地措施和手段,完全是临时大总统一权独大。可见,《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设计的政体,只不过是徒具总统制之名而不符总统制之实,实质上构建的仍然是一元权力体系。在这个权力体系中,临时大总统自洽圆融于权力的顶点,一元权力归诸于临时大总统。
《临时约法》中有关国家权力配置的规定同样是对一元权力观的诠释。从权力分工上看,强势的参议院与弱势的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责任内阁制的政体下,通常议会拥有立法权、监察权和财政权三项大的职权,行政机关则拥有任免权、军事权以及外交权等行政职权。议会和总统等行政机关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与之相对比,在《临时约法》的设计下,参议院的权力具有明显的优势,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的权力则大大受限。《临时约法》所明文列举的十二项参议院的职权,不但包括了立法权、监察权和财政权三项大的职权,而且还进一步挤压行政权。最明显之处莫过于《临时约法》的第三十四条,根据该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而按照各国惯例,无论是对国务员的任免权,还是对外交使节的任免权,都属于行政权的范畴,议会无权干预。因为“在采用责任内阁制的国家,行政元首之任用国务员,实际上虽不能不以议会多数的意志为标准,而形式上却无提经议会征求同意的手续。”①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3页。对外交人员的任免“当然以属诸行政元首为宜。”②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7页。
从权力制衡上看,由于一元权力观导致权力制约的单向性,从而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形成了参议院一权独大、三权失衡的现象。在《临时约法》中,权力制约的单向性主要表现为立法权对行政权和司法权单向制约,特别是参议院对临时大总统的制约。根据《临时约法》第三十三、三十四及三十五条的规定,临时大总统的“制定官制官规”权、“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权、“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权受到参议院同意权的限制。这是明文规定的参议院对临时大总统的制约。根据《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要受到国务员副署权的制约。表面上看,这只是行政权内部的制约机制,但考虑到参议院掌握了国务员的任免权,并拥有对国务员的弹劾权,该条实质上也就变相规定了参议院对临时大总统的制约。与上述规定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责任内阁制通行的内阁解散议会的权力及其它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制约在《临时约法》中却只字未提。此外,《临时约法》也未规定司法权对参议院的有效制约机制。
可见,这种以参议院的立法权为主导的政体设计虽然在外观形式上采用了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政原理,形成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权治理的局面,但是由于一元权力观的潜行作用,国家权力之间并没有形成相互制衡的有效机制,行政权、司法权完全从属于立法权。因此,这种政体是违背三权分立宪政精神的,实质上仍是一元权力观指导下的一元权力体系。只不过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相比,一元权力核心从临时大总统转而归诸于参议院。
综上所述,无论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确立的总统制,还是《临时约法》确立的责任内阁制,实质上都受一元权力观的支配。文化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当外来思想制度冲击原有的文化结构,为了适应潮流,文化的表层结构会率先发生变化,但文化的深层结构却非常稳定,仍然支配着文化的表层结构。民元时期,我们虽说在文化的表层结构上接受和移植了西方的政体学说和制度,但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上仍然受到一元权力观的支配。通过对政体理论的文化重构,我们实现了在表达西方宪政术语的同时,形成一元权力结构的目的。
经过民元时期国家政体的变更,中国进入了宪法极度虚置、极度文本浪漫化的时期。此后,袁世凯的中央政治会议,段祺瑞的安抚俱乐部,曹锟的假宪法,丑剧一幕幕不断上演。追本溯源,南京临时约法为始作俑者。在这种宪法极度虚置的过程中,中国人如何去寻找一种真实的控权结构,这已经不是政体概念可容纳的,主要是通过列宁主义的以党控军、以党控政的政党集权方式完成的。国民党一大直接宣布以党训政,此时的政体概念已经脱离了西方宪法中政体的含义,完全是一种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以一党集权作为最高的权力来源,政府和议会服从党的权威的领导,向党负责,一直到四七宪法,虚化国家主权机关国民代表大会,加强各个行政部门职权,并且在国民代表大会组织中,安排一党权威为核心的代表,实行集权式的控制。一元权力观经过了辛亥革命,经过了军阀对政体这个理念在构成要素上的改造,再经过列宁主义的传播,形成党军、党政高度一元化的体制。至此,基本完成了对政体概念的中国文化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