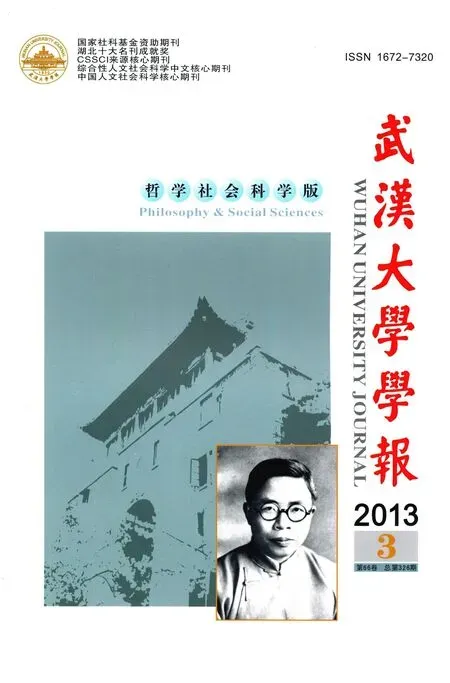“权力政治”下的“贸易法治”——对WTO法律体系的几点反思
2013-03-18黄志雄
曾 晖 黄志雄
在战后多边贸易体制过去60年的发展中,贸易规则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①早在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杰克逊教授就提出关贸总协定体系正在从“实力导向”向“规则导向”演进,这一观点现在已得到国际经济法学界的普遍接受。See John Jackson,The Crumbling Institutions of the Liberal Trade System,in Journal of World Trade Law,vol.12 (1978),pp.93~106;John Jackson,The World Trading System: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2ndedition),the MIT Press,1997,pp.109~111.。与这一走向相契合,从国际法治(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的视角对 WTO及其法律体系的探讨在近年来渐趋流行。最具代表性的也许是前WTO上诉机构成员巴克斯(James Bacchus)的以下观点:WTO在全世界越来越受关注,最重要的原因是WTO“第一次向世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确实存在可以被称为国际法的某种东西,以及确实存在国际法治”②James Bacchus,Groping Towards Grotius.“The WTO a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03,44,p.541.。国际法治的概念,无疑是理解国际法(包括作为其分支或子系统的WTO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个新视角。不过,现有关于WTO与国际法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对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是其上诉程序)加以分析③See e.g.James Bacchus,Groping Towards Grotius:“The WTO a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03,44,pp.533~550;Ernst-Ulrich Petersmann,How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Contributions b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ppellate Review Syste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1998,1,pp.25~48.。诚然,被称为“皇冠上的珍珠”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发挥着十分重要和独特的作用,但国际贸易关系的法治化(本文也称为“国际贸易法治”),终究难以同WTO体制乃至一般国际法的整体属性相切割。事实上,也只有借助对WTO和一般国际法的宏观审视,才能更为全面、客观地理解国际贸易法治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一、从关贸总协定到WTO:迈向国际法治
(一)关贸总协定——一个脆弱的法律体系
1948年1月1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下称“关贸总协定”或“总协定”)开始生效,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和组织框架由此诞生。总协定最初包括的3个部分、35条,大多属于该体制内最为核心的多边贸易规则,并在总协定随后举行的各轮多边贸易谈判中不断得到发展。多边贸易体制的设计树立起了国家间依循多边贸易规则开展国际贸易合作的新里程。
但不能不看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原本仅仅是正式成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ITO)之前填补真空的临时性过渡安排,从法律上讲,总协定并不是一个拥有国际法律人格的正式国际组织,甚至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条约,因而从一开始就在组织机构、法律效力和地位等方面存在种种“先天不足”①See John Jackson:The World Trading System: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the MIT Press,1997,36~43.。从实质内容来看,总协定所包含的条文规定较为简单、模糊之处很多;有关规则的管辖范围也较为有限,不仅不涉及货物贸易之外的服务贸易等领域,而且农产品、纺织品等重要产品也事实上被排除在外。而从规则的适用来看,总协定并没有明确的争端解决条款和确定的争端解决程序。
除了上述“先天不足”,关贸总协定法律体系还面临着各种“后天”困扰,著名学者休德克(Robert E.Hudec)教授指出:理解关贸总协定法律体系的关键是认识到该法律体系的设计和运作被当作一种外交工具了,这突出表现在把“灵活性”作为首要关注,坚持法律的强制性压力应当以可控制的方式加以运用,以便在争端解决程序的每一阶段都留有操作空间;为了获得这种灵活性,总协定发展起了一系列形式和技巧来控制法律对确定裁决的追求,裁决(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并不是通常理解的终局结果,在某个结果出现之前没有哪个答案是最终的,即便到最后也难以确证②See id,p.17,p.75.。总协定秘书处在从1948-1983年的长时期内没有任何法律官员的职位,则是总协定运作中重外交、轻法律的另一表现。
综上,关贸总协定所承载的是一个脆弱的法律体系,换言之,总协定的有关发展只能说是处于萌芽阶段。
(二)WTO法律体系与国际贸易法治的发展
关贸总协定之乌拉圭回合,对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演变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该轮谈判不仅催生了一个有着国际法律人格的正式国际组织并设立了较为系统、健全的组织机构③参见《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8条、第4条之规定。,而且从管辖范围、实质内容、争端解决等方面对该体制所管辖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造,从而大大推动了贸易领域国际法治的发展。依照阿瑟·瓦茨爵士对国际法治内涵的阐释,可以看到:
第一,在WTO体制下,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确定性大大增加。从完整性来说,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文件》,包括《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附件为主干、共计29份单独法律文件、25份以上附加部长宣言、决定和谅解以及22500页的关税减让表组成的法律文件群,其规则体系之庞大和管辖范围之广在国际法领域都难有出其右者④被称为“海洋法典”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包括17个部分、320条、9个附件,可能是除 WTO法律体系之外规则数量较多、内容较为完整的国际法领域之一。。这套宏大的规则体系,仍通过后续的贸易谈判处于持续发展之中。从确定性上看,乌拉圭回合达成并经各国立法机关正式批准生效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所附各贸易协定,其正式国际条约的地位无可置疑,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作为临时适用的行政协定在国内法上地位较为低下的缺陷。而且,作为对关贸总协定法律体系较为系统地“编纂”和“进一步发展”的成果⑤关于国际法的“编纂”和“进一步发展”的含义,参见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第2版),第37页。,WTO法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条约法规则,而习惯法在WTO法律体系内极少存在,这种情况在国际法各主要分支中是不多见的,相比不成文的习惯法规则,成文的WTO法在确定性方面显然也更胜一筹。最后,与关贸总协定相比,WTO的有关规则内容更为详尽、完善,从而有助于在相关问题上提供更大的确定性⑥例如,关贸总协定关于保障措施仅有第19条(共3款)加以规定,在WTO体制内,除了这一条款(作为1994年《关贸总协定》的一部分)继续适用外,还有一个单独的《保障措施协定》(共14条)同时适用。。第二,法律面前的平等性在WTO法律体系内得到了更好的体现。这首先表现在,除了少数几个所谓的“诸边协定”外,WTO要求各成员必须以“一揽子协定”(package deal)的方式接受其他所有协定和全部条款,这就意味着,此前东京回合谈判允许各缔约方自愿选择是否接受某一所有协议(主要是关于非关税措施的各项“守则”)的情况不复存在,WTO成员在WTO规则体系内承担义务的范围是相同的。另外,总协定时期,发达国家利用其主导地位强行迫使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农产品、纺织品贸易自由化等问题长期游离于总协定体制之外,造成了世界贸易的严重扭曲。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农产品和纺织品两个领域的“回归”,这一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尽管在WTO体制下这两个领域通过《农产品协定》和《纺织品协定》仍然处于某种特殊地位)。
第三,WTO法律体系对大国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专断权予以有力制约。在国际贸易关系中,一些国家基于一己利益而无视共同确立的多边贸易规则的情况的确屡有出现。前文所述美、欧等国基于国内政治因素而强行迫使农产品和纺织品贸易游离于总协定体制之外,就是一个上升到体制层面的明显例证。作为一个建立在多边贸易规则基础上的贸易体制,必然要求对此加以有效控制。1995年《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明确要求:“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WTO《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下称“DSU”)第23条规定:“当成员寻求纠正违反义务情形或寻求纠正其他造成适用协定项下利益丧失或减损的情形,或寻求纠正妨碍适用协定任何目标的实现的情形时,它们应援用并遵守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根据WTO法的有关规定,可以认为,单边贸易措施(包括进行单边贸易报复)受到了较为明确、严格的约束①相关讨论可参见孔庆江:《浅论单边贸易措施的适法性》,载孙琬钟、孔庆江主编:《WTO理论和实践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当然,多边贸易体制内多边主义与大国单边主义的较量仍将长期存在②参见陈安:《美国单边主义对抗WTO多边主义的第三回合——“201条款”争端之法理探源和展望》,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第153~164页。。第四,WTO法律体系,特别是其争端解决机制的重大发展,显著地推动了贸易规则的有效实施。以“反向协商一致”(reverse consensus)决策规则为核心枢纽的这一机制,体现了高度的统一性和强制性,从而为WTO所管辖贸易规则的执行提供了有效的保障③余敏友等:《WTO争端解决机制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91页。。“反向协商一致”决策规则的引入,改变了关贸总协定时期被投诉方可以任意阻止投诉方请求设立专家组、通过专家组报告和获得报复授权等与法治要求明显抵触的情况。加上WTO成员应以“一揽子协定”方式接受WTO协定(包括DSU)的要求和DSU第23条关于各成员解决贸易争端“应援用并遵守本谅解的规则和程序”的规定,WTO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确立了其在处理各成员间贸易争端方面的强制管辖权。与一般国际法上国际司法机构原则上以各当事方自愿为基础行使管辖权的情况相比,这可以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突破④例如,参见《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关于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的规定。当然,从根本上说,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处理成员间贸易争端方面的强制管辖权仍然是WTO成员自愿WTO规则体系的结果,所谓强制管辖,是指任何已加入WTO的成员既不能一般地也不能基于个案排除该机制的管辖权。。以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程序中关于授权报复的实践为基础,WTO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规定了胜诉方经授权可以对拒不遵守生效裁决的败诉方进行“交叉报复”,从而加大了对违反义务成员的威慑力和制裁的有效性。此外,DSU第一次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规定了上诉审查程序,这不仅有助于加强WTO争端解决报告的权威性,也是该机制向较为成熟的国内司法机制靠拢的一个表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述发展,使之呈现出若干有别于现有大多数国际司法或准司法机制的突出特征(或者说是某种程度上的超前性),并成为WTO法推动国际贸易法治的强有力因素。
由此可见,与国际关系领域相比,国际贸易中的法治化状况已经表现出某种超前性。上述法治化发展,其核心是对权力(特别是强权)的抑制和对规则的推崇,这为国际贸易关系提供必不可少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对于抑制贸易领域的霸权主义、保护弱小国家的利益意义重大。但不能不看到,在WTO的运作中,权力政治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因素。
二、“成员主导”:挥之不去的权力政治
在WTO官方出版物《贸易走向未来》中,对“到底是谁的WTO?”作了这样的解释:“WTO是由成员国政府管理的。所有重大的决定都是由全体成员共同作出的,或者是由各国部长在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会议上,或者是由各国官员在日内瓦定期召开的会议上。……如果说WTO的规则将纪律施加于各国政策之上,那是指WTO成员间通过谈判达成的结果。成员自己根据谈判议定的程序执行WTO规则,有时执行还包括威胁采取贸易制裁。但是,这些制裁都是有关成员实施的,而不是WTO本身。”⑤WTO,Trading into the Future,资料来源: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0_e.htm,2000-12-06,访问日期为2009年1月13日。。在WTO其他各种正式文件中,也一再强调WTO是一个“成员主导”(member-driven)的组织。
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目的是为各国提供一套协调贸易关系的规则体系,无论是WTO还是作为事实上国际组织的关贸总协定,从根本上说仅仅是负责提供一个“论坛”(forum)或“共同机构框架”,为其成员间...的贸易关系服务。因此,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WTO的活动并共同作出有关决定,正是WTO上述属性的自然反映和合理的逻辑结果。但是,在WTO成员的贸易实力和参与能力还存在明显差别的情况下,“成员主导”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权力政治的温床——各成员在WTO内对本国利益的维护,是以自身实力特别是谈判实力(bargaining power)⑥一般认为,一国在WTO中的谈判实力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市场份额;对本国和他国经贸信息进行分析和加以应对的能力;联络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联盟的能力;有关国内贸易政策制定和谈判授权等问题的国内机制。See Peter Drahos,When the Weak Bargain with the Strong:Negotiation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vol.8(2003),pp.82~84.为基础的;其结果是,不同成员间的实力不均得以在WTO的运作中得到直接反映,最强大的成员拥有最好的资源并有能力通过谈判得到它们想要的结果⑦See A.Narlikar,WTO Decision-Mak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South Center T.R.A.D.E.Working Paper),p.8,资料来源:http://www.southcentre.org/publications/wtodecis/workingpapers11.pdf,访问日期为2008年12月24日。。这一点,在WTO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决策规则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⑧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及其注释1的规定,WTO应继续沿用1947年关贸总协定以“协商一致”(consensus)进行决策的惯例;具体来说,在提交讨论事项的会议上,如果到会的成员都不对该项拟作出的决定正式提出反对,就视为该机构以协商一致作出了决定。。固然,协商一致规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依此种方法作出的决定将获得所有成员的接受,并为各成员利益得到适当的考虑提供了一定的保证,但更重要的是,正如一位颇具影响的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该程序能够同时反映实力不平等的现实和主权平等在观念上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一种“组织化的虚伪”(organized hypocrisy),即主权平等和协商一致的程序假象被用作为针对各国民众的“表演”,以使WTO的谈判结果取得合法性,但大国借助协商一致获得“看不见的加权”,并在不同程度上主导着WTO的议程制定和谈判结果①R.H.Steinberg.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02,56,p.342,p.365.。换言之,WTO协商一致程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形式上的平等与实质上的寡头专制②F.Weiss.WTO Decision-Making:Is It Reformable?in Daniel L.M.Kennedy &James D.Southwick(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E.Hude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76.。
在笔者看来,权力政治对国际贸易法治的困扰,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表述。
1.对贸易法治的明显背离。例如,出于不同原因,某些成员在WTO法律体系内公然受到歧视待遇的做法仍然存在,这不仅与WTO的非歧视原则这一核心价值相抵触,也背离了各国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性和规则的统一适用这一国际法治的必然和基本要求。《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各种针对中国制定的歧视性条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一些主要成员出于对中国经济贸易迅速发展的担心,强行要求中国接受一系列所谓的“超 WTO”(WTO-plus)义务。这些涵盖中国的贸易管理体制(透明度、司法审查、地方政府、过渡性审议)、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承诺)以及投资领域(投资措施和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国民待遇)的特殊条款,阐释、扩展、修改或者背离了现有的WTO协定,其结果是使WTO的行为规则在适用于中国贸易时被显著修正了③Julia Ya Qin.“WTO-Plus”Oblig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egal System:An Appraisal of the China Accession Protocol,Journal of World Trade,2003,4,p.518.。少数大国滥用其主导地位,针对一个新成员要求其接受歧视性待遇的作法,导致了一种将WTO成员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局面,破坏了WTO规则的统一性。有学者就此指出:如果这一作法在今后的“入世”实践(如俄罗斯、乌克兰这样的主要转型国家的加入)中继续下去,WTO将会再次变成一个零散破碎的规则体系,并遭受这样一个体系曾给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带来的种种弊病④See id.。这一警告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2.贸易法治的“名存实亡”。WTO的一些规则即便符合法律的完整性、统一性和效力的加强等国际法治的表现形式,但却背离了更深层次的正义要求而与法治的目标背道而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所以纳入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新议题,作为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的市场领导者的美国跨国公司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并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在该自贸区内锁定了同样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并分化了拉美国家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的反对,另一方面通过国内立法在1988年制定了一个授权对被认为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单边贸易制裁的“特别301条款”,这迫使巴西不再反对TRIPS协议而印度遭到孤立⑤Sylvia Ostry.The World Trading System:in the Fog of Uncertain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06,1,p.143.。以TRIPS协定为代表的这类规则,虽然从形式上推动了多边贸易规则的完整性和确定性,但它带给WTO成员的是“劫贫济富”、“抑弱扶强”而不是真正的贸易法治。
而且,在发展中国家要求有关新议题的协定应当以类似东京回合“守则”的方式由各国自愿决定是否接受时,美国谈判代表坚持认为发展中国家接受有关协定对于谈判成果获得国会的支持必不可少,同时希望消除东京回合“守则”带来的所谓“免费搭车”(free riding)问题。最终,美国和欧盟利用其谈判实力,联手逼迫发展中国家同意以“一揽子协定”通过最终成果⑥John H.Barton.The Evolution of the Trade Regime:Politics,Law,and Economics of the GATT and WTO,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p.65~66.。除了有关规则的公正性问题之外,“一揽子协定”的谈判方式还显著加大了WTO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商一致的难度,成为当前多哈回合谈判一再搁浅的一个重要原因⑦简单的逻辑就是:“协商一致”意味着只要有一个成员反对,决定就不能作出;“一揽子协议”意味着只要有一个议题不能达成协议,其他所有议题就都不能达成协议。两者综合起来,表明只要有一个成员对一个议题不能接受,全部谈判就不能达成协议。。这一点,从2008年7月WTO小型部长会议的失败得到了充分体现⑧此次会议是WTO为了力争在2008年底结束此前一再延期的多哈回合谈判进行的一次“冲刺“,但由于几个主要成员在农产品自由化的特殊产品等个别议题上存在分歧,会议最终仍无果而终。。可见,尽管“一揽子协定”理论上对加强WTO规则的统一适用和成员间的平等性有着重要意义,但在各成员发展水平和贸易利益的差异化还较为明显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有悖于与国际法治的目标。
3.贸易法治的“盲点”。不仅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多边贸易谈判受到了权力政治的明显影响,在WTO争端解决程序这一高度司法化的领域,也难免由于各成员间政治经济实力不平等而存在贸易法治无从着力的“盲点”。最为明显的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救济措施方面规定的是一种受害者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的“私力救济”,而由于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实力弱小,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很大,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贸易报复对于它们来说很难说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手段,当报复对象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大国时尤其如此。因此,这些国家在实践中往往会发现,“报复是多边贸易体制中一种自己成为被报复者比行使报复可能性更大的工具”⑨South Center,Issues Regarding the Review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p.12,资料来源:http://www.southcentre.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72%3Aissues-regarding-the-review-of-the-wto-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catid=63%3Aworld-trade-organization-governance&Itemid=67&lang=en,访问日期为2008年12月15日。。也就是说,在保障多边贸易规则的有效实施方面,实力的不对称实际上成为了贸易法治的“阿喀琉斯之踵”。
三、何去何从:几点思考和展望
综上所述,在充分肯定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贸易法治的积极成就的同时,对此也不应估计过高。迄今为止,WTO法律体系在本质上还是一种“贸易法治”与“权力政治”并存的独特生态:权力政治时隐时现的影响,仍是国际贸易法治一个无从回避的因素;距离理想状态的国际贸易法治,WTO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实,从根本上说,WTO法律体系在国际法治方面的上述局限性,问题并不在于WTO本身,而是由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决定的。在以高度分权和“无政府状态”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社会,一方面,国际法主要调整各主权国家的交往关系,另一方面,这种法律本身又主要依靠各主权国家(而不是任何世界政府)共同制定和实施。只要国际社会的上述基本特征不发生根本变化,国家实力与国际法的相互制约就必然是国际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条主线;而只要国际法仍然是一种“国际”法,就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也不可能超然于权力政治在各国相互关系中的运作。在特定情况下,国际法治甚至可能成为权力政治外表华丽的“包装”和附庸。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分析恰恰可以解释:日益走向法治化的WTO体制,为何在推动贸易谈判和多边合作方面陷入了不断加深的困境乃至危机①关于多边贸易体制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参见:Ann Capling.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t Risk?Three Challenges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in Ross P.Buckley(ed.),The WTO and the Doha Round:The Changing Face of World Trad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3,pp.37~58.?这也表明,国际法治本身是一种“治”(理)的方式或手段,无论对其内涵作何种界定,它归根结底要为特定的“目标价值”服务。在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日益深化的今天,WTO的使命应当是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 good),使各国得以在该体制提供的制度框架内化解问题,对全球化经济加以有效治理,包括纠正现有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衡性和不公正性,使更广大民众得以在这一进程中分享利益、减少风险②关于“全球公共物品”的进一步探讨,参见黄志雄:《战后多边贸易体制六十周年的反思与前瞻——以“全球公共物品”为视角》,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64~70页。。只有当“国际贸易法治”这一治理手段与上述目标价值相互协调、相辅相成,前者才能更好地成为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的工具。
由此,WTO及其法律体系的未来发展,应当着眼于消除权力政治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纠正以往重效率轻公平、重形式平等轻实质正义的倾向,最大限度地避免“成员主导”被异化为“大国主导”,并从实质正义和程序民主两方面加强WTO规则的正当性。就前者而言,如何促使WTO规则更好地与“分配正义”的要求相结合,使之真正反映全体成员而非少数大国的共同利益,是WTO推动国际贸易法治的一个重大挑战。就后者而言,在不具备取消协商一致规则的条件下,应当本着WTO体制和各成员的根本利益,以决策民主性和有效性两大价值为指导,稳妥而积极地加以改革。同时,有必要考虑采取加强WTO决策灵活性的其他措施,包括用各成员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接受的“诸边协定”(plurilateral agreements)适当限制“一揽子协议”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大国在WTO特别是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中,一再提议加强相关机制的灵活性和“成员控制”,例如:允许WTO争端解决机构通过协商一致决定不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的部分裁定;允许争端各方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中止已开始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程序而通过谈判寻求争端的解决,等等③Flexibility and Member Control.Revised Textual Proposal by 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Communication from 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TN/DS/W/89,31May 2007;Negotiations on Improvements and Clarifications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Further Contrib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Improving Flexibility and Member Control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TN/DS/W/82,24October 2005;Negotiations on Improvements and Clarifications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on Improving Flexibility and Member Control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Textual Contribution by 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N/DS/W/52,14March 2003.资料来源:http://www.wto.org,访问日期为2010年3月23日。。这些看似尊重争端各方意愿的措施,其实质是试图逆转WTO体制的法治化发展而重新回归权力政治的角逐,它将不可避免地赋予实力强大的一方向其他成员施加压力和影响的更大空间。与权力政治相比,贸易法治总体上更符合中小国家的利益和反映国际关系的进步,这是不可否认的。WTO未来的应有发展,只能是推动国际贸易法治的完善,而不是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潮流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