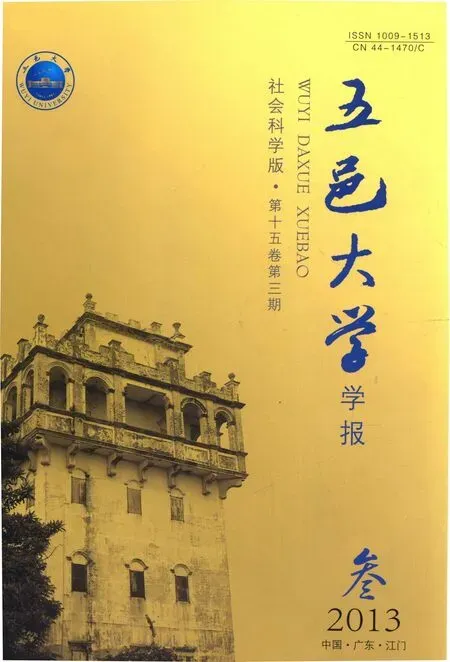梁启超社会公德思想简论
2013-03-18孟祥荣
孟祥荣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一
虽然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 “新民”是否就是“公民”还存有争议,但是梁启超把人的公德意识看作是 “新民”的核心素质,则是毫无疑义的。“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矣”。[1]14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具备了新道德——公德的国民,才是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民和能够振兴中华民族的合格国民。可以说,梁启超的公德 (新道德)思想,不仅是梁启超社会改革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在要求以及近现代国民性格改造的重要体现。何谓公德?梁启超的定义是:“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1]119这个定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就其本体言之,公德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中的人所具有的公共德性;另一方面,就其作用而言之,公德是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共同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公共观念或伦理共识中所引申出来的公共德性。在梁启超这里,公德既有就整个民族之公共德性的整体性,也有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所应该遵守的社会公共生活之道德准则与根基。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道德根基,才能够 “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人有公德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人之所以能群能为民族国家,公德的维系是关键。若无此,“人群”就只能是一个物群,而非真正的社会群体,也就只能是一盘散沙而毫无凝聚力;国家也只能是一个国民的集合体,而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更不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只有当国民都具备了 “公共之德性”,人人才能 “相善其群”,个人、群体、国家才可能形成强大的群体凝聚力,即 “无公德则不能团”。[1]12梁启超的 “公德”,是与所谓的 “私德”并举而论的。所谓公德,指的是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个人对于社会、群体、国家应尽的各种义务。梁启超称之为 “泰西新伦理”,将其定义为 “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的道德。而私德,则主要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道德意识以及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准则。梁启超把私德称为 “中国旧伦理”即 “家族伦理”。他说:“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1]12。也就是说,梁启超提出的私德公德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面的 “独善其身”是个人对自身的关系,即个体道德;“相善其群”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即社会道德。第二个层面则是基于交往对象或范围的不同,将私德和公德分别视为私人生活伦理和公共生活伦理。这里,“独善其身”和 “相善其群”分别成为私德和公德的最主要含义。梁启超认为公德的作用就是 “相善其群”,也只有那些“相善其群”的德性,才属于公德范畴。而 “相善其群”的具体体现就是 “为群”和 “利群”,因此“为群”和 “利群”就构成了公德的两大支柱。“群”在这里既指社会群体 (民族),又指国家之整体。“为群”是指公德具有使社会群体或国家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凝聚力的群体或整体的功能;而 “利群”是指公德有利于社会群体或国家的团结与进步、繁荣与富强。在这里梁启超注重的是国家之为国家所需要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的形成,需要的是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他强调:“公德之大目的,即在利群。”[1]15尽管每一个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不一,其所适用的道德规范也不相同,但这种道德力量必须要 “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为一群之公益而已”。“是故公德者,诸国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 (无益而有害者为大恶,无害也无益者为小恶),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1]15梁启超认为,“利群”之所以是道德成立之目的、根本与精神,能使社会或国家得到团结与巩固,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强大繁荣,是因为 “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1]12。这即是说,道德是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产生于一己之私利,因此道德本身产生的过程就蕴含了社会公德。“相善其群”作为公德的一种德性,其目的也最终体现在 “利群”上。如此,利群即成为衡量善恶的标准,“利群”则善,反之亦然。一种行为是善是恶,就看它是否 “利群”。而无论大恶小恶,在梁启超看来,都是不赦的行为。任何不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大恶不说,即便是 “无害亦无益”的小恶行为,也是不 “利群”的。因此,我们要使自己的行为是善的,就要使自己的行为“利群”,这样才是一个有公德的人,才是国家发展与强大所依仗的 “新民”。
二
但是,就中国长达几千年的道德形态而言,“私德”是远远超过 “公德”的。在梁启超眼里,甚至就是没有 “公德”的,是一种 “公德阙如”。因为 “公德”必须 “利群”,“利群”就必须爱国,爱国则必须首先要知道有国家,必须有国家思想。“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1]16在上述与国家的诸种关系中,“国家”始终是处在第一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 “公德”甚至可以和 “国家”划等号。不幸的是,中国的传统道德恰恰最缺乏国家思想。“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为虎,而自为其伥;其贤者亦仅以尧跖为主,而自为其刍狗也。”[1]18“吾中国人之缺点可得而论次矣,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2]总之,中国人只知族民,不知市民;只具村落家族思想,而无民族国家思想。所以他在对中国社会伦理进行归类分析的时候,“今试以中国的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 (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1]12。梁启超把中国传统伦理的 “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都归属于 “私德”,因为他们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尽管他也对之作了进一步的细分: “关于家族伦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者一,君臣也”,但是即便如属于 “社会伦理”的朋友关系和属于 “国家伦理”的君臣关系,都仍然不属于 “公德”。因为 “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何也?凡人对于社会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1]12。其原因仍在于要么是未尽社会义务,要么 “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仍不属于 “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意即与“利群”无关,所以仍然是 “私德”。既然传统伦理的 “五伦”都成了 “私德”,那么 “私德”岂不是成了一无是处的东西?自然不是。只不过他倾向于认为,私德同私人慎独、反省的生活相关,是一个人 “独善其身”的道德,如 “温良恭俭让”、“忠信笃敬”、“刚毅木讷”等等。[1]12私德的基本内涵就是“独善其身”,及 “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的道义”。私德的主要功能是提升个人修为和遵从家族伦理。所以他说,私德如粮,人人不可须臾离;无私德,无以立。但是仅有私德,则既不能完善独立之人格,亦不可能培养出国家意识和公德思想。这是因为,私德体现人的品性与自律,然人格之内涵不只是包含人的品性和自律,不只是 “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内省就可以达到的,它还包含价值、精神、心理、信仰等诸多的社会内容,而这些内容既源自人的自我认同,也来自人的社会认同。而只有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能更好地处理家国关系,才能更关注国家的命运,才能真正培育出公德之心。同时,传统之 “私德”由于过度重视家族伦理,导致 “家国同构”的恶性膨胀,从而也混乱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主要表现即在于以为对君尽忠就是在对国家尽义务,有家无国,以家为国,国家的社会组织结构等同于家族的宗法血缘结构。其恶果诚如刘师培所言,这种家族聚民传统,“导致民众上不与国接,中不与群接,仅受范于一族之中。以己身为家族之身,一若舍孝弟而外别无道德,舍家族而外别无义务。凡事于家族有利则经营恐后,凡事于家族有害则退避不前。人人能尽其家族伦理,即为完全无缺之人,而一群之公益,则无暇兼营”①。
尽管梁启超认为 “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1]12,从而使私德成为一个意义过于广泛的概念,让自己陷身于两难的境地,甚至构成一个 “梁启超问题”②,但是客观地说,梁启超对于 “公德”与 “私德”之关系的论述,还是非常辨证的。梁启超把公德与私德放在并行不悖的位置上,“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1]12。公德和私德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品德,二者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私德是公德之基础,“私德者,人人之粮,而不可须臾离者也”[1]130。欲新民德,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性,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1]119。因此,“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1]119。梁启超认为,私德能使人成为一个独立完善的人,只有当一个人具备完善的私德时,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才会具有公德;反之,即使组成一个群体,也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群体。“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故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性,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1]119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公德是私德的延续和发展。唯有 “合公私而兼善之”,民族才能兴旺,国家才能强盛。因此要塑造现代国民,还是要从培养私德开始,“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1]119。缺少公德不行,缺少私德亦不行,公德、私德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能依存,不能相离。“夫私人之所以自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其间必贵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虽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也。全体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1]13这也是梁启超建构的 “新民”伦理的两个必备条件。在这里,梁启超肯定了私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没有私德也很难成就公德,私德外推即为公德。“有私德淳美而公德尚多未完备,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1]119不过,梁启超把私德和公德的关系如此类推,实则失之简单了。现代很多学人都看到了这一点。“私德和公德虽然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和一致性,但私德和公德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应用在不同的领域。私德主要是解决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而公德是用以解决个人和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私德主要用以规范私人行为,公德主要用于规范个人在社会公共生活空间中的行为;私德主要用来提高个人的道德自觉性,而公德则用来提升个体的责任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两者在应用的领域、目标、价值判断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将私德直接外推即为公德显然是缺少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和说服力的。”[3]“私德外推即为公德”,“忽视了公德生成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规律性,是对公德与私德关系的一种简单化、表面化的理解”[4]。
三
关于梁启超 “公德”“私德”关系的思考,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 “梁启超在用西方资产阶级 ‘公德’批判中国传统 ‘私德’,他只批判中国传统 ‘私德’缺乏权利、自由、平等观念,他从来也没有批判过中国传统 ‘私德’中所包含家族伦理及个人品德等思想内容”[5]。刘兴邦先生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梁启超对孔子所讲的“五伦”、 “私德”不仅不否定,反而把 “五伦”、“私德”说成是平等的人际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私德”与西方资产阶级 “公德”相融互补性。梁氏对孟子的 “仁政”基础 “性善论”也作了同样的诠释,认为孟子 “仁政”思想基础的实质就是平等。从孔子的 “仁者爱人”到孟子的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道德原则。梁启超用中国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原则去诠释西方资产阶级伦理的平等原则,说明他在努力寻找中西伦理共同的普世价值原则。与此相关的一点是,梁启超肯定 “私德”,除了它自身有着值得肯定的价值和功能外,重要的还在于他所期待的具有泰西价值涵义的新 “公德”尚未建立之际,社会秩序尚需一种道德来维系,不能既无新 “公德”也无旧 “私德”。对此,他用了 “破坏”和“建设”来设喻。 “实则破坏与建设,相倚而不可离,而其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苟有所缺,则靡特建设不可得期,即破坏亦不可得望也。”[1]131社会不能处在一种没有道德规范的真空状态下,他甚至认为这种状况所带来的危害会比旧道德本身的危害更大。 “苟不尔者,则一病未去,他病复来,而后病必更难治于前病。故一切破坏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1]131因此,在新道德还未建立起来的时候维持社会秩序还要靠旧道德,“然则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1]132。
二是梁启超对于 “私德”与 “公德”关系的思考,有一个比较曲折而变化的过程。这可以从 《新民说》的写作中看出来。梁启超起初是把 “公德”作为重点来考虑的,所以其先写下了 《论公德》,所强调的是 “立新德”和 “道德革命”。而对旧道德的论述,多放在其弊端上,就其立场和态度而言,是很激进的。他要求以摧毁旧道德的代价来建立新道德,以为只要新道德一建立,中国国民性格和观念里的许多旧有的东西就可以革除,而国民的素质就可以很快提高,从而很快地适应新的社会体制。或许是因为其社会体制的变革并非如其设想的那样顺利进行,或许是后来重新回过头来梳理了旧道德,进一步发见了中国传统伦理的合理性,并认识到新道德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再写下 《论私德》,来论证私德自身的合理性和在公德建立过程中私德存在的必要性。而1903年梁启超访问美国,亲眼看到美国所奉行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个人主义伦理原则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危机,这也成为他由西方的 “公德”伦理向中国传统的 “私德”伦理回归的重要因素。由此,梁启超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内容儒家伦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写下了 《德育鉴》、《孔学论纲》、《孟子》、《儒家哲学》等一系列体现儒家 “私德”思想的著作。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不仅让梁启超自己认识到了文化传承的现实性和国民素质改造的长期性,也使后来人在对待 “私德”、“公德”的关系与评价上多了一份审慎。
梁启超公德思想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对 “公德”内涵的改造。西方新伦理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以及建立在个人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个人权利、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这也是所谓 “公德”的基本内涵。但是在中国, “公德”本就赋之阙如,加之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共伦理本就是以血亲为辐射中心放大扩展开来的亲族关系伦理,所以即使梁启超从 “五伦”中勉力区分出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也依然无法跳出 “私德”的范畴。如何建构一个用之 “新民”的 “公德”,并在改造公民素质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则对 “公德”涵义的界定和诠释就显得尤其重要。梁启超的意义在于,“他在对中国传统旧伦理进行批判时,不是用西方资产阶级伦理的个人主义原则去批判中国传统旧伦理,而是用建立在个人主义原则基础上的 “公德”去批判中国传统的旧伦理”[6]90。换句话说,即用西方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的 “公德”来济中国传统 “公德”之阙如。具体说来,就是在建构中国社会新 “公德”的时候,大量采纳和借鉴西方新伦理中的自由、平等、权利等思想元素。这也符合梁启超新民说要“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初衷。那么在新 “公德”的内涵建设中,梁启超究竟采纳了哪些 “本无”的东西呢?概言之,其一,要有自由意识。梁启超说,自由是十八九世纪欧美国家的国民立国的本原,中国虽与欧美等国有所不同,但自由之义,同样适合于中国。“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也。”[1]40梁启超把自由看成是人的天赋权利,是人的本质价值的体现。他说:“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所以人者有二大要件 :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之生命也。”[6]45梁启超大力倡导思想自由的原则:“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出也。”“文明之所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7]只是与西方新伦理所主张的个人自由是国家自由的前提不同,梁启超认为国家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前提,并进而认为自由就是国家自由,不是个人自由。 “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1]44这样,梁启超就把西方资产阶级立足于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个人权利、自由、平等完全变成了立足于团体基础上的国家权利、自由、平等,体现了与西方新伦理伦理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这也可见梁启超的新 “公德”虽然借鉴了西方新伦理的价值元素,其骨子里面所持的依然是传统中国的价值立场。其二,要有自治精神。自治之精神就是要有制裁,有秩序,有法律。梁启超认为,如果国民不能自治,则就会被别人统治。因此一国要自强于世界之上,就必须要有自治的精神。“群之自治之极也,举其群如一军队然,进则齐进,止则齐止。一群之公律罔不守,一群之公益罔不趋,一群之公责罔不尽,如是之人。如是之群,而不能自强立于世界者,吾未之闻也。不如是焉,而能自强立于世界者,吾未之闻也。”[1]52而中国之传统伦理,缺乏自治之精神,故导致现在的积贫积弱。要摆脱这种状况,就得有自治之精神。其三要有国家意识。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关心,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是公民的应有职责和美德。他认为培养国民的国家认同观念是中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近代国家思想体现为 “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故真爱国者 ,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1]16。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其四,要有权利思想和义务观念。梁启超针对当时国人毫无 “民权”的状况,提出 “权利思想”的概念。他大力倡导 “天生之人,权利平等”,要求 “新民”树立权利思想,敢于认定自己的权利,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与此同时,国家和政府也必须承认国民的权利,保护国民的权利。在梁启超看来:“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私人者,无论士焉、农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1]32强调 “权利思想”的同时,梁启超还强调个人要尽“义务”。他将个人与国家、己与群的关系,比作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国家给个人以权利,则个人有报效祖国的义务。如果人人都只知享受群体和国家给予的权利,却不知对群对国家尽自己的义务,则权利也就没有保障了。权利思想不只是国民自身对自己要尽义务,实际上更是国民自身对于社会和国家应尽的义务。因此梁启超认为,培养国民的权利与责任意识,是一件与国家民族利益相关的事情,是有利于社会与国家的事情,而这与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公德意识与公德素养是一致的。
虽然历史进程延展了100多年,但是梁启超的社会公德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的翻页而褪色。相反,他在 《新民说》中所希望实现的 “公德”建设,依旧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转引自赵炎才 《刘师培近代 “公德”“私德”思想述论》一文,载于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②参见廖申白 《论公民伦理——兼谈梁启超的 “公德”、“私德”问题》,载于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 [M].北京:中华书局,2008:121-124.
[3]吴蓉.梁启超的 “公德”“私德”观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2):83-86.
[4]程立涛,苏建勇.“私德外推即为公德”吗?——兼论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 [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2):54-58.
[5]刘兴邦.梁启超的 “新民”伦理与普世伦理 [J].伦理学研究,2010 (3):88-91.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 [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 [M].北京:中华书局,200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