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和+非常建筑:唯物主义
2013-0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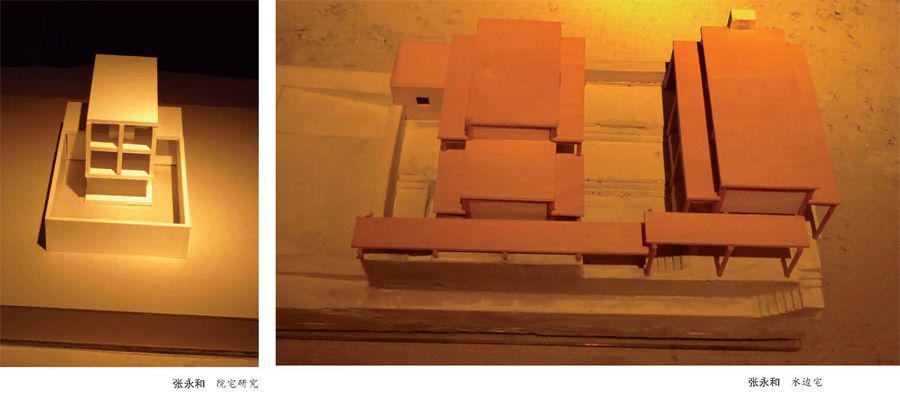

主持语:
张永和的作品在九十年代为闭塞的中国建筑学界引入一股新风,并一直坚持着实践。作为成功的建筑师,他的事务所培养了一大批当今活跃的独立青年建筑师。作为建筑教育者,他历任多所国内外建筑院校的教授、院长,为培养下一代建筑师作了不懈的努力。作为普利茨克奖及多个国际大奖的评委,他显示了中国建筑师的影响力。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影响力已经跨越了建筑本身,进而进入房地产界,乃至时尚和广泛的设计领域。
采访时间:2012年11月28日
采访地点: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受访人:张永和
采访人:田霏宇 陈 星
SHMJ:我想问一个最广泛的问题,您能给我们讲一下“非常建筑”这个展览背后的思路吗?
张永和:其实此时此刻我觉得好像说什么都是很多余的,其实看一下作品就明白了。这个展览既是个回顾展,也不是一个回顾展,为什么这么讲呢?说是回顾展,因为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最古老的作品有我在83年的时候画的图,快30年前了。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又不是一个典型的回顾展,是因为我把尤伦斯这个现场做成了非常巨大的装置。因为我想把“非常建筑”这样一种工作状态在UCCA展现。作为建筑师,我整天跟材料打交道,而且我觉得必须跟材料打交道,还要有想象力地和材料打交道才能真正做建筑。因此光画图,光在纸上和计算机上看到一些图形是无法真正把我们带入到一个真正的建筑师的工作状态,实际上我所描述的这种工作状态更接近于一个工匠。这次在UCCA的展厅,我实际上展现了6个不同的建造过程,这六个不同的建筑过程用了不同的建筑组合。我用了混凝土、石膏,还用了生土。混凝土有两套不同的模具,石膏也有不同的模具,夯土也有不同的模具。所以结合出来了六种完全不同的材料的质量。
SHMJ:我们聊这个展览的标题,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唯物主义”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哲学的词,但是它的英文material-ism的翻译还要考虑到那个“-”,这样这个词其实是有双重意义的,关于这个标题您是怎么选的?
张永和:其实可能是有三重的意义。我选用这个词,当然首先是出于这个词的英文本意。material-ism首先要有material这个材料。其实从建筑学的角度说,因为我们打交道的一定是可以触摸的,也就是看得见的世界,所以材料是首位的,它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基础。但是在中国有个很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在60年代到70年代,每天都能听到这个哲学概念叫“唯物主义”,我每天都被它困惑,因为当时是物质极大的匮乏的时代。缺少物质却还要谈唯物主义,我觉得非常不可理解,觉得“唯物主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到了今天,我还是感到很困惑,虽然如今的物质极大地丰富,好像又没有主义了!当然这个词还有一种理解:唯物主义的另外一个翻译是物质主义,它是针对市场经济来说的。
SHMJ:其实您最终主张的是材料主义?
张永和:对。可是我觉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物质主义是两者都不要偏废,因为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显然是很荒谬的,当然也不要忘记,除了物质以外还有其它的东西。所以我们展览里头大家最后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是有人用时髦的话说我是跨界,一方面是按传统的说法,认为我是不务正业,可能都对。除了这些,对于我来说还包含着一个“大文化计划”在里面。
SHMJ:转到一个具体些的问题,能不能讲一下展览里面摆出的那个装置,几年前在伦敦的维多利亚阿沃波特展览过。这个展览里,您提出了建筑里面的时间概念。那么,您可不可以通过时间来阐释建筑?
张永和:这个装置当时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非常晦涩。作品的材料实际上是大家都见过的,就是咱们中国到处看得到的停车场里植草的格子,可是放到伦敦的维艾町(音译)博物馆就变成了一个喝下午茶的地方。其实这个材料对我来说特别难看,它就是停车场的植草格子,所以我的出发点完全不是为了审美。我想在这儿解释一下,我也不是道德先生,什么浪费啊、污染啊,这不是我的工作。之所以采用它,我是觉得这个材料它平的时候可以受力,竖的时候也可以受力,构造是对称的,受力非常好。那我就在想,能不能利用这个材料受力的特性做点什么,我的工作方法就是弄了一堆植草格子,搭建成最后的这个装置。在这我想简单地加一句,做这种材料的试验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我们建筑师自己对材料的认识。当然后来顺着这个思路我又发现它可以百分之百回收、非常轻等特质。其实做所有的建筑项目,我觉得不应该为了一个孤立的原因,比如说好看或者难看而去做一个设计。
SHMJ:我想您的建筑实践包括你自己的个人生活史。其实您以北京这个城市的背景为一个比较主要的笔触来创作。是这样吗?如果您的建筑跟北京有关系,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永和:其实关系相当大。我小的时候住在四合院里,你去别人家串门就是到另外一个四合院,这些院子有大有小、有高有低,那会儿全北京城的房子长得都是一个样,从来没觉得千篇一律是个问题。后来我就觉得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每个房子一定要看上去不同。当然我也知道现在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欲望,就是要表达自身就等于要有一个独立的存在、独立的个性等等。
SHMJ:我再问一个问题,所谓建筑界跟艺术圈的跨界,作为一名建筑师对您有过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干扰吗?
张永和:我不太知道“跨界”这个词流行了多久了。我这样一个不务正业的建筑师有责任来对“跨界”这个词做出一些反映。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做的事情不是三年前才开始喜欢的,可能是三十年前我就喜欢了,所以没有这个风潮出现而影响到我的创作方向。事实上我从很小开始就喜欢美术,我念大学的时候想去学油画,可是我画得太差了,每个人看了我的画以后都说:“你千万别去考美术学院。”
SHMJ:不是您父母要求你去的?
张永和:不是,我父母根本不管我。我当时想学跟美术有关的学科,有个专业叫工业设计,相当于产品设计。可是我画得实在是不够好,因为当时学工业设计的人也要求画得非常好的,所以后来我就不得不放弃了。直到后来,大概是从98年、99年开始,我得到一些机会可以参加一些当代艺术展览,认识了很多艺术家,还有策展人,他们很多也是跟我年龄相当的中国人,后来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徐冰,他比我大一岁。有一次我去他纽约的家里做客,大家谈了很多,有一点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受益到今天。我们是经历过文革时期的人,他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从文革中受益了。因为文革,我们把权威在脑子里彻底打破了。他说的一点也不错,我们也很清楚地意识到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我跟很多年轻人接触,发现他们非常迷信权威,这个权威可以是明星、建筑师、艺术家,总之他们觉得很神秘。可是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不会相信有什么权威,最后只有回过来,一定程度上是信自己。
SHMJ:我刚才去展厅里面看了一下,您的作品里边用了很多材料,包括混凝土、钢筋、砖这些材料。我想请问一下这些材料在展览以后它们的命运是怎样的?是不是可以得到一种可循环的应用?
张永和:这些材料有的是可以的,有的是不可以的。因为我的这次展览要讨论的问题可能跟刚才讲到的植草格子一样,它最终的重心并不是在于探讨环保,而是在于探讨一些最常用的建筑技术提供的可能性,还有那些在今天看起来完全不着边际的建筑技术又会有什么新的可能出现,我想讨论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我用PVC管子做模板,虽然PVC管子现在到处都是,可是把它用来浇混凝土的模板我还没见过。我想用这种方式把这两种最普通材料结合起来,看看能够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质量,这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
SHMJ:您觉得建筑是否要以人为本?因为有一些建筑师认为,人应该去适应建筑,而不是要建筑去适应人。
张永和: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或许他认为建筑有那么严重,其实我觉得建筑没那么严重。建筑就是想把人的环境稍微改善一点。至于建筑是不是应该影响一个人日常的视觉,这个事实际上很微妙。我觉得像北京这座城市,如果某些建筑以某种形式给一个人带来了特别好的视觉经验,可能也无妨。可是视觉不是建筑的本质功能,建筑的功能就是很简单的舒适和便利。当然你也可以说,建筑应该上升成人的一种经验,但是这种经验不应该仅仅是视觉的,它也不仅仅是一个物体,它应该是空间,所以它跟时间也有关系。建筑强迫性地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的情况,我想肯定是有的。比如说监狱、疯人院等等,可能都是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更多的时候建筑是给人发出一个邀请:我设计了一个很好的院子,这时候你是不是就更愿意到室外?我设计了一个房子是让你愿意走楼梯上去等等。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走出去,选择不上楼梯。所以我觉得建筑师一定程度上都有一点强迫症,显然你刚才说到的那位建筑师比我的强迫症更厉害一点,我和他可以一起去看心理医生,哈哈哈哈。
SHMJ:我知道您近些年做了一些室内的设计项目,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做室内的设计和做建筑设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我还看到“非常建筑”这个展览里也做一些产品设计和家具,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张永和: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其实我做的室内设计还是很少的,室内设计真的开始偏设计了,因为建筑用设计作为一个工具,可是实际上它更工程,可能这个词用得不太对。建筑是一个组合式,把几个不同的体系整合在一起,使用的、空间的和结构的整合在一起,设计不是一个真正的主导。可是越到偏美术多一点的东西,工程性少一点的东西,实际上设计的含量就占得比较多了。其实我们平常挑选做的室内项目常常需要做比较大量的刚才提到的这种整合的工作,像这次展览里放的两个餐厅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的空间非常大,我们通过做室内设计去组合。还有一个例子,最近在北京有家餐馆想做软装,我们就遭遇到了建筑师的滑铁卢。软装包括摆设啊什么的,桌子上摆个花瓶、墙上贴个画都叫软装,实际上我们不会做,所以最后在包间里我在墙上画了张小漫画,那就变成了我的软装了。第二个问题又转回到跨界了,首先我想说一句挺长的话,听起来有点像建筑师的自大狂,实际上是这样的:在所有领域里涉及复杂程度都是不同的,其中最复杂的就是建筑,最简单的是平面。其实我跟平面设计师朋友也会谈到这个问题。实际上从建筑往下走是容易一点。在有些国家,像意大利,建筑教育相当于一门普及课程,你将来无论干什么都要学一点建筑。说完这个话并不意味着建筑师什么都能做,我们很幸运地跟很多人合作,包括设计公司、瓷器的专家、家具的专家、服装的专家。肯定有人想知道我为什么做建筑。最好的,也是最真实的一个答案就是喜欢嘛,当然也因为遇到机会。其实我自己的兴趣从来离日常的生活不远,所以我也对做玩具特别感兴趣。其实这说明什么呢?可能有的人工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他就对这个感兴趣,而我感兴趣的是每日的生活,在这个领域里面所有的事情,衣食住行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SHMJ:西方的建筑明显感觉到更轻盈、绿色、环保、注重空间感、视觉透视。看到您的展览更多的感觉是厚重、大气、沉着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刚才您说您今年56了,您经历过文革等等。那么您的作品有没有受到东方美学的影响?您的建筑美学的营养是从哪儿来的?
张永和:实际上我的教育过程是比较偏西方化的,因为我父亲比较“崇洋媚外”,哈哈!他把这个坏影响带给了我。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是对西方的这些古典音乐、古典绘画、古典文学特别喜爱和熟悉。后来去美国留学就开始接触到了现代艺术,我是非常感兴趣的。我的这个展览里有一幅小图,我估计你看到一定莫名其妙,名字是《一个伪科学家实验室》,它的创作灵感是哪儿来的呢?其实是从杜尚那来的。现代建筑里有很多奇思妙想,这个“伪”不是做一个非科学的科学去骗人,不是像中文里说的伪造的概念,而是根本没想去做真科学,只是把科学变成了一个想象力的源泉。这种影响一直到后来,特别是60年代的法国的电影、法国的文学、美国的视觉艺术等等都是我的最爱。但是也正是因为身处西方,我发现其实中国,包括视觉艺术、建筑等等其实真的与西方是不一样的,而且特别有意思。所以今天的我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我对很多中国的东西是非常感兴趣的,比如我现在就特别喜欢清末的绘本,我强烈给你推荐《红楼梦》绘本。但是我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节,甚至有些时候也不是很理解。所以我想总结一下:我觉得今天我个人要接受我自己实际上是不同文化的一个混合的产物,所以一定要强调我是中国人,我当然是!但是西方的影响每天都跟我生活在一起。
SHMJ:现在国际化趋势已经越来越强,想请教一下您,建筑师有没有地域性?面对现在的国际化,中国本土的建筑师应该如何应对?
张永和:实际上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建筑是有地域性的,为什么呢?他不像我们设计一件衣服,中国传统的长袍,西方的西装,它们在中国穿和在西方穿都有道理,到处都适用。可是房子有一些不同,它是长在地上的,这已经使得它在这样的气侯,这样的地理条件下跟其它的房子是不一样的了。中国有很多不同的生活习惯使得一个中国的公寓跟美国的公寓尽管看起来差不多,但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差异。所以可以这样说,一个对当地文化非常了解的人,即使他是中国人,他一定也比一个不熟悉当地文化的本土建筑师更有他的优势。现在中国建筑师的问题是没有特殊性,它们对中国传统与当代的文化不是缺乏了解,其中好多中国建筑师比我了解得多多了,他们是缺乏自信,所以使得很多中国建筑师的中国文化背景不发挥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缺乏自信,不太敢,也不太愿意去把中国的历史摆在桌面上作为自己工作参考的一部分。我讲一个故事,对我来说真是很感动,我认识一个日本的结构工程师,他搞的结构体系特别先进。这个人的爱好是唱传统的日本歌曲,他唱的时候还要换上传统的服饰,拿着一个架子演唱。我就觉得类似这种结合中国建筑师要多一点是一个好事,北京建筑师要是组织一个京剧的戏社我肯定第一个报名参加。我觉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的理解,是会有好处的。
SHMJ:您对您父亲张开济这一代老建筑人是什么看法?
张永和: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自己有一根古典的弦儿。受父亲的影响,古典的东西我早就知道了,是我最熟悉的。我自己觉得,我不应该做古典建筑,是因为时代变了,今天的生活方式变了、整个城市的环境变了,造房子的方法也变了。我觉得古典建筑,不论是西洋古典还是中国古典都没关系,已经都不适合现代生活了。可是实际上我对它非常熟悉。我父亲在中国培养出来的古典建筑师里面,是技巧非常高的一位。我跟着他看得多了,就会有感觉的。一般别人会觉得:“你那么喜欢古典,那你为什么不做古典?”其实根本不是这个道理,按照这个道理的话,毕加索还应该去画写实的画,杜尚也应该去做古典艺术,他的功力很好,都是从那儿过来的。对吧。
SHMJ:现在有人称您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之父”。您对“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这个议题本身怎么看?
张永和:现代主义建筑之父这名头我也不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这么说也有点偏颇。要说这个,真的应该看看当时真正把现代主义带到中国,开始进行现代主义的建筑设计方法实践的人,特别是华揽洪和林克明这两位。他们是很重要的,是真的称得上“之父”这种称呼的人物。而对于“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这样的讨论,现在最大的问题,倒不是不讨论,而是大家实际上只是看到建筑本身,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现代主义后来出现了跟古典主义一样的教条,出现了很明确的设计上的操作方式。但我根本就不认为是这样。因为现代主义后面有一些特别重要的社会议题,这才是特别值得咱们去想的事情。比方说,在德国,就像密斯、柯布他们都参与设计的一种住宅,叫工人住宅。在斯图加特有最出名的一个,“白房子”。它特别强调人性化,现在中产阶级的住宅区这种东西,就是从这种工人住宅开始的。在当时都是为工人阶级设计的。
SHMJ:但是在中国的城市里,最不缺乏的是各种钢筋水泥加玻璃的建筑。打着要为人服务的旗号,到最后却是一个又难看又难用,又不环保的钢筋水泥疙瘩。这种情况到底怎么破解?
张永和:这个是能够说得清楚的:城市的现代化跟建筑现代化根本不是一回事。城市是一个大的复杂的有机系统,它可以在某些方面来是组织、或者是重新组织,使得它能够满足现代人的生活。这里面包括了不仅仅是就业机会,创业机会,最重要的是健康、便利、节能、少污染等。有一系列具体的举措能力达到这种目标,可是因为这套东西很难跟政绩联系起来,所以各地的这些官员对它都毫无兴趣。造一条特别宽的、绿化特别好的大马路,别人都看得见。而你要说24小时服务的商业网点的密度不对了,这个政绩听起来就太没劲了(笑)。可是这样的事实际上对老百姓的生活改善非常大,今天此时此刻,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知道什么样是一个可居、宜居的城市。但就是让真正的决策者,掌握了资源和权利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又是比登天还难,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不是说我们很迷茫,不知道什么样的城市是宜居的,我们完全知道。
SHMJ:您是90年代回国的,正好碰上中国大拆除、大建造的浪潮。这么二十年过去了,您觉得在中国做一个建筑师最难的地方在哪儿?
张永和:实际上可能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因为在中国,建筑是市场主导的,往往是在跟地产商的市场部谈。而真正住房子的人,建筑师常常是接触不到的。地产商当然都在讲市场是什么样。其实,跟使用者的需要并不是一回事。
SHMJ:但是商业化就是这样。
张永和: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另外,一般的业主是不希望我们过多参与施工过程的。他觉得你就是出个主意,现场参与多了惹麻烦。除此以外,刚才已经提到了,现在的很多,咱们整个这套规范,不幸地反映了制定规范人对城市的理解,对建筑技术的了解等等。现在整个中国城市的生活质量有很大问题,又非常难改。因为规划者想象的一个城市,就是大宽马路,“哗哗”地跑车。这种规划实际上是反城市的,既无法步行,也无法骑车等。这问题出在国家那个层次上的一系列规范。有时候,大家看单体建筑可能好一点,一看到那个城市问题就很多。建筑师其实是无能为力的。
SHMJ:现在一提起现代主义有时候会招人反感。中国城市规划里的现代主义和您所说的现代主义,不是一回事。
张永和:关于现代有三个词: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化。大家觉得现代化就是一个抽水马桶、一个空调机、一辆汽车。它和“主义”没关系,跟“现代性”也没关系。它就是摩天楼,这是非常片断的。
SHMJ:是非常具体的、局部的。
张永和:实际上,在现代化生活中,人作为个体是有意义的,建筑牵涉到人应该居住在一个什么环境里等问题。所以现在中国有好多特别奇怪的建筑,一个现代主义建筑,如果它的一层是架空的,那它一定不能有大台阶。而现在许多机构建筑里仍然用大台阶吓唬人。这在真正的现代主义里其实就被干掉了。前面提到的工人住宅其实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它的天花板特别低,因为格罗皮乌斯(包豪斯学派创始人,现代设计创始人)他想到了一种特别人性的生活,他说,居住者一定要能够一抬手就换灯泡。当时人家是很严肃地想这个问题。
SHMJ:在这个时代里,一个身为知识分子的建筑师能做些什么呢?
张永和:其实很难做的,像我们这行,有各式各样的权力、势力都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但你常常做不到。可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就像一个医生一样,你一定要告诉病人你的病情是怎么样,不管病人自己怎么理解。他死活弄不清楚那你也没办法,可是你不能连说都不敢说。比如城市非要修宽马路,这就是不对,它不能解决交通问题,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作为一个建筑师,你应该把这句话说出来、说清楚。
SHMJ:听了您的见解,我们对建筑、对艺术又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再次感谢张老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张永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