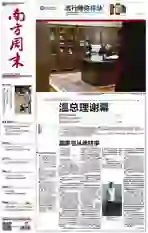红灯前的人群
2013-03-07
童明
几十年前,黑白电视机都还稀有,现代化还没有到中国。我生长其中的C市,楼房低矮,路灯昏暗,路上除了公交、卡车和吉普,多数人骑单车。清贫生活中的少年人毕竟是少年,喜欢骑单车追无轨电车,转弯时电车上的吊杆和电线碰撞出一串串的火花,好不兴奋!早晚碰上进城出城的马车,孩子们跳上去坐在马车尾部搭一程,车老大通常不甩鞭子警告,马车晃晃悠悠像摇篮,时常一坐就远了,误了回家的时间。
孩子会问长辈:现代化实现了是什么样子?大人心里根本没谱儿,用模糊的词语填补想象力:城里高楼林立,路上车水马龙,还有,食品不再定量。(末了的一句最有吸引力。)
回忆当中,过去显得不真实。有一次,见一位进城的农家少女,拦住城里的男孩问路。男孩说:看见前面亮红灯的路口了?过了红灯,直走就到。
少女谢过,一溜小跑向前去了。过一会儿,她跑回来,抓住男孩的衣袖说:兄弟兄弟,红灯变绿了,咋办?
男孩笑了,索性给姑娘带路,送她过了有交通灯的路口,这才挥手告别。
……终于,现代化来了。果然,食品不再定量,只是非常担心食品安全。果然,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钢筋水泥的森林里,难见日光和星光。马车看不见了,时而有铁皮的宝马现身。路上汽车不是多,是实在太多。路通时,车流是活水,堵塞了,就是死水。喇叭声此起彼伏,一潭死水里的蛙鸣。
车道上,人行道上,谋生的、谋财的、谋权的人都在赶路。走不动,谁也不让,越不让越走不动,人不怕车,车不怕人,车不怕车。
在C市,见到一种有特色的过马路方式。正常的情况是:绿灯亮,行人起步,从街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红灯亮,禁止通行,行人停下来等。有特色的方式是:红灯亮起,如果人少,我不走,不敢走;如果人多到一大群,大家视红灯而不见,一起过马路,车水马龙开过来也无所畏惧,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进!
交管不在,红灯亮又怎样。人群里,我不看别人,别人也不看我,正所谓目中无人。而且,目中无车。本该前行的汽车现在走不动了,喇叭声咽,人群里偶有勇者,会对驾车人做出奇异的手势。客气点儿的,轻轻拍拍你的车头说:哥们儿,别急呀。
红灯前的人群,大概不会存在于所有城市吧,但似乎也不限于C市。总之,初次见到令人瞠目结舌,多了居然见怪不怪。
于是想到欧美关于城市现代化和“人群”的文字叙述。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已经城市现代化,随之出现了许多我们今天才体会到的问题。比如,现代城市里两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雾霾和“人群”(crowd);人们对雾霾无法忽略,对“人群”却司空见惯,不以为意。在汉语目前的语境里,“人群”还没有贬义。但英语里的crowd并非没有贬义。如果译出来,似可造一词,称之为“盲众”。
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人”具有了工具和商品的特质。利益使人情淡薄,工具般的生活使个性差异消逝。简单说,人被异化。
“人性”消减,“人群”出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恩格斯曾对此表达了忧虑:“伦敦人为了创造他们城市里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点……人们彼此从身旁匆匆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对“人群”的厌恶、担忧乃至恐惧,在19世纪欧美文学中时有所见。雨果、爱伦坡、E.T.豪夫曼、波德莱尔等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探讨这个现象。
市民社会与“人群”有本质区别。市民社会是有机的群体,以真实的人际关系为基调。例如,我们去晨练、上课、朝拜、聚会、购物、理发时,通常有交流,也有个性的表达,佐证市民社会的存在。19世纪欧洲兴起社会主义,源于市民社会的事实。当社会主义走向空想之后,市民社会的实质被抽空。
“人群”(crowd)则是彼此不相干的人聚集在一起。其盲众特征和人的个性恰好相反。在变化和多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如能保持自己的判断,凸显自己的特征,发挥自己的作用,那是个性,符合人性的个性。但是,人很容易在融入“人群”那一刻,被成群的冷漠湮没,个性因为被同化而泯灭。一个人若长期保留“人群”的特征,渐渐丧失独立判断。
具有盲众特征的“人群”现象在当今社会屡见不鲜。闯红灯的人群几乎不足为道。而两岁的小悦悦被车碾过,唯拾荒的陈阿姨看见路上躺着受伤的悦悦,施以援手,可见人性和盲众截然相反。
细想之下,欧美哲学和文学中对“人群”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这种红灯前的“人群”现象。
西方的“人群”固然冷漠,见到红灯不会像我们这样有特色。据说,德国人遇到红灯,有车没车都等,而法国人看见红灯亮,如果没车有些人会横穿马路,有车过来却不会动。我们的现象(至少是C市)是:红灯亮了,车流也过来了,照样过马路,而且是一群人,必须是一群人,不如此不壮观。这样的“人群”,除冷漠之外,或许还有一些集体无意识的因素,试归纳为几种可能:
1.社会上的法则屡屡被蔑视、违反、践踏,已经形同虚设。红灯的法则又算什么。
2.有车族群中个别人太霸气,出现过无视行人安全和尊严的事件。潜意识里“人群”视所有的车主为霸王车主。
3.一群人顶着红灯过马路,法不敌众,还可以占个小便宜。
4.什么也没想,大家走,我也走。大家停,我也停。这是“人群”的惯性。
人群:有群无“人”。盲众:因盲而众。进一步推断:如果“人群”中出现“个性”,“人群”惯性即被打断,群中之“人”可能惊醒。
吾国之“人群”现象,至少部分原因可追溯到现代化之前的文化。封建专制的本质,只需要盲众,因而无情地压抑个性。鲁迅先生在他那个时代,对扼杀个性的“众”视为中国的弊病,深恶痛绝。他反的是封建。而以后,以后的事怎么说呢?不妨以“文革”为例。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全方位地淹没个性,把所有个人变成“人群”。那些往事,不堪回首。而往事的不堪,却不能用来反证今天就一定都是进步。忘记了“人”的现代化,应该不是进步。
今天种种的“人群”现象里,混合着封建压抑的后果和资本异化的效应。与“人群”闯红灯过马路相似的,还有:崇拜某些奢侈品的现代信众;追捧各种明星的“粉丝”群体;影视俗趣味节目引发的时尚潮流;还有不切题、无厚道、无知无智的网络讨论,人多而强辞,势众而夺理,如此等等。幸好,市民社会的土壤还在。以互联网为例,它既可以是“人群”的聚集,也可以是市民社会的新形式。当网友们幽默诙谐,切磋讨论,批评时弊之时,言论自然而然生,思想裕然卓然长。思想产生于个体,因其个性而有社会性。思想受保护而得以生长时,盲众消失。
(作者为加州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