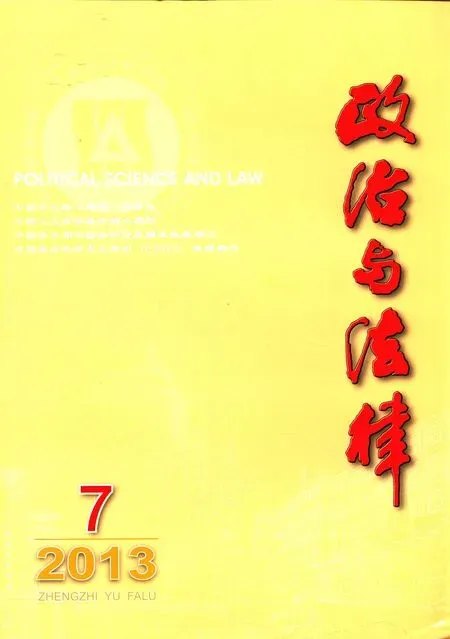强制缔约制度与经济法的契合性解读
2013-01-30翟艳
翟 艳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德国学者Biermann在1893年提出了“从法律强制到强制缔约”1的命题。德国学者Nipperdey阐述强制缔约的定义是“根据法律制度规范及其解释,为一个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在无权利主体意思拘束的情况下,使一个权利主体负担与该受益人签订具有特定内容或者应由中立方指定内容的合同的义务”。2台湾学者王泽鉴将强制缔约解释为“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易言之,即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承诺”3。邱聪智将强制缔约再区分为强制契约和契约强制,强制契约是法律规定强制承诺,使契约因一方之要约而成立;契约强制是以法律规定承诺义务,课违反者赔偿他方所受损害。强制契约不问承诺人意思如何,强制成立契约,契约强制尚不直接成立契约。4尹田研究了法国合同法中强制性合同的种类和适用的现象,而未深入进行法理解释。易军和宁红丽从私法社会化的角度对强制缔约制度的产生问题进行了阐述,此外还有崔建远、朱岩、冉克平等人对强制缔约制度进行具体研究,论证了其产生是近代民法的嬗变,是对契约自由和竞争自由的补充,是追求契约正义的结果。5德国学者维尔纳·弗卢沫甚至认为强制缔约是一种排除合同法的私法制度,6德国学者埃里希·莫利托对强制缔约制度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改革。7笔者认为,从传统民商法的角度无法自圆其说地解释强制缔约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坚持法社会化的观点、从经济法的角度才可以找到强制缔约制度存在的真谛。
一、强制缔约制度与经济法产生背景的同步性
国家经济职能的演变经历了从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的历史过程。18世纪以来,伴随着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市场配置资源,契约已经成为市场经济配置人力物资等各种资源的手段和工具,契约法也成为19世纪私法的核心。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生产和资本加速集中,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组织出现,原本经济地位和实力相对平等的主体,在市场社会化的推动下,出现畸形的实质不平等。这些垄断组织的形成就是把契约自由用到极致,滥用了契约自由的结果。他们通过操纵价格、排斥中小经营者等行为对市场进行垄断,限制竞争,或者从事不正当的竞争和其他不公平交易活动,获取高额的暴利,这些行为都是在“契约自由”的保护伞下,以形式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其结果导致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失灵,中小企业、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涌现,国家干预呼之欲出,国家职能不再仅仅局限于政治,还要调节私人经济生活。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和不断出现的社会失业现象,需要国家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对于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行为需要相应的法律依据,这就是经济法。8国家经济调节作为一种新的国家职能出现后,国家由原来主要关注统治阶级及其统治集团的政治统治利益,向为体现更多民众意志的社会利益服务方向转变。9国家调节经济的原因也在于实现民众的意志和服务社会利益,经济法的产生源于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出现。
强制性合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国家经济调节的职能和经济法独立部门的形成而在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中出现的法律现象。“一战”后,德国国内经济萧条,物质紧缺,政府为了尽快解决民生问题,使经济快速恢复,采取措施干预经济,这种国家强制意志体现在各个领域,指令性合同随处可见。德国最早出现的强制性合同(Zwangs vertrag)是命令契约(Difenl Vertrag),又称为指令性合同,这一名称由德国学者Hedemann所创10,在20世纪初是作为战争中国家统制社会经济的形式而被加以运用。国家机关利用命令契约的目的在于操纵私人之间的财货交易或分配活动,通过国家的意志来实现社会资源或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移转。11当时在德国,强制性合同都是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对合同自由的完全限制。在法国,伴随着垄断等各种阻碍市场机制的经济现象,强制性合同(contract imposé ou contract forc ē)在主体经济地位不平等、不能实现交易公平的合同领域中出现。“强制性合同是法国‘统制经济’即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一种经济模式的特征之一,是法国合同法在现代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2除此以外,在美国和英国,也出现了为保障社会大众的利益对契约自由进行的限制,例如美国某些州政府对火灾保险(fire insurance)契约的限定,美国联邦政府对海运提单条款的限定性规定,再如为防止经济权力过度集中,对于传播媒体(communications)、交通、银行、保险契约之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等的限定13,都是国家调节经济的典型表现。
可见,强制缔约制度的出现是在社会本位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推动下,国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弱者利益、实现社会公正的目的,通过国家经济调节职权对契约自由的限制;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在契约法中的折射,是经济法中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对调节微观经济行为的民商法的再调节。强制缔约制度的出现和经济法是相伴而生的,这绝对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强制缔约制度与经济法价值理念的同源性
法的价值包括自由、正义、公平、效率、秩序等,强制缔约制度在各项价值取向上和经济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经济法追求的自由是经济自由,国家是为了自由而干预、限制契约自由,而不是通过干预而限制乃至扼杀经济自由。14强制缔约是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对契约自由限制的具体内容包括:对是否缔约自由的限制和对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的限制,同时缔约人权利义务的可实现性是实现强制缔约义务的前提。强制缔约制度和经济法都是国家为了自由而调节,要实现的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为了实现社会大多数人的实质自由而进行的干预和调节,具有社会性的特点。若无法实现社会实质自由,作为社会中的个体自由根本无从谈起,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干预自由不是抛弃个人自由,而是基于社会利益的需要对个体自由和权利行使的调节,彰显社会受益权,两者并没有对立性的矛盾,而是要实现个人自由和实质自由的统一。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把正义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15形式正义要求法律给予人们平等的机会,所有人平等适用法律和制度;实质正义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实现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正义和公平,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给予人们结果的公平。16经济法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强调社会公平,追求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并兼顾结果公平,实现社会实质正义。在契约中要实现实质正义需要由个人本位主义转向社会本位,更多地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这种协调在遵从个人本位的民商法中很难实现,需要国家站在公正的第三方立场来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从而实现契约的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统一。限制契约自由成为现代国家经济调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强制缔约制度就是其手段,是实现契约实质正义而对契约自由的约束和补充;其不但避免了无限制契约自由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而且使契约自由和契约实质正义得到有机融合,维护了缔约各方的利益,实现了实质上的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是经济法优先选择的价值取向,涵盖竞争公平、发展公平、分配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经济法要实现的社会公平是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订立完成了各自的利益分配,这种初次利益的分配是合同当事人双方合意的结果,同时法律认可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力,即合同一旦生效当事人就要遵守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使相对方享有权利。这种经“权”确认后之“利”即为“权利”。17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市场调节失灵,很多垄断企业利用合同这一法律形式在权力的保护伞下获得更多利益,经济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合同作为市场经济循环中再生产要素流动的最基本法律形式已经无法实现当事人订立合同之初的目的。国家为维护市场秩序,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分配公平,对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施加特别的限制,强制缔约制度就是国家经济调节权力对合同权利干预的结果。当然,国家调节也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既非集权也非完全放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将政府对市场的全面管制权逐步削弱、减少,并依靠法律将其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使政府调节市场行为有法可依,将国家调节权法治化。18合同法对私权的保护是实现初级公平,国家经济调节之法(经济法)是通过对私权的合理干预实现高级公平,强制缔约制度是国家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分配公平的必然选择。
强制缔约制度的价值理念和经济法(国家调节职权)有着相同的内容和特点,都是通过对社会实质自由和正义的追求,为维护社会整体经济秩序,对个体利益和权利进行再分配而达到社会利益的交易公平和结果公平,以实现社会整体效率和长远利益(效率)。
三、强制缔约制度与经济法法律性质的同质性
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19除上文所述的价值、产生、属性等方面外,强制缔约的社会公共性还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强制缔约制度中的主体,不是普通的民事合同主体,主体或因经济优势地位,或因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承担着缔结强制性合同的义务;其二,强制缔约制度中的权力、权利和义务关系是国家为适应经济社会的要求,用国家权力之手,协调和平衡缔约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达到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公共利益整体性的和谐;其三,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责任人,不一定仅承担民事责任,其可能只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但有时可能只承担行政责任,有些情况下则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这种复合性责任体制是经济法独有的责任体制。可见,社会性是强制缔约制度最为显著的特征。
经济法是规范和保护国家经济调节行为而产生的。国家调节是经济法的显著特征,也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和各种特征的引发点和集中体现。20强制缔约是国家调节(经济法)渗透于民商法的产物。契约的缔结原本是属于民商法领域的范畴,但强制缔约不能简单归结于民商法领域,其已超越了民商法的界限。强制缔约是国家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手段,是国家利用经济调节权干预民事主体缔结合同的自由权利,是国家经济调节与市场调节机制的结合,体现了国家经济调节权力的强制性;强制缔约体现的是国家调节的目的,即通过国家职能活动调整、影响社会经济运行,从而达到国家意志和社会意志的统一;强制缔约的产生来源于国家对民众经济自由和权利的维护,表达的就是社会的意志,是国家经济权力对微观经济行为的限定与修正。
国家制定强制缔约制度首先关注微观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生产者、单个消费者、单个市场经济活动)的生产、销售、消费活动,再从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衡量单个经济单位的具体交易行为的合理性。当单个经济单位的市场交易行为出现经济利益失衡并不断累加,导致的是经济社会中某一类经济利益失衡方的不满,此时会出现经济结构的变化,甚至政治秩序的混乱。国家出于社会整体利益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开始关注宏观经济中国家“看得见的手”对这些经济交易活动的矫正。强制缔约制度从未迈出过经济领域,是微观经济领域中单个经济单位所承担的义务。强制缔约制度实际上是经济法在经济领域中对经济主体的具体经济行为进行调节的一种制度。强制缔约是国家经济调节权力对契约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限于某些领域和行业,而非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其主要干预的是提供社会民众生活和生存所必需的公用事业行业,对这些行业中单个契约自由的限制体现的是单个契约的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统一,而无数个契约自由的限制的累计就可实现整个社会整体的利益平衡和社会公平与稳定,这也是国家调节和经济法的最终目的。
总之,强制缔约制度和经济法都具有社会公共性、国家调节性和经济性这三种本质特征,反映的都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意志,要实现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实质公平,是国家调节职能直接作用于市场运行的表现。
四、强制缔约制度在经济法律体系中具有可衔接性法律制度
市场存在三种缺陷,包括市场障碍、市场唯利性和市场调节的被动性与滞后性,现代国家采用对市场强行干预、参与直接投资经营和对社会经济实行引导调控的三种基本方式调节社会经济。国家为了规范和保障这种国家调节,制定和实施三个方面的法律: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宏观调控法。21经济法体系下的上述三方面立法都有与强制缔约制度相衔接的具体法律制度。
(一)市场规制法与强制缔约制度
强制缔约制度与反垄断法的衔接主要体现在规制垄断企业滥用其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对中小企业进行的歧视性待遇上。垄断企业和组织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会排斥其他竞争者和损害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如果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其优势地位选择性地和部分相对人交易,那么另一些相对人就被排除在交易之外,完全失去了缔结契约的机会。这类行为包含剥削性的滥用和排他性的滥用,主要采取的手段有掠夺性定价、独家交易、价格歧视、垄断高价等,这些针对不同对象的交易行为都以买卖合同的形式实现。为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实现交易公平,在具体的交易过程中,国家(地区)会取消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或组织滥用契约自由的权利,施以强制缔约义务。例如,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0条规定“禁止在通常交易中以不公平的方式妨碍其他企业,或者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同类的企业给予差别待遇”。22该法第33条规定了违背禁止歧视义务的责任形式。我国《反垄断法》第3条概括列举了三种垄断行为,其中包括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该法第17条列举了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行为,如拒绝交易、价格歧视和限制其他经营者的选择自由的行为。再如我国台湾地区“电信法”要求电信事业市场主导者,不得拒绝其他第一类电信事业提出网路互连和租用网路元件之请求。强制缔约制度在这里的体现在于给予处于交易劣势的同行业者和交易相对人以公平交易的机会。
强制缔约制度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衔接,主要体现在使实施不正当交易行为者承担强制缔约的义务。具有经济优势的企业为追逐高额利润,往往会借契约自由之便,采取强制交易行为。强制缔约是对这种强制交易行为的再强制,这种再强制来源于国家经济调节权力,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否定前一个强制性契约的内容。低价销售或掠夺性的定价,都是经营者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强制缔约制度中的国家意志体现在否定了其合同中的价格条款,保护了其他竞争者的利益,从而实现交易公平。
强制缔约制度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衔接最为紧密,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提供消费者生活必需品的自然垄断行业经济主体的强制,各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科以公共服务企业或组织及个人强制缔约的义务,防止他们选择服务对象,影响消费者取得生活必需品,主要涉及四供(供电、供水、供热、供暖)企业、电信、邮政、公共运输(包括出租车)和医疗事业领域。二是基于第三方的权利保护,给予订约的当事人以强制缔约的义务。其最为典型的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中,车辆的所有人必须投保,保险公司必须承保,其目的在于最大程度上保护利益可能受损的第三方(交通事故受害者)的利益和基本保障。23再如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在房屋买卖行为中,出租人本来可以与承租人以外的购买人进行房屋买卖交易,而出于对作为第三方的承租方的特别保护,同等条件下出租人有强制缔约的义务。24
(二)宏观调控法与强制缔约制度
宏观调控是国家从社会经济整体宏观的角度,运用计划和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引导约束社会经济活动,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以实现国家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目标。强制缔约在宏观调控法中主要出现在国家基于特定时期或者完成特定目标而进行的产业政策立法。在战争时期,国家往往出于政治目的,应对非常危机时期,急需短期集中物力人力,而向国民颁行强制与国家缔约的行政命令或相关法律法规,这种战期的宏观调控更多地带有行政性色彩。在和平时代,强制缔约制度更多的是国家(地区)基于经济和社会职能对市场微观主体交易行为的作用。例如美国1933年《农业调整法》是为应付农业经济危机解决农产品过剩问题而紧急出台的一部法律。该法律要求与农业部签订“市场协议”的农户,缩减耕地面积和基本农产品的产量。1934年在《班克黑德棉花控制法》中国家强制缔约的意图更加明显,其直接规定对不参加减产协议和破坏协议提高棉花产量的农民施以重罚。25再如我国台湾地区“粮食管理法”第19条规定:“中央主管机关因天然灾害或突发事件,致粮食供需失调或有失调之虞时,对于所列事项应报请行政院核备公告管理:一、关于粮食买卖之期限、数量及价格。二、关于粮食储藏、运输及加工。三、关于粮食之紧急征购与配售。”26此外国家出于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的考虑,也会干预市场自由竞争机制。例如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第14条明确要求“电网企业应当与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送备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德国、丹麦等国家也有类似规定。27
在政府的公共采购过程中,国家要求政府部门和某些公共机构或在某一领域内获得了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的私营企业强制招标,同时要求采购方对供货方的资质进行审查。28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和保障公共服务,限定这一类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范围,体现了强制缔约制度的国家意图。
(三)国家投资经营法与强制缔约制度
强制缔约制度在国家投资经营法中的体现主要是当市场中出现危机,国家为市场稳定以投资经营的方式干预缔约过程。美国的《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就是想通过政府购买金融机构中的不良资产而将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剥离。由财政部提交购买困境资产计划,内容包括购买困境资产的范围、价格和由谁购买等。作为金融机构应无选择接受并与政府签订购买协议。我国对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的处理也曾采用这种方式。1999年我国为接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五家银行的不良贷款成立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等资产管理公司,29其后进行了不良贷款的剥离和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给谁、由谁来收购等,均由国务院制定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的文件直接规定。作为不良资产剥离收购的主体双方(银行和资产公司)没有任何意思自治的余地。30这种不良贷款剥离和接受,就是典型的国家强制缔约形式。此外,在劳动合同中,国家基于对雇员利益的保护而对劳动合同自由的限制和工伤保险中雇主对劳动者工伤保险的义务等,都是突破民法意思自治基本原则,31采取强制缔约制度的体现。
五、结语
强制缔约制度与国家干预有着紧密的联系,单纯用民商法学理论对其进行学理解释无法阐明其根本内涵与蕴意。其与民法崇尚的私权自治、契约神圣显得格格不入,而用经济法学理对其解释,可以发现两者在产生、价值、法律性质以及相关制度上都有天然的契合性。通过对这种契合性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强制缔约制度实际上是国家意志在契约法(合同法)领域中的体现和干预的结果,也可以印证经济法学独立学科的地位。
注:
1 参见Johannes Biermann,Rechtszwang zum Kontrahierungszwang,in:Ihering-Unger,Jahrbucher fur die Dogmatik des Privatrechts Bd.52(Bd.20 N.F.),Jena,1893,S:267-322。
2 [德]尼佩代:《强制订约与强制性合同》(1920年版,第7页),转引自[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3 王泽鉴:《王泽鉴法学全集(第12卷)(债法原理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4 参见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作者印行,台北,2003年版,第45页。
5 参见尹田:《法国合同法中的“强制性合同”》,《现代法学》1995年第1期;易军、宁红丽:《强制缔约制度研究——兼论近代民法的嬗变与革新》,《法学家》2003年第3期;崔建远:《强制缔约制度及其中国化》,《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5期;冉克平:《强制缔约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6 参见Werner Flume,Allgemeiner Teil des Btirger lichen Rechts,Bd Ⅱ :Das Rechtsgeschaft,3 A.1979,S.611。
7 参见 Erich Molitor,Zur Theorie des Vert ragszwangs,in:Jherings Jahrbticher flr die Dogmatik des burger lichen Rechts Bd.37 N.F.,Jena 1923.S.1。转引自朱岩:《强制缔约制度研究》,《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
8、20 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第66页。
9 漆多俊:《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10 参见 Justus Wilhelm Hedemann,Das burgerliche Recht und die neue Zeit,Jena 1919,S.1(17)。Hedemann在其著作中提到指令合同缔结形式。
11 易军、宁红丽:《强制缔约制度研究——兼论近代民法的嬗变与革新》,《法学家》2003年第3期。
12 尹田:《法国合同法中的“强制性合同”》,《现代法学》1995年第1期。
13 参见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14 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15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16 参见崔明石:《解析契约正义的演进——兼论强制缔约的产生》,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4586,2012年12月25日访问。
17 漆多俊:《转变中的法律:以经济法为中心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18 陈云良:《转轨经济法学:西方范式与中国现实之抉择》,《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
19 王保树、邱本:《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
21 参见漆多俊:《转变中的法律——以经济法为中心视角》,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9页。
22 邵建东译:《德国反限制竞争法》,《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1期。
23 详见德国《责任保险法》第五章第四节(5Ⅳ有关机动车强制保险)和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第76条和我国《强制保险条例》第2条之规定。
24 例如1985年英国《房产法》和1993年通过的《租赁改革、房屋和城市发展法》以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之规定。
25 参见蔡东丽、谢加书:《论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农业立法》,《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27期。
26 黄立:《契约自由的限制》,《月旦法学》总第125期。
27 德国《可再生能源法》第4条。丹麦《电力供应法》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必须优先上网,电网有责任收购并付款。
28 详见我国《政府采购法》第2条和第22条的规定。
29 唐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两次剥离不良贷款的反思》,《经济管理》2006年第7期。
30 易宪容:《新政府如何化解不良贷款》,《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3月26日。
31 马跃如、夏冰:《论〈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的现状与问题——以对非杳无音信劳动关系的立法规范为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