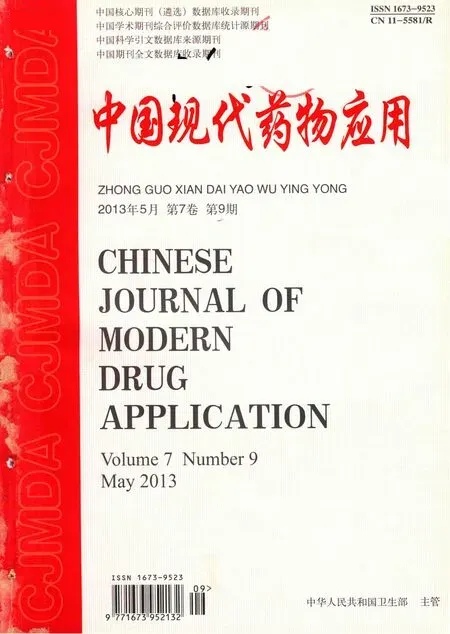浅谈大肠癌的内外兼施中医治法
2013-01-23贾建伟戚淑娟
贾建伟 戚淑娟
大肠癌是起源于大肠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包括结肠癌和直肠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并且青年人的大肠癌发病率逐年升高[1]。常见表现为血便或粘液脓血便,大便形状或大便习惯的改变、腹痛、腹胀等。大肠癌是我国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中预后最好的,手术切除联合放疗或化疗是大肠癌主要的治疗方法[2]。然而,传统医药对大肠癌也有自己的优势,笔者结合临床临证,浅谈中医对大肠癌发病的认识及治疗方法。
1 中医对大肠癌病因病机的认识
大肠癌在祖国医学文献中没有确切称谓,根据其症状和体征,被命名为肠覃、脏毒、锁肛痔等。如金代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中说:“脏毒者,其大肠尽头是脏头……毒者其势凶恶也……肛门肿痛,大便坚硬则殊痛,其旁小者如贯珠,大者如李核,煎寒作热,疼痛难安,势盛肿胀,翻凸虚浮。”
大肠为六腑之一,“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概括了大肠的生理作用。凡影响大肠传导排泄的功能,均是导致大肠癌发生的病因,可分为外因、内因和不内外因。寒温失节,或久坐湿地,寒气客于肠外;或素体正亏,脏腑功能失调,脾气虚弱而运化失调,致湿热邪毒蕴结,浸淫肠道,气滞血瘀,湿毒瘀滞凝结;或饮食不节,恣食肥甘厚味,损伤脾胃,致脾胃运化失司,大肠传导功能失常,湿热内生,热毒蕴结,流注大肠,瘀毒结于脏腑,火热注于肛门,结而为癌肿[3]。
2 中医对大肠癌的治疗方法
中医对于大肠癌的治疗有内、外治法,二者需有机的结合,内外兼施,以扬长避短,既可从整体论治,调整机体的阴阳气血,又可使药物直接作用于病变处,提高临床疗效。
大肠癌内治法以健脾益气,化湿解毒为基本原则,在此辨病的基础上结合辨证,辩明寒、热、虚、实。临证以湿热型、瘀毒型、脾肾亏虚型和气血两虚型最为常见。湿热型便下粘液臭秽,或夹有脓血,里急后重,肛门灼热,口干口苦,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治以槐角地榆丸加减;瘀毒型腹痛固定,粘液脓血便,里急后重,大便溏细,舌暗红或有瘀斑,苔薄黄,脉弦数,治以桃红四物汤加减;脾肾亏虚型腹痛隐隐,久泄久痢,便下脓血,苍白消瘦,气怯纳呆,肢冷酸软,舌黯淡胖,苔白脉细,治以参苓白术散加减;气血两虚腹部隐痛,面白乏力,头晕体倦,舌淡苔薄白,脉细,治以归脾汤加减。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大肠癌的发生也不例外。人体正气先虚,脏腑阴阳失谓,六淫、七情等诱发所致,故应重视扶正。尤其是年老体弱、不适手术及化疗者,尤应以扶正为主。切忌一味攻邪,滥伐虚体,使正气更伤,邪实更甚,毒邪内陷,加速病情恶化。但也不可一味温补固涩,或滋腻养阴,以防闭门留寇,阻抑气机,使邪毒蕴结不得泄。
外治法是中医常用的治疗方法。大肠癌外治法主要为保留灌肠法[4]。笔者临床上多以下方灌肠。生大黄20 g,黄柏 15 g,山栀子 15 g,蒲公英 30 g,金银花 20 g,苦参 20 g,红花10 g。腹痛,脓血便者,易山栀子为山栀炭,加罂粟壳15 g,五倍子15;高热、腹水者,加白花蛇舌草30 g,徐长卿30 g,芒硝15 g。
3 病案举例
刘XX,男,67岁,因“便秘1个月”于2009年10月9日入院。患者1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便秘,在门诊服用泻药后便秘可缓解,但反复发作,出现便中带血,并间中出现腹痛,乏力,体重下降。有冠心病病史。体格检查:生命体征平稳,消瘦,皮肤无黄染,结膜苍白,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心肺(-),腹软平坦,右下腹可及约3 cm×5 cm质韧包块,可推动,余未见异常,直肠指诊未及异常。辅助检查:大便潜血(++),贫血(Hb 80 g/L),CEA 57ng/ml,CA199 216ng/ml,肠镜提示结肠癌,病理分型为高分化腺癌。行手术根治治疗,术后未进行化疗,出院后一直在门诊予中医治疗,内外治法兼顾,内治以健脾固肾,行气化瘀为法,以参苓白术散加减,间中以中药灌肠。病情稳定后,中药制为丸剂口服,随诊3年,无复发。
4 体会
大肠癌是消化系统常见肿瘤,手术联合化疗是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但中医药疗法广泛应用于大肠癌的各个阶段,个性化治疗,疗效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同时,中医强调整体观念,治疗的目的不但是消除或抑制肿瘤细胞,更注重整体治疗,使机体处于阴阳协调的平衡状态。现代中药药理研究表明,多种中药具有杀灭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细胞的作用。虽然,中药复方治疗肿瘤的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中药复方多方位、多靶点的治疗作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医治疗大肠癌,内外兼施,可改善生存质量,提高生存率,降低复发转移危险,值得进一步探索。
[1] 沈杰,李智,邹玉.青年大肠癌45例临床分析.临床医学,2011,31(1):63-64.
[2] 肖冰,王媛媛.大肠癌的药物治疗.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2011,20(3):206-210.
[3] 庾庆丽.大肠癌中医治疗现状.中医学报,2010,25(1):31-33.
[4] 浦琼华,尤建良.中医治疗大肠癌的研究进展.贵阳中医学院学报,2010,33(5):12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