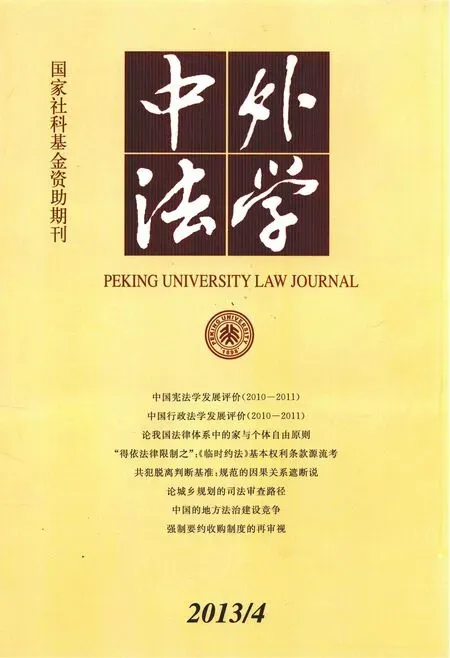由起草修改过程看《临时约法》的政体选择倾向
2013-01-21成方晓
成方晓
立法过程中法律条文的修改过程往往更能体现立法者的真实意图。研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下称“《临时约法》”或“约法”)所确定的政体形式的论著中,尚无对约法起草和条文修改过程详加探究的专论。对《临时约法》立法过程记载最详的原始文献当推《参议院议事录》(下称“《议事录》”)。〔1〕《参议院议事录(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本文所引《议事录》,均出自该书,不再一一说明。本文主要对《议事录》中记载的约法草案定稿过程和条文修改过程加以梳理分析,发现《临时约法》从起草到审议通过的经过颇为曲折,“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做法受到参议员的抵制未能成功,其最终定稿对于政体设计采用了比较模糊柔和的或可称为“议会总统制”的折衷方案。
一、《临时约法》的第一次起草
关于《临时约法》的起草过程和起止日期,既往学者其说不一。顾敦鍒称:“《临时约法》由宋教仁等起草,经起草二次,会议亘三十二日,自二月初七日开始,至三月初八日,全案告终,即日宣布。”〔2〕顾敦鍒:《中国议会史》,木渎心正堂1931年版,页114。钱端升则笼统地说,“该(参议)院正式成立后,即进行制定临时约法,以为组织大纲的代替”,〔3〕钱端升:《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页279。似乎制订临时约法是1912年1月28日参议院正式成立以后才开始考虑的。张国福和邱远猷则主张将《临时约法》的起草时间提前到1月5日。〔4〕张国福:“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1期;“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3期。邱远猷、张希坡:《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355。《临时约法》第一次起草阶段共出现三个草案,分别是1月25日起草员向代理参议院提交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1月30日孙文咨送参议院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和2月7日“编辑委员会”向参议院提交的临时约法草案。那么《临时约法》的两次起草究竟始自何时,经过如何,终于何日,为什么第一次起草有三个草案呢?本文剖析史料,给出自己的答案。
1912年1月5日,鄂、赣、闽、滇、粤、桂六省代表提出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案和湘、赣、浙、滇、秦五省代表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应加入人民权利义务一章案。对于这两个提案,代表们“公决先付审查,审查后即由审查员拟具修正案”,举定景耀月、张一鹏、吕志伊、王有兰、马君武为审查员,是为《组织大纲》的第四次修正。1月25日,起草员向临时参议院提出《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可见,《临时约法》的起草肇始于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对《组织大纲》的第四次修正。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草案虽未将内阁单设一章,也未设内阁总理,但其中的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与临时约法的最终通过稿相比,对于国务员的地位和职权有更加明确的规定。〔5〕《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申报》1912年2月1日、2日。这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精英们在共和政体设计方面的诸多考虑,也是以孙文与宋教仁为代表的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的延续,是当时局势下同盟会内部对内对外政策矛盾斗争的体现。
1月30日,孙文咨请参议院审议由法制局草拟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案》(下称“组织法案”)。〔6〕《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全文,《民立报》1912年1月27日。引人注目的是,该文中遗漏了第五章的章名“第五章 参议院”。1912年1月29日法制院在《民立报》刊登启事将该法案更名为《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但对于这一明显的错误未加说明。2月1日,参议院以此项法案之制定属于立法权,“今遽由法制局纂拟未免逾越权限”,将该草案退还。〔7〕《议事录》1月30、31日条;“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案”,张国福选编:《参议院议事录 参议院议决案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与1月25日起草员提交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相比,孙文提交的组织法案最大的不同有两点:一是将“内阁”单设一章,置于临时大总统之后、参议院之前,并有内阁总理之设;一是含有“典试院、察吏院、审计院、平政院”等孙文“五权宪法”的内容。2月6日,参议员刘彦提议“临时约法案关系甚重,应先交审议会审议,俟讨究大刚后再付特别审查会审查”,该议案获得通过。从刘彦的提案可以看出参议院对孙文咨送的组织法案的否定态度。一些学者认为该组织法案是由宋教仁“呈拟”、由孙文咨行参议院“参叙”。〔8〕张国福,见前注〔4〕;邹小站:“关于南京临时政府与《临时约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事实上,除了孙文咨文中提到外,该草案是否由宋教仁主持制定,并没有其他史料支持。〔9〕据居正回忆,“……迨孙公辞职,袁氏继任,中央政府须得改组,约法问题因之而起。孙公命胡汉民先生召集同志参议员及我等讨论大体,……至中央则宜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拟先由法制院起草,宋先生力辞曰:‘今日原则上多有提出,参议员有许多在座,最好由参议院自行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作成草案,提出大会审议,依法议决,但总希望袁氏未就职以前公布之’。”这说明宋教仁没有参与《临时约法》的起草工作。参见陈三井、居蜜合编:《居正先生全集》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页194;参见吴相湘:《宋教仁传——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122。宋教仁也从没有过赞同孙文“五权宪法”的言论。薛恒认为《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是宋教仁等同盟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暗度陈仓”之举,而孙中山咨送组织法案或许是一场为了杜绝今后袁世凯干预参议院立法的“苦肉计”。〔10〕薛恒:《民国议会制度研究(1911-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250。这种推理颇富创意和戏剧性,但没有史料支持,尚待进一步研究。2月1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荣作致函日外相内田康哉,称革命党推袁出任大总统,并非想把一切政务交袁一手处理,袁将“仍是临时大总统”,只是要他当作一傀儡,临时予以推戴;将由“孙文任内阁总理”,“黄兴仍任陆军部总长,掌握真权”;并“置参议院于革命党掌握之中”。〔11〕1912年2月1日铃木驻南京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函,《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页343-345。该函可谓透露出此时孙文希望“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基本意图。
2月7日,“编辑委员会”提出临时约法草案,是为《临时约法》的第三个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蹊跷,没有文本传世,《议事录》中也没有所谓“编辑委员会”的成立记载和成员名单,学者多有猜测。对此笔者提出自己的分析如下:
第一,《议事录》对于编辑委员会成员未加记载,因为它不是合法的提案机构。查参议院并没有编辑委员会的编制,也没有成立编辑委员会的记录。张亦工认为编辑委员会即1月25日委任的“林森等九人审查委员会”,〔12〕张亦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人辨正”,《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似无依据。据薛恒考证,查南、北参议院的全部记录,议案的提出者用“编辑”这一名称只用在临时约法的提出者身上一次。〔13〕薛恒,见前注〔10〕,页246。这是很不正常的。笔者认为所谓“编辑委员会”是由某些企图重新提交孙文咨送过的草案的议员组成,而他们的行为未获参议院的认可,故《议事录》用曲笔交代,自然也就没有文本传世。孙文后来回忆:“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14〕《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页497。这也说明孙文承认他所主张的“五权宪法”和“内阁制”未为参议院所采纳。
第二,邹小站认为2月7日“编辑委员会”向参议院提出的“约法草案”基本就是景耀月等人提供的草案,参议院是以这一草案为基础重新组织审议、二读、三读的。〔15〕邹小站,见前注〔8〕。谷丽娟、袁香甫:《中华民国国会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页216中说代理参议院“议决由上述5名参议员组成编辑委员会,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1月25日,“编辑委员会将拟定的草案提交代理参议院审议”。查《组织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纪事》中无”编辑委员会“的记载。笔者认为该说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第一,参议院既已接受起草员提交的正式草案,不可能也没必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再委派一个机构提交一个相似的提案。据《议事录》记载,2月7日,当“编辑委员会提出临时约法草案”后,谷锺秀提议该案“先交付审议会审议”。下午续议,讨论未终,定初八日上午续开审议会。2月8日上午续开审议会,审议长李肇甫宣布续议临时约法草案请继续讨论,讨论未终散会。7、8两日均讨论编辑委员会提出的草案而“未终”,可见参议员们对该草案分歧很大。据《申报》报道,“昨日午后会议宪法,有少数议员主张不设内阁,致未议决”,〔16〕“专电”,《申报》1912年2月9日。这似乎说明“编辑委员会”提交的草案中有内阁的内容。景耀月等人的草案中没有内阁的说法,而恰恰孙文咨送的组织法草案中有内阁和总理之设,说明编辑委员会的“草案”与孙文咨送的“草案”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据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律顾问、直接参加了约法制定工作的日本法学博士副岛义一回忆,在政体问题上.他主张于大总统下设内阁总理大臣,但未获参议院赞同。〔17〕(日)副岛义一:“我参加中国革命的抱负与经历”,见《早稻田大学演讲集》1911年5月改卷纪念号,页46-52。转引自《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页292-293。他参与制订的也许正是孙文咨送的草案和编辑委员会递交的草案。
第二,“编辑委员会”如果是合法的提案机构,《议事录》对其成立和组成人员应当有所记载。
第三,2月9日下午参议院通过“增设责任内阁”的议案,说明自2月9日起参议院讨论的仍是《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正因为该草案中没有内阁之设,参议院才有“增设责任内阁”之议。
第四,编辑委员会提交的临时约法草案没有被采用。2月13日下午,仅有十五名参议员出席,却就临时约法草案议决七项,其中第一项为“议决凡案内冠于中华国上之大字均删去”,第六项为“议决增第五章,改称‘国务员’为‘内阁’”。这说明本日讨论的草案仍是景耀月等人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而不是编辑委员会提交的草案,因为前者才有“中华国上之大字”,且没有内阁一章。张国福认为编辑委员会提出的草案是临时约法讨论的基础,〔18〕张国福,见前注〔4〕。该说大概出自王世杰、钱端升所著《比较宪法》,〔19〕“《临时约法》系由南京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名为编辑委员会者,起草”,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407。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说难以成立。
此次参议院对约法草案作出重大修改者三:一为从顺序上将原第四章“参议院”提到“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一章之前。这是临时约法立法思想与之前的《组织大纲》及各种草案相比最大的变化,从立法结构上确立了立法至上的原则。这说明在临时约法立法过程中,除总统与国务员的关系之外,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亦是参议员们考量的重点。二为增设一章,并将“国务员”改为“内阁”。此项修改中将“国务员”单列一章得以确认,但改“国务员”为“内阁”最终未被采纳。三为“议决内阁总理由参议院推举三人,总统得于三人中委任之”。此条旨在由参议院确定总理人选,是强化参议院权力、实行内阁制的重要体现,但2月17日即被参议院自身否决。
本日议定七项内容后,主席林森即报告“审议临时约法草案已告结局”,但看来这次只有15位参议员出席的突击审议结果并未得到多数参议员的认可,因此,15日重新“审议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并引起临时约法的第二次起草。
二、临时约法的第二次起草和草案的定稿
2月16日上午第一项议程即为审议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报告,但由于其他议案上午未议。下午续议,出席议员仅14人,公议请将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报告先付特别审查会审查,多数赞同。主席遂指定特别审查员邓家彦、谷锺秀等九人。二时半,以到会议员未及半数,主席宣告散会。〔20〕《议事录》2月16日条。临时约法的第二次起草即是2月16日邓家彦等特别审查会依据2月13日审议会的决定对第一次的草案修改而成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3日下午出席议员仅15人,却通过了对临时约法草案作出重大修改的重要议案,已经十分勉强;16日下午出席议员仅14人,为《临时约法》审议以来出席人数最少的一天,以到会议员未及半数而散会,显示出多数议员对临时约法审议过程中的某些不寻常做法的消极抵制态度。〔21〕1912年1月3日《修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十三条规定:“参议院会议时以到会参议员过半数之所决为准,但关于第四条事条非有到会议员三分之二之同意不得决议。”1月31日参议院会议上用抽签法制定参议员席次,共计42席。1912年2月2日通过的《参议院议事细则》第二条:“凡会议须有半数以上之议员到会方可开议。”第十六条:“凡表决以多数为准。其可否同数时议长得以己意决之。”第五十五条:“会期之始由议长命秘书长抽签定各议员之席次,并附以号数。议员应按照签定之号数入席。”因此,可以认定南京参议院的法定议员人数为42人,到会议员人数须达到21人或以上时,会议做出的决定才是有效的。《参议院议事细则》第二十九条:“审议会非有议员三分之一以上到会不得开议。”但根据《参议院议事细则》第三十五至三十七条之规定,审议会无权作出任何决定。可见,2月13日和16日两个下午所做出的决定是不符合《参议院议事细则》的。既然未能开会,则议长指定特别审查会也是不合程序的。从后面的审查和读会修改条文的情况看,林森指定的这个特别审查会删改完成的草案就是临时约法第二次起草的结果,也就是后来读会讨论所依据的版本。程序上的不合法给临时约法的制订蒙上了阴影,反映出某些人欲“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勉强,也给中国宪政开了恶例。作为此次特别审查员的谷锺秀,在其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中没有透露特别审查的过程。另一位特别审查员邓家彦当时任职孙文秘书,他到台湾后所作口述历史的访谈中,对于他亲身参与的临时约法起草工作也避而不谈,只以一句“民国元年国父让大总统于袁世凯后,余即辞参议员之职,在沪发刊中华民报,专事反袁”草草带过。〔22〕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 邓家彦先生访问记录》,1990年版,页5。他们是否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衷呢?
特别审查会以第一次起草员起草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为蓝本,结合孙文咨送的草案和2月13日议决的内容进行了删改,增加了“内阁”一章,设置了内阁总理,但孙文“五权宪法”的内容最终没有被采纳。至此,经过一番波折,临时约法终于完成起草,“增设责任内阁”进入了临时约法的草案之中。自2月17日起,临时约法进入读会程序。
三、《临时约法》的读会和最终通过
从《临时约法》读会的过程看,多数议员对第二次起草的草案和当前参议院议事的现状颇不满意,并不认同“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使得临时约法的读会一波三折,并不顺利。直到最后一刻,经过重大妥协和修改,《临时约法》方才通过。具体有如下几方面的表现:
(一)参议员自行限制参议院的职权
第一,2月17日,第一项议事日程即为审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报告。谷锺秀请先将审议报告大纲关于内阁总理由参议院推举三人一节宣付表决,主席用举手表决法少数否决后,才开始逐条讨论。〔23〕《议事录》2月17日条。内阁总理人选由参议院推举是2月13日议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内阁制的重要标志,参议院首先否决了该方案之后方才开始一读会,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2月20日,“主席请自第三章第十六条起逐条讨论公决。讨论未终即散会。”〔24〕《议事录》2月20日条。第三章为“参议院”,第十六条应为“中华民国之立法权,由参议院行之”。立法权属于参议院本是天经地义,但看来这一条费时良久,进行得并不顺利。2月21日,续议审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上午讨论第十六、十七、十八三条,下午二时至五时讨论第十九条“参议院之职权”,历时三小时而未终。〔25〕《议事录》2月21日条。这些都说明,《临时约法》制订过程中的争论不仅涉及行政系统的架构,也涉及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第三,2月23日第五项议程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续开第二读会。议决第四章第三十二条删改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以总员四分三以上之出席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二以上者为当选”,确立了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从程序方面看,《组织大纲》和《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中均规定“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此次则明确了参议院讨论重大事项时,出席人数当在总员四分之三以上,同意票数占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方为有效,强调参议院议事不应由少数人操纵。这一删改是对2月13日、16日极少数人突击决定重大事项的抗议,也是3月8日有人提出“出席人数未及四分之三应否开议”之渊源。
第四,3月5日,临时约法案续开第二读会。张耀曾提议第三章末条后应增一条,其条文为“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主席用起立表决法以二十四人起立,多数可决。汤漪提议宪法须由参议院制定之,主席用起立表决法二人起立,少数否决。下午续议至第五十五条,主席宣告第二读会终了,照议事细则规定即付法律审查会修改其条款字句。〔26〕《议事录》3月5日条。可以说,参议院以否定自身的立宪权结束了临时约法的第二读会。
(二)有人急于制定内阁制的临时约法,但这种做法遭到多数参议员的抵制
2月14日孙文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及三项办法,其中第一条即为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议员们一方面“承认总统辞职”,另一方面以二十票对八票通过了李肇甫提出的“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北京”的提案。〔27〕《议事录》2月14日条。2月15日,议长林森宣布第一审议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报告,赵士北却提议先选出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投票事竣随将投票柜封就”后才由林森宣布总统覆议临时政府地点,“参议院覆议时,争论异常激烈”,〔28〕“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6年版,1912年2月15日条。最终改为定都南京之后才开箱验票,满场一致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由此可见,此时参议院议事中充满博弈,并非“以同盟会员占多数的参议员一心要限制袁世凯”。当日原定的六项议程均未开议。参议院当即电袁世凯云:“公得全场一致,足见南方人民信任我公之深……愿公为世界第二之华盛顿,为东方第一之华盛顿,保人民之幸福,巩国家之宏基。南北统一,为公是赖。”〔29〕《民立报》1912年2月21日。人心思定,可见一斑。2月17日为星期六,也是辛亥年的最后一天大年三十,原应休会,该日开始约法的一读会,当属参议院议事细则中规定的“遇有紧急事件特别开会”,但此后近半月进展缓慢。2月27日第五项议程为临时约法案续开第二读会。汤漪提议审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报告续议多日尚未终结,应请自本日起逐日继续开议,主席宣告即自本日起逐日开议。但2月28、29两日均因到会议员人数不足,无法开议。2月29日夜北京发生兵变。3月1日,本日唯一议程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续开第二读会,但因讨论议程之外的议题,实际未议。
根据《参议院议事细则》,参议院议长在拟定每日议程、议题是否属于紧急事件可否提前开议、对于重要问题提议开审议会审议、临时提出动议、委任特别审查员、宣告讨论终局等方面具有主导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参议院议事的进程。细读《议事录》可以发现,在清廷退位、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已成定局后,林森倾向于尽快制定更多地制约临时大总统权力的约法,而多数参议员以缺席等方式进行了抵制。
(三)约法草案中有关内阁权力的内容几被全部删去,有关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职权的重要条款是在最后一刻才删改完成,“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最终未能如愿
3月2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续开第二读会,议决第三十六条至第四十三条,其中删去原第四十条,内容应为“国务员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谷锺秀提议原文第四十二条后应增一条,其条文为“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之弹劾后,由各地方议会各选一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主席用举手表决法多数可决。〔30〕《议事录》3月2日条。
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本是内阁制下国务员的重要职权,今日删去。这项删改明确地显示了参议员们对内阁制的否定态度。《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第二十六条:“国务员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第二十八条:“国务员于政府一切政务,任连带之责,于本部事务各自任其责,临时大总统非认为有大逆罪不任其责”。《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第三十四条:“内阁员执行法律,处理政务,发布命令,负担责任”;第三十五条:“内阁员得提出法律案于参议院,并得出席发言。”应当说,两个草案均包含了较为完整的内阁制内容,即内阁员执行政务、承担行政责任,并对议会负责,而最终这些实质性的内容被全部删去。《临时约法》中有关国务员与参议院的联系,仅仅保留了“国务员及其委员,得于参议院出席及发言”一项。
关于参议院对于大总统的弹劾权,自《组织大纲》到《临时约法》的各个草案均没有规定。无论是美国宪法还是法国宪法,对于被弹劾的大总统,审判权均明确地归于参议院。而《临时约法》中关于临时大总统的弹劾审判制度与美法均不相同。谷锺秀提出的弹劾条款,使得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时不受参议院的审判。3月8日弹劾条款最终改为“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将受弹劾的临时大总统的审判权归于最高法院的法官。根据《临时约法》第四十八条:“法院以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之法官组织之”,这样临时大总统可以运用他对于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权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被弹劾后的审判施加影响。王世杰、钱端升认为,“就当时制定《约法》者的本意而言,《约法》所采为责任内阁制,殆不容否认”,之所以“论者间亦有认《临时约法》为采用总统制者”,是因为“制定约法之人对于责任内阁制缺乏充分的认识”,“遂使制定《约法》者的本意,不甚明了 ”。〔31〕王世杰、钱端升,见前注〔19〕,页290。但考诸《临时约法》的审议修改过程,可以看出参议员们对每一条文的涵义孰轻孰重非常清楚,增删修改都是有针对性的。
3月8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开第三读会。上午讨论未终,主席宣布下午开临时会议。下午开会,议长林森报告出席人数未及四分之三应否开议,公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与本院议事细则均无规定明文,应请开议。主席用起立表决法以二十一人起立多数可决应行开议。议决原第三十条之后第三十一条之前增一条,其条文为“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原第四十条后半改为“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余仍原文。主席用起立表决法以全体起立可决第四章全文。第五章议决原第四十三条删改为:“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原第四十四条后半删改为“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主席用起立表决法以二十人起立,多数可决第五章全文;议决第六章、第七章。主席宣告第三读会终了,用起立表决法以全体起立可决全案。〔32〕《议事录》3月8日条。
新增加的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将所谓国务员的“副署权”弱化于无形。与过去的草案相比,总统的权力明显加强了。而对于国务员,《临时约法》最终仅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以及“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使得国务员的地位和职权大大地模糊化了。凭借这两项修改,总统已可一举突破所谓“国务员副署权”的藩篱。缺少“国务员执行政务,负担责任”和“国务员对议会负责”这两条,“内阁制”就失去了灵魂;仅凭设置国务总理和国务员副署制度两条是不能构成内阁制的。应当说,日后唐绍仪在副署权上的纠缠并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采用总统制的国家也有规定元首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始生效力的,但由于国务员的进退以元首的意志为转移,故这种总统制下的副署制度没有实际意义。〔33〕王世杰、钱端升,见前注〔19〕,页285。
值得注意的是,《参议院议事细则》第二十六条:“第三读会议决全案之可否,但除更正文字或发见其中前后矛盾及与他种法律相抵触外,不得提议修改。”本日于第三读会中对约法条文做重大修改的做法违反了《参议院议事细则》中规定的立法程序。3月8日下午所做的三项修改表明,《临时约法》的制订在最后一刻由于各方的妥协,以扩大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削弱参议院对临时大总统的监督权,以及限制国务员的行政权力而告完成。
四、简短的结语
《临时约法》的立法肇始于1月5日《组织大纲》的第四次修正。自1月25日审查员提出《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至3月8日全院通过共计44天,其中星期休会8天,议题实际论及临时约法案的共计17天,其中不足半日的10天,不足一日的6天,全天的只有3月8日。第一次起草中出现了起草员起草的《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孙文咨送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和由“编辑委员会”提交的临时约法草案。围绕着草案,参议院于2月9日和13日作出重要议案。最终由林森指定的九位特别审查员于2月16日在《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基础上进行第二次起草,加入“增设责任内阁”的内容,完成了草案的定稿。一读会3天,涉及条文第1-19条;二读会5天,涉及条文第19-55条;三读会1天,修改四条,议决全文。《临时约法》审议到读会过程中,到会议员最多时31人,最少时14人。从《参议院议事录》的记载看,审议过程中对于草案做出最大改动的是2月9日、13日、16日和3月8日,且临时大总统的命令发布权、被弹劾总统审判权和国务员副署权等至关重要的条文是在3月8日下午法案通过前的最后一刻才匆匆删改完成的。不能不说,《临时约法》的制定是相当匆促的。
《临时约法》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以共和制取代了千年帝制,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维护了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领土的完整统一。《临时约法》从结构上将参议院置于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之前,是与《组织大纲》和诸草案最大的区别,与美国宪法国会居于总统之前一致,确立了参议院的立法权。这一改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参议院的职权和对于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外交公使以及宣战、媾和、签订条约等的同意权方面,基本没有超出美国宪法中参议院的职权范围。约法更多地规定了总统所行使的行政权,而对于总理却没有规定任何权力。国务员由总统任命,居于辅佐总统的地位,似乎应对总统而不是议会负责;参议院对总统有弹劾权,总统却没有解散议会之权。这样就使得立法与行政之间、总统与总理之间形成了一种“责权不明的双重行政体制”。〔34〕鲍明钤:“中国民治主义”,《鲍明钤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页75-83。其结果是,使中国在建立共和的最初那些年里总统与议会僵持对立,行政与立法机关之间冲突不断,宪法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最终导致持续的混乱和内战的局面。应当说,《临时约法》确立的是一种不成功的议会总统制政体。以往论及《临时约法》往往只着眼于同盟会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而忽视了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就已经存在着权力的争夺和斗争。我们回看当年的历史时不能否认,相对于“改总统制为内阁制”,“非袁不可”更是当时社会各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袁世凯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就是明证。谷锺秀、张耀曾、吴景濂这三位当年参与《临时约法》审议的参议员,都曾经否认制订《临时约法》是为了限制袁世凯。〔35〕谷锺秀认为《临时约法》采内阁制,其原因是“建为统一国家如法兰西之集权政府,故采法之内阁制。”吴景濂称:“议约法时,关于取美国制度,抑取法国制度,当时争论甚多,有速记录可证。并非为袁氏要做临时大总统,故定此约法,以为牵制。”见吴景濂著《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亲身经历》,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亲历辛亥革命:见证者的讲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页1110-1114。张耀曾则说:“有人说这是专为对付袁世凯,但我辈相信革命的正当进程当然如此,决不是专为一人。”见张耀曾:《民国制宪史概观》,载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75。
在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制订《临时约法》之战总算落幕。与法国1875年宪法相似,《临时约法》只是在匆忙中建立起一个模糊不清的勉强可称之为议会总统制的东西:它不是完整而合于理论的,但“却是那时政治状况的结晶”。〔36〕钱端升:《法国的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4-15。它以法律形式确认在中国结束千年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它客观地反映出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时人对同盟会革命历史的尊重和“非袁不可”的共识。但在《临时约法》制订过程中出现的以行政干预立法、以武力威胁议员、不尊重立法程序、搞突然袭击、议员以缺席怠工阻挠立法等不良的先例,在后来的国会中不断重演,使得中国的民主立宪长期在崎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英国法学家白芝浩指出,“每部宪法都有两个必须达成的目标:先获得权威,然后运用权威”。〔37〕(英)白芝浩:《英国宪法》,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页56-57。应当说,这两个目标《临时约法》都未能完满地达成。事实上,对于如何设计制定中国的立宪政体,早在1912年1月初章太炎就指出:“因地制宜,不尚虚美,非欲尽效法兰西、美利坚之治也。……民主立宪起于法,昌于美。中国当继起为第三种,宁可一意刻画,施不可行之术于域中耶?”“若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弗为”。〔38〕《本报发刊辞》,《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4日。
王宠惠指出,宪法者,不祥之物也。非因一人而定,乃因一国而定也;非因一时而定,乃因永久而定也。〔39〕摘录自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转引自夏新华等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诚哉斯言!时隔百年,我们当以更加客观和清醒的态度,考察当年政治精英在历史的漩涡中为创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所付出的努力,对《临时约法》作出正确的文本解读,对其所确立的政体形式和民初政治形势作出更清晰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