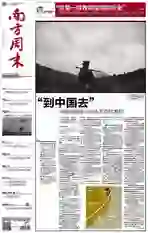崔健和他的年代
2013-01-17
◀上接第22版
2005年9月24日:“他不是麻烦制造者,他是沟通者”
对自己无法在北京举办大型演出的这十几年,崔健从未公开评价和抗议过。“我感觉不到自己被封杀……我们小型演出、外地演出一直没断。”
尽管他不排斥接受采访,但从来都只说观点,极少提及具体现实,更不用说心理动作了。公众和媒体只能从他1994年出版的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中,窥测一二。“我们看谁能够,一直坚持到底”、“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我要结束这最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
《红旗下的蛋》也是崔健最后一张被歌迷广泛接受的专辑。至今,他的演唱会绝大部分曲目都出自他的前三张专辑。
崔健女儿的干爸爸、美籍犹太人Kenny Bloom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那段时间崔健极为难受。“他说,如果在成都演出,会有三万人去听。可北京是他的家乡,却不能在这里演唱。”
“有人可能会以为崔健是一个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但他不是,他是沟通者。”Bloom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二十年前给崔健担任法律顾问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大中表达了与此相似的意见。年过五旬,他仍记得崔健对他的长篇内心倾诉:“搞摇滚乐,就要对现实批判,以一个批判者的角度,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社会批判。摇滚乐是在西方世界产生的,最初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要批判现实。社会是要有人歌颂,也要有人批判的。批判最终极的目标,是使社会得到改进,文明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等到文明进步了,我还应该站在更高的标准再去批判。我永远是批判的。”
1999年,陈戈回国创立了普徕文化公司,打算把美国经纪公司的模式搬到中国,签约的第一个歌手便是崔健。他在北大上学时是崔健的歌迷,想了很多办法打破“封杀”。
他选择电视作为突破口,找杨澜给崔健做了一次专访。她和丈夫吴征都听崔健。然后他联系湖南卫视,对方很有兴趣,请崔健在现场演出。“演出之前接到广电(总局)的电话,说最好别办这个;湖南说那好,您给我下个文,我就停。那边就没回音了。”
2000年10月9日,崔健参加了十二家唱片公司为宣传反盗版联合发起的大型演唱会,“反盗维权中国华语力量总动员”,经过一番至今不能详说的运作,文化部允许他的名字出现在演出名单上。陈戈说,此举是北京方面后来逐渐敢于放开对崔健限制的原因之一:演出性质是公益的,而且“国家部委都批了”。此后,他继续打这种擦边球,一步步地消除崔健的“敏感”印象。
2004年初,陈戈和崔健的合约到期了,没有续。由于盗版猖獗和网络下载,他的公司几乎收不到唱片版税,濒临倒闭。
也在这一年的1月16日,崔健为伍佰的北京演唱会当演出嘉宾,他自己买了些票送给朋友。曹军是受赠者之一。他说:“我终于能在北京演了,你来看看吧。”
“我正好认识伍佰的团队,就想,这或许是个机会。”时年26岁的原普徕公司员工尤尤成功地帮崔健申请了这次登台演出。之后,就是2005年9月24日的首体演唱会,“阳光下的梦”。崔健的“封杀”状态彻底解除。
尤尤问崔健:“你说过,年轻人永远是对的。那么你能不能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崔健想了想说:“好。”她就这样做了崔健的经纪人,一直到今天。
许多人都在思考这段“封杀”的历史,试图理解它与崔健的关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采访他:你的成功是否来自对你的限制和压力?崔健沉下脸说:你这么问是对我的侮辱。
王小峰把意见写在了博客里:“我并没有小看崔健,也没有侮辱他,这是事实……崔健的很大一部分魅力来自他的叛逆,这种叛逆的反作用力确实来自对他的压抑,生活中的和官方的。”
被崔健称之为“中国最早研究摇滚乐的人”的曹平见解颇为独特:如果不是“封杀”,崔健的地位可能会下降,“放开了演,商业上他会获得的利益更大一些,但可能观众也看腻了。”
“封杀”未尝不是一种机遇,文博提起自己的往事:北京交响乐团强迫“七合板”乐队解散,也劝退了“执迷不悟”的崔健,但不久就无法忽视社会对电声乐队的需求市场。文博在团里找几个乐手,以歌舞团的名义搞演出,每人分得的收入可达工资十倍以上。
1990年左右,他以这些乐手为核心,停薪留职去福建等地的歌厅演出了两年,有时候一个人每月能分上万块。
2012年:“你可以随便站了,你却站不起来了”
“封杀”的年代远去了。不知不觉间,当年那个眼神锋锐、一身绿军装的愤怒青年已届知天命。“改革开放”也早过了它在中国的三十周岁生日。
几十年来凌晨五点睡觉、下午两点起床,崔健眼袋还是很深。他从不碰毒品,酷爱游泳健身。当时总桀骜不羁抿着的嘴角,现在时常露出笑意,下巴上总是刮得很干净的胡茬已经见白。聊起当年批准他上台演唱《一无所有》的王昆,他说:永远都应该感谢她。
接受媒体采访时,崔健坦言,自己的经济能力已经超越了年轻时的几十倍。他不认为经济地位变化会削弱他的力量,强调“批判性尖锐性比过去强100倍,你们听不懂”;但他也承认,已经从“感受生活”,变为“观察生活”。
如今崔健的演出审批已不受什么限制。相反,他开始主动抗拒。当年电视台不让他上节目,现在则是他拒绝电视,因为现场演出效果很难达到他的要求。经纪人尤尤劝说了他很久:“不是观众不选择你,是你没给他们选择你的机会。”他才有限地参加几次。
“现在电视台都找我们,去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摇滚乐到底是被中国接受了。可是滞后了二十年。”崔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现在写的歌上电视也不可能。这就是面子在作怪。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早晚会接受,但他们宁可放慢历史发展的步伐。”
现在的崔健,与现实有了某种程度的相互宽容。尽管他仍然不愿意在采访中谈《一无所有》,但已经对摄影师更加耐心;在演唱会上也一定会唱那些他最经典的老歌。而不再像十年前的他那样非跟观众较劲。他似乎理解了歌迷们对青春理想的怀念,正如他不再穿绿军装,却坚持用一颗大大的红五星作为自己的标志。
不再一无所有的崔健还愤怒吗?这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没有答案。
他的音乐,正和他的脸庞一样,少了很多棱角。他对编曲技巧的操控更为圆熟,他的现场演出越来越像一场展示个人才艺的音乐盛宴,他也一如既往地对新歌坚持完美主义,稍有不满意就推翻重来。但他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演唱会上,他费尽心血写出的新歌引不起共鸣。它们不在这场万人合唱的卡拉OK大赛曲目里。
“连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讲不清楚现在这个年代是怎么回事,你又能要求崔健说什么呢?”王小峰持续采访了崔健十几年。他认为,崔健不再能代言时代原因不在于他本人,而在于这个混乱、光怪陆离而又浓缩爆炸式发展的时代和现实。
Kenny Bloom谈到这里一耸肩:“大概微博取代了崔健的作用。”
在2012年12月15日的北京演唱会上,崔健几次号召观众站起来听,但现场观众站起来的并不多。“比崔健更尴尬的是观众,你可以随便站了,你却站不起来了。”二十年前看过崔健演出的诗人高星如此写道。
尴尬的原因主要在于:演出场所万事达中心的一万余个座位大多设在高高的看台上,稍一站起来就有令人腿软的危机感。真正站起来的,还是2013年1月6日西安的“向信念致敬”。
西安市国际会展中心的一间展厅,空空如也,椅子都是临时摆放的。所有人都脚踏实地,导致惊心的一幕出现得很快。事先警方已经声明不许观众站着,结果崔健刚唱第二首歌就一声令下:“大家都站起来跳舞好吗?”全场五千人轰隆一声,齐齐地站起来。还有人站在椅子上。不少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头缠红布,跳着喊着。
没多久,后排观众开始举着荧光棒和相机涌向前排,最后整个展厅变成了一个巨型的live house,所有的人都成了票价2013元的VIP观众,把他们按回座位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种狂热背后的甘苦唯有主办方——西安音乐厅知道。他们没想到,办一场崔健的演出是如此艰难。
能让观众站起来的演出地点不好挑,西安的演出场所要么太小要么太远。等签了合同,去审批时,赶上一切活动审批暂停。“你搞摇滚乐的演出,人都站着,太可怕了,我们都心惊胆颤的。”负责具体操办这场演出的西安音乐厅市场部部长罗敏每天都得去跟警方磨合,汇报安保方案、票务方案、现场搭建方案……一直磨合了几个月。
最惊心的一幕,也是歌迷们最狂热的时刻出现时,现场一位负责安保的人揪着罗敏:“再有人站着,我就把你抓起来……我要给你断电!你现在就上台去说,演出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