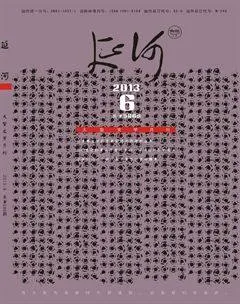语言与陕西现代性写作的种子
2013-01-01阎安
1
在时间概念产生的伊始,人类用“善”来囊括万物,一切生灵用本能感知着自然与生命的本原。当自作聪明的人用语言为万物命名之始,它宣告了文明的诞生,也宣告了生命从此将坠入与世界反复撕扯的纷争里。
语言,从源初世界的立场上说,其实是一个极具破坏力的世界事变。它让人类自我分裂,让原本自然而丰富地喧嚣的世界消声,从此世间只充斥着人类的咆哮,让自然产生出了主体与客体的纠缠。不可思议的是,也正是如此具有破坏力的“语言”,却又是人类完成自我救赎的唯一筹码。所以,当人类手捧“语言”这一瑰宝时,一直希望它能点亮“人性”这一盏明灯,照亮人之内核中那阴暗的恐惧,让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握有更多包含着再生性可能的依据。
在经过漫长的岁月后,人类逐渐明白,在语言规范的世界秩序中,最具神性的表达不是创造,而是感知。正是这种与世界达成和解的姿态,才让语言又一次承担起了救赎的重任。人类曾粗鲁地摒弃了与自然的沟通而进入历史这一时间课题,在这注定要屡经劫难幻灭的行程之中,人类不断地修复矫正自己,直至再次卑微地希望通过语言重新参悟宇宙的真理,借以调整自我在世界中的定位。
然而事到如今的人类,在这样的定位中,唯一拥有的参照物却只剩下“语言”。而语言,作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命名体系和探索体系,它的最高形态也是变动不居的,今天它指向了现代写作。
现代写作,如果从当下这个平面维度与传统这一纵向经度的交叉视角观看的话,不难发现,它其实是以一个拯救的姿态出现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之中。它试图在已经支离破碎的文明废墟上,完成一种重建与寻找,试图通过建立与源初“传统”对接的观照体系,以便重新发现并确认自己。这样的行为,不同于建筑学范畴里所发生的创造与革新,这是在被巨流般此消彼长的物质一再篡改之后,对于人类自我灵魂的再一次挖掘、拯救、再现与回归。
在当代,文学最大的转型和变革正在发生,那就是写作与语言正史无前例地契合在一起,凝炼着一颗颗充满创世冲动与生机的新种子,正准备着破土而发。我们应当敏锐地观察和感知这一事变,感受语言自身在麻木不仁的巢窠中意欲自强图变的挣扎。
2
无论是什么,寄予厚望,不一定回报丰厚。语言如此,书写更是如此。
一个时代的写作,总是在感叹另一个时代的作品,这是因为写作之路和语言本质渐行渐远。人类语言的发展,让写作逐渐背离神性,不再具有早先和真理之间构建起来的朴素的传达性,而是成为了各自为营、以自我创造为核心的一个以命名为主的符号体系。毫无疑问,在这种语言下书写的文明,已经存在了同化、统括、收编的变异式惯性,这时话语往往不再直接和意义相关联,随之带来的是难以克制的分裂与异化。语言向物质一再妥协,人的感知能力退化,语言的诗性在逐渐消失。
整理与重建一个时代的文化,首先要破除的就是那些空中楼阁般的虚假语言的存在。此时对于传统的发掘与回归,就不单单是史学意义上的纪实描述,重建与自然本质沟通的那个内在传达链,有着更为迫切重大的意义。当我们试图借语言打破一个平面,借写作重建一种构架时,实际上是在用革命的机制来寻找一条回归的秘径,我们期望传统能穿越文明的废墟荣耀而归。
我们欣喜地看到,曾经借助无数次历史契机担当过这一重任的陕西文化,今天在继承的同时俨然又一次开始了探索的道路。在为数不少的陕西作家的作品中,或许我们业已看到了那种对自然本质的有意识的主动寻找,这是在语言神性回归的向度上,对语言现代性机制的更符合文学本性的表现。
3
历史如何觉醒,回归在现代语言新形态的层面如何实现它的新生,始终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在这个语言大变革的时代,陕西文学的内修外化再一次逼近了重建的临界点。
站在当代中国文坛回望,在陕西文坛,诸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样的作家,毫无疑问地都属大树之列,然而如果站在文学史的角度探索,我个人则更希望他们是一颗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他们的写作,曾经重建了与世界沟通的方式,这样的重建,是摒弃破坏力极强的创造性之后的一种传达性的表述,这是一种回归式的人类写作。这样的作品,它在一个时代的语言链条中注入着正本清源的新鲜血液,因为人是一个古老的传承,它有走多远的强度,就要有回归多深的强度。这样的一种回归,它是与陕西这块独具特色的土地历史以来惯常的爆发力紧密相联的,这里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仿佛与某种天命有约的群众基础,为当代陕西的文学方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但是,当一个地域的文化需要一次深层次的挖掘与重建时,这样的探索又是远为不够的。以陕西为重镇的整个西北地区,沉淀着巨大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可它们时至今日依旧在大范围地沉睡,它缺少的正是一颗颗饱满的种子,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让土壤中的营养通过种子的发育、根枝的蔓延,重新觉醒,深层次地将它展现出来。勿庸讳言,更多已有的停留在表层的探索,这些浅显的发掘,有功于过去,但当开掘的进程不能在现代的维度上进行得更为饱满透彻的时候,反而会对它造成另外一种误读,产生深层次的破坏。
在忽视传统的现代文明中,对西北地域文化如何发掘,等同于对现代文明的另一个层面上的拯救,我们一直缺乏有效的现代性方式。回归不是倒退,而是升华,这是一个常识。我们再也不能单纯收集和陈列地域历史文化素材了,而是要对传统和人性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性构建与整合。因为任何形式的记录想重现乃至重建一个时代的精神与文化时,都必将带有其局限的狭隘性。任何一个时代,即使是传统中屡经反复的那些时代,都是多层面、多元化的,所以对于它们的重建,必将要调动更大范围的资源,突破历史既已给出的比例尺,在历史的不可能性中发掘出比历史更大的可能性,才能再一次的寻找到属于它的回归之路。
这条路荆棘满布,却异常荣耀。本期《延河》杂志推出的《四妹子》、《民歌》、《黑家洼》三部中篇小说,系同一主题内容的个性化创作,亦是著名陕北民歌《三十里铺》主题的另一种艺术发掘与演绎。在同一题材同一故事原型上进行同一种文体的创作并同时推出,这无疑对三位小说家是一种挑战和考量。我们意欲以这样的一个方式,通过陕北文化体系中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人性维度,为现代精神的语言重建作一次偿试性的努力。
吴克敬的小说《四妹子》,就是陕北民歌《三十里铺》中的主人公。它倔强地讲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这无疑是一次冒险。可喜的是,吴克敬成功了,他成功地塑造出战争状态下陕北女性独特的倔强和性情,跳过形容枯槁的历史,在人性深处奋力开拓出历史和文化不曾站位的可能性维度与时空资源气象。当四妹子成为陕北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时,对她的任何书写,都必将是现代文本表达对历史文化的一次重建。
常胜国的小说《民歌》,也属类似的一次觉醒。它用貌似传统的写实手法进行了一次先锋式的摸索。小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对平常事物的刻画,引发读者的非常规感受。小说用一个平凡的爱情故事无限延伸着对命运的深刻触感,最大亮点在于作者对主人公王凤英与喜来最终命运转折的处理,他巧妙地用朴素的语言道出平凡人改变命运的真谛,那不是英雄式的救赎,是和无数普通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逐渐出现的转机。此时,小说恰到好处地结束,让人有着意味深长的回味。
夏坚德的小说《黑家洼》讲述了黑丁香偕忘年交师母前往绥德走访“四妹子”的种种经历。通过黑家洼女人们各种款式的爱情:姑姑李玉川古典的一见钟情,四妹子王凤英的有情人难成眷属,婆婆李窗花的一生追随等等。小说刻画了这些黑家洼女人对爱情有如《诗经》里女子一般的执著与淳朴,勾勒了一部淳朴且具传奇意味的爱情之书风俗之书。家世故事的叙述别具一格,跨时空的结构性转换在地域文化色块的依依开掘中,延伸着刻骨铭心的触觉。
让我们重拾秦人的荣耀,以睿智、博学为矛,以坚强、隐忍为盾,向另一个时代展开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让语言和文学不再是一种草本互织的季节性植物生态体系,而是时间中的种子,象灵魂一样包蕴于一切可能性的时空形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