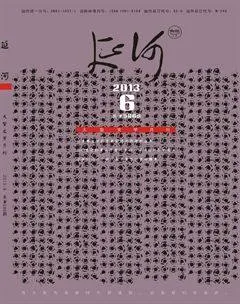创作谈:我为什么写作
2013-01-01常胜国
某一天,我和徐教授(雄慷)先生争论一些事情,他问我为什么写作,为什么人写作?难得他对一些事情始终坚持着严肃的思考。但以我的学识,三言两语是答不好的,我只好说,我写作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是我写什么,如何写。
就文学写作而言,如果我能回答我为什么人写作,也就能得出为什么写作的答案来。这个问题可能不止我一个人为难,就算我一厢情愿专心为某个群落的人写作,这个群落也根本不会买我的账(学生课本除外)。应该早就是这种状况了——我如果大声说为崇高的理想写作,得到讥诮的声音会更大。但跟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不能回答为什么人写作,我肯定就不再承担某些具体的责任,我的作品就不再承担感染、感化和教育人的责任,没有了这种责任,我的作品就可以是取悦、讨好和娱乐人的东西。我为什么写作IuXRG9rtgqjwSzwxjlEQeHjeR5LBXQyGp8Y/rjGgeFE=也就很清楚了。
(作为“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的德国著名翻译家顾彬曾经毫不客气在全世界的媒体上断言,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了解非常差,当代中国的文学是垃圾文学。研究这个东西让他耗时耗力,其结果让他非常生气。2012年他收受中国内地某作家40万德国马克“中介费”助其“公关”2012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常务秘书彼得·恩隆德“运作”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引起世界文坛震荡)写什么,如何写,逞的是手艺技巧,抖的是看家本领。
——你不觉得我们太多的中国作家学到了卡夫卡、加西亚、布尔加可夫的皮毛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吗?你不觉得我们因为“对外国文学了解非常差”不算,还“有根有据”地制造了许多垃圾有失体面吗?我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不甚了解,我只对五维六维或十二维写作一二略知。当我急切地要表现五维或六维空间、骑着扫把满屋子转悠,想飞上天体验五维或六维空间生活的时候,你能肯定我不是在逗小孩玩吗?我得了个什么奖,你也不能肯定那是不是小孩颁给我的,或者是小孩们通过我的手颁给卡夫卡的(在多维空间里是可能的)。所以,我为复制卡夫卡而写的越多,丢人也就越大发。
我从理论上来讲是一个专业作家,也就是被供养起来的作家,被供养起来的作家应该清楚为谁和为什么写作,因为我拿着俸禄,我必须,最起码要完成人家规定的任务。人家还用奖品来鼓励我的写作,我需要养家糊口,这一切我太需要了(当年张恨水先生每天同时给七八家报纸创作连载小说,他不仅用连载小说救活了多种报纸,且以一支笔养活着数十人口的大家族)。但是我基本上还是不知道我为谁写作,因为我的作品写成那个样子多半是因为俸禄的作用,而不是受众的作用。离开俸禄我养活不了家口,就算我同时给七八家报纸创作连载小说,也养活不了几口人(与当年恨水先生比,写作如此廉价是对进步社会的一大讽刺),事实上我不可能比恨水先生更出色。所以我不知为谁写作我只知为俸禄写作也在情理之中。
与网络写作相比,纸质时代的写作让我养成一个难以医治的怪癖,我假想人类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责任需要我来担当。在写作之前,我事先给自己背一个大包袱,我要让自己作品的主题得到升华,但是这个被升华的主题究竟是谁的旨意呢?它究竟是牛奶一样的菁华还是一缸酸菜呢?但我不再细想这些事了,我已经被自己的包袱压得够呛了,为了卸掉这个沉重的包袱,我必须写作。
“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写作又怎能不写作。……如果我没有写作,我早已成为难以医治的酒徒(杜拉斯)”如果我没有写作,我在世人眼里是怎样一个面目,我将怎样行走我的人生,我不知道。在许多情况下,我的作品是一个漂流瓶,谁捞取它,谁看清里面的东西,谁对它进行肯定性的品评都是未知的,我又怎能知道这种修行比一个种田人修得的正果更可靠?如此选择入世以后的个人修为,又怎能不被人怀疑不被自己怀疑?但就我为什么写作而言,那也许是我寻找到的最得体和最靠谱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