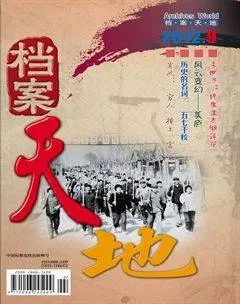五七干校
2012-12-31王琳
档案天地 2012年9期


当我们打开石家庄市行政区划图,一条名叫滹沱河的天然河流横亘在省会北部,与这条河几乎平行的走向,有一条用数字命名的路。这条路,就是具有时代烙印的五七路——现今学府路的前身。今天在这条路上的河北经贸大学校区便是当年省里干部集中学习、劳动“改造”的地方——河北省五七干部学校。五七干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实际上却是一种对一部分人“变相劳改”的场所。
五七干校的产生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而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如何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经过这些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脱离人民,毛泽东形成8106ec7f0724bed67cc7c812f9bab58f0b2ab724558277dd3b197c6b638c2500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到了1966年,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许多地方都是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看完报告后,毛泽东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于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5月l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这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机关也要办军队式的“大学校”。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对《五七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及推广。
在毛泽东发出的《五七指示》里,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地党政机关不断实施机构精简,精简出大批干部,如何安置这些精简下来的干部以及之前被关进“牛棚”的干部,成为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在考虑的问题。就在此时,黑龙江突然出现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成立后的柳河干校共有学员504人。他们到干校后,按照“五七”指示中“学军事”的要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伙食按部队标准每人每月12.5元,吃集体食堂。建制按工种分为农业、基建、工业、畜牧、后勤五个排。干校共耕种土地3000余亩,还发展牧、渔、副各业,并自力更生办了小型工厂。毛泽东在看到柳河“五七”干校的这些报告材料后,甚是高兴,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于是,柳河“五七”干校就成为了典型。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从1968年10月起,全国出现一个兴办“五七”干校的高潮。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冀、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仅河北省截止到1969年底,就办了100多所五七干校,其中省直5所,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的干部4.983万人,其中省直1.2万人。在五七干校劳动的人,不仅有大批机关干部,甚至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被迫到干校劳动,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干校劳动上,而所学专长无法施展,从而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科技建设造成了重大影响。“五七干校”由此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
五七干校的发展
1、五七干校开展的情况
五七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地方,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
五七干校的教育方针最早由柳河干校提出,即以《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作为办校的方针,以抗大为榜样,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培养造就一批永远忠于毛主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后来,它又被概括为:组织学员通过结合现实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这样三条途径,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即“三条途径,一个目的”。“这是干部教育的一场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新鲜经验”。
五七干校的教育包含三个基本的方面:
第一,“下放劳动”。多数干校在建立过程中,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并且多以农业为主,兼搞工业、副业,力争实现“粮油肉蛋四自给”。也正因如此,干校给“学员”安排了各种高强度的劳动,这种劳动被认为是密切联系群众、改造世界观、克服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的有力武器,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站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必由之路。干校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模式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按部队建制以连、排、班为单位编队,设置各种条件使学员的生活接近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环境。“在干校学习劳动,破除了等级观念,不搞特殊化,不论职位高低、资历长短,都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过着类似革命战争年代‘官兵待遇平等’的集体生活”。“劳动的汗水有力地冲刷着一些干部身上的官、暮、骄、娇四气”,“劳动是艰苦的,也正是这样艰苦的劳动,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达到了“与工农群众划等号”的目的。著名诗人郭小川说,他在文化部五七干校时,“经常泡在膝盖深的沼泽水中,到晚上还不断开会”。春夏之季,“秧田里的水都晒得发烫”,“而在雨里又得穿棉衣”,每天“要走30里路,快速地插一遍秧,在水田里泡一天,风里来,雨里去,水里滚,泥里爬”。
第二,“政治学习”。根据《五七指示》中“批判资产阶级”的要求,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五七干校还安排了各种理论学习。五七干校的理论学习带有强烈的政治运动色彩和实用主义倾向,这就是“坚持把组织学员认真看书学习和积极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学习的内容完全由当时各种名目的运动所决定。如一些干校1970年至1971年的“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整风”时要求学6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批判林彪的“先验论”;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学习革命理论,研究儒法斗争”,声称“五七干校是批林批孔的重要战场”。1975年又提出干校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挥干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到1976年,干校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批‘三项指示为纲’”,声称“批邓是办好五七干校的动力”,等等。五七干校初期的学习,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运动进行的“天天读”式的学习。后来,干校陆续由安置干部转入轮训干部后,学习内容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学习由“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方式,发展为比较有系统、读原著、课堂学习;学习的时间有所增加,学习和劳动的比例要么是一半对一半,要么是学习时间略多一点。1974年后还强调五七干校要开办短期轮训班,“积极为基层培训理论骨干”,“注重培养一支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理论队伍”。
第三,“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五七干校还进行了各种各样、不间断的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切活动政治化。干校学员日常的生活、劳动、言行举止都被提升到政治高度,随意上纲上线。例如,初建时的文化部干校,“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干校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思想改造、搞运动。工余时的大批判、忆苦思甜、搞讲用、访贫问苦、表决心等”。干校学员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