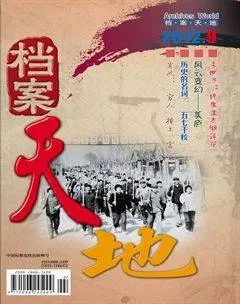“穷人”撞上“富人”
2012-12-31肖凤
档案天地 2012年9期
(一)
在今天,在中国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我的确不能算是穷人,更不能算是富人;我只是一个依靠工资维持生活的脑力劳动者,现在,被统称为“工薪阶层”中的普通一员。
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贫富之间的认知鸿沟,近乎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为富不仁”几乎是每个时代穷者对富人的第一感觉。尽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人们奉行的一条道德准则,但是在一个“家天下”的时代,“士农工商”的社会身份顺序,要想取得“受尊敬的财富”变得几无可能。实质上,我们没有必要盲目去“妖魔化”富人,更没有必要去美化穷人。
那么,“穷人”、“富人”是两个被严重打扮的时代名词,究竟怎样算是富人,怎样算是穷人呢?仔细回想,在上世纪著名的“三反五反”年代,富人身处“地富反坏右”之列;在改革开放初期,富人则被王朔在小说里嘲笑得狗血喷头;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富人是经济学家普及经济常识的阶段性工具,是个变量。
非常有趣的是,过去一些年,政治经济学倾向于所谓“两极对立”的阶级划分法,即把社会简单地划成“穷人——富人”、“企业家——劳动者”,即非贫即富的分法。而发达国家,这种阶级“两分法”,从50年前起就逐渐被抛弃,代之以强调中产阶层的崛起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
听听多么有意思,时代变,人的思想也跟着变。想来想去还是那一套问题:目前,到底谁是富人,谁是穷人呢?穷富是相对的概念。相对于农民,城市人口普遍是富人;在城市,相对于普通工人,包括官员在内的白领阶层是富人;在白领之上有金领,与这两个阶层相当的是中小企业主。到财富的最顶端,则是较大的企业主及一些比较另类的富人。类似的看法,派生出来了一大堆。
说实话,我没有所谓的“仇富情绪”,我认为,像著名科学家袁隆平这样,为民造福的科学家,获得几百万元的大奖,是非常应该的事;如果他和与他一样的人日子过得不好,倒恰恰说明了社会的不稳定,而且不正常。当然,对另外的某些人,是如何绞尽了脑汁,把国家的钱,或者别人的钱,统统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我因为对此一窍不通,因此,也就自始至终迷惑不解。
值得自我安慰的是,本人既不羡慕金钱,也不羡慕权势。从心里说,我更同情穷人。四十多年前,在大学读书时,坐在阅览室里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泪流满面又怕同学看见,狼狈掩饰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尽管岁月流逝,我依然一看到穷人,就非常投入地心酸。
我在祖国的土地上,看见过的最穷的穷人。那个人属于住在河南省“黄泛区”腹地的农民。他们住的是用土坯砖搭建的房子,土坯砖是用当地的黄色黏土,在土窑里烧成的。在黄泥墙上掏一个洞,就是窗户,连一张糊窗纸都没有。屋顶上,摊着一层又一层的白薯干;屋檐旁边,也挂着一串又一串的白薯干;说心里话,这就是他们整年的口粮。
简陋的屋子里没有桌子,吃饭时,一个人端着一只碗,蹲在屋外的地上,如果刮风,黄土就会飘起来,落在碗里,他们也都麻木地统统吃下去。我与这些农民兄弟作邻居时,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他们都是我所在的劳改农场的“农工”,“政治地位”要比我们高不少。三十多年来,我会常常涌起想要回去看看他们的愿望,也许今天,他们的生存状态有了很多的改变。
有时,会和友人谈起这段经历和见闻,他们总会批评我“少见多怪”。有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看见过更穷的,在大西北的沙漠腹地,在大西南的边远山脊,有的地方至今未通水电,有的人家仍如解放前一样,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
我在世界“首富”的美国,也曾看见过真正的穷人。
一次,是在好莱坞的所在地洛杉矶市,这里是千千万万做着明星梦的青少年们向往的地方。著名的贝弗利山庄是洛城的富人区,云集着政客、巨贾、影星、歌星等等“富翁”们的豪宅。而恰恰是在距离贝弗利山庄的不远处,我亲眼看见了一堆又一堆的无家可归者。
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几年前一个春日的晚上,常住洛杉矶的东北小伙子小赵对我们说:“你们不是要看看洛杉矶的市中心吗?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当夜幕降临以后,我们坐上了他的面包车,穿行于洛城市中心“当趟”的大街小巷之中。就在那些摩天大楼旁边的马路上,我看见了几个胡乱地躺在垃圾箱侧的人,他们用来铺在身下和盖在身上的东西,都是报纸。在另一个用垃圾箱当作火炉的篝火边,又有几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烤火。凄惨的情形,与有些美国电视剧里展现的一模一样。
小赵开着车走过了一条街、又一条街,每条街上,都站着或者躺着一堆或者几堆无家可归的人。其中有的人,正用发亮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车,篝火映红了他们肮脏的面孔,让我觉得有些恐怖。我和同行者都被吓坏了,连声催促小赵说:“快走吧!快回去吧!”小赵问:“看够了?”我们说:“看够了,不看了。赶快回住处吧!”
另一次,是在从迈阿密去奥兰多的路上,也是坐着小赵的车,经过了一个聚集着黑人的小村庄。这个村庄的面积很小,跟它前后左右的环境比,显得很凋敝。虽然也是两层的小楼,或一层的平房,但是很破旧,大门敞开着,屋内很昏暗。一小堆一小堆的年轻黑人,正无聊地站在路上,无所事事地东张西望。小赵吓唬我们说:“把车停了,下去看看?”我们连声说:“不必,真的不必了!”他哈哈一笑说:“我最怕车坏在这儿。”他一边说,一边就踩大了油门。
至今,我已经到过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也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里长住过。我的观感是:不论在哪里,富贵人都是极少数,赤贫者也是少数,大多数的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过的都是“自食其力”的平常日子。
(二)
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理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别的先不提及,仅就对“财产”或曰“钱”的态度上,已经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过去饱尝过贫困的中华大地上,很多人现在都把追逐金钱当作人生奋斗的目标。在评价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时,也把能挣多少钱放在衡量标准的第一位。有的媒体,经常介绍美国“福布斯”富人榜,还给中国的富人排名次。有的名牌大学,为新生组织的成功人士讲座,首先强调的是,此人年薪多少多少。在这种价值观的导引之下,滋生出一批“哈富族”来,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哈富族”崇尚金钱的价值取向,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不少青少年。在聚集着富家子弟的小学和中学里,比穿名牌衣鞋,拿名牌手机,已经成为“过去式”。现在,有的“富人”家的孩子,或者有的并不太富的孩子,竟然公开“比阔”,比谁的父母官大、钱多,比谁家住的房子好,比谁家开的是“香车”。一位朋友告诉我,这种现象,甚至已经出现在了一向以“知识”和“品德”为追求目标的百年名校里,以至于,有的虽然经济宽裕,但仍然坚持操守的家长,不敢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害怕这种被扭曲了的价值观,影响了自己年轻的孩子。我的这位朋友就是如此。
如今,在大学校园里,仍然依仗家长,或者依靠国家供养的莘莘学子中,也有人开始崇拜金钱了。他们以富为荣,以穷为耻,这种现象催人思考。当然,马加爵是个心胸狭窄、暴戾残忍的人,他杀死了自己的同窗,触犯了刑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严惩。然而,再往深处想一想,为什么都是同窗、“朋友”,本人也并不富裕,却要嘲笑另一个好友的“穷”呢?他出生在偏远的农村,生来就是穷的,这是他的宿命,他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奋斗,逐步改善自己的命运,友好者应该鼓励他和关怀他,为什么却要冷漠地嘲笑他呢?“穷”与人的品格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不应该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仿佛是追逐金钱的孪生兄弟,有些刚刚富裕起来的人,同时开始追逐“贵族”身份了。住房要在什么什么“贵族小区”,孩子要上所谓的“贵族学校”。举个例子,北京郊区一条偏僻小街上的饭铺,竟然起名叫做“五人贵族”,我看到后,不禁哑然失笑。这种“贵族情节”,或曰对“贵族”二字的崇拜与向往,正是国民性中“奴性”的反映,这是鲁迅先生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指出过的。钦羡贵族的人,也许不知道,卢梭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不知道人权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都不必在另一个人的面前屈膝,任何人都没有主宰别人命运的权力,大家都应该彼此互相尊重,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人”,无所谓“贵”“贱”之分。
前些日子,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位作者给“贵族”二字所下的讽刺性定义,说:什么叫“贵族”?“贵族”就是那些上辈子是乞丐,或者自己的上半辈子是乞丐的人。这句话听起来虽然有些刻薄,但对某些“穷人乍富”的暴发户心理,也是入木三分的描绘。
两百多年前,法国的1789年大革命,就已经把皇室连同贵族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我国,推翻了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也已经成功了将近一百年。九十几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宗师们,就高高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可是,今天,有的人仍然把“贵族”二字当作自己追逐的对象。这种现象不仅我国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
一位常住发达国家的中国青年学者曾经撰文指出,同样是女性,同样是“名人”,逝世的时间也相近,媒体对她们的关注程度却大不相同——对把一生都贡献给了穷苦大众的特丽莎修女兴趣不大,虽然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对享尽了荣华富贵的戴安娜王妃,却兴致盎然,连篇累牍地报道仍嫌不够,总想借题发挥。
(三)
当然,在我国,在世界上,都生活着一些令我钦佩的人。
他们耐得住寂寞。社会生活中的浮躁氛围影响不了他们,动摇不了他们。他们一心一意地埋头书中,钻研着自己热爱的专业。心态平和,轻松,坦然,远离市井的喧嚣,与一切负面的东西不搭界,过着平静而充实的日子。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吃得饱,穿得暖,有间房子住,就很知足了。
我很喜欢“宏志班”的孩子,虽然我与他们素不相识。他们的家境都很贫寒,可是他们个个有志气,自尊自强。我更敬重他们的老师和学校,把培养这样的学生当作自己的责任。艰苦的生活环境可以锻炼出坚强的意志,若干年后,他们就是社会的栋粱,你能够因为他们现在的“穷”,就浅薄地讥笑他们吗?
其实,很多杰出的人物,都曾经是形形色色的“贫困儿”或者“苦孩子”。
著名记者、作家、翻译家萧乾先生,就有一个贫困的童年,他是遗腹子,母亲做过女佣,常常寄人篱下,他从不回避这段经历,相反,他在自己的散文和小说里,还经常叙述与描写过去的“穷”和“苦”。
鲁迅先生在少年时代,也曾经饱尝过苦楚与苦闷的滋味,他的那句名言:“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真是对复杂人生与现实社会的思考和透视。
俄国作家高尔基,也是一个苦到家了的人,如果他本人不在自己的自传三部曲中如此这般地写出他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窘迫和痛苦,外国读者如我等,又怎么会知道他呢?
然而,这些有过苦难历史的人物,又个个具有慈悲的心肠,他们对穷人,对青年,都表现出了真诚的爱心。
有时,我还会想起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是封建制度下的“世袭伯爵”,可是在他的作品里,贵族们大都虚伪无耻,而农奴和穷人们却个个纯朴善良。这位真正的贵族,在他晚年的时候,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伯爵”头衔。
我曾经拜谒过他宣布放弃头衔的故居,那是位于距莫斯科市中心不远处的一所房子,那所房子所在的街,今天就叫“托尔斯泰街”,他在这里完成了长篇小说《复活》。他的行为,令千千万万个世界各地的读者,由衷地敬仰,但是,那些梦寐以求钻入“贵族”营垒的人,能够理解他吗?
(四)
每一个国家,都是它的人民大众的国家。地球,是全人类的共有家园。古希腊的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说过:“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让所有的人都富裕,才是高尚的人追求的目标。
我从媒体上看到了不少案例,有些在过去拼命地追求权力的人,现在,转而追求金钱了。权钱交易,钱权互动。他们学着因为腐败而倒了台的历史上的贪官,把人民大众的血汗钱据为己有,吃喝嫖赌,有的甚至把赃款转出国门,让子女成为寄生虫。
唐朝著名诗人杜甫,留下了两句著名的诗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话已经传诵了千余年。“智取生辰纲”的《水浒》好汉们吟咏的“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甚至唱到了今天的电视屏幕上。方志敏烈士,为了穷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民族魂”鲁迅先生,决不屈从于权势者和“钱”势者,而对待青年人和贫穷的人,却慈祥如父。
中外古今的许多人道主义作家,都悲天悯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过贫苦大众的生活惨状。
富裕起来的人,应该帮助穷人和无助的人。这不仅是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要与国际接轨吗?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这位哈佛大学的“辍学生”,用科学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常常拿出大笔资金,资助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项目,他还成立了一个专门救助非洲穷人的基金会,请他的律师父亲担任这个基金会的主席,为此,这位年逾古稀的主席,不得不时常坐着飞机跨越美洲和非洲。比尔·盖茨本人没有花天酒地,没有“包二奶”,没有去赌场狂赌,而是把相当大的一笔财产拿了出来,回报世界。他的这种行为,说明了他有仁慈与高尚的品格,但是同时也说明了他的聪明与智慧。因为他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有大部分原因是法律促成的。
按照我的理解,号称“天下首富”的美国,属于一个法制国家,它的法律多如牛毛。只谈有关税收的,在美国,收入愈多,纳税的比例愈高,收入少的,年薪在多少美元以下的,就不用交税。在个人所得税的项目中,收税最高的,要数遗产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遗产税要收50%至60%。对偷税漏税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要么让你破产,要么让你坐牢。因此,没有什么人敢于和税务部门捉迷藏。每一个人,包括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只要有收入,都很自觉,往往要乖乖地在规定的时间内去交纳税款,不敢耍滑头。善于敛财的富翁们都很精明,他把应该交税的大量金钱捐献出来,据了解,如果个人捐款升至一定数量,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免税了,这样一来,每一位纳税人既可以不再纳税,又可以赢得“慈善家”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
也是从媒体上得知,我国“大款”们偷税漏税的行为严重。他们也非常害怕上“富人榜”,因为有人的致富原因非常可疑。还有一发了财,就沾染上恶习的。老百姓里不是早就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吗:“男人一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变坏就有钱。”用法律约束富人的行为,缩小贫富的差距,这应该是我国向“发达国家”借鉴的重要一条吧?
什么是幸福?幸福的含义是什么?著名哲学家叔本华曾说过:“寓于健康身体内的健全的精神,乃是幸福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我非常赞同他的话。
忽然想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贫富悬殊,社会矛盾突出。有一天,一个叫罗伯特的电视记者,拍摄到这样两组画面:一组的主人公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此人在办公室里超负荷地忙碌着,虽然西装笔挺,但神情憔悴,满面疲惫;另一组的主人公,是一位在写字楼工作的清洁工,他身着蓝色帆布衣服,破旧但不脏乱,只见他一边清扫垃圾,一边哼着乡村歌曲,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总经理是美国典型的富人代表,而清洁工是美国典型的穷人代表。这两组镜头在电视上播出之后,奇迹出现了——许多穷人不再仇恨富人,居然还有很多富人开始羡慕穷人的生活。
贫富冲突由来已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可记者的两组镜头,却让奇迹出现:许多穷人不再仇恨富人,甚至还有很多富人开始羡慕穷人的生活。读到这里,不禁要发问:“是什么化解了穷与富的矛盾?”经过一番琢磨,领悟到,是强有力的事实――那两组真实的画面。这时,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记者的匠心独运。原来事实是化解矛盾的橄榄枝啊。
富人究竟是靠什么致富的?“超负荷地忙碌”、“神情憔悴”、“满面疲惫”……原来他的成功靠的是辛勤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成功源于付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那位代表着穷人的清洁工,他生活得怎么样?“衣服破旧但不脏乱”,“一边清扫垃圾,一边哼着乡村歌曲”,神情“怡然自得”。从他的身上,人们看到的不正是坦然与诗意、淡泊与潇洒、快乐与满足吗?他那笑对人生,笑对生活的达观与睿智,让大家平添了羡慕与向往。
返回来细想,仍然可以招来很多念头,当今时代,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人?应该如何看待贫穷与富有呢?一经追问,天南地北的朋友都绽放出了崭新的发现:物质的富有并非真正的富裕,物质的匮乏也并不代表着精神的荒芜,古人笃信:“斯是陋室,唯吾德馨”。那么,这种富含哲理的思维,不正表明,传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相互吻合吗?多么好玩,“穷人”居然撞上了“富人”,这也恰恰是我深刻的思索与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