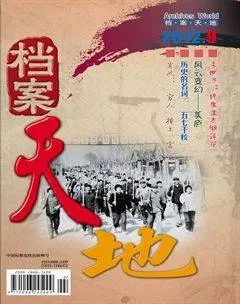终生立志做莲花
2012-12-31李世济
档案天地 2012年9期

编者按:李世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女,1933年出生于苏州,长于上海,祖籍广东梅县。中国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工青衣,宗程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京剧程派艺术私淑传人中的杰出代表。世界青年联欢节银质奖章获得者。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京剧前辈大师程砚秋的义女。她擅演的剧目有《文姬归汉》、《锁麟囊》、《英台抗婚》、《梅妃》、《陈三两》、《武则天轶事》等及现代剧《党的女儿》、《南方来信》等。
我就顺着这条路把戏都整理了,不出程先生的方圆。还是他的东西,还是他的动作。他的动作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太极拳的东西,你必须得知道太极拳的原理。就这样一出戏一出戏地搞,居然很成功。我敢说在那个时代,我的粉丝是相当之多,到现在我这么老了,出去溜个大街,人家都拽着你喋喋不休。我教这么多学生,只有吕洋她跟我说:“老师,我尝到你教我东西的甜头了,我发誓我也不改了。”她就演好人物,果然上座率是最高的。我就是让她自己去体会,我不要强加给她。因为这些也不是老师强加给我的,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所以我告诉你第二条我的工作,在文献没有的,是怎么拿声音来表达人物,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把人物演细腻,演得越细越好,这是我第二条的工作。
我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老同志又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同志是谁,说叫我演《锁麟囊》。哎呦,我摇手摇头的,我抖得多厉害呀,几乎到死啊,现在我敢唱吗?我说我不唱,杀死了我也不唱。他们说是老同志嘱咐你的,老同志嘱咐我,我也不唱,我发过誓的,不唱。他后来说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是,那你必须得唱。那我一点话没说,唱吧,我说可不可以在内部唱?我不公开唱。没有人公开唱传统戏,你让我唱可以,先唱一个《英台抗婚》,反抗的戏总没有错吧?后来点我的《锁麟囊》。我是在戏校唱,我的天哪,那个窗户上都没有脑袋可以钻进来的缝隙了。唱完了,没有几天,老同志又来话了,叫我到工人俱乐部去唱,没把我吓死,没有办法。不但我得唱,我还得说服所有的配角都得唱,大家都吓怕了。
就这样唱了。那天来的人,你要看见了,你会一夜也睡不着觉。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有的眼睛瞎了一只,有的胳膊断了,有的腿不能走了,有扶着的,有背着的,甚至还有一个老太太,她的儿子、儿媳妇拿平板三轮,被褥铺好了,叫老太太躺在上头,坐在第一排旁边第三个座位。那个儿子、儿媳妇把被褥铺好了,把老太太抱上去,躺在那儿看戏。
大家在后台看得都掉眼泪,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这场戏演好,本来都不愿意演。哎呀,太感人了那场戏!这些老同志都是怀旧来的,真是死里逃生过来的,我们那天演得非常好。到最后,“啪”,电灯一亮,触目惊心,台下白花花的一片头发,没有黑发人。有的哗哗流眼泪,感动。他终于看到了我们。这样台上的人都跳到台下去,扶老携幼,搀着、送着,把一个个送到车上。
刚才我说的那个妈妈,儿子、儿媳妇又给她背出去,放在那个平板三轮上。你说作为一个演员,你能无动于衷吗?那真是哗哗流眼泪,感动得不得了。他们是以怀旧心情来看看你们。
回到家,我们几乎都睡不着觉。我本来演戏一晚上就睡不着,那天到五点还没有睡着。我想了半天,这些演员能不能够下次还背来,下次他的家人还给他搀来,每场戏都搀他来,不可能啊!
那么我们的观众呢,断档了,是吧?那天五点钟天亮了,我明白了,我说我想办法使得我的观众从白头发变成灰头发,灰头发变成黑头发。那么怎么努力才能有这个变化?我有半个月没有演戏,那个时候不可能半个月没演戏,我真是没有演戏。我到所有青年人愿意去的地方去了,唱歌的场合也去了,话剧的场合也去了,电影的场合也去了。年轻人什么地方拍手,什么地方欢笑,什么地方走了,我都看在眼里。原来我们跟青年人的距离是他们嫌我们节奏慢。为什么呢?时代不同了,我们那个捂肚子、笑不露齿、鞋不露足的时代过去了。他们希望感情奔放,爱你就爱个透,如果不爱你就恨个透。直截了当,不能什么都闷在肚子里,含蓄着,人家不要看。
总结出来,年轻人是什么?这个梁祝真是奇怪,两个人跑掉算了。那个时代可以跑掉吗?但是说明人的思想,时代不同了,直截了当。
我才懂周总理说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对不对?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我才懂时代发展了,年轻人需要的直截了当,感情要强烈、充沛,把人物演活了。看现在的唱歌,台上跟台下手绢都丢来丢去。我们距离太远了。这样又开始把从前的戏捋了一大遍,一部《锁麟囊》,最后团圆了,见到母亲,见到儿子,见到丈夫,三个人是三种不同的情况下发生的,你能用一个感情吗?你能用一个声音吗?都不可以。一个是母爱,一个是你对孩子的感情,一个是对丈夫的感情,还不能流露在众人面前。角色出发点全都不同,你怎么能在表现形式上一样呢?
总而言之,时代变化了,人家要看你人物,不是要看你的技巧。你技巧再好,没有人物,无动于衷,人家也不喜欢的。我又重新把戏捋了一遍,把人物什么的又捋了一遍,我认为这方面也是我的成绩。
我把人物演活了,观众非常喜欢,我现在教徒弟,点点滴滴都告诉她你现在在想什么。她们说:“李老师,我们跟你学戏完了以后,台上不是想一抬腿、一投足,这是什么?就是想到我这个人物要这样,这样很充实。我觉得这是我对程先生的一种创新、一种丰富,随着时代而发展。
时时念及我的老伴
2001年,我惟一的孩子在一场车祸中不幸离世,那年他才27岁,撇下了两个女儿。老唐受不了老年丧子的巨大打击,从此一病不起。整个家庭的担子就都落在我的肩上。
老唐是我的良师益友。都80岁了,我今天的耳音那么好,音准那么好,我不带差半个字调门的,都是他给我训练出来的。从我12岁我们就认识了,就在一起,我吊嗓子一吊吊四个钟头。你说人对良师益友会是怎样的感情?所以我们不是爱情,你知道吗?我们是一种师生的感情。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对我的培养上,我能不感恩吗?我能没有同情心吗?不可能的。
我也不可能说他在我身上付出那么多,我到最后把他甩掉,我去找对象。再说我去找谁呀,人家知道你们一天老在一起,说也说不清楚,你说对不对呀?这很简单,要不有的人问我:你怎么不讲爱情故事?我说我们没有什么爱情故事,我们只有感情、同情、友情、师道之情。就这些,很简单。
他留下的东西非常宝贵,几乎我一整理从前的东西,就会想到这一点。他平时不需要带谱子的,你问他哪个戏哪个腔调,我要是忘了,他马上就能哼起来给你。人家说神童,那真是神了。就是后来得病后不能动了,坐在椅子上,你说他哪个腔调是怎么回事,他也能马上给你哼出来,一点不带错的。
我们都是艺术人,为艺术奉献了一辈子。我们的一生就是艺术人生。真是这样的,你说给人说不相信的呀。毕竟他是你的老伴儿呀,我们一辈子在一起只有艺术可谈。你想想看,我们儿子在27就没有了,我在他面前一个字不提,其实他内心也是痛不欲生啊。
就这样对付了六年的时光,不容易啊。现在京剧院在给他出书,把他的谱子全部记录下来。在他还在世的时候,我给他办过一个音乐会,把他大部分的曲子拿出来,搞了一次演唱。他跟我说:“世济,你给我搞这个真好,比那个悼词好得多,等于我一生的总结。”你说他走了我不难过吗?非常难过,人生有几个知己呀?不光是知己,他也是第二个师傅呀!
“老同志”扶植了样板团
关于老同志对戏剧院团的支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这个团叫中国京剧院一团,文革以后,有人提出来承包。那个时候卓琳阿姨经常过来,一个礼拜要来两三次。她带着一个破的儿童毯子,把它盖在身上,跟我和老唐聊天。当时我不知道她是带着任务来的呀,我们跟她很亲,什么话都说,她也跟我们聊天,她知道我对“承包”有自己的看法。最后她跟我约法三章,因为有几个人要来抓你的团,邓伯伯要来抓我们的工作。但是有一样,你不能对外说,否则外头会有人误会,觉得江青走了,又来了卓琳或者邓小平,你要绝对保密。我说:“行,我保密。”我始终没有露一个字。
不久后,剧院内举行承包签字仪式,承包团有七十五人,我担任团长。一个星期以后,全团去了山东,开始了四个月的巡回演出。
建团之初,我就跟全体团员说:“在这儿谁也发不了大财,顶多维持到小康水平。真想发财,跑买卖去!在这儿要搞艺术!这是我们的责任呀,‘责’,当然要放到‘权’和‘利’的前面。这一条是我们的建团宗旨。不同意的,当然可以退出……”
当时,我在团里分配上考虑是分两步走:剧团每日向演员发饭费和岗位津贴,全团按一个标准执行;等到演出后期或演出结束,再从“分红”上拉开档次,根据贡献大小获得不同的报酬。大家一看都知道饭费和岗位津贴是小意思,最后的分红才是真格的。到最后分配时,会不会大吵大闹,出什么事情?我心里也没底。
头一站是山东宁津。首场我唱了程派名剧《锁麟囊》,一炮打响。随团出来的老导演骆洪年为几位主演排了戏。我排了《陈三两》与《英台抗婚》,冯志孝排了《打严篙》与《法门寺》,李光排了《连环套》。由于扎扎实实地抓了演出质量,使剧团获得了威望,当地剧场一再要求延长演出期限,不断有别处的剧场经理远道来请我们前去演出。
剧团越是走红,我心里越急。分红该怎么做?我以前也没搞过。大家经过商量,决定“走稳求实迈小步”的分配原则。具体说,就是分等不宜太多。最低一等的人一定要多,最高一等所拿金额至多是最低一等的三倍。我觉得,“大锅饭”一定要砸烂,但具体做时,要让群众自觉自愿,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从大家反馈来的信息看,群众对“砸烂大锅饭”的认识已有明显提高。他们不但赞成主演与配演间要拉大距离,而且建议主演之间也拉开距离。经过研究,全团划为五等分红,二等定为一千元,五等定做四百元,根据一等至多是末等的三倍的决定,我可以拿一千二百元。但最后我只拿了一千零五十元。经研究还决定三等、四等、五等之间各差一百。这种粗线条的划分方法有助于从大面儿上稳定局势,但也必然使不少同志略受委屈。在略受委屈的行列中,就包括我的爱人老唐。老唐接受了,其他“略受委屈”的同志也就不说话了。
分红的时候,大家拆开红包后,有几位略受委屈的同志意外地发现他们拿到的钱,比自己那个档次应得之数略多几十元。信封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分别写有几句感谢的话,话不尽相同,但都把每个人的特点和实际贡献写得清清楚楚。每张纸条都有我的签名。这时,他们才知道,多出来的这几十元,是从我自己的奖金中抽出来的。几十元并不多,但纸条上的内容,却深深地感动了这些同志。
就这样,我们这个团在邓小平的亲自扶植下一步步发展起来。不光是我们所有的改戏、改词要征求他的同意,就连我们每天的演出都会打电话跟他汇报。谁分多少钱,谁怎么样,他都知道。所以今天的改革,所有的模式跟当年我们做的事情很有关系。我不是讨功劳,但是我必须说小平同志不是只抓经济的,他文化抓得很紧,我亲身体会到。一直到卓琳去世,我才把这事说出来,因为她故去了,我又要悼念这些老同志,悼念他们对文化建设上的默默无闻的工作,怀念他们对我们的支持。所以我们这个团是小平同志自己抓的一个团,也是个样板团,我现在也希望这个团继续还能够成为全国最好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