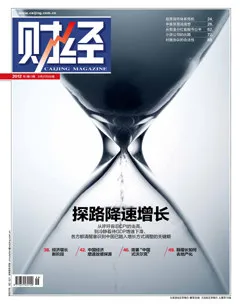欧洲在劫难逃
2012-12-29迈克尔·佩蒂斯
财经 2012年29期

目前,全球需求非常疲弱;随着一些高消费国家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接下来的几年,全球需求会进一步走软。中国这类高储蓄国家将因此面临巨大压力。为了应对变局,高储蓄国家将需要迅速扩大消费。
例如,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在缓慢增长。这个进程几乎可以肯定会在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后加速。当然,美国储蓄率的上升将会自然带动美国贸易逆差下降。
由于上世纪80年代长期的浪费性投资,日本也是负债累累,备受煎熬。现在为了设法应付沉重的债务负担,该国将提高消费税。这样一来也会导致消费下降,储蓄上升,自动迫使日本贸易顺差上升。
但是在欧洲,这种消费与储蓄的调整可能会产生最为灾难性的后果。多年以来,欧洲非核心国家的储蓄率极低,结果产生了巨额的贸易逆差。过去,这些国家都依靠德国的资金流入来平衡贸易逆差。现在非核心国家们也必须提高储蓄率,但随之而来的可能会是一轮货币危机和消费崩溃。
为什么我们预见欧洲会产生危机呢?很多分析师认为,如果欧洲国家的决策者们能够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并且行之有效,欧洲的债务问题可能迎刃而解。例如,上个月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文称,“消除恐慌最好的办法是安定人心。如果西班牙政府能彰显更强的政治能力,而布鲁塞尔的官员们不再那么优柔寡断,可能会产生奇迹。”
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政策不对头也许会加剧欧洲问题,但是对于拯救欧债危机,再好的政策也回天乏术,因为为时已晚。为什么债台高筑、储蓄率极低的欧洲非核心国家会感觉难以继续留在欧元区?为什么他们很有可能坠入债务危机?原因有两个:一是与国际收支平衡的逻辑有关;二是与推动金融危机发展的内在因素有关。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原因。由于2000年-2001年之后,德国主导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后10年间,很多欧洲国家因此失去竞争力,并出现庞大贸易逆差。这些国家必须先要逆转贸易逆差,实现贸易顺差,否则就只能继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不断上涨的债务压垮。换言之,如果它们不能实现贸易顺差,那么偿还债务就无从谈起。
这是个国际收支平衡的基本等式: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必须始终保持平衡,互相抵消。根据定义,一个国家必须在经常项目账户有盈余,才能从资本项目账户进行净支出。实际上,只有当欧元区非核心国家贸易顺差大幅增长,且超过外债水平(并且超过高额的资本外逃),才能真正降低外债。
西班牙别无选择
西班牙已经走到了欧债危机的最前沿,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它的处境。如果德国不能向其提供更多的贷款,西班牙又不能实现贸易顺差,那么它就无法偿还外债。这一点非常重要,需要牢记。西班牙要想实现贸易顺差,有以下三种切实可行的途径可供选择:
首先,德国和其他核心国家能大幅削减消费税和所得税,以降低国内储蓄水平,刺激国内消费。如果德国能把这样的措施推行到足够深入的程度,就会自动产生贸易逆差,相应地就能使其他欧洲国家产生贸易顺差。
第二,西班牙可以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并在未来若干年内忍受由于工资水平减少和物价降低所带来的高失业率。
第三,西班牙可以退出欧元区,启用本币并让其贬值。这样会带来以欧元计价的债务相对本国GDP的比例大幅上升的问题。那样的话,西班牙很有可能会被迫中止债务偿还,进行债务重组。而该国的国内消费也会崩溃。
理论上还有其他解决办法,但它们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比如,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尤其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等——都能刺激国内经济、提高消费水平,同时又都能实现大幅贸易逆差,并保持其增长。与这些贸易逆差相对应的将是欧洲国家的庞大贸易顺差,欧元区GDP增速将得到提振。一旦它们的GDP增速超过其债务再融资利率,便能摆脱困境。然而,这种局面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因为全球其他国家也都在苦苦挣扎,想方设法提高GDP增速,都不愿增加进口。
另一种可能就是欧洲突然实现全面的财政同盟,从实际需要角度出发,将各国主权全面转移到布鲁塞尔(或柏林)。但这也是天方夜谭。如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正蔓延整个欧洲,这个办法过去就一直不太可能发生,时至今日更是希望渺茫。
那么实际上就只有上述三种办法能助推西班牙贸易顺差上升到使其具有偿债能力的程度。那么到底哪种情景能真正实现呢?
第一种方法是让德国逆转贸易顺差,产生大幅贸易逆差,这对全球经济最为有利,但却几乎不可能发生。沒有迹象表明柏林正在准备采取实现贸易逆差的必要举措。反之,它甚至表示要进一步加强财政紧缩政策。部分原因是德国也有潜在的巨额债务问题。由于在这场危机来临之前的十年间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德国的国内储蓄率大幅上升,远远超过其应有水平。德国也一直不得不把过剩资本贷给欧元区非核心国家,来平衡他们的贸易逆差。
由于有了这些贷款的存在,德国非常担心一旦欧洲债务违约风潮袭来,会殃及池鱼,使自己的银行系统也需要国家救助,因此它不愿意减税和降低储蓄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国不会愿意采取必要措施用自己的贸易逆差换取西班牙的贸易顺差。
第二种方法,要求西班牙大幅下调工资和物价水平,直到其工资和物价水平低于德国。这样的政策基本会产生两种后果:要么会使西班牙高企的失业率持续很多年,直到工资水平相对于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力增速发生下降;要么只有德国通货膨胀率高企或者西班牙出现通货紧缩,才可能使西班牙相对价格水平下降,所以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来应对西班牙国内债务的实际增长。
这两种后果中的任意一种都会使西班牙债务的实际成本大幅攀升。这样一来,西班牙不得不通过向中小企业和中产阶级大幅增税的方式来应对增加的债务负担。就是说,为了采用第二种方法,西班牙必须在此后多年忍受高企的失业率,同时必须对中小企业和中产阶级征收重税。虽然西班牙目前正采用这种方法,但这几乎一定会导致一场政治危机,因此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当前,西班牙国民的愤怒情绪已经极度高涨并且仍在加剧。
如果上述两种方法都行不通的话,就只剩下一个选择:西班牙必须退出欧元区。通过退出欧元区,启用本币并使之贬值,西班牙的工资水平会相对德国大幅下降。同时随着消费下降,西班牙储蓄率将被迫上升,该国经济就能重拾竞争力。这样一来,西班牙自然而然地就能将贸易逆差转化为顺差了。由于无论是德国保持大幅贸易逆差,或是让西班牙长年保持失业率高企和经济缓慢增长长期运行,都无法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约束意味着西班牙只能选择退出欧元区。此外,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使西班牙不得不离开欧元区——历史先例表明,包括西班牙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开始螺旋式下降,这导致危机无可避免。
危机恶化成定局
我们已经在现代历史上见识过,每当主权债务危机到来之际,这种螺旋式下降就会出现。它是怎么起作用的?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机械的过程。当某个政府的偿债能力受到质疑,并且这种质疑达到一定程度时,该国所有重要经济主体的行为就开始朝着使债务问题每况愈下的方向发展。
当债务问题愈演愈烈,这些主体的行为也会随之进一步恶化。为了理解这个过程,有必要看清楚这些主体的表现:他们出于完全理性的动机,却采取看似非理性的方式。而且事与愿违的是,主体们的反应并不是朝着杜绝非理性行为的方向发展。
具体而言,由于遭到侵蚀的国家主权信用会创造出扭曲的激励机制,所以当那些主体们对扭曲的激励机制做出反应时,他们的行为却在实际上导致了国家的经济状况继续恶化。如果不那么做,他们几乎肯定是自蹈死地。
要对这些主体的自毁性和自发式的行为加以概括总结的话,我们要首先确认他们的身份,并解释他们通常会如何应对主权违约风险的上升:
私人和官方债权人方面。由于西班牙的信用状况恶化,债权人在向西班牙提供贷款时将会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以及更短的期限。这将产生双重影响。
首先,更高的利率意味着债务上升速度超过GDP增速。其次,更短的期限意味着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加剧、违约概率上升。
1.储户方面。由于西班牙退出欧元区的概率上升,届时银行存款将被冻结并以较弱势的货币重新计价,储户的应对方法是提前将资金撤出银行体系并将之汇到国外。若他们这样做,银行将被迫收缩贷款规模,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2.职工方面。失业率上升导致工会变得越来越激进,而这又会使得企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高的成本,企业进而被迫进行减产和裁员。
3.中小型企业主们。中小型企业主心里都明白,在危机中,他们的财富会因为税收、价格管制和劳动力局限等因素变得更容易缩水。他们会通过减少投资以及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方式来防止财富的缩水。
4.政界领袖们。由于政绩考核的时间跨度缩短和政治博弈变得愈发困难,决策者日益注重解决短期性问题,甚至不惜牺牲长期增长。此外,他们还会发表排外言论以争取爱国主义者的支持。这将导致企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一旦某个国家陷入这种恶性债务循环,上述过程几乎是必然的。人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欧洲许多国家,上述所有现象都已经在发生:信用状况不断恶化迫使经济主体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免受信贷活动削弱的后果打击。他们的调整导致债务上升、增长放缓,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信用状况。这种循环会不断自我强化。
换句话说,不同经济主体的这些行为将使得GDP增速放缓、债务增加,并加剧资产负债表的脆弱程度。当然,这也会进一步弱化政府的可信度,并强化这些经济主体的行为。政治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会去呼吁公民和企业放下个人利益,以国家利益为重,但这些呼吁将是徒劳的。减缓经济主体的这些行为是不够的,必须彻底扭转它。
但是,怎么去扭转呢?沒有哪个国家能够强大到能为所有陷入困境的欧洲国家做信用担保,即便德国也做不到。沒有可靠的担保,螺旋式的恶性循环将继续下去,直到它明显无法阻挡。
似乎所有的这一切都正在欧洲发生着。政府每隔几个月公布一系列最新的经济和债务数据时,这些数据总是比人们预期的要差。在目前情况下,这恰恰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例如,在西班牙,已经有近四分之一的西班牙人处于失业状态。企业正在减少投资。资金也在逃离西班牙,西班牙的资本外流比去年同期翻了两番。事实上,在过去12个月,占西班牙GDP近30%的资金已出逃,只有德国和欧洲央行提供更多贷款才能抵消这些资本外流的负面影响。
那么,人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吗?在目前的时间节点上,基本上已经沒什么行动可以阻止危机进一步恶化,直到陷入困境的国家被迫退出欧元区。这一切已经被历史先例反复证明。未来的形势会一月不如一月。
中国当警惕
认识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两三年全球贸易环境将大幅恶化,低储蓄国家的储蓄率将上升,要么是因为相关国家实施的政策会推升国内储蓄率(例如日本和美国),要么是因为危机导致消费崩溃(例如许多欧洲非核心国家)。
对于将国内消费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的国家而言,前景不容乐观。如今,由于低储蓄国家都在努力提高本国储蓄率,包括中国和德国在内的高储蓄国家将首当其冲,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和出口走软的最沉重打击。
若寄希望于欧洲会平安挺过这场危机,无异于无视所有历史先例——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都不应该抱有这个念头。考虑到欧债危机仍在发酵且解决无门,中国改善国内储蓄失衡的任务就显得更加迫切。即便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大幅放缓,中国也必须这么做。别忘了世界经济状况非常糟糕,欧债危机只会让形势雪上加霜。
作者为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兼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