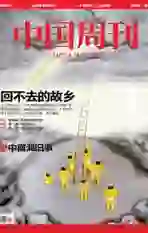葬我于何方
2012-12-29周昂
中国周刊 2012年1期

我1946年出生,祖籍河南漯河,父亲是一名陆军上尉。1949年,随着军队撤退,我随父母迁到了台湾。
小时候,我常常向长辈们问起老家的情况。后来我得知,我们刘家是当地一个大家族,光爷爷一辈就有兄弟十三个,五十多口亲戚都住在一起,因此家中平时备着四口大锅,每天至少要用两口来做饭。爸爸身边带着家族不同时期的全家福照片,有的就拍摄于老房的大门前,那种亲人之间的血脉联系,非常浓重。
这六十多年,在父母跟我们谈话中经常回忆故乡的往事,常常提示我们不能“忘本”。到台湾后,我父亲从军队退下来,在乡下当了一个小公务员,我们全家居住在单位公房里,那是日据时代日本人盖的房子,有“榻榻米”。我们作为外省的小孩,为了和本省的小孩打成一片,就要学着本省小孩的样子,上“榻榻米”前先打一盆水洗脚。但是,只要我和妹妹在家中一说闽南话,父亲两个大耳刮子就招呼过来了,他的意思就是怕我们闽南话讲惯了,就忘了家乡话或者是国语。父亲还在家中挂上了《正气歌》和《朱子家训》,每天早上要求我们背诵一遍。
2000年初我退休,4月23日第一次回大陆,第一站先到上海。当快要落地前,我从空中鸟瞰祖国的土地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澎湃的情绪久久不能自已。我是最后一个下飞机,空中小姐喊我,一转脸,她看我满脸泪痕,那种激动之情好不尴尬。
因为我早年是飞行员,空军军歌的歌词是“遨游昆仑山,俯看太平洋”,抒发的都是大中国情怀,我们那时也在喊“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结果今天终于回到故国的乡土,就感觉那种思乡情怀终于落地了。
我老家的村子叫做“宁沟刘”村。在回去之前,我曾经跟我在大陆的二叔讲,自己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在老家盖一个祠堂。因为台湾有很多的客家家族和河洛家族,他们对于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在祠堂里或者是他们的祖坟上,都用石碑刻得很清楚。我觉得大陆在经过了一些运动之后,老家的祠堂恐怕是没有了,我想把它重新建起来,为的是让刘家的人不要忘本,也通过这种形式,加强亲戚之间的互动跟联谊。另外,大陆亲戚的经济条件不大好,如果盖一个祠堂的话,里面的厅房就可以做成图书馆,让孩子们有地方读书,或者有地方来接受功课辅导,就像台湾的社区活动中心那样。
但是,二叔那时就跟我讲,“以善啊,没有家了,没有家了,以后哪里能活下去,哪里就是家。”
直到回到老家,我才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首先我发现,城里面是“朱门酒肉臭”,村里面却是那样的贫穷。村里没有自来水,有两个连在一起的水塘,叫做“南坑”和“北坑”,中间的一口井,是全村水源的命脉。听爸爸讲,当年爷爷会不时放一些鱼苗在水塘里放养。当我进村时,看到一群妇女在那里用发黄的水洗衣服,那完全是一池死水。眼前的景象,和我脑海中想象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有的人家,在外面打工钱攒得多,就回去把房子盖得稍好一点,如果家里挣不到钱的,那还是住土墙房子,一点点大的那种。而且新房子盖得好像很不像中国的风格,既不是明式建筑,也不是清式建筑,虽然是水泥的房子,但是都没有美的感觉。但如果你在台湾看客家的农村,那整片老房子都维持着中国的风貌,有些古迹甚至是立法保护的。但这样的老房子,我在老家一栋也看不到。
我爷爷在村里是一个做善事的乡绅,1952年被批斗致死。之前他预感到情况不妙,就把他的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二姑和小姑送走了。今天老家已经没有我们家里的亲戚了,一个都没有。祖宅也很早就没有了。
过去,我们的祖坟埋在宁沟刘的一片柏树林里,“大跃进”的时候土法炼钢,需要用柴火,那片林子全被砍了,后来不兴建坟地,那片坟也被平掉了。因此,我爸爸在1988年第一次回家探亲,以及我后来每次回去烧香祭拜爷爷的地方,堆的是一堆新坟,亲戚们说约摸着是这个地点吧。
记得我第三次回老家祭拜完后,准备回漯河城里,一上汽车,有个亲戚突然冒出一句,“活人的事情都管不了,还管死人”,当时车里气氛一下子就像是凝结住了,路途上没有一个人讲话,我当时心里太难受了,下午我就决定离开,至今我再没回去过。若干年后我从别人口中得知,其实是那个亲戚不忍心看到我每一年都回去,都在一堆土上乱磕头,明明是个假坟嘛!
更让我痛心的是两岸人在传统观念的差别。我感觉台湾的人文情怀比较重一点,大陆功利主义观念比较重一点,经过运动以后,人心之间就没有那样坦诚了。记得第一次回老家,我坐火车时看那些扫地的服务人员,对文化程度差一点的乘客态度很不好,扫地的时候,拿着扫把,让他把脚挪开,那种态度我完全不可想象,就是一个“礼”字都没有了,怎么对人这么不尊重呢?两岸同样都是中国人,同样的文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
在台湾,我们家里不管走到哪里,我爸爸都会写一个祖先牌位,就是用红纸写上刘氏历代宗亲几个字,然后用玻璃框起来,然后放在供桌上。再放几个杯子,常年不断地放着水果,一天到晚点蜡烛烧香,把屋顶都熏黑了。可回到大陆,我发现不管哪里的亲戚,没有一户有牌位。我们每年过年都要对着老祖先磕头,我有一个在大陆的亲戚,退休了以后来到台湾,她当时手扶着那个桌,想了一会,可是并没有鞠躬,可能觉得这是封建迷信思想吧。
我父母看在眼里没有说话,但是我知道他们心里很难受的。
而且很讽刺的是,我发现我不回大陆的时候,大陆的亲戚们,不管兄弟姐妹,还是堂兄弟姐妹,彼此都不联系,我去了以后才联系,我就觉得很奇怪。
有一个亲戚,他的长辈是淮海战役中阵亡的,我爸爸费了好大力,在台湾帮他申领了抚恤金,结果我一回去,他就说,你给我们点钱花花。我当时真的是想逃离,一晚上睡不上觉,一大早起来我就走了,我就在想,故乡怎么会变成这样。
现在有时候我也在想,我的根在哪里,因为经过了这些年在大陆往返之后,知道河南的老家已经没有家了,我们已经被扫地出门了。回去以后看老家的景象,还有老家的人情世故,有一种感觉,老话说,落叶归根,可现在,我们已经无处可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