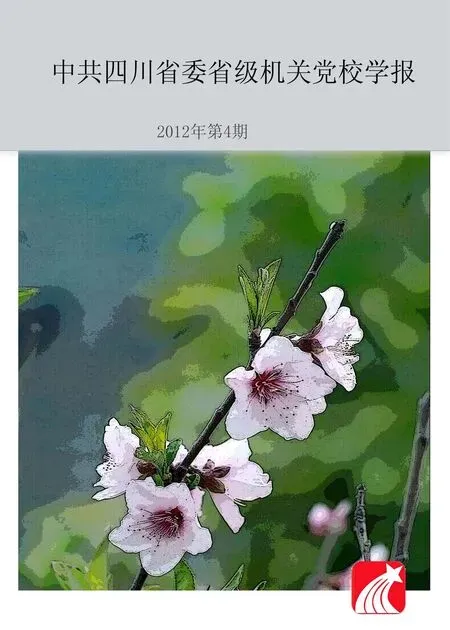战后公共行政研究的主题嬗变与学科危机
2012-12-21张康之张乾友
张康之 张乾友
战后公共行政研究的主题嬗变与学科危机
张康之 张乾友
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学者们对公共行政学产生以来的理论成就进行了一场集体性反思,希望藉此去为公共行政研究寻找新的视角和开辟新的途径。然而,作为这场反思运动的结果是“政策科学”的兴起,致使公共行政研究陷入了低潮。本来,公共行政学者早已意识到政策与行政之不可分离的关系,认识到了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分析方法与工具,他们却并未承担起政策研究的职责,而在二战后的公共行政反思运动中却把这一职责让给了新兴的政策科学家,使政策研究变成了“政策科学”的专利。另一方面,由于政策视角的失落,公共行政研究重新回到了“组织与管理”的主题上,并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冲击下使自己逐渐蜕变成了一种“组织理论”,从而失去了公共意识。这就是学者们常常提起的“公共行政的危机”。正是这种危机,孕育了试图重振公共行政研究的“新公共行政运动”。不过,我们也看到,公共行政这一学科并没有消失,它的合法性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公共行政的概念仍然具有标示研究对象与研究名称的功能。
政策科学;组织理论;公共行政;行政学
对于今天的行政学者而言,“新公共行政运动”是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的一场无人不知的学术运动。但是,对于新公共行政运动发生的原因,可能很少人去加以追究。然而,任何一场学术运动的发生,都有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原因,了解其发生原因,就能够把握科学发展的规律,这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是有价值的。因而,我们希望分析新公共行政运动发生的原因,并以此助益于公共行政这门科学的发展。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发生是与“二战”后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一场反思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它所表现出的是在二战后的公共行政反思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建构的努力。或者说,在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上,二战后的反思运动是一个转折点,在直接的意义上,这场反思运动引发了公共政策研究的热潮,导致了公共行政研究自身的衰落。然而,正是这种衰落再次引发了关于公共行政学科合法性的思考,唤回了“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出场。我们知道,战后学者们集体反思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否定了政治—行政二分的观念,这一些从事公共行政研究的学者转向了对公共政策问题的关注,并将“政策科学”从公共行政学中剥离了出来。结果,公共行政学失去了政策研究的内容与视角。随着政策视角的剥离,公共行政研究重新确立起了科学化的理论建构方向,并丧失了公共行政应有的公共意识,失去了公共问题的解题能力。当然,在20世纪50、60年代,公共行政研究中也存在着“比较行政运动”的学术亮点,但是,就“比较公共行政运动”的目的是要推广和复制美国经验而言,无论是对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增长还是对美国政府的行政改进而言,都无法产生积极意义。所以,这一时期的公共行政研究实际上是陷入了所谓“公共行政危机”之中了。不过,正是这种危机,孕育了试图重振公共行政研究的“新公共行政运动”。
一、公共行政学政策视角的转移
在“二战”之后,学者们深刻地体验到“新政”时期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特别是那些在“新政”与“二战”期间就职于联邦机构的学者,产生了对传统公共行政研究进行反思的要求,因而,“二战”后出现了一场对公共行政研究的集体性反思运动,试图根据“新政”与“二战”期间的现实来刷新公共行政研究。然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二战”之后的社会现实与“二战”期间的社会现实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公共行政学者们的集体性反思虽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世纪初“市政研究运动”的新的公共行政概念,但是,对于当时的社会治理现实而言,还是远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具体来讲,实践者比学者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经验,他们早就发现了行政不只是一个执行过程,也同样包含了政策制定甚至政治斗争的内容。也就是说,对于公共行政的实践者而言,并不需要学者们去告诉他们公共行政包含着政策职能,而是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如何承担起这种职能,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制定、分析与评估一项公共政策。这显然是当时的公共行政学者们所无法向他们提供帮助的事情。所以,尽管“二战”后学者们的集体性反思取得了许多成果,却并未达到使公共行政研究与公共行政实践者的要求相吻合的地步。特别是在公共政策已经成为二战后的一种主要的和基本的社会治理工具的情况下,公共行政研究的这一缺陷也就暴露得更加明显了。
应当看到,在“二战”后的那一代公共行政学者那里,是普遍承认公共行政包含着政策制定内容的,他们并没有在主观上排斥关于政策过程的科学分析议题,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却没有表现出有所作为状况,其原因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在这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他们缺乏必要的政策分析工具。我们知道,市政研究运动所开创的公共行政研究是一种关于“组织与管理”的研究,用高斯的话说,就是一种关于“公共管家”的研究,它的所有分析工具都是服务于探究组织内部管理问题的,他们在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时候,是把城市作为一种组织来看待的。战后的公共行政学者虽然认识到了这种研究存在着某种缺陷,也试图扭转研究的方向,可是,由于他们都是在市政研究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知识结构也是在市政研究运动中形成的,他们所精通的是“组织与管理”方面的问题,对于涉及组织外部关系的政策问题,则显得力不从心。虽然“公共关系”在这时也被纳入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仅仅拥有公共关系的视角是无法解释与公共政策相关的各种复杂现象的。要想认识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的完整过程,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与分析方法,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需求,“政策科学”诞生了。
在学术史上,政策科学的产生通常被认为是以拉斯维尔50年代发表的几部作品为标志的,认为这些作品提出了建立一门政策科学的倡议,而在实际上,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研究,公共政策科学直接源于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项重要行政创制,这项创制就是由出自福特公司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力主推广的“规划项目预算”(英文简称PPBS)。60年代初,为了履行开拓“新边疆”的竞选承诺,肯尼迪在就任总统之后大量起用了政府外部的精英人士,从大学与私人企业中招募高级官员,从而使因现代管理学的繁荣而变得高度发达的私人部门中的管理技术被引入到公共机构之中。以兰德公司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的PPBS就是美国国防部对私人部门管理技术的一种创造性运用。1965年,鉴于PPBS每年可以为联邦政府节省巨额财政支出的诱人前景,约翰逊总统要求在联邦机构内全面推广PPBS,从而将PPBS变成了60年代的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也同时成为公共行政学界乃至整个政治科学界的关注重心。
应当看到,在罗斯福政府中,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也是一项政策,但在当时,由于政策意识的缺失,无论实践者还是研究者,都没有把它当成一项政策看待,致使它的出台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到了60年代,经过早期政策科学家们的启蒙,PPBS一出现,其公共政策的性质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同。所以,约翰逊要求推广他的提议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对。随着PPBS的推广被提上了联邦官员们的议事日程,政策研究也被写入了政府研究者和相关研究机构的议事日程之中。“考虑到发展与监管PPBS所需的高度专业化技能,联邦政府需要一支新的受到严格训练的分析师队伍。针对这一需求,各主要大学通过成立公共政策分析的学生培训项目而作出了回应。1967-1971年间,在研究生层次建立的公共政策硕士或博士项目包括:密歇根大学的公共政策研究所;哈佛肯尼迪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政策研究生院;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城市与公共事务学院;兰德公司的研究生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公共政策与管理系;明尼苏达大学的公共事务学院;德州大学的林登·约翰逊学院;以及杜克大学的政策科学与公共事务研究所。”〔1〕显而易见,由于PPBS的推广带来了进行政策研究与政策分析的巨大需求,设立独立的公共政策——而不是公共行政——研究生院成了大学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一种共同选择。“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以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能够做得更好,进而教授这一心得,这些是建立致力于公共政策分析的研究生院的主要动机。”〔2〕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共政策研究生院不仅在名称上而且在具体的活动内容上,也力求把自己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区别开来。总体情况是,“公共政策学院希望把他们自己与公共行政学院区别开来,后者所关注的,仅仅是对由其他人在其他地方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administration)这一狭隘问题。”〔3〕相反,公共政策学院则希望培养出能够实际参与政策制定与实施(implementation)的政府工作人员。“在1968-1971年间的短暂时期里,每十来个主要大学中便有一个决定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公共事务或公共政策研究所或学院来改组或替代原有的公共行政项目。”〔4〕“这些项目的一个关键革新是使重心从‘公共行政’转向‘公共政策’。而在强调政策时,这些学院既强调目的,也强调手段。这一重心的改变,要求对政策由以形成和执行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它也要求培养可以告知决策制定者各备选政策之可能结果的政策分析师——而不只是公共行政官员。……传统公共行政学院寻求培养胜任、中立的管理者,公共政策学院则面临着识别可以造就一位优秀分析师的特殊品质的任务。”〔5〕
在某种意义上,经过“二战”后的反思,公共行政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如何培养胜任、中立的管理者的方面了,而是同样重视公共政策的制定问题,重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要考虑的各种价值因素。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虽然政策研究并不包含抛弃公共行政概念的要求,但是,由于公共行政研究缺乏必要的政策分析工具,对于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执行中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从而导致了公共行政研究在整个50年代的名声不佳。正是由于公共行政研究已经无法满足公共政策发展的需要,它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以及价值受到了人们的怀疑,才使政策研究学者们要求把自己的工作与公共行政研究区分开来,以求藉此而避免公共行政的概念可能给它带来的不良影响,并获得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研究生院创立者威尔达夫斯基的回忆:“它们反对既有的公共行政、区域研究及所有从事单一学科工作的学院。无论这些学院表现好坏,它们的名声都很差。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我们的校长要求我成立一个新学院的时候,我问他,‘什么样的?’而他的回答是,‘不是旧的行政学院就行。’(事实上,一个名为‘组织理论’的全新领域已经与公共行政领域并肩成长了起来,它与后者覆盖的是差不多的范围,目的是使其重新得到尊重)。”〔6〕
今天看来,公共行政研究在50年代的名声是否真的低落到了威尔达夫斯基所说的这种地步,可能还是一个需要重新评价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公共行政的概念在当时已经不适宜于用来指涉新兴的政策研究,确是一项事实。正如克雷辛(John P. Crecine)所指出的,“作为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公共行政学做得最好的,大多是关于公共官僚机构在政策形成与执行中的角色研究。”〔7〕也就是说,在政策问题上,公共行政研究仍然停留在职能的层面,即认为政策制定是公共行政的一项职能,从而认为行政机构和官员需要在政策过程中承担某种角色,而对于具体的政策过程与政策要素的研究,公共行政研究则显得无能为力。根据李帕斯基(Albert Lepawsky)的看法,“……公共行政学这一具有部分政策导向的政治科学分支学科已经在美国的大学里建立起了自己的课程与独立的学院。在某些机构中,公共行政学正在加入根据政策研究的方向拓宽其视野的新潮流,在某些时候,它虽然明显地表现出对政策问题的关注,所采用的却是公共事务这一更加宽泛的概念。……作为一个系统化的概念,公共事务可能显得过于宽泛,而不具有学科上的可控性,由于公共行政仅仅被当成一个执行性学科,因而显得过于狭隘。在当前的所有途径中,具有包含社会—政治科学及其多种多样的分支学科的可能性的,就是以政策科学的面目而为我们所知的这门超学科(superdiscipline),它是一门最具包容性的科学。”〔8〕也就是说,对于新兴的政策研究而言,带有浓厚“公共管家”色彩的公共行政概念过于狭隘,公共事务的概念又过于宽泛,只有政策科学才是最为适当的。
李帕斯基的观点得到了奎德(E. S. Quade)的赞同,在《政策科学》杂志的创刊词上,奎德作出了这样的阐述,“在关于政策的性质以及它是如何或应当如何得到制定的基本观念上,过去30年可以说发生了一场革命。管理学与决策科学——仅举几个例子,如操作研究、系统分析、仿真学、‘战争’游戏、博弈理论、政策分析、项目预算与线性规划——的哲学思想、程序、技术与工具等,在企业、工业与国防领域中得到了接受,并开始渗入国内政治舞台,甚至深入到了外交事务这一纯粹直觉主义者的最后堡垒之中。但是,在那些为了公众而制定的政策领域中,这场革命却步履蹒跚,也许很快就会遭遇一次中断。这场革命所包含的是两个相向而行的路径:一方面,把体现在‘软的’或行为科学中的知识与程序引入系统工程和空间技术;另一方面,把系统分析与操作研究的定量方法引入社会和政治科学家所采用的规范途径之中。与其尝试处理交织在边缘地带的一种松散联合,支持公共事务分析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如果这场革命要继续下去,就必须把各个学科整合到一场运动之中去,并融合定量与定性途径。于是就有了政策科学——一种试图融合决策与行为科学的跨学科活动。”〔9〕随着《政策科学》杂志的创立,政策科学作为政策研究这一新兴领域名称的地位得到了公认。当然,由于政策科学研究集中在了政策分析的主题上,这一领域也经常被称作政策分析,但无论如何,它作为一个与公共行政学相并立的研究领域则成了无可争议的事实。
在《政策科学》创刊的同年——1970年,前公共行政研究生教育委员会被重新命名为全国公共政策与行政学院协会(NASPAA),新兴的政策科学家们拥有了一个独立的专业团体。不久,公共政策硕士(MPP)也从公共行政硕士(MPA)中独立了出来,成为与工商管理硕士(MBA)、MPA并列的三大专业硕士学位之一。至此,政策研究有了自己的学术身份,有了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人员,有了自己的课程设置,有了自己的专业团体以及自己的专业学位。这标志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得以建立的条件业已具备,所以,原先作为公共行政学中的那些政策研究职能也就被剥离了出来,形成了政策科学。为了表示与公共行政学之间的区别,政策科学家们甚至选择了implementation一词来表达政策执行的含义,以表明与公共行政学意义上的administration或execution不同。如果说“二战”后的反思的最大成就就是确认了公共行政的政策职能,进而将公共行政学从“组织与管理”的狭隘主题中解放了出来,那么,随着政策科学承担起了政策研究的职责,公共行政学反而只剩下了“组织与管理”的内容。这就是著名的“赫尼报告”(Honey report)所指出的,“作为研究生学习的领域,公共行政多年以来被广泛认为是与政府的中央人事或管理职能——如预算、组织与管理、人事行政、项目或管理计划——以及城市的管理职能(尤其市政经理的职能)有关的。在越来越多研究机构中,它已经开始关注或想要关注诸如交通、都市事务、自然资源监管、卫生与福利管理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公共政策的形成与执行。在某些地方,公共行政项目突出了行为科学与决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在另一些地方,则强调在系统分析的框架下对决策制定进行定量研究。近年来,它也被赋予了管理海外技术援助项目、通过帮助政府现代化与发展传统人事职能来管理社会与经济变革、以及管理国际组织的职能。……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仍然认为美国式的公共行政学是一个集中于预算、人事、以及组织与管理问题的培训与实践领域。”〔10〕
二、公共行政学公共意识的丧失
正如前引威尔达夫斯基的话所指出的,在政策科学兴起的同时,一个名为“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也在公共行政研究中成长了起来,并且,如果说“政策科学”的追随者只是想把自己与传统公共行政的研究区别开来的话,那么,50年代兴起的“组织理论”则大有取“公共行政学”而代之的趋势。应当说,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组织理论绝不是一个新事物,沃尔多就曾戏谑,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就专门安排了一个名为“组织”的章节,因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50年代的组织理论家来宣布自己对于组织理论的发明权。〔11〕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今天的几乎所有行政学和管理学教科书中,我们又都能找到类似于“组织理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断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我们看来,合理的解释是:虽然组织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科学管理运动等理论运动也早已提供了某种系统的组织理论,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甚至描绘了一个典型的组织模型,但是,“组织理论”(organizational theory和theory of organization,组织理论家们还曾就这两种表达式发生过争论)这一提法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得以流行的。就此而言,学者们把组织理论的发生史定格在了20世纪50年代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当然,一个概念的流行背后一定有着现实或理论上的深层原由,组织理论在50年代的异军突起也必然包含了不同以往组织研究的内容——50年代的组织理论是所谓“行为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组织研究中的行为主义取向发源于20年代的“霍桑实验”,并在巴纳德的《管理者的职能》中得到了系统化的总结。这种取向反对科学管理运动将组织管理视为一个纯粹的制度问题的观点,而是要求重视组织管理中人的因素,重视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对于组织效率的影响。在此意义上,它代表了组织研究视角的一种转变,即在组织研究中引入了一种个体主义的视角,并从个体主义的视角出发而将组织看作为一个人际协作的系统。作为以制度或体制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管理运动所追求的是事实以及客观性,要求排除任何主观的价值因素。与之不同,作为以个体为出发点的行为主义研究取向则必然会涉及到个人在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因素,因此,组织研究中的行为主义是对科学管理的否定,也是对受到科学管理运动影响的公共行政研究的否定。然而,价值因素的引入也给行为主义带来了极大的困惑。这是因为,行为主义者虽然反对科学管理无视个体的做法,但他们自身也是科学信念的追随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之所以反对科学管理,并不是因为他们反科学,而是出于这样一种理由,那就是认为科学管理排除了个体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因而,行为主义者要求在组织研究中超越科学管理的科学概念,要求在关照作为行为体的个人价值因素的前提下形成更为科学的研究结论。
不过,行为主义在对组织研究的科学追求中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个体行为出发开展的研究如何才能是科学的呢?或者说,个体主义视角下的所有研究都是科学的吗?有关个体行为的所有观点都能够被视为一种科学的见解吗?对于这些问题,行为主义者无法回答,然而,当时正在向社会科学进军的哲学流派——逻辑实证主义却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答案,那就是:只有关于个体行为中事实因素的研究才是科学的。也就是说,“人的因素”并不等同于价值因素,而同时包含了价值因素与事实因素,人所作出的判断也并不仅仅是价值判断,而同样包括事实判断。比如,在不考虑二进制的情况下,1加1等于2,这就是一种价值无涉的事实判断,而且这种判断是科学的。反之,如果一个人非要说1加1不等于2,则这种判断就变成了一个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显然是不科学的。所以,科学的行为研究只能是关于个体行为中事实因素的研究。根据这一似乎无法反驳的逻辑,行为主义的组织研究很快就臣服于逻辑实证主义了,“它们被许多人认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当今的社会科学世界中经常是‘彼此交融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方面。”〔12〕这种臣服的结果是,逻辑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崛起也被冠以“行为主义革命”的称号,到了这个时候,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概念已经雌雄难辨了。
当然,“行为主义革命”并不是“组织理论”兴起的全部背景,而只是这种背景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高斯在战后的反思运动中曾提出过“行政生态学”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战后关于公共行政公共方面的探讨也可以被称作公共行政研究中的生态途径或环境主义。虽然这种途径因为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而得不到实践者的认同,但由于它的倡导者普遍拥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依然是不容小觑的。根据沃尔多的看法,环境主义与行为主义实际上构成了50年代公共行政研究的两大途径,“在行为意味着法则而环境意味着各别的意义上,它们当然是相反的。这就是说,在定义上,法则与各别代表了关于现实或至少它是如何得到掌控与理解的相反观点:严格意义上的行为主义者的愿望与意图自然是去发现‘合乎法则的规律’,而后者则倾向于寻求与环境有关的‘理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的进步,行为主义与环境主义互相交织甚至或多或少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某些方面,它们不是彼此相反而是互为补充和相互协调的途径:行为主义的视角与目标可以被扩大到全部或部分地包含环境。……另一方面,对于理解一个特定问题而言,适当的环境变量的考虑可能是有利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样一来,就将一个明智且自制的人引向了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这一非常值得尊重的领域。”〔13〕也就是说,在极端化的意义上,行为主义的途径和环境主义的途径都发现了自己在解释现实上的缺陷。因而,在持续的互动中逐步走向融合,至少是达成了某种妥协,环境主义者缩小了自己的视野,行为主义者则放宽了自己的目光,在这种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两种途径都将自己的焦点转移到了一个中间地带。在中程理论的视野中,这种中间地带就是系统,而行政世界中的系统就是组织。所以,公共行政研究中“组织理论”的兴起,其实也是环境主义与行为主义两大途径相互妥协的结果。同时,作为一种中程理论,50年代的组织理论更多的是在系统的意义上看待组织的,这使它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超出了以往组织研究的范围:在广度上,它不仅关注单个组织,而且关注组织间的关系,关注由组织间关系所构成的行政系统;在深度上,它不仅关注组织的结构与功能,而且关注组织的个体成员,重视组织成员作为行动者的积极性,即注重组织管理中人的因素(当然,这里的人的因素是指事实因素)。
随着“组织理论”的兴起,公共行政的概念很快就显得不适应实践的要求,在中程理论的视野中,“行政”的概念显得过于宏大;而在行为主义的视阈中,“公共”的概念又与科学的标准背道而驰。结果,“在那些赞同关于‘协作行动’的科学路径的人中,存在着一种从‘行政’、‘行政的’与‘行政理论’转向‘组织’、‘组织的’与‘组织理论’的运动。据假定(借用我们的作者们所喜欢的一种表达),行为主义的方式与方法应当对这一运动负责。对此,……行为主义者最希望在关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中达到科学的水平,并将他们所理解的物理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作为模型。其总体目标是,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现象在给定条件下如何表现做出一种价值无涉的概括。……而行政(私人或公共)是一门应用科学——如果不是一项专业、一门艺术或者其他更卑微的事物的话。‘行政理论’则意味着对世界的一种参与,一种价值指导下的奋斗。……另一方面,‘组织’则意味着某种‘就在那里’的东西。当然,组织是充满价值的,但研究者不仅可以独立于某些组织的价值,而且可以免于像行政官员一样被不自觉地卷入到组织价值之中。他可以成为一名人类学家,完全超然于他所观察的社会。简单地说,组织理论——‘事情是怎么回事’——比行政理论——‘事情应当如何完成(至少如果你希望实现什么什么的话)’——意味着更少的价值参与。”〔14〕于是,在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行为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前提下,行政与公共行政的概念逐渐地被组织理论的基本概念所取代了。
与科学管理理论一样,“组织理论”所持有的也是一种一般性的视角,它强调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间的共性,淡化两者间的差异。比如,西蒙在他根据“组织理论”的一般观念写就并出版于1950年的《公共行政》教科书中是这样定义行政的:“当两个人协力推翻一块他们任何一人都无法单独移动的石头时,行政的雏形就出现了。这一简单的动作包含了被称为行政的两大基本特征。这里既有一个目的——移动石头,也有一种协力的行动——许多人使用结合起来的力量以完成没有这种结合就无法完成的事。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行政可以被定义为群体间协作达成共同目标的活动。”〔15〕根据这一定义,公共行政与私人行政显然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此,“公共行政研究可以有两大目标,它们在观念上可以分开,但在实践中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它可以关注(1)理解组织中的人如何行动,组织如何运作;(2)得到机构如何成为最有效组织的实际建议。当然,正如医学实践只能以关于人体生物学的科学知识的进步速度一样进步,有效组织和行政的技术也必须以一种关于组织中的人及其行为的健全理论为基础。”〔16〕在这段话中,我们看不到关于公共行政独特性的任何说明,在这一点上,它显然不符于战后公共行政学界集体性反思的总体趋势,因此,当西蒙试图将“组织理论”的观念引入公共行政研究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强烈反对。包括达尔、沃尔多与朗(Norton E. Long)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二战”后的反思运动所依据的是学者们在“新政”与战争期间的实际任职经验,而这种经验到了20世纪50年代已经过时了。对于反思浪潮中的那一代学者来说,基于这种经验而对西蒙所作的批评是有说服力的,但对于在新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潮流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来说,则显得文不对题。所以,尽管西蒙的观点在战后的反思浪潮中被视为异类,但随着这一反思运动因为理论基础的薄弱和现实环境的改变而迅速消退时,随着在“行为主义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逐渐登上了学术舞台后,西蒙的观点却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组织理论也逐渐成为了公共行政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一个替代性概念。甚至连西蒙最为坚决的反对者沃尔多,也在其出版于1955年的《公共行政研究》中采纳了“组织理论”式的公共行政定义:“公共行政是属于行政属类的一种,这个属类反过来又是我们称为‘人类合作行为’家族中的一员。”〔17〕当然,沃尔多是坚持公共行政之独特性的,但在上述定义中,他已明显受到了“组织理论”的影响,这充分证明,“组织理论”已经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的主流。与此同时,公共行政的概念则走向衰落。
如考夫曼(Herbert Kaufman)所说,“政治理论家高度依赖那些从历史、哲学与个人经历中获得的观点与证据,组织理论家则高度依赖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如果条件允许)控制性实验。政治理论家坦率地承认他们的规范取向,组织理论家通常只相信其工作是价值无涉的。政治理论家很乐意于与人际联合的无形方面打交道,因为很难对政府与政府机构的产出进行衡量;组织理论家则更习惯于与制造有形产品的组织打交道,并最终根据利润来衡量它们的效益。”〔18〕因此,随着“组织理论”的兴起,“50年代出现了两股非常独立的公共行政思想。一个强调其‘公共’的方面,另一个则强调其‘行政’的方面。但两者又都因为一整套全新的环境条件的出现而被遗忘或受到挑战。……顺带需要提及的是,50年代中期,对公共行政的兴趣出现了明显消退。许多学校取消了他们关于这一领域的本科课程,行政也越来越被视作——尤其在年轻人看来——一种由价值中立的专家所主导的技术领域。人们同意,行政官员有必要理解他在工作中所处的政治环境,但他的目标仍然是对他人制定的政策的中立执行。”〔19〕也就是说,随着“组织理论”的兴起,战后学者们关于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反思受到了否定,尽管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但公共行政研究却再度回到了“组织与管理”的传统范畴之内,从而失去了它刚刚意识到的赖以生存的根本——对于公共问题的独特关注。
三、公共行政学的危机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早期公共行政研究在“组织与管理”的范畴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现在回归这一研究主题又有何不可呢?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显然是没有考虑到当时管理学的突飞猛进。我们知道,在市政研究运动中,关于企业管理的研究还只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市政研究者与企业研究者基本处于一个同等的科学竞争平台上,两类研究者关于“组织与管理”问题的看法都有着独创性的价值,因而都能够为其所属的学科赢得社会的承认和尊重。然而,自“新政”以来,市政研究者纷纷转型为政府研究者,他们关注的对象早已从微观的“组织与管理”上升到了更加宏观、也更具有特殊性的公共问题,至于在“组织与管理”等一般性问题上的发言权,则拱手让给了企业研究者。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企业研究者及其所开创的管理学已经牢牢掌握了在“组织与管理”等问题上的话语权,也掌握了公共行政研究者所不拥有的一整套分析方法和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行政学向“组织与管理”回归,只能是自取其辱。比如,在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史上,以古利克为代表的早期公共行政学者占有无可争议的地位,而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除了西蒙之外,我们是无法举出一个可以被称为管理学家的公共行政学者,即便是西蒙,也远不及古利克等早期学者。这充分说明公共行政学在20世纪后期被组织管理研究所边缘化了。
既要以组织管理问题为研究对象,又不能在组织理论的方向上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更无法回应政府在实际运行中所面对的特殊问题,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吗?因此,当公共行政学实际上蜕变为“组织理论”后,公共行政研究也就全面地陷入了低潮。并且,这种低潮并不是暂时的,而是20世纪后期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基本状况,即使在“新公共行政运动”之后,也没能摆脱这种不景气的状况。在80年代的一篇采访中,沃尔多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公共行政’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人而言并不是一个名声很好的词语,我同意这一假设。但要加上‘不幸地’。我的公开态度,如你所知,倾向于一种拥有自己的组织身份并以公共行政为名的项目。……在总体上,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即如果公共行政研究被安排到政策项目或企业学院中会带来更多的名望、资金与切题性。我认为政策研究的倡议是适当的。尽管已经认识到了政策制定是行政的一个部分,但公共行政研究并没有对这一挑战作出人们所期望的回应。另一方面,一个新名称与新开端的最初优势已经消失。我所看见正在发生的是,体现在某些传统公共行政学和某些新政策研究中的兴趣的融合——无论怎么称呼它。……就被安排到企业或管理学院中的情况来说,名望和资源严重不均的问题也没能得到解决。事实上,它可能得到了强化。当我与企业学院中的公共行政学者谈到这一最重要的主题时,只有一次,他们没有一种被孤立、忽视和作为二等公民的感觉。”〔20〕事实上,从政策科学、组织理论到后来的公共管理的复兴,都包含着一种试图抛弃公共行政概念的倾向,从而致使公共行政学成为学术王国中二等公民,而且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沃尔多所描述的其实不只是20世纪中后期的情况,而且在今天依然是公共行政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公共行政学者中,沃尔多是较为擅长修辞的一位,因此,尽管他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多原创性的贡献,但他的一些宣言性的文章却总是能够在当时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比如,在1968年的“明诺布鲁克会议”上,学者们之所以能够展开如此激烈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沃尔多的《骚乱年代中的公共行政》一文在参会者们的头脑中投射进了可供争论的无穷话题。除了沃尔多的这篇论文之外,明诺布鲁克会议的组织者还提前向每位参会者提供了当时的另一份重要文献,那就是以公共行政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为主题的“赫尼报告”,这份报告对当时公共行政研究生教育的窘境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报告指出,“这一领域是很小的:公共机构中居于可以承担责任级别的官员的主要培训经历显示,来自公共行政项目的人所占比例可能不超过3%到4%。1964年一共只授出了约400个公共行政研究生学位。”〔21〕这一数据表明,公共行政研究在实践者群体中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同。“在实践者之间存在这样一种感觉,认为公共行政学者的学术兴趣是琐碎的,是与真正的公共服务问题无关的,而且学者与实际工作距离太远,因而根本无法成为好的教师、咨询对象或研究者。”〔22〕由于有了这种认识,实践者当然不会给予公共行政研究以充分的支持,相反的情况是,“本领域中普遍缺乏各种资源……,由于奖学金的严重不足,被吸引到公共行政领域的优秀学生的数目远远不够。教员数量通常也存在短缺,与之相伴的是过度拥挤的教室、办公室和图书馆。研究基金很难获取,尤其对于那些非项目性质的研究和除了那些高度应用性的调查以外。在大多数项目中,院长、所长们都在抱怨总是需要为了在财政上生存下去而不断挣扎,抱怨不可能在研究、课程开发以及相关培训活动上作出创造性的开拓。”〔23〕
由于存在着这些不利条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人们对公共行政的地位仍然缺乏共识:它被认为既不是一个专业、一门科学,也不是一个知识门类。在学术上,它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个训练基地,不断制造出伪装成通才的专家。简言之,公共行政的学术领域仍然处于一个未经定义和没有得到承认的状况之下。”〔24〕甚至,根据巴洛维茨(James M. Banovetz)的看法,“公共行政学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之中。它对公共机构和学术共同体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赫尼报告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没能足够响亮地拉响警报。这一领域正站在十字路口:它既可以冒着消失或被其他领域吞并的风险而维护其既有的存在,也可以通过扩大其对于公共机构和大学中公共事务项目的影响而使自己得到重组、重新定位与再度振兴。”〔25〕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公共行政学科的基本状况,在这种日益紧迫的危机形势面前,公共行政学者们必须作出选择,新公共行政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总的说来,在“政策科学”将政策研究从公共行政学中剥离出去之后,“组织理论”确立了行为主义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主导地位。随着行为主义取得了垄断地位后,“二战”后学者们对公共行政的集体性反思却受到了否定。这个时候,公共行政研究既不关注政策问题,也不强调公共行政相对于私人行政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公共行政研究既失去了政策视角,又失去了公共意识,结果,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行政学就从市政研究运动以来的长期繁荣而逐步走向衰落,陷入了学科危机之中。不过,我们也看到,公共行政这一学科并没有消失,它的合法性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动摇,这是由于政策科学和组织理论研究上的缺陷造成的。因为,政策科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事实上反对任何学科导向的研究;“组织理论”也只是关于组织的理论,一直没有把自己宣示为一门学科。所以,公共行政的概念仍然具有标示研究对象与研究名称的功能。不过,公共行政学的危机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危机,才孕育了试图重振公共行政研究的“新公共行政运动”。从理论倾向上看,“新公共行政运动”与战后的公共行政反思运动有着诸多相似的方面,但是,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学者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称作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呢?是由其具体的学术背景所决定的。因为,20世纪50、60年代以“组织理论”为基本内容的公共行政研究否定了战后的公共行政反思运动,对这一状态的否定也就称作为“新公共行政运动”了。
〔1〕〔3〕〔5〕Graham Allison, Emergence of Schools of Public Policy: Reflections by a Founding Dean, in Michael Moran, Martin Rein and Robert E. Goodin, (eds.),TheOxfordHandbookofPublic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64,p.65,pp.64-65.
〔2〕〔6〕Aaron Wildavsky, The Once and Futur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ThePublicInterest, Number 79, (Spring, 1985), pp. 25-41, pp. 25-41.
〔4〕John Brandl, Public Service Education in the 1970s,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nimeo., January 1976, p. 2, quoted in H. George Fredericks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1970s: Developments and Directions,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Vol. 36, No. 5, Special Bicentennial Issue: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ree Centuries (Sep. - Oct., 1976), pp. 564-576.
〔7〕John P. Crecine, University Centers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Organizational Viability,PolicySciences, Vol. 2, No. 1 (Mar., 1971), pp. 7-32.
〔8〕Albert Lepawsky, Graduate Education in Public Policy,PolicySciences, Vol. 1, No. 4 (Winter, 1970), pp. 443-457.
〔9〕E. S. Quade, Why Policy Sciences?PolicySciences, Vol. 1, No. 1 (Spring, 1970), pp. 1-2.
〔10〕〔21〕〔22〕〔23〕John C. Honey, A Report: Higher Education for Public Service,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Vol. 27, No. 4, Special Issue (Nov., 1967), pp. 294-321, pp. 294-321, pp. 294-321, pp. 294-321.
〔11〕〔14〕Dwight Waldo, Organization Theory: An Elephantine Problem,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Vol. 21, No. 4 (Autumn, 1961), pp. 210-225, pp. 210-225.
〔12〕Dwight Waldo,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Revisited,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Vol. 25, No. 1,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Issue (Mar., 1965), pp. 5-30.
〔13〕Dwight Waldo,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JournalofPolitics, Vol. 30, No. 2 (May, 1968), pp. 443-479.
〔15〕〔16〕Herbert A. Simon, Donald W. Smithburg, Victor A. Thompson,PublicAdministratio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p. 3,p.19.
〔17〕〔美〕德怀特·沃尔多.什么是公共行政学〔A〕.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87.
〔18〕Herbert Kaufman,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olitical Theory,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Vol. 58, No. 1 (Mar., 1964), pp. 5-14.
〔19〕Alan K. Campbell, Old and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1970's,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Vol. 32, No. 4 (Jul. - Aug., 1972), pp. 343-347.
〔20〕Brack Brown, Richard J. Stillman II, Dwight Waldo, A Conversation with Dwight Waldo: An Agenda for Future Reflections,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Vol. 45, No. 4 (Jul. - Aug., 1985), pp. 459-467.
〔24〕〔25〕James M. Banovetz, Needed: New Expertis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Vol. 27, No. 4, Special Issue (Nov., 1967), pp. 321-324, pp. 321-324.
【责任编辑:刘明】
D523
A
1008-9187-(2012)04-0005-10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985工程三期”改革型项目资助研究
张康之,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3;
张乾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