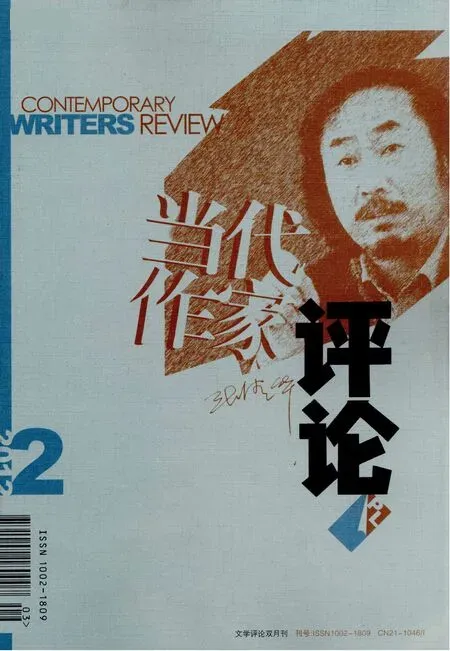“莫若以明”——读《庄子·齐物论》感北岛诗艺
2012-12-18亚思明
亚思明
《齐物论》是《庄子》全书中义理最为丰富的一篇,它以一种“齐物”的价值观、宇宙观来烛照万物,以齐“物论”,于百家争鸣的是非争端中跳脱出来,“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是哲学家、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语言风格用清代学者刘熙载的话来说,“如空中捉鸟,捉不住则飞去”,“意出尘外,怪生笔端”。①刘熙载:《艺概》,第18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正是这种模糊多义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使得庄子学说得以突破认识论的藩篱而带有一种语言哲学的特质。
例如《庄子·齐物论》中有这样一段被后人称之为“相对主义”的精彩论述: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黄锦钅宏的译文如下:
人们的言论,和自然的风吹并不相同,所以学者们尽管发议论,但他们议论的对象是没有一定的准则。(既然这样)那他们究竟是发了议论呢?还是没有发议论呢?他们都以为所发议论是有分别的,和小鸟有声无意的叫声有所不同,可是究竟是有分别呢?还是没有分别呢?“道”被什么隐蔽了而有真伪?“言论”被什么隐蔽了而有是非?“道”在那里而不存在呢?言论怎么会有不可的呢?“道”是被小成有偏见的人隐蔽了的,言论是被浮华巧饰的人隐蔽了的。因此才有儒家、墨家的是非争论,他们都以自己认为“是”的意见去批别人的“非”,而以自己认为“非”的意见,去批别人的“是”。要想纠正他们的错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莫过于“以明”。②黄锦钅宏注译:《新译庄子读本》,第72页,台北,三民书局,2007。
庄子的这段论述令我想起诗人北岛的一个观点:“文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正面对抗,往往会成为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③北岛:《艾基》,《时间的玫瑰》,第282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因此,若要减弱语言的暴力倾向,解构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就必须从词语出发带来形式上的开放,如罗兰·巴特在《零度写作》中所说的那样:“闪烁出无限自由的光辉,随时向四周散射而指向一千种灵活而可能的联系。”
作为新诗潮的领军人物,北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部分创作被贴以“朦胧诗”的标签存入文学史的档案馆。这一称谓的含混指涉①引起争议的北岛的《太阳城札记》、《结局或开始》、《回答》和《一切》都是构思或完成于1974年到1977年,然而,迟至1980年它们才被冠以“朦胧诗”之名。见李润霞编《被放逐的诗神》,第411、413-417页,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无碍于那些锐利而凛冽的诗作,连同诗人勇于质疑现状以及高声呐喊的英雄形象的深入人心。“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警句。但今天如果有人提及《回答》,他会觉得惭愧,因为站在“文化大革命”废墟上的北岛,他在《回答》里的石破天惊的那一句“我──不──相——信!”与诗相比更像口号,从一个是非之端滑向另一个是非之端,正如庄子所说的,“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刘小枫将北岛这一代人划为四五一代,并说:“四五一代从真诚地相信走向真诚的不信,为拒斥意义话语的物件性失误提供了条件,也给出了新的危险。”②刘小枫:《“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第13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八十年代末期,北岛开始进入一种漂泊及孤悬状态,北岛坦言:“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在北欧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陷入绝望,默默祈祷,为了此刻也为了来生,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经历无边的虚无才知道存在有限的意义。”③北岛:《自序》,《失败之书》,第2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这种虚无之旅在认识论上有些类似于“心斋”(《庄子·人间世》)、“坐忘”(《庄子·大宗师》)的直觉体悟,从而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的六年之间,搬了七个国十五次家的北岛经历了包括年龄、心态到语言的转换。直至他后来从欧洲迁居北美,再从北美回归香港,近二十年的多国游历不仅开拓了视野,也因此而让他获得某种思维越界的批判能力:远离权力中心和大众喧嚣,行走在物质世界的边缘,忍受孤独,但也有勇气否定自己,“重估一切价值判断”。跳出以往的是非成见之圈,北岛对自己早期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④翟頔、北岛:《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书城》2003年第2期。
静观北岛九十年代以后的创作,不难发觉心路的变化也在他的笔端留下了痕迹:诗韵由激越趋于平静,文字暗藏锋芒而内敛幽思,远是非而近乎道,用庄子的话来讲:摈弃“是故滑疑之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庄子·齐物论》)。也就是说,他不再炫耀智慧和言论,而是将之寄托于中庸之道,这就叫做“以明”。
例如《旧地》中,他写道:
此刻我从窗口
看见我年轻时的落日
旧地重游
我急于说出真相
可在天黑前
又能说出什么
饮过词语之杯
更让人干渴
与河水一起援引大地
我在空山倾听
吹笛人内心的呜咽①北岛:《旧地》,《午夜歌手》,第222页,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
这首诗给人一种“欲语还休”的苍凉之感。真相是无法言说的。“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庄子·齐物论》)言之不尽,不如“与河水一起援引大地”,在空山倾听,“吹笛人内心的呜咽”,是地籁,是人籁,还是天籁?
海德格尔曾说,“诗是那无法表达的东西的语言”。海德格尔认为:“诗意并不是作为异想天开的无目的的想象,单纯概念与幻想的飞翔去进入非现实的领域。诗作为澄明的投射,在敞开性中所相互重叠和在形态的间隙中所预先投射下的,正是敞开。诗意让敞开性发生,并且以这种方式,即现在敞开在存在物中间才使存在物发光和鸣响。”②海德格尔:《诗·言·思》,第6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因此,诗意是真理投射的一种方式,诗意的天性即投射的天性。这在北岛的《夜》中也有类似描述:
夜比所有的厄运
更雄辩
夜在我们脚下
这遮蔽诗的灯罩
已经破碎③北岛:《夜》,《零度以上的风景》,第96页,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
“夜”是一种隐喻,暗示未知的黑暗,它的雄辩在于谬误的言说。而“诗”好比澄明的投射,一旦让“遮蔽诗的灯罩”破碎,真理之光就能照进黑暗,改变我们的厄运。
诗意也是一种道的言说,即庄子所谓的“照之于天”或“以明”。正是以诗意为媒,我们才能从北岛的诗中读出“庄味”。例如《二月》中的一段与“庄周梦蝶”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早晨的寒冷中
一只觉醒的鸟
更接近真理
而我和我的诗
一起下沉④北岛:《二月》,《零度以上的风景》,第56页,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
究竟是“我”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了鸟,还是鸟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了“我”?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与鸟必定是有分别的,但从道的角度来看,两者皆是梦,好比《庄子·齐物论》里的庄周与蝴蝶,不过是“物化”的幻象而已。而觉醒的鸟“更接近真理”,寓意着生命的觉悟和超升。
了解到庄子的“物化”之理,就能更好地辨析被语言歧义所遮蔽的诗意的微光。而“所有的诗艺和所有的诗情/不过是对现实之梦的说明”。⑤这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亨斯·萨克斯(Hans Sachs)在《善歌者》(Meistersinger)中的诗句:“朋友呵,这正是诗人的责任;去阐明和记下自己的梦境。信我吧,人间最真实的幻影/往往是在梦中对人们显现;所有的诗艺和所有的诗情/不过是对现实之梦的说明。”
以一种释梦的心态阅读难懂程度不下于梦中呓语的北岛诗语,洞彻时的快慰感不啻于“开锁”:
一扇窗户打开
像高音C穿透沉默
大地与罗盘转动
对着密码——
破晓!⑥北岛:《开锁》,《开锁》,第 164页,台北,九歌出版社,1999。
而北岛后期诗风的变化令“开锁”的关键词的语义由大变小,从强到弱,由实质转为虚空,正如《关键词》一诗中所表现出的:
,我的影子
捶打着梦中之铁
踏着那节奏
一只孤狼走进
无人失败的黄昏
鹭鸶在水上书写
一生一天一个句子
结束①北岛:《关键词》,《零度以上的风景》,第126页,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
关键词带有语言暴力的色彩。在官方话语体系里,词语没有呼吸,没有生命,词语的意义被刻意地扭曲——意识形态化。例如:祖国即母亲,党即父亲,红色即革命。“这就是权力在语言深处的延伸,从而改变人们的言说和思维方式”。②北岛:《艾基》,《时间的玫瑰》,第308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一心追求诗艺精进的北岛试图摆脱关键词的束缚,就像持灯的使者试图摆脱自己的影子。但自由之于暴力、光明之于阴影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纵行空谷亦闻足音。正是踏着这种暴力的金属的铮铮之音,诗人好比一只孤狼走进他梦中的诗境。这是艺术的臻境。这是“无人失败的黄昏”。而在庄子看来,世上本来就没有成功与失败的分别:“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惟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庄子·齐物论》)。
万物乃在成就另一物,而另一物的成就,也就是建立在毁坏他物上。其实万物是没有什么生成与毁灭的,而是通而为“一”的。只有得道明达的人才能了解这通而为“一”的道理。因此就不用辩论,而把智慧寄托于平庸的道理中。③黄锦钅宏注译:《新译庄子读本》,第73页,台北,三民书局,2007。
“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也就是“以明”。没有大是大非的争辩,好比“鹭鸶在水上书写”,写下的一刻也是消逝的一刻,生成与毁灭都是通而为“一”的。一生如此,一天如此,一个句子亦是如此,直至“结束”。
据说,汉学家魏斐德曾经朗诵北岛这首诗的英文版,读到“一只孤狼走进/无人失败的黄昏”时,不禁流下了眼泪。④见王寅《魏斐德:熟悉的陌生人》,《南方周末》2006年11月9日文化版。打动他的一定是那一只孤狼。孤狼是现实社会里的失败者。北岛如此,庄子如此,魏斐德如此,卡夫卡亦是如此。⑤德国文艺评论家和哲学家本雅明曾说:“要理解卡夫卡的作品,在所有的事情里,首先要有一个简单的认识,那就是,他是一个失败者。”对此,北岛有自己的理解:“失败,在我看来是个伟大的主题,它代表了人类的精神向度、漂泊的家园、悲哀的能量、无权的权力。我所谓的失败者是没有真正归属的人,他们可能是伟大的作家,也可能是小人物,他们与民族国家拉开距离,对所有话语系统保持警惕。失败其实是一种宿命,是沉沦到底并自愿穿越黑暗的人。”⑥王寅、北岛:《失败者是没有真正归属的人》,《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1月26日第D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