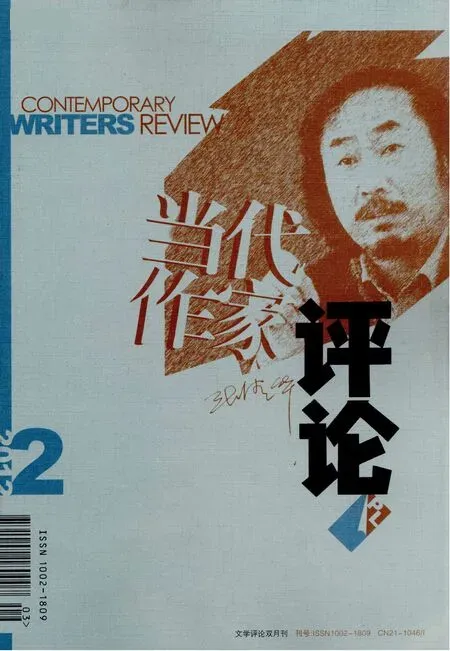“主旋律”报告文学的叙事优化——读《朋友,我能给你什么》
2012-12-18丁晓原
丁晓原
一
报告文学是别为一类的写作样式。按写作价值取向的不同,有言者将其析为“问题报告文学”和“主旋律报告文学”。对于前者,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郭冬、李炳银等做过命名和论述。①郭冬:《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面面观》,《文艺报》1988年1月2日;李炳银:《“问题报告文学”面面观》,《解放日报》1988年1月26日。而于后者,虽多有约定俗成的意会言说,但却没有较为正式的释义。“主旋律”一词原是意指音乐作品或乐章的旋律主题。显然,在命名当代文学艺术的类型时使用这一语词是一种喻指。有学者曾经对“主旋律小说”进行某种定义:“主旋律小说就是特指那些以当代政治为背景,以转型期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反映当前政治体制下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直接地或借历史的方式反思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引起人民对当今政治体制和社会问题关注的一种小说形式。”②谢金生:《转型期主旋律小说研究——以现代化为视角》,第12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其实,在我看来,定义主旋律文学不必这样复杂。构成主旋律文学的有两个核心关键词:一是表现体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二是体现出歌颂式的政治修辞特征。由此可见,所谓“主旋律报告文学”可以表述为反映并歌颂当代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传导主流价值观念的非虚构作品。这里的主旋律所表示的主流价值观念,通常可以用“时代精神”置换表述,而表现时代精神正是当代中国通讯写作一再强调的基本要求。穆青就认为人物通讯应写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人民群众“他们的精神境界、思想风貌,就是他们作为国家、社会主人翁那种历史主动性的最本质的表现。这种精神和思想,应该成为人物通讯的基本的主题”。③穆青:《谈谈人物通讯采写中的几个问题》,《穆青论新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从文体的流转我们可以看出,主旋律报告文学基本上导源于新闻通讯。我们现在所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也被指称为著名通讯。这一类写作就是一种典型的主旋律报告文学。
我们将报告文学视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以现实报告为基本特征、以社会批判为重要价值取向的报告文学与以人类基本价值守护为使命,以人文关怀和启蒙性、批判性为基本职志的知识分子之间,具有相互契合的内在逻辑”。①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第25-2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基于这样的文体理念,一般地认为主旋律一类的作品缺失报告文学应有的文体品格和精神。得出这种判断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写作方式理解的不完整。作为人类良知的守望者和公共理性的代言人,知识分子当然要对良知泯灭、理性缺失的存在履行批判的职志;但与此同时,对体现人类崇高精神、美好人性的人与事进行讴歌,也应当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应体现为公共理性的精神。无论批判还是歌颂,都应持守这样的理性精神和逻辑。其二与主旋律报告文学写作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这些问题主要有:在主题呈现上,主旋律写作成为政治化写作,主流价值的表达成为某种形式的说教;在叙事设置上,对表现对象作过度的典型化提纯,弱化了客体存在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淡化了生活原有的质感;在表达形制上,多通讯化模式,少非虚构文学应有的意趣情味和主体的个人性。根据以上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主旋律报告文学是这一文体重要的构成部分,但在写作中应对其作更多优化的处理。
二
正是在这里,我们有了对《朋友,我能给你什么》进行解读的必要。无疑,辽宁作家周建新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也可归为“主旋律”非虚构。报告文学写作并不是周建新的主业,他以小说创作在文坛立业,曾著有长篇小说八部。写作《朋友,我能给你什么》之前,周建新发表了叙写家乡航天英雄杨利伟成长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飞天骄子——杨利伟》。《朋友,我能给你什么》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辽宁鞍钢齐大山铁矿的全国道德模范郭明义。这部作品的生成模式体现了一般主旋律报告文学写作的基本特点。首先人物郭明义是国家主流力推的全国性重大典型,主流媒体对其作有大量的报道,其中重要的报道有《人民日报》长篇通讯《新时期的道德模范——郭明义》、新华社长篇通讯《世界上什么最幸福》等。其次作品的写作是一种“政治任务”,作者随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和省总工会联合调研采访团采写对象,是一种具有很强“规定性”的写作行为。再次,人物本身具有突出的政治性。郭明义给定了自己的政治身份:“有怎样的人生追求,就会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成为一名党员是我毕生的光荣,我会一辈子按照党指引的道路走下去。”党的最高领导人也特别地揭示郭明义的形象价值:是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是新时期学习实践雷锋精神的优秀代表。这样多种写作的先在和背景,一方面为作者的写作创造了一些便利,但另一方面显然也增加了作者写作的难度系数。事物辨证的关联无处不在,“便利”的另一端可能就是某种“有限”。因此有价值的“再写作”,应在“有限”之中开拓富有主体能动性的“无限”。而就郭明义的长篇非虚构写作而言,就是要寻得既能满足主旋律写作的一些规制,同时又能体现文学叙事基本要求的某种“协调”。从《朋友,我能给你什么》的写作实际看,作者在实现两者的“协调”上作出了自觉的努力,并且这种努力是有效的。不仅如此,作者在协调两者的具体处理中,更多地注意到了向文学的非虚构叙事的偏重。这是《朋友,我能给你什么》具有更多的叙事滋味的本源性因素。
作为写实体的报告文学,因其独特的非虚构的文体规定,无法像小说那样进行虚构,这样对实体对象作出选择,就成为这类写作的关键环节。在这一点上,报告文学与新闻通讯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文类属性、功能以及篇幅容量等的不同,新闻通讯更多地考虑其宣传性、新闻性,强化报道人物事件的典型性,围绕主旨,注意突出先进事迹,选材取事较为凝练集中;报告文学则更重视叙事的文学价值,更多地从实际生活出发,还原人物和事件的本真存在,通过日常生活图景的叙述,展示人性的诸种构成。《朋友,我能给你什么》作者周建新注意到了这两种文体的不同,在选择报告对象时,重视从非虚构文学写作的角度提取质料。报告对象是丰富的,“考验我的是剪裁能力,取舍的本事。我不能把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郭明义写成一个好人好事的堆砌物,我不能不去深入地探究郭明义心灵最深处的东西,不能不去挖掘郭明义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之源”(《朋友,我能给你什么·后记》)。周建新对于郭明义这种取舍考虑是很得报告文学之体的,舍的是一般的“好人好事的堆砌物”,取的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郭明义”;舍的是外在的表层的浅叙事,取的是对于人物“心灵最深处的东西”的“挖掘”。从作品的结构设计看,《朋友,我能给你什么》具有纪传体报告文学的特点,但这种纪传体是不完全的。全篇十四章前五章,从家庭、从军、工作等,纵向地展示郭明义的人生历程,这里局部地采用了纪传体结构;第六章后叙写郭明义多方面的“爱的奉献”,采用的共时平行的分述结构。纪传体部分给出了人物成长的轨迹和精神渊源,分述部分则多维度地叙写人物仁者爱人、乐于助人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品格。一部《朋友,我能给你什么》,既是郭明义先进事迹的荟萃,更是展示他美好心灵的精神成长史。
三
人物自身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物类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朋友,我能给你什么》的主人公郭明义在新世纪新的社会语境中推出,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时代意义。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更为深刻的转型,市场经济倡导物质优先,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思潮纷杂,价值多元,物质主义至上,人的精神性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滞后。社会现代化有多种观照的尺度,经济的尺度无疑是基础性的,十分重要。但人的尺度更为重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是人,其发展的旨归也是人。如果没有人的全面发展,人丢失了人之为人的精神和品性,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真正的现代化。正如康德所言:“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最能震撼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如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没有了“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那么物质的现代化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新世纪以来尽管我们每年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心灵崇高感动得潸然流下,但现实中人基本的道德法则被丢弃的事件屡见不鲜。有鉴于此,主流意识形态强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传,通过树立道德模范在全社会弘扬正面的价值伦理。从这一点看,郭明义符合主流价值在这一特殊时期的需要,在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中华民族的美德和现代公民的良好素质。爱岗敬业,干一行成一行,遭遇下岗不怨怒,当公路管理员十五年,“起早贪黑,不休节假及休息日,多干了五年的工作量”;热爱国家,外资企业高薪吸引,不为所动;心想他人,助人为乐,“工作二十八年,总收入二十九万元,为‘希望工程’、困难职工和灾区群众累计捐款十四万元”,“二十年来,累计义务献血六万毫升,相当于自身总血量的十倍”。值得注意的是在郭明义身上,不只具有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主流政治价值,同时也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的人类精神。他的精神的核心是敬业仁爱,正是在这一点上,主流价值与人之为人的公共价值实现了谐和融通。也正是由于两者的谐和融通,使得这一主旋律作品的叙事有了可以优化、能够优化的内在肌理。
一般而言,主旋律报告文学其报告的客体具有某种典型性。只有具有典型的价值,才能使之成为传输主流价值的载体。但报告文学的典型性不同于那种“比普遍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虚构生成,它是基于客体现实存在本身的,在其内部所作的典型化选择。周建新在叙写郭明义时,注意把握对象作为先进典型与凡朴个人的关系,既注意凸显郭明义这一重大典型的某种高度,如开篇从党的总书记的批示切实,突出人物不同一般的重要价值。第九章《携爱而行》,有“播撒爱的种子”、“爱洒北京”、“情满重庆”和“心系九州”,叙写郭明义巡回演讲及其关爱他人的事迹,展示人物先进事迹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同时更注意将人物置于生活原本中加以再现,立体地反映他作为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和平凡中显示出的崇高。郭明义身份定位中既有共产党员一面,也有普通人的自我确认:“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做的也是普通的事儿,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周建新对典型有着自己清晰的认知:“典型更需要有人性的价值”。人物自身和作家主体关于对象独特性所形成的这种“共识”,使《朋友,我能给你什么》写作的重心定位和结构安排有了内在的逻辑理据。作品中所写的郭明义是一个平民模范,所呈现的人物是平民中模范,模范中的平民。这样的人物多了生活感、真实感、亲切感,自然也增强了作品叙事的美感。作品中“承诺粪土也是金”、“意外成了火头军”、“养猪也不差”、“遭遇分流”、“岗位上的犟牛”、“‘小抠’郭明义”等小节,从标题就可看出叙述的内容,人物的普通人生景象。由于作品不限于表现作为典型的人物而注重日常生活中的人物,所以所给出的人物是多维多面的立体。在第六章《生命的宽度》“多面郭明义”中,作者借工友的评价和议论,将多面的人物作了诸多的描述:“大傻”、“大侠”、“大使”、“大彪”、“大狂”、“大倔”、“大烦”、“大魔”、“大凿”、“大怪”、“大圣”、“大好人”等等。这些命名表示着生活中的郭明义的真实存在。作品对人物这样的再现,使郭明义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棱有角的“圆形人物”。
除了要协调对象的主流价值与公共价值,把握表现内容的典型性与日常性等以外,主旋律报告文学的叙事优化,还应处理好政治修辞与个人修辞的。文学不是政治,但政治是文学反映的重要存在;从历史传统到现实实在看,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相对鲜明的政治意味或泛政治化色彩的文体。主旋律报告文学更是无法回避与政治的关联,需要讨论的是作家如何以文学的修辞来表现对象。在实际的写作中,主旋律作品会有政治的修辞进入,需要注意的是作家应以文学的方式“中和”政治的表述。从《朋友,我能给你什么》作品看来,作者周建新为适应一些政治性内容表达的需要,运用相应的政治修辞,但是有限的。作者更多的是基于对郭明义价值、叙事重心等把握,采用更多的个人修辞。作品的叙事是低调的、朴素的,这与人物品格合致,与一些政治叙事的高调不同。作者的小说家的背景以及对郭明义较为深入的认知,使作者自觉地注意以对象自身的独特性反映其个人性,既反映郭明义的先进性,又呈现其趣味性。作品的题目《朋友,我能给你什么》是一句诗语,一、二人称的表述显示出作品的真切而别致,而这出自郭明义自己的诗作。作品中插入郭明义的诗歌、散文,这既是作品叙事的有机构成,同时也以这种方式凸显了人物的情趣和心灵世界,“文学是郭明义灵魂的伙伴,崇高的支撑”。作者还特别注意以个性化的行为细节和人物语言,强化郭明义的个人特质品格。外出时妻子给郭明义一千元钱,“一路上郭明义没舍得花,心里盘算的是可以接济几个孩子”,在商店见到款式别致的“钻戒”,“一打听价格,才二十八块钱。不耽误援助一个孩子。他一咬牙,就买下了”。这一细节将人物的夫妻情与助人为乐的大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是个简单的人,是个还保留着童真的人”,“我能走到今天,感谢我没有当上官,真的”。这样的语言是祛政治化的,是人物本色语。
以上我从主旋律作品的角度对《朋友,我能给你什么》作了一些解读。我并不是说《朋友,我能给你什么》的写作已经尽善尽美,但这部作品确实在多个方面可以给同类写作提供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