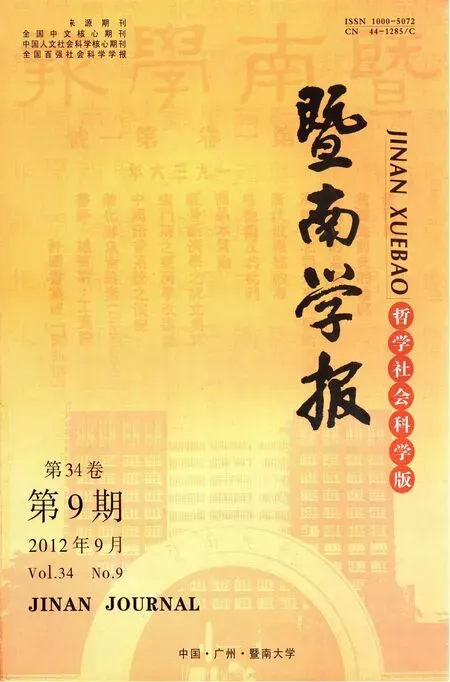论《黄帝四经》对老子思想的修正
2012-12-17乔健
乔 健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黄老思想是战国时期的“显学”[1]重排版序、[2]92,黄老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1]序27-28①陈鼓应的《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前一部分由《北京商务印书馆重排版序》、《序》、《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关于帛书〈黄帝四经〉成书年代等问题的研究》等构成,为了标注的方便,本文将这一部分的《重排版序》之外的全部内容统称为“序”。,而作为“现存最早也最完整的黄老道家的作品”的《黄帝四经》②《黄帝四经》是1973年于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抄于帛书《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种古佚书,有学者将其称之为《黄帝四经》,有学者不同意这一称呼,但目前“《黄帝四经》”的命名多少算得上是约定成俗了(参见曹峰《楚地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研究》第2-3页),所以本文也权且采用《黄帝四经》的名称,很多时候简称为《四经》,文字以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为准。曹峰提出“反对将这四种卷前古佚书看作是由一人一时完成的一部完整的著作”(曹峰《楚地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研究》第3页),但陈鼓应则认为《黄帝四经》是“一人一时之作”(《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序第35页)。本人认为《黄帝四经》即便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其基本观念的相通相合处也甚多,更何况有人把这四篇东西放到一起也应该与其基本观念和思维逻辑的相通相近有关,所以本文将《黄帝四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1]序1在黄老思想系统中又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3]30。《黄帝四经》吸收《老子》之处甚多[1]序5,但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黄帝四经》又在根本上“修正”了老子③严格说来“老子”是书名而非人名,《老子》中的内容也可能不全是“老子”本人的东西,所以严谨的学者往往给“老子”加上书名号,但本文为了行文的方便一般不加书名号。以“自然→无为→自为”为主干的思想[4]。
老子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和总依据,自然也是老子对人类社会进行认知和批判的依据,因而它带有浓重的“终极价值”的色彩,具有极强的“超越性”,而《黄帝四经》则将老子的“道”向“社会性倾斜”[1]序6,一旦如此《四经》就必然更加关注“道”的“现实性”、“实用性”和“操作性”,这样老子思想的“超越性”和“批判性”就必然会随之而大大减弱,老子思想中最根本、最有价值的内容也会被“修正”,最终老子主要着眼于“理想”、“应然”和“批判”的“道”,实际上就会被“修正”成主要着眼于“现实”、“实然”和“操作”的“术”[3]序4、65。
特别关注思想理论的“现实性”、“实用性”和“操作性”使得《黄帝四经》特别强调了“时”而抛开了“常”,因为“时”与必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因而具有“实用性”和“操作性”的“术”密切关联,就像“常”总是与“永恒”、“应然”的“道”相一致。当然老子对社会现实的认知非常深刻,他并没有脱离现实而在纯形而上的天国中恣意遨游,但相对于“现实”和“实然”,老子思维的触角更多地指向了“理想”和“应然”及以“理想”和“应然”为支撑的“社会批判”,而《四经》则表现出了一种认同和佐助当权者的思想倾向。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了老子提出的“理想”、“应然”及“社会批判”具有永恒普世的警示、参照和引领的价值,而《四经》的思想则仅仅有一时的作用。
《四经》对“时”的强调还使其特别注重更加“确定”、“实用”但却只能作用于“一时”的“法”和“形名”,同时也在强调贵贱等级的基础上突出了“君王”的地位,因为“君王”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从“一时”来看“君王”的作用巨大,把各种权力和资源集于君王一手,使君王能够凭借“法度”等有效地掌控、役使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和手段的寻常百姓,在“一时”间的确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把寻常百姓变成工具和手段就必须采取有效的“御民”之“术”,这种“术”的核心内容就是“文”与“武”、“刑”与“德”两手的相互配合、交相为用,这与老子具有“绝对”性质的“任人自为”观念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也与老子对“雌”、“弱”、“下”的“绝对”偏重及与这种偏重密切关联的“绝对反战”根本不同[4]。另外老子一系列带有“绝对性”的思想观念具有突出的价值“一元”的性质,而《四经》作者的“文武”、“刑德”观则是一种“二元”性质的价值观,《四经》作者与老子的这种根本性区别的产生,应该与《四经》作者将老子的“道”修正成“术”密切相关,因为强调“术”往往就要强调各种手段的相互配合和灵活运用,这就使其在特定的“手段”的意义上有“二元”的倾向,而强调“常”则往往必然会执着地强调和追求具有“绝对”性质的价值,就必然会产生“一元”的倾向。下面就对上述问题进行具体的论述。
一、《黄帝四经》的“时”、“天”、“常”等所体现的对老子思想的修正
强调“时”是《黄帝四经》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与老子强调“常”[5]327,[6]95有着根本的区别。陈鼓应指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称赞道家的一大特长为善于掌握时机(‘与时推移’),指的就是黄老道家”[1]序15;“讲究实际、实用、实效,因时制宜,乃是黄老思想之特点。‘时异则事变’之说盖滥觞于此”[1]300; “‘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则是黄老道家的另一个特出的优点。《黄帝四经》有言:‘圣人不朽,时反是守’、“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宜,兵]必有成功”、‘静作得时,天地与之’,这些都是黄老派的名言。……在政治上讲时功、重时效及其善于掌握时机,这正是黄老派在现实上取得数百年主导地位的重要因素”[1]序29。“时”就是暂时的,就不是恒“常”的。太过关注“时”,对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作为“常”的理念和原则的关注重视就必然不够。强调“时”还与强调“用”相关联,与强调“现实”的“操作”相关联,这样对“时”的强调就与对“术”的强调相一致了,同时与对“恒常”的“道”及作为“道”的具体化形式的“理想”、“道义”、“道理”的忽视和背离关联起来了。强调“时”、强调“术”也与对“人的主观能动性”[1]41的强调相一致,一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自然而然地偏重“时”和“术”,同时轻慢“常道”,因为对“常道”的严格恪守就要求恪守的主体“无我”地执着于“常道”,这种“执着”往往是排斥“主观能动性”的。因而说《黄帝四经》“‘动善时’的观念源于老子”[1]序20就有商榷的余地,因为“时”在《老子》一书中仅被偶尔提及,而非老子强调的重点,老子始终强调的是与对“道”的持守相一致的“常”。另外欠缺了永恒的“道”,确定的东西就只能在法度和君王处找了,对“法度”和“君王”的遵循顺从甚至成了人们自信心的源泉,这大约就是《四经》“援法入道”[1]序22和强调“尊君”的一个重要原因[3]109。
《四经》中也曾屡次提到“天”、“地”的“桓”和“常”,以及在“天地”的支配、制约下万物的“有常”和“不失其常”[1]126,但《四经》的“天地”之“桓常”基本上指的是天地的“自然”或“客观”的“规律”[1]25,141,169,正如陈鼓应所言“‘天当’,就是‘天道’,就是自然、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1]20,“‘当’,就是适度。‘天当’,就是自然、社会所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的‘度’或曰规律”[1]24;陈丽桂也指出《黄帝四经》“强调‘天道’,只是为了从中提练出‘名’、‘分’、‘理’、‘度’来,作为建立政治秩序和人事行为的准据。原本《老子》那个超乎万物之上的至高律则之源的‘道’,由是而不得不依次递降而为天地四时之象、人事之理,乃至刑名法术了。换句话说:黄老帛书是很强调道的规律性的,但它在强调道之规律时,却总是向下降一大格,用天地之象来代表道”[3]72。《四经》的“道”与“天”有着密切的关联,两者有时甚至可以划等号,而“《四经》中的‘天道’常常具化为‘人道’,特指‘人事’,此为‘道’说之一变”[1]5。本应具有超越性质的在“人”之“上”的“天道”一旦向“下”降落,“具化”为“人道”和“人事”,它的“恒常性”就荡然无存了,它就变成应时趣势的观念和原则了。
《四经》提出“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当,立为[圣]王;取予不当,流之死亡。天有环刑,反受其央(殃)。·世恒不可择(释)法而用我,用我不可,是以生祸”[1]362;“行非恒者,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1]295。《四经》将“天”、“地”、“君”(及在很大程度上单指作为“君”的“人”)并列,将“君”与“天地”摆在同样的位置,实际上是以不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天地”来凸显“君”“客观”的毋庸置疑的崇高地位①“世恒不可择(释)法而用我”一句之前有一个墨点,表示要说另一层意思的话。这一句中的“我”应该既指君王,也指众人。君王的“不可择(释)法而用我”强调的是君王也应该尊重“客观”、“确定”的法度,这样其权力才能更加稳固;众人的“不可择(释)法而用我”强调的是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众人对自己自主性的放弃,强调的是完全依从“客观”的“法度”进而完全依从至高无上的“君王”,君王地位的至高无上性与芸芸众生完全无关,因而具有极强的“客观性”。之所以将两项“依从”联系起来,是因为在确定君王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候“法度”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依从法度的最为关键的内容就是依从君王。。同时《四经》强调天地的“客观规律”性质也是为了证明实施“法度”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合理性,及进而证明掌握“法度”的君王等所作所为的合理性[1]16,126。这与老子强调天地的“恒常性”是为了确定一种永恒的“理想”,确定一种普世的价值参照、价值判断和社会批判尺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同时也说明仅仅着眼于“现实”、“实用”而提出的观念和原则就必然不具有恒常性,只有基于既着眼现实、又超越现实的“理想”所提出的观念原则才有可能具有恒常性。
《四经》提出“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刑(形)名。刑(形)名已定,逆顺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是故万举不失理,论天下无遗策。故能立天子,置三公,而天下化之。之胃(谓)有道”[1]173。这一段是综合论述,它说明“天地之恒道”仅仅是人世间的“形名”(《四经》中“形名”或“名形”与“法”有着紧密的关联[7]6-7,10)等确定之后人们“参”的对象,实际上也就是证明“刑名”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的较为次要的“参考”,而不是确定“形名”的依从标准,因而可以说“人为”确立的“形名”、“逆顺”、“位”、“分”等均在“恒道”之前乃至之上,“有道”的核心内容也是恰当地“立天子”、“置三公”等等,这实际上反映了《四经》将老子的“道”具体化、实用化──即“术”化了,将老子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理想“修正”了,这种“修正”就使老子思想的批判性被大大削弱了。
《四经》提出“知天之所始,察地之理,圣人麋论天地之纪。……故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正敌(嫡)者,不使庶孽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婢妾疑焉:疑则相伤,杂则相方”[1]357。《四经》在这里对“天地”的强调最终实际上是为了突出“圣人”,只有“圣人”有资格有能力来“麋论天地之纪”[8]84,而“天地之纪”是严格区分等级上下的,等级上下被严格地区分之后,人们就必然会“向上”追求跻身于更高的等级,就不可能充分“自为”了。因此《四经》所强调的“天地之纪”与老子“天之道”所强调的内容完全不同,老子的“天之道”所强调的是这种“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即其“抑高举下”的特性,这一强调又与其“齐物观”密切相关[9]165注②。老子之所以提出“齐物观”,是要淡化和消解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老子讲“天地万物”重点还是在讲“人”),因为如果要进行比较,就必须要确定“客观”和“外在”的比较标准,就必须以“圣贤”所确定的价值尺度为依归,人们就必然会在顺从在上者的基础上追求跻身于更高的社会等级,这样人们就不可能“自为”了。陈鼓应提出“老子对贵贱、高下的差别采取认同的态度,但并不极力鼓吹。”[1]247这种说法恐怕有商榷的余地,老子似乎说的是现实中存在着贵贱高下的等差,但人们应该通过仿效抑高举下的“天之道”的精神和原则,通过“齐物”等来极力消弥而非强化这种等差,因此老子在内心深处是不大可能“认同”贵贱高下的。
《四经》提出“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輮(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立(位),贤不宵(肖)不相放。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变恒过度,以奇相御。正、奇有立(位),而名[形]弗去。凡事无小大,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刑(形)已定,物自为正”[1]25。首先这里的“恒常”仅仅是“客观规律”,而非老子作为绝对的价值参照和价值判断尺度的“恒常”。更为重要的是在老子那里根本就没有“使民”的问题,老子始终关注的是在上者“无为”基础上的“人人自为”。“去私立公”看似不错,但如果能够在“无为”的前提下做到“任人自为”、“人人自为”,明确区分“公”与“私”往往就没有必要了,“公”与“私”的剧烈冲突往往就不会产生了,所以相对于“任人自为”,“去私立公”显然是一种倒退。本段的归结点是“物自为正”,这看似与老子的“自为”非常相近,其实两者间有本质的差异,因为在《四经》看来“名形”确定之后“物”①陈鼓应认为“物”是“事物”,但将这里的“物”理解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且这里的“物”甚至主要指的就是“人”可能更为妥当。方能“自为正”,因此“名刑”是“物自为正”趋向的目标和依从的准绳,而以“名刑”为目标为准绳的“自正”肯定与充分自主前提下的“自为”相隔天壤。另外确定“刑名”的人只能是在上者而不是寻常百姓,照在上者所确定的“刑名”去“为正”显然也不是“自为”。总之《四经》心目中的“物自为正”不是使“物”成为它自己,而是成为在上者所希望的样子,正如“君臣上下,交得其志”[1]223这样的“政治理想”完全不可能存在于老子的思想系统中,其核心“所指”实际上是顺从在上者,而不是“无为”前提下的“自为”。
二、《黄帝四经》对“法”的强调所体现的对老子思想的修正
陈鼓应指出“道家黄老派与老庄一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援法入道”[1]序22。对“法”(《四经》中的“法”基本上指的是法度、法则[1]3)的强调因而成为《四经》的重要内容和特点,对“法”的强调也是《四经》将“天”、“道”具体化和实用化的重要体现和落实,更为关键的是,《四经》对“法”的强调的最终目的是强调尊卑贵贱的客观合理和凸显“君王”至高无上的地位。
《四经》提出“规之内曰员(圆),拒(矩)之内曰[方],[悬]之下曰正,水之[上]曰平。尺寸之度曰小大短长,权衡之称曰轻重不爽,斗石之量曰小(少)多有数。八度者,用之稽也。日月星辰之期,四时之度,[动静]之立(位),外内之处,天之稽也。高[下]不敝(蔽)其刑(形),美亚(恶)不匿其请(情),地之稽也。君臣不失其立(位),士不失其处,任能毋过其所长,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美亚(恶)有名,逆顺有刑(形),请(情)伪有实,王公执[之]以为天下正”[1]115。度量衡的特点是“客观”和“确定”,《四经》将度量衡与“法度”紧密联系起来①将度量衡与“法度”紧密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普遍的思维方式,但《四经》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地方极多,因此可以看作是《四经》的一个特点。显然是在强调“法度”的确定性,对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性的强调也与对“法度”确定性的强调密切相关,而对“法度”确定性的强调的最终归结点则是对等级贵贱确定性的完全认同,对“王公”的崇高地位和非凡作用的彻底肯定。另外本段中认为应该去掉的“私”中间不大可能不包括寻常人等实实在在的个人利益,而“公”的很重要的内容应该包括对“君”的尊崇,实施“法”的重要目的也是“尊君”,正如本段中的“正”是以对尊卑贵贱的“等差”的“恰当”确定为重要内容的。强调以尊卑贵贱的严格确定为核心内容的“法”就与老子强调“天之道”所逻辑地引发的“齐物”、“责上”、“无为→自为”观念[4]截然相悖,而“自然→无为→自为”的实现则必须始终与“齐物”相伴随。
《四经》提出“有义(仪)而义(仪)则不过,侍(恃)表而望则不惑,案法而治则不乱。圣人不为始,不剸(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辤福,因天之则。·失其天者死,欺其主者死,翟其上者危。·……弗能令者弗能有”[1]348。本段有三个墨点,但各小段之间的内在联系似乎更紧密一些。《四经》在本段中首先强调了“仪”、“表”、“法”的价值和功用,特别是强调了法度、规范的客观性和确定性,这是《四经》将老子之“道”具体化、操作化和实在化的具体体现。接下来的一小段看似与老子的“无为”非常接近,实际上它强调的是“圣人”的约束自己、尊重法度,因为只有这样“圣人”的权柄及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方能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反之“圣人”的肆意妄为只能使自己的权威权柄遭到削弱甚至彻底失去。再接下来的一小段强调了不准“失天”、“欺主”和“翟(即“敌”)上”,但“天”在这里是非常“虚”的,所以更加“实在”的内容只剩下不准“欺主”和“敌上”,即完全顺从在上者。最后的“弗能令者弗能有”强调的是无法“命令”百姓就无法占有百姓,其根本目的是对寻常百姓的统治和占有,这与老子“任人自为”的观念显然是南辕北辙的。
《四经》还提出“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1]71它强调了“法”的特性、价值和功用,且对“法度”的特性等予以了极高的评价,但在老子那里“法度”从来就不是一个“正面”的概念,在老子看来在上者只要“无为”了,寻常百姓只要能够充分“自为”了,世间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就在根本上被解决了,此时此刻人世间虽然仍有麻烦和问题,但根本性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而“法度”只能把原本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搞乱和搞坏。另外老子对法度的不信任与其对“人”、特别是在上者的智慧等的不信任密切相关,在老子那里根本不存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知全能的“圣人”,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圣人”,就不可能存在一种由“圣人”主导的包医百病的“法度”,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圣人”和这样的“法度”,在上者“无为”前提下的“任人自为”就是人们在施政进程中的最佳选择。老子的上述理念当然具有“理想”的性质,但这种理想却能够切实而有效地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能够极大地启发人们的思维,能够成为批判现实的重要依凭。
在老子那里“圣人”只是“道”的人格化形式,而非现实的君王,《四经》中的“圣人”却是全知全能的君主:“唯圣人能察无刑(形),能听无[声]。知虚之实,后能大虚;乃通天地之精,通同而无间,周袭而不盈。服此道者,是胃(谓)能精。明者固能察极,知人之所不能知,服人之所不能得。是胃(谓)察稽知极。圣王用此,天下服。”接下来的一大段集中展现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君主的存在价值、基本特性和根本功用:“无好无亚(恶),上用口口而民不麋(迷)惑。上虚下静而道得其正。信能无欲,可为民命;上信无事,则万物周扁: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万物自定。不为治劝,不为乱解(懈)。广大,弗务及也;深微,弗索得也。夫为一而不化:得道之本,握少以知多;得事之要,操正以政(正)畸(奇)。前知大(太)古,后[能]精明。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1]406-409。本段用了一些与老子相通相合的语言概念,但根本处却与老子思想有根本性的差异。本段第二句缺了两个关键的字,陈鼓应认为二字疑为“察极”,整句的意思大体上是“君主如果能察知最为广大深微的东西则百姓就不会迷惑”[1]409,这与老子的“无为”→“自为”完全不同,老子的“无为”具有鲜明的“否定性”而非“建构性”,即在上者“不”怎么怎么样寻常百姓方有“自为”的可能,而非在上者具有了什么了不得的能力并进而“积极”地怎么怎么样了百姓才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认识与老子对“圣人”的认知是密切关联的,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道”的人格化形式,他是保障“人人自为”得以实现的重要人物,但寻常百姓在“自为”的过程中却感受不到“圣人”的存在,因而“圣人”在老子那里是一种很“虚”的存在,他完全用不着也不可能为了百姓的“不迷惑”而去“察极”,反过来说一旦“圣人”为了使百姓“不犯迷惑”而替他们去“察极”及进而为百姓确定其“职分”、指明其努力的方向,那么寻常百姓就不可能“自为”了。《四经》作者在这方面的认识与老子恰恰相反,他认为全知全能的“圣人”能够通过制定和推行“法度”而为寻常百姓确定其“职分”,也就是为他们找到一个努力的目标和行为的准则,寻常百姓完全按照这一目标和准则前行就能保持和实现自己的“本分”、实现“自我的价值”、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寻常百姓都按照《四经》的理念去做,他们最终只能成为在上者实现富国强兵等功利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根本不可能在充分“自为”的前提下去实现其独特的“本真自我”(实现“人”的“本真自我”应该是老子“自然”理想的人格化实现,因而是“自然”最为关键的内涵)。另外本段中的“虚静”也与老子根本不同,本段中的“虚”是在上者面对“法”的“虚”,即在上者对“法”一定程度的尊重和面对“法”适当的自我收敛(这与“法”在根本上强化了君主的地位并不矛盾,因为君主适当尊重法度不仅不会削弱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反而会强化之,反过来如果一位专制君主完全无视法度而肆无忌惮地肆意妄为,其地位将会被大大削弱而不是被强化),而“法”则是把寻常百姓变成富国强兵的工具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对“法”的尊重的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把百姓更加有效地变成工具。本段中的“静”的核心内容就是寻常百姓的“服法”和“听话”,本段中的“正道”实际上是“正法”,即端正和搞好一整套制度,而端正和搞好一整套制度——即“抱道执度”(“抱道执度”的重心是“执度”,另外这里的“道”很“虚”而“度”则非常的“实在”)的最终归结点是“天下一”,“一”既指地域的“一”,也指“人”的“一”——即将所有的百姓全部“统一”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和手段。
《四经》中的“法”及作为“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主要是针对“民”的:“黄帝问力黑:唯余一人,兼有天下,滑(猾)民将生,年(佞)辩用知(智),不可法组,吾恐或用之以乱天下。请问天下有成法可以正民者?力黑曰:然。昔天地既成,正若有名,合若有刑(形),[乃]以守一名。上捦之天,下施之四海。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复一,民无乱纪”[1]286。作为掌握着绝对化权力的号称“一人”的“黄帝”最为担心的事情就是“猾民”的“乱天下”,他最关心的事就是如何以“成法”来“正民”,“力黑”提出应对办法和原则最终被归结为“循名复一”,即遵循名刑而复归于“道”[1]287,[8]64,通过“循名”来实现的“一”——即“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实在化”为“法”了,因为“复一”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是“民无乱纪”。
《四经》提出“天执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然后[施于四极,而四极]之中无不[听命]矣。”[1]126这里出现了一二三四等数目字,《四经》中类似的表述非常之多,频繁出现数目字往往就与老子的核心观念和致思方式不相吻合了,这种表述实际上清晰地表明《四经》将核心为抽象空灵的理论原则、理想目标的老子思想具体化、实用化了,因为抽象空灵的东西是无法被具体化为“一二三四”的。本段的最后归结点是“[四极]之中无不[听命]”,即实施“法度”的最终目的,是以寻常百姓为主体的全天下的人全部听从在上者的“命令”。陈鼓应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提到“《四经》中多次出现的‘民无不听’、‘则民听令’、‘令行天下而莫敢不听’等等”[1]127,说明《四经》作者对使民“听”非常重视,甚至可以说“使民听令”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富国强兵”是整个《四经》最终的归结点,这当然与老子“无为→自为”的目标和理念截然相悖。另外实施“法”和“术”需以君王的专权为前提,实施“法”和“术”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专权”而非“分权”,而老子“自然→无为→自为”系统下“小邦寡民”的“人”的“理想”的存在模式的“分权”倾向则十分明显,这应该与老子对春秋晚期开始的通过严密的户籍制度来强化对百姓的控制[10]24,50,34以实现“富国强兵”、“广土众民”的“宏大”目标的否定密切相关。
《四经》提出“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从其俗,则知民则。二年用[其德],民则力。三年无赋敛,则民有得。四年发号令,则民畏敬。五年以刑正,则民不幸。六年[民畏敬,则知刑罚]。七年而可以正(征),则朕(胜)强适(敌)”[1]53。这里的“从其俗”应该是“最初级”的作为“手段”的“权宜之计”,“从其俗”、“用其德”等的最终目的,则是通过顺畅的“发号令”及使“民畏敬”而去“征”并最终“取胜”,其中所透显出的以“刑”为后盾去利用百姓而非真的“爱民”、更非使民“自为”的深层意蕴非常明显,正如“俗者,顺民心殹(也)。德者,爱勉之[也]。[有]得者,发禁拕(弛)关市之正(征)殹(也)。号令者,连为什伍,巽(选)练贤不宵(肖)有别殹(也)。以刑正者,罪杀不赦殹(也)。[畏敬者,民不犯刑罚]殹(也)。可以正(征)者,民死节殹(也)”[1]56的前一部分内容仅仅是初步的“手段”和“权宜”,后一部分内容才是最终的目的,而严酷的刑罚则是从“顺民心”到“可以正(征)、民死节”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
三、《黄帝四经》的文武刑德观所体现的对老子思想的修正
陈鼓应指出“在先秦诸子典籍中,‘文’、‘武’并提始见于帛书《四经》”[1]序21;“刑德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文武,因而,《经法》中多次讲要文武并用”[1]序45。《四经》所强调的“文”与“武”、“德”与“刑”的两种统治手段相互配合、交相为用与老子的核心观念根本不同,在老子那里“武”完全是负面的东西,老子是非“武”而超越“文”的,老子的基本主张、特别是其“自为观”完全是在“刑”、“德”之“上”的,因而与“刑”、“德”两手的交相为用完全是不相干的。
在某些时候《四经》似乎更加强调“文”、“德”一些[1]119,这大约就是黄老和法家的根本区别,但《四经》却又提出“强则令,弱则听,敌则循绳而争。”[1]372它充分表现了《四经》作者对“强”的认同和对“弱”的否定,这与其有时更强调“文”、“德”是不一致的,因此表现了《四经》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矛盾和两难,即一方面《四经》作者仍然认同“文”和“德”,这反映了《四经》作者在内心深处仍然具有一些“理想性”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残酷的客观现实却无时无处不在显现“武”和“刑”的巨大价值和作用,所以只要“面向现实”、“注重实用”,就不可能不对“武”和“刑”更加重视一些,这就使《四经》作者实际上往往会更加注重使一个政权变得更“强”的“武”和“刑”。经常将目光投向客观现实而非超越性的“理想”,更加关注“实然”而非“应然”是《四经》的特点,也是《四经》与《老子》的根本性区别,这就使得《四经》往往会在根本处抛弃“理想”和“道义”,同时认同与“理想”、“道义”不相干的“强力”和“强者”。
《四经》对“强”的认同与其对君主专权的认同密切相关,《四经》提出:“适(嫡)子父,命曰上曊,群臣离志。大臣主,命曰??(壅)塞。在强国削,在中国破,在小国亡。谋臣[在]外立(位)者,命曰逆成,国将不宁;在强国危,在中国削,在小国破。主失立(位),臣不失处,命曰外根,将与祸閵(邻),在强国忧,在中国危,在小国削;主失立(位),臣失处,命曰无本,上下无根,国将大损;在强国破,在中国亡,在小国灭”[1]81;“凡观国,有六逆:其子父。其臣主。虽强大不王”[1]77;“为人主,南面而立。臣肃敬,不敢蔽(这里的“蔽”是“敝”字之误[8]19)(蔽)其主。下比顺,不敢敝(蔽)其上。万民和辑而乐为其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适(敌)”[1]87;“主主臣臣,上下不? 者,其国强”[1]84。上述内容归结起来都是在说明君主专权是国势强盛的前提和基础,这种认识与战国时代的社会状况和人们普遍的思想倾向是紧密关联的。在战国时代与富国强兵密切关联的君主专权已经成为一种人们普遍追求的政治目标[11]180,210,因为君主专权就能使“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就能使一个国家短时间内在各个方面变得更“强”,就能实现“富国强兵”这一当时最高的政治理想。
“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1]263是《四经》屡屡强调的内容[1]236,如果对“功利”性质的“成功”很注重,就不可能不去“争”,如果要“争”,就必然会关注和认同“强”,因为只有“强”了才能在“争”中取胜,这当然与老子的“不争”截然相悖,同时也与老子对战争及暴力的绝对否定不相一致。如果特别关注和追求君主专权基础上的的“强”,“武”和“刑”就必然得到更加实质性的强调,而“文”和“德”就必然在实际上受到轻慢,甚至必然变成一种说辞和缘饰。
《四经》提出“凡论必以阴阳口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伸)者阳而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取(娶)妇姓(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1]394。本段中“天”、“春夏”、“大国”、“重国”、“主”、“上”、“男”、“父”、“长”、“贵”、“达”、“制人者”等等令人感觉愉快的、地位在上的人和事物均被归入了“阳”的范畴,而与“阳”相对的令人感觉不愉快的、地位在下者则被归于“阴”的范围,其重“阳”轻“阴”的倾向十分明显,这与老子在根本上的重“阴”轻“阳”有本质的区别[4]。《四经》的重“阳”轻“阴”与其对“上、大、贵”的事物的崇尚相一致,这与老子对“雌、弱、下”的绝对偏重根本不同,这应该与《四经》对等级贵贱的认同、对君王和权势的崇尚相一致。《四经》也修正了老子对“地”及与“在下”的“地”相一致的“谷”和“水”的认识,在老子那里“地”及“谷”和“水”虽然“在下”,但却博大深厚,容纳一切,它完全没有“低贱”的使人不舒服的感觉,这应该与老子的“民众立场”相一致[12]导论77,[5]355,[6]164,而《四经》则在根本处站在了在上者的立场上。另外陈鼓应提出“执守雌节,则无论是动是静、是先是后,都会左右逢源的。因此说,黄老的雌节与老子的‘雌’是有区别的。”[1]271也就是说《四经》等黄老的“执守雌节”是一种着眼于“权术”的考虑和行为,它与老子依从抑高举下的“天道”而倾向于“雌、弱、下”的“价值偏向”根本不同。
《四经》提出“天有环刑,反受其央(殃)。”[1]362陈鼓应对此的解释是“就人道而言,人们取予得当,就会得到‘天德’的褒奖;反之,就会受到‘天刑’的惩罚。取予、与夺、德刑,是交替循环运行的,这便是‘天有环刑’的含义。这两句是说天道循环运行,有德必有刑,取予不当,就要受到天刑的惩罚,自取祸殃”[1]363。老子之“天”是绝对偏向弱势群体的,因此当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之“天”面对弱势群体时是纯粹“予”、“与”、“德”的,老子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所持的是一种以“绝对”“补民”为归趋的“一元”性质的价值观,而《四经》以“用民”为根本目的的“文武”、“刑德”交相为用的“二元”性质的价值观的提出则是对老子思想的根本性修正。
《四经》提出“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矣。号令阖(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1]73兼行“文武之道”的根本目的是使“民听令”、“民亲上”,其功利目的十分明显,而且推行“文武之道”的“手段”性质也十分明显,所以这里的“道”实际上就是“术”,正如《四经》在他处所言“参于天地,阖(合)于民心。文武并立,命之曰上同。”[1]103说明《四经》引入“文”、“武”概念最终是为了实现“上同”这样的功利性目的,“上同”当然与老子“人人自为”的政治理念截然相悖。
“绝对反战”[13]187,[14]338-341,[4]是老子的重要观念,而《四经》则将“天地之道”及与“天地之道”密切关联的“圣人之功”与把握战机最终取胜紧密联系起来:“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人,兵不可成。参□□□□□□□□□□之,天地刑之,圣人因而成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秉[宜],[兵]必有成功。圣人不达刑,不襦传。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280。这里的“天地之道”成为“圣人”指挥作战的重要依凭,成为把握胜机、及时决断的重要参照,老子心目中作为“理想”的“道”的人格化形式的“圣人”就被《四经》修正成了“战神”,这样老子心目中的“圣人”的“理想性”就荡然无存了,《四经》心目中的“圣人”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被明确地凸显出来了。
既然“圣人”不再具有“理想性”,既然“圣人”已被《四经》修正成“战神”,那么作为“战神”的“圣人”残酷地对待作为敌人、残酷地对待敌国也就顺理成章了:“故圣人之伐殹(也),兼人之国,隋(堕)其城郭,棼(焚)其钟鼓,布其齑(资)财,散其子女,列(裂)其地土,以封贤者,是胃(谓)天功。功成不废,后不奉(逢)央(殃)”[1]45。这么理解“天功”就把老子思想系统中的“天”大大贬低了,把老子的“天道”修正成在上者独操、以残酷的惩处为核心内容的东西了[1]260-261,同时《四经》的“圣人”与老子心目中的“圣人”也就相距十万八千里了;“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擒)之。(剥)其口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其发而建之天,名曰之(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鞫(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酭(醢),使天下()之”[1]258。说明《四经》认为对战败被俘的敌人极尽暴虐之能事是合情合理的,这与老子“报怨以德”的“对敌态度”实在是相隔天壤[14]603-606。在老子心目中其实干脆就没有什么“敌人”的概念[14]339,因此老子完全不可能想到如何残酷地对待敌人。对待“敌人”是残酷无情还是相对宽厚,是衡量一种文明和一种思想高低上下的重要尺度。
[1]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白奚.稷下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98.
[3]陈丽桂.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
[4]乔健.论老子思想中所内涵的“绝对性”因素[J].文史哲,2010,(4).
[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
[6]王邦雄.老子的哲学[M].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
[7]曹峰.楚地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研究[M].台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10.
[8]谷斌,张慧姝.黄帝四经注译[M].郑开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乔健.中国古代思想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10]杜正胜.编户齐民[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
[1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2]杜正胜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M].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
[13]王淮.老子探义[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9.
[14]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