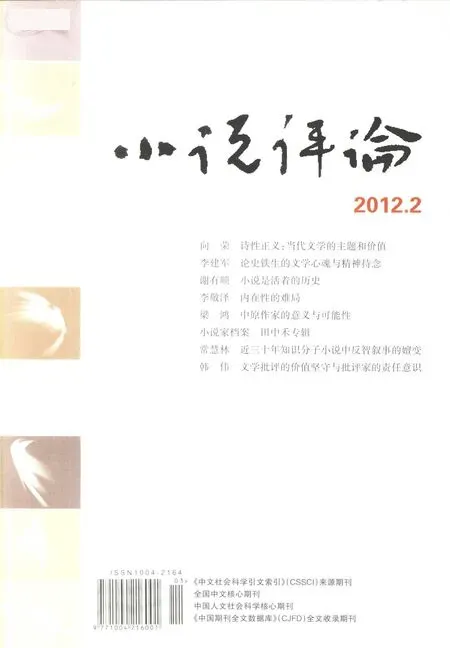“伪纪录片”的真实性讨论——以《二十四城记》为例
2012-12-17吴胤君
吴胤君
近年来,伪纪录片这种特殊的影像艺术形式逐渐流行起来,越来越多的导演运用这种拥有纪录片的很多特征又与纪录片明显不同的艺术形式拍摄影片。很多人对这种影片嗤之以鼻,认为它不具备起码的真实性,也有人认为伪纪录片表达的是主题真实这种更高的层次上的真实性。本文借用长镜头理论、纪录片定义、电视纪录片的美学意义、广播电视制作规律等有关知识,从层次性角度出发,探析伪纪录片的真实性。
一、伪纪录片
“伪纪录片”,又称“仿纪录片”英文名称是mockumentary,也就是mock和documentary的结合,它常被归类为一种纪录片或电视节目类型,通常带有喜剧的嬉闹性格,但也有非常严肃的伪纪录片。虽然它和纪录片一样都记录着真实的生活,但实际上却是虚构的,运用讽刺或仿拟的方式来分析社会上的大事件或问题,挑战着人们对于既定事实的认知,以及对于纪录片里的核心命题“真实”的观念。
在伪纪录片里,常常使用历史资料画面或者人物访谈来讨论过去的事件,要不然就是以真实电影的方式去跟拍事件里的当事人。像《科洛佛档案》、《死亡录像》都属于伪纪录片。伊文思说过:当代纪录片的趋势是,故事片向纪录片靠拢,纪录片向故事片靠拢。于是,故事片与纪录片界限的日益模糊,成为当代电影的一大特征。贾樟柯、张艺谋的写实风格电影《小武》、《三峡好人》、《24城记》、《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都或多或少的使用了纪录片的手法。
二、关于伪纪录片的真实性
1.从外在题材看
从纪录片真实性的讨论中我们就能发现纪录片的真实也是相对而言的,任何电视电影作品都必然带着作者自身主观的想法,并不是绝对超然的。
伪纪录片之所以与纪录片区分开来,就在于描述事件的方法,纪录片使用真实还原的方法,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在事件发生的同时被忠实记录下来的,片中的采访也是实地进行的,片中人物并不是演员,而是事件本身真实的主人公。而伪纪录片更多是单纯套用纪录片手法,内容本身并不是实时拍摄,但大多数伪纪录片所表现的事件真实发生过,仅仅是时态的不同,这样的伪纪录片采用模拟,重新排演,甚至演员的使用,将发生过的事件再现于荧幕,这种伪纪录片真实性的基础就在于事件本身的真实发生。
以《二十四城记》为例,贾樟柯实地考察了成都420厂,采访笔记达十万字,片中所有的420厂场景均为实景拍摄,部分职工也是真实存在的,所有采访内容都收入了一本《中国工人访谈录》,在影片中,吕丽萍饰演了一位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420厂做事的女工,虽然她在片中诉说的经历并不是自身的,但是她的台词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据《中国工人访谈录》中的内容,台词是有很多女工的亲身经历拼接出来,例如寻找孩子那段来源于一名叫侯丽君的女工,这位女工最后也出现在了影片之中。吕丽萍的经历是有高度的典型性的,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都有相关的体会,片中提到的国有企业大家庭,子弟学校,三线建设,以及后来的恢复高考,日本剧《血疑》的热播,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我们不能说这些没有真实性,因为他们确实发生过,只是贾樟柯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抽象出来放在几个主人公身上,他们的故事并不是编剧的杜撰,而是真实事件的再现。
同样的,影片中吕丽萍的女儿,赵涛饰演的苏娜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八零后与家长的观念上的冲突,我们已经没有工厂观念,对于那种吃穿住行全在工厂的集体生活很是陌生,自然也就对于上一辈的集体主义观念不甚理解,对于上一辈所做的也就不以为然。中国社会正是经过这种从集体主义为荣到提倡个性宣扬的时代,而这一切的就是在千万个如吕丽萍,苏娜这样的小人物中体现出来的,只不过《二十四城记》采取了一个典型化的方法,将420厂的几位工人的故事集合在一个人的身上表达出来从而更具典型意义。
其他的伪纪录片也大多如此,伪纪录片从题材上说并不是浪漫主义风格,而是完全的现实主义影片,不管的电视还是电影,这一类片种往往是因为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不可逆性,无法现场实录,而采取了典型化的手法,要么从主人公身上抽取最具典型意义的一面,要么则是将多位人物结合于一位人物,从典型中表达普遍意义。这类影片大多反映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客观现实性大于主观意愿的表达,本身题材内容并不是凭空臆想,我们不能因为有剧本,有演员的存在就怀疑伪纪录片的真实性。
戏剧讲究间离效果,他时时刻刻提醒着台下的观众,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是虚构的。但是电影不同,他总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是在真实发生着,但是为了观众的观赏兴趣,迎合观众的审美期待,很多时候贾樟柯也在刻意的制造间离效果,比如《二十四城记》中关于爱情的描写,贾樟柯特意处理的很唯美,但事实上在当时动荡的社会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影片的真实性,只能看作是艺术化的加工手段罢了。
2.从核心思想上看
伪纪录片的兴起不得不回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欧洲,美国好莱坞的商业片大量涌入欧洲,再加上战后民不聊生,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整个欧洲都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之中,战争对于经济的创伤难以愈合,对于心理的冲击更为巨大,人们失去信仰,社会混乱不堪,而当时的商业电影还沉浸在上层社会生活的浮华之中,在这样的社会和艺术背景下,很多年轻的电影工作者用纪录片一样的手法,拍摄底层小人物的痛苦,这就是欧洲的新现实主义,新浪潮等去商业化电影运动。这个时期的很多电影都有伪纪录片的影子,德国新电影领军人物,新德国四大导演之一的赫尔措格就说过:如果所谓的真实电影只是单纯扛着摄像机去记录那么这种真实仅仅是表象的真实,是会计师的真实。
所以我们以往认为的纪录片真实性其实是混淆了事实与真实的概念,我们把一些机械的事实作为真实来考虑。最终也导致我们浮于表面。事实上电影或者纪录片的灵魂在于内在的真实,而不简简单单的是事实的记录。
就《二十四城记》而言,伪纪录片的剧本是贾樟柯虚构的,结构也不是纪录片的时间线性而是列传模式,采访对象说的话也并不是他们本人的经历,而是根据很多人的经历糅合改编以及润色而成。片中提到的人物也是虚构的。但是这部伪纪录片横跨新中国建设近四十年的时间,期间经历过四代人,经历过国有企业的兴衰,经历过国人思想的开放,观念的转变,当初一个个小小的选择如今都直接影响了几代国人的命运。每一代人都能在这部影片中找到自己的青春痕迹,这才是真正的真实,不仅仅停留在事实上,而是真正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落实在每一个真真切切的小人物身上所带来的影响。
三、结论
伪纪录片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各种佳作层出不穷,比起纪录片,这种形式能表现出以往记录片不便于表现的题材。我们在看待伪纪录片时也不能因为它不是实时记录的就一概否定他的真实性,甚至把这类影片归于故事片中。伪纪录片应该以一种全新的片种来研究和看待。这种片种的存在更新了人们对于影片真实性的认识,将机械的记录真实提炼为主题的真实,真正把事实和真实区分开来。
中国电影一直有现实主义传统,以第六代导演贾樟柯为代表的伪纪录片拍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种系那是主义传统,他们不再纠结于影像的真实,而是将真实深入到影片之中,不仅是画面的真实更是意义的真实。他们通过自己的摄影机记录了中国几十年来的变迁,记录了最普通的小人物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所思所想。我们在看待影片的真实性时也要“与时俱进”。不但要考察影片在影像,灯光,声音上的真实。更关键的是影片在主题意义上的真实,脱离社会,脱离现实的影片即使是实时拍摄的“纪录片”,依旧要摒弃。
注释:
①贾樟柯.中国工人访谈录[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4.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
③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12.
④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M].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12.
⑤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