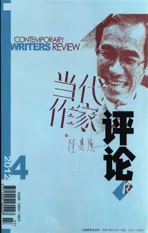作家、作品论研究对现代文学的经典化意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论的理论与方法”会议综述
2012-12-17刘恋
刘 恋
二〇一二年四月一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论的理论与方法的深入探讨”学术会议在扬州召开。此次会议由扬州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当代作家评论》主办。会议在多个视阈与问题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论”展开热烈讨论与深入探究,产生出较大的论辩空间。
多数专家有所共识:作家、作品论研究,客观上对现代文学的经典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主观上呈现了特定时期的从事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品格。陈思和指出:建国后,国家意识形态的介入,将原本只是以“运动”形态出现的现代文学,整合成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即所谓“现代文学史”,其中有着一整套非常强烈的主流话语体系,而曾华鹏、范伯群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二代学者的卓越代表,其早年的作家、作品论,重新评估一些“非经典性”作家(如郁达夫、王鲁彦等),乃至一些被否定的作家(如张资平),挖掘出许多的文学史资料,并使得文学研究回到文学史内部,回到作家立场,奠定了以后“重写文学史”的研究起点,真正起到一个经典化、典范化的作用。刘祥安特别强调“第二代学人”以其深入的研究参与学术传统的建构过程,不为僵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去抬轿子吹喇叭,使“经典化”传统不至于那么僵化,让它容纳相当的复杂性。
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基本完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成为专家学者们普遍关注与焦虑的话题。吴义勤提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没有完成,其原因就是当下作家作品论的研究水平跟不上,因为文学的经典化不能单靠文学史归纳。陈思和认为,当代的严肃文学很难与通俗文学进行消费市场的抗争,但学者们有义务有责任通过高水平的作家、作品解读,使其进入教育体制,从而实现“经典化”。徐德明认为,应该将前辈学者典范性的作家、作品论,与经典的作家、作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实现该学科学术规范的经典化。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论,不仅丰富了学科内的学术研究,而且以论著者们的主观创作精神参与了现代文化传统的建构,并在其中凸显出现代知识分子曲折的人生际遇、真挚的人格品质。葛红兵认为杰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论中,充溢着对于作家的同情和理解,对现代作家、作品研究恰恰是让每一种个性化思想真正展露,充分展示了现代思想的丰富性,而这种以“人”为基点的研究可以突破现代文学的学科范畴,上升到现代知识分子思想人格研究的高度。杨剑龙则指出,“第二代学人”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坚持还原式研究,独抒己见,使得作家、作品论客观、厚实,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彰显。刘祥安从“岗位意识”角度出发,深刻认同“第二代学人”通过作家、作品论的研究,以自己的学术工作,参与到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建设当中去,并在其中彰显着知识分子品格。黄善明以作家、作品论中的“实证性”为基点,认为不屈从于任何权威的“学术中立”态度,是著述者们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强烈体现。
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是学界关注的持久性话题。范伯群通过对冰心、杜鹏程所作的相关作家论证实:“写作家论,是帮助作家更加认识自己。”丁帆肯定了作家、作品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具有一定的指示性与启发性作用,认为好的作家、作品论,一定不是站在作家之下,也不是站在作家之中,而是站在作家之上。陈军则认为,作家作品论是站在作家作品“之内”,尊重作家本身的诗学理论,以“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理解”的方式细读与体认,并由内而外,综合社会学、审美学等诸种方法的研究。
陈思和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强调作家、作品是文学史最关键的构成。没有深入研究作家、作品,就不可能对文学史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当下的认知误区是:丧失了直面文学史、直面作家作品、直接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陷于现成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预设的问题中,最终将形成一种简单、武断的“批评风格”。杨剑龙认为,文学史的发展,作家作品是基础,理论是阐释的工具,而作家、作品是文学本身的问题。吴义勤、徐德明都提出在当下研究普遍地重理论、重宏观的情况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重回基点”,亦即作家、作品论。林建法则从学术刊物立场出发,认为现在的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严重缺席,充斥着的是思潮史、运动史、意识形态史。吴义勤也表示《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有意打通现代与当代,但实施起来却发现真正研究当代文学文本的论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尽如人意。
但对于理论和作家、作品,学者们认为在更高的层次上,可以并且应该相互融合与促进。陈思和表示,不能将作家、作品论与理论对立起来,理论作为一种学术修养与准备,还是必需的;作家、作品论与理论的连接点应该是“解决问题”,他提倡从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再选择不同理论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曾华鹏从研究郁达夫而发现的颓废个性与五四时代思潮之关系、范伯群从研究通俗文学而发现的文学史之重新整合,这些都是非常典范的从具体对象的研究中生发出来的、但同时又具备重大理论价值的“大问题”。林建法认为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去阐释;阐释的过程中,会自然地透露出理论的观点;这种自我阐释与理论结合无间的优秀的作家作品论,才是当代文学学术杂志刊物所亟需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研究生培养的得失,是会议集中讨论与关切的话题。不少与会者认为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后继队伍培养存在误区。就能力而言,丁帆以研究者与教育者的双重身份,呼吁年轻学人、学生要在“基本功”上下功夫,也就是进一步提升三个层次的学术能力:第一个层次是对作家作品分析的能力,第二个层次是对文学现象、文学社团和文学思潮把握分析的能力,第三个层次是对文学史整体把握的能力。
与会学者的高度共识还有一点:曾华鹏、范伯群的作家、作品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第二代学人”的代表,建立了一种科学的、朴实的、具有很强生命力的学术范型,对于学科的建设、规范与发展而言,具有重大贡献。今天回到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探究这个学术范型产生的语境,有助于当下的研究者形成更为全面、明晰的认识。范伯群讲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写作家、作品论时的政治高压、学界反应、作家反馈以及个人遭际。曾华鹏归结了作家、作品论受到的三次冲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宏观研究、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的方法论研究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研究,他特别强调,各种研究模式都有优点、长处,很难用一种代替另一种。陈思和将这种在高度意识形态化语境里产生出来的作家、作品论,看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逆境中“一个学术的起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重新起步、重新整合的“一个奠基石”。杨剑龙则用“能朝着既定目标蹒跚前行”,形喻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论的著书者们艰难曲折而又扎实坚定的学术道路。
系统规范的学术训练与研究方法,是建立学术范型的基础。张王飞(江苏省作家协会)梳理了进行作家、作品论研究的一整套学术训练与方法,包括:占有资料、制作作家年谱与著作纪年、尊重作家的诗学理念等。陈思和也认为这样的一种学术方法是科学合理的,即读某个作家的全部作品,梳理其学术年谱,然后上升到理论研究。葛红兵从作家、作品论的研究中,概括出几个具体的方法值得继续学习:观点来自材料、读原刊杂志与知人论世。
对“第二代学人”作家、作品论学术特色的探讨,也成为与会学者们的一个自觉行为。吴周文将“第二代学人”作家、作品论的核心理念概括为三点:一是“文学史定位”,即一个作家在文学史的纵向上应该定在哪个位置上;二是“知人与论世”,即对作家要进行多方面了解,比如作家去过哪些地方、提出过什么问题,等等;三是“多视角交叉”,这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美学、社会学等。杨剑龙以曾华鹏的作家、作品论为个案,研究认为社会历史批评是其主要运用的方法,“论从史出”的学术视阈、“求真尚美”的学术追求以及“平实严谨”的学术风格,则是其个性特点。葛红兵分析了“第二代学人”作家、作品论的三个特色:一是“夹缝中的开创者”,在生活夹缝、政治夹缝中让文学出场,让审美出场;二是“过渡当中的永恒”,作家、作品论作为一种模式,在文学研究的历史长河的流动过程中,是一种过渡,但具有永恒的生命魅力;三是“相对模式中的绝对巅峰”,曾华鹏和范伯群的作家、作品论,事实上成为这一相对学术范型中的典范。
作家、作品论,作为一种研究范型或模式,因其植根于活生生的作家作品,而有着相当的生命力,具体到研究方式上也是不断拓展的。莫绍裘认为过去的学者在他们的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如果还让现在的学者继续一成不变地使用这种方法则无甚意义;更关键的是,其研究对象(作家或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立体的、可以多方挖掘的生命体,所以他建议年轻人既要接受有关作家、作评论的学术观点、学术方法,但不能限于此,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找到突破,找到新的研究路数,这样学术前途才是广阔的。徐德明用“看家功夫”比喻作家、作品论给予自己的学术启发,指出前辈学人的作家、作品论研究已然达到一个高峰,但由于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当年没有可能继续往下走;他们留下的绝非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充满着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后辈学人沿此路往前走的时候,应加上自己的开拓,不断挖掘、发现、丰富种种的可能性。翟业军强调文学研究中,所有的矛盾、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感悟都应该是从最细节中绽放出来的。他以鲁迅、屠格涅夫、王安忆、毕飞宇等人的小说为例,从比较文学(中西文学的比较、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比较)的角度、从语义辨析的角度,实证了文本细读、作家作品论的研究路数中,实际存在着若干的、向前推进的可能性空间。
会议讨论对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论,但学术研讨却没有 限于一隅,而是显示出强烈的学理反思与学科交融。曾华鹏以强烈的自省精神,对他所处其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代学人”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总结。他明确指出:文学史研究的方式和视角不应该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部合唱,无论是哪种方法的研究都有可能成为经典。他从中外文学比较的角度例证:宏观研究方面成为经典的有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微观研究成为经典的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钱理群《天地玄黄:1948》;单篇的作品研究成为经典的有杜勃罗留波夫的《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论冈察洛夫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论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大雷雨》)与《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论屠格涅夫小说《前夜》);单个作家研究成为经典的有欧文·斯通、罗曼·罗兰、安德烈·莫鲁瓦的人物传记研究,扩而至社团、流派、期刊,甚至小报的研究,只要是秉持认真严肃的态度,都可能会出好成果,乃至经典。徐德明作学术总结时提出“第二代学人”的作家、作品论已然成为学科内的经典,我们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秉承作家、作品论传统的同时,寻求新的方法与空间。如何在试图摆脱经典论述阴影的同时,不误入研究的歧途。如何在坚持文学文本文人立场的同时,创造性地进行文本和理论的互动并提升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