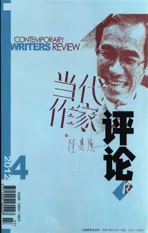小说评点与准文本
2012-12-17陆楠楠
格 非 陆楠楠
准文本
一个文本在编辑、印刷、出版、行世的过程中,在正式文本之外,也会增殖出一些其他的信息。如序言、跋、作者简介、内容提要、出版说明、编校体例,书籍的封套广告。①此处见格非《文学的邀约》,第97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文字信息以外,另有封面设计、书内插图等图像信息。如今的书甚至可能还有腰封,腰封通常采用更显眼的字体,包含不适宜印刷在封面上的具有广告效用的其他说明,如小说的获奖记录、销售情况等。书的后封常常印有作家评论,至于正文开始之前的序,正文结束后的跋,都作为小说正文的准文本(paratext),成为一本书重要的组成部分。讨论小说评点,可以切入的角度很多,比如文学史的角度,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角度,文化研究的角度,而由“准文本”的概念入手,也是见微知著的一种尝试。
准文本之所以重要,因为它虽然不是正文,但却能对读者的阅读产生一定影响。糟糕的内容提要可能败坏读者对于一部佳作的阅读兴味,从而造成遗珠之憾;同样,精彩的序言也可能吸引读者去阅读一部平庸之作,白白耗费宝贵的时间。在图书市场商业化程度日益加深并逐渐系统化的今天,出版行业几乎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工业化包装流程,准文本在这一方面的效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与强调。
我们可以轻易地跳过他人为作品写的序或跋,但却很难放过一些更重要的信息,比如由作者本人直接为自己作品的出版所撰写的序、跋等。由于作者中心论观念的深入人心,作者本人为自己作品所做的阐释与说明,虽然读者未见得会照单全收,但多数时候还是会在这里花费必要的时间。当然,对阅读而言,它们仍然是参考性的,而非强制性的,读者完全有理由跳过不读。不过,当某一类序跋与正文的内容构成了更为紧密的关系时,读者往往不能将其视为备用性的提示信息,轻而易举地选择放弃。比如说,韩邦庆为《海上花列传》一书所做的那个著名的跋,即属此类。
韩邦庆在这个跋中,先对读者的反馈意见作了评述(这部小说是在杂志上连载的),然后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回应了读者。由于许多人来信询问小说主要人物后来的命运,韩邦庆对这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人物,做了进一步说明。一方面,人物的虚构性与“跋”在人们常识中和现实的关联性,产生了奇妙的张力,使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混淆;另一方面,由于事关主要人物的“将来”,也由于作者煞有介事的态度,准文本与正式文本之间的界限也变得含混而暧昧。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这个“跋”事实上也成为正式文本的延伸。也许作者的意图是对读者的好奇心做一个玩笑性质的回应,但准文本在此处特殊的介入性,却值得注意。而当准文本被作为一种修辞,成为作者意图的一部分时,情况会变得更为复杂。让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段文字:
在利德尔·哈特所著的《欧战史》第二十二页上,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记载:十三个团的英军(配备的一千四百门大炮),原计划于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向塞勒-蒙陶朋一线发动进攻,后来却不得不延期到二十九日上午。倾泻的大雨是使这次进攻推迟的原因(利德尔·哈特上尉指出)。当然,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可是下面这一段由俞琛博士口述,经过他复核并且签名的声明,却给这个事件投上了一线值得怀疑的光芒。俞琛博士担任过青岛市Hochschule①德文,意指高等学校。的英语教员,他的声明的开头两页已经遗失。②豪·路·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第69页,王央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这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的前言。前言之后,是以省略号引起的一段正文。博尔赫斯此处摹仿了一个真的文本,这个文本前两页丢失了,叙事者所做的工作是将丢失的文本呈现给读者。“丢失的文本”是俞琛的口述,使用了第一人称(前言部分是第三人称),作者将一个虚构的名字俞琛与一个真实的名字利德尔·哈特并置,一方面造成了故事实有其事的假象,同时也部分地清除了虚构与历史文献的界限。通常聪明的读者不会被作者欺骗,他们会识破前面所谓的声明是虚构的,也即准文本其实是伪装出来的,它实际上是正文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整篇小说的虚构性就不言而喻了。
伪装的准文本由于其不易辨认,难以与正文作严格的区分,也使叙事变得更为缠绕,阅读过程更为复杂,也因此成为叙事中重要的概念。博尔赫斯所使用的技巧在文学史上并非特例。爱伦·坡问世于一八三七年的小说《亚瑟·高顿·皮姆的陈述》,完全以准文本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昂贝托·艾柯在《悠游小说林》中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③见〔意〕昂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第21-25页,俞冰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而对于伪装的准文本的使用,纳博科夫也许走得更远。他在小说《微暗的火》中,做了更为大胆和极端的尝试。
这部书分为目录、前言、正文、评注、索引五个部分。小说是这样开始的,一个叫金波特的人有一天遇到了一位流亡诗人约翰·弗朗西斯·谢德。谢德创作了一首英雄对偶诗体的诗作,共四章,九百九十九行。全诗完稿之后,谢德死去了。诗稿落在金波特手中,他于是承担起研究、复现此书的使命。小说前言部分,金波特交代了谢德的生平,以及自己同诗人的交往,与谢德写作这本书的过程。正文部分重现了九百九十九行长诗。评注部分是金波特对这首诗所作的注解式评论,包含诗句注解,并对不同的诗句之间进行了互文关联的对照解读。这一部分占据了全书二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小说最后竟然还附有人物与地名的索引。整部作品是叙事者金波特为谢德遗作所编订的遗稿目录。
作者在叙事技巧上的花哨和夸张程度,远远超过我在此处的简要分析。这个名叫金波特的伪托的叙事者,很有可能是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波特金的化名。富有阅读经验的读者一望即知,波特金与谢德都是作者纳博科夫编造出来的人物,作者将故事说成是别人的,又将故事打散,小说因此全是准文本,没有正文。写一本完全由准文本构成的书,是纳博科夫对小说文体探索的一个梦想。《微暗的火》也因此成为小说文体学研究中重要的个案。它一方面试图彻底混淆人物、叙事者、作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模糊了文学写作、批评和学术研究之间的界限,小说似乎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学术论文。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也精于此道。他一生中最大的梦想是写一部引语式的小说,也即只有前言,没有内容的小说。这部梦想中的书最终未能实现。此前有一位法国作家写过一部篇幅很长的小说,据称小说中完全没有动词,从中也可见西方小说家对于小说文体所做的探索与尝试之极端。当然,小说作为现代文学的门类之一,还有走得更远的个案。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徐冰曾经在台湾出版过一本奇特的“小说”。这本名为《地书》的“书”中居然没有一个文字。我看不出所以然,回家后将它放在床边。十三岁的儿子躺在床上,顺手拿起来开始阅读。他说书中讲的是地球的某个地方,林木丛生,林中有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人,这个人躺在床上,闹钟忽然响了,他很烦恼,于是关掉闹钟,继续睡觉。之后他又一次醒来。儿子在没有任何阅读准备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读完了这本书。当然,这本书似乎原本就是写给孩子的,没有一个汉字,全部由图画构成。这也是图像时代的特殊产物吧。
回到卡尔维诺,尽管那部“引言式”小说未能成书,但他的《寒冬夜行人》也已向读者传统的阅读习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书中讲的是《寒冬夜行人》的装订者不小心将书页订错了,于是只好呈现给读者这个订错的版本。作品的时序极为混乱,将小说的装订过程和小说正文穿插在一起,极尽捉弄读者之能事的同时,却也难免卖弄之嫌。
作家利用伪装的准文本去模糊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这样的做法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甚至可以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寻找到呼应。以《红楼梦》为例,其开篇一段作者自述,①原文如下: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交代作品的缘起,庚辰本和甲戌本都将它列入凡例,置于正文前;戚序本等其他版本则直接将其放入正文,作为第一回。
开头这一段之后,作者在正文部分,再次对虚构的作者进行假托,即《红楼梦》之故事来源,是一块女娲补天时剩下的顽石到世间游历的经历,被刻在大荒山无稽崖的一块巨石上。有一天,空空道人经过此地,偶然窥见,便将石头上的字迹抄录下来,以《行僧录》流传于世。之后作者笔锋又一转,这样写道:
(空空道人)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这段文字虽已进入正文,但仍明显带有凡例的性质。如果我们完全听信作者提供的信息,按照以上提示,《红楼梦》的作者(编定者)共有以下七位:①格非:《文学的邀约》,第10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一、以叙事者面目现身说法,交代写作缘起的那个作者
二、石头
三、空空道人
四、吴玉峰
五、孔梅溪
六、曹雪芹
七、脂砚斋
与《微暗的火》相比,纳博科夫的准文本完全是杜撰的,作者的花招读者一望即知。而曹雪芹将其本人与虚假作者放在一起,又虚构了漫长的创作历程和流传史;读者不得不猜测这样一段文字的真实性,进而考究凡例的来源,作者的身份。“作者”因此成谜。
要探究此处伪装准文本的意图,先要将这一叙事策略置于中国小说传统和时代背景中加以考虑。首先,虚构文学在中国古代地位卑贱,文人在写小说时不愿意署名,经常化名或是假托他人之名,至今仍有许多学者认为明末大儒王世贞就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
其次,文字狱对于这段“凡例”公案也功不可没。康乾之后,因小说罹祸的事时有发生。曹雪芹所写的是金陵,但很多读者误认为作品发生在北方。楔子刻意将背景一再虚化,也是为了避免其与真实的历史与现实发生关联。
此外,“烟云障眼”的叙事方式体现着作者的叙事意图和美学观念。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与假之间的关系,也许是《红楼梦》中最核心的一对辩证概念。看似真实,其实是虚假,看似虚假,也许反而是真实的。真假、虚实界限的消除,也在以上一段关于“作者”的说明中得到了实现。
顺便说一句,有一位外籍学者去年曾在清华做过一个讲演,题目是关于镜子在《红楼梦》中的作用。中国古代的镜子是青铜镜,使用并不普遍。刘姥姥逛大观园时所看到的镜子则是西洋镜。她被镜中的自己吓了一跳。镜中映像是真还是假呢?再进一步,我们知道,《红楼梦》中有真宝玉,也有贾宝玉,最后留在世上的是真宝玉。那么,镜子这个物象,对《红楼梦》的创作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尤其是对曹雪芹的文本策略和哲学观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小说评点
中国古典小说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准文本,即小说评点。它不是正式文本,但附着在正文之中。读者无法像对待“凡例”、“序”或“前言”那样,享受轻易跳过的自由。因为它镶嵌在正文中,只从阅读过程的物理性去思考,我们就知道它是难以被忽视的。某处词句下忽然出现圈点,旁边有夹批,回前总论,回后总评,随时写在正文文字旁边大段的议论,而且常常用红笔批注,以示与正文相区分。读者不可能完全不受它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中国小说评点的重要特点,即它带有某种强制性,读者无法对它视而不见。我想这在西方文学史中是极为少见的,即便在中国的其他文学样式中也不常见,可以说是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所特有的。
我的小说《人面桃花》出版以后,诗人马季在小说正文中做了评点,并配以插图。从读者反响和我个人的感受来讲,这样的尝试新鲜有趣,也与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构成遥远的呼应。
小说评点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特殊组成部分,它为古典小说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独有的表现形式。由于脂砚斋、张竹坡、金圣叹、叶昼等重要评点者的出现,文本意义因之得到进一步发掘、强化与彰显,评点的价值和功能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我在这里,仍然试图从“准文本”的角度进入评点。
中国的文学理论因其呈现出与西方文学理论不同的面貌,常常被诟病为含混、模糊、不成体系。何以至此呢?这或许可以归咎于传统文人不愿解读作品,不愿做深入的分析。汪曾祺曾经对我讲过刘文典的一桩轶事。当年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刘文典是著名的教授,研究庄子的大家。他给学生上课的方式是将一首诗读三遍,然后再读三遍,又唱一遍,再读一遍。在此过程中,他不会对诗句作出任何解释。文本都是神秘的,任何解释都可能导致支离破碎和意义偏差,对缄默的偏好使文本的完整性和意义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留。
当然,中国古代仍然存在着体系完整、思辨性强的文学理论著作,比如《文心雕龙》。但除此之外,现存的文学批评主要还是以非理论表述的方式进行的。比如,“话”所代表的一类批评方式,小说中是为“例话”,诗歌中是为“诗话”。①“诗话”一词也用于古代说唱艺术。属于“词话”系统,其体制有诗也有散文。如宋、元时印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分十七章,今所见小说分章回者始此;每章必有诗,故曰诗话。”诗话理论在诗歌研究中已经形成传统,从古代文人到今日的学者,都对其非常重视。所谓的诗话,主要是从《诗式》或是《本事诗》这样的作品延伸出来的,也即是中国古代的诗歌评论模式。与今天的评论不同,诗话主要的功用并非评价诗的好坏,或提供诗的中心思想,更不会去归结诗的艺术手法,甚或对诗作出多样化的阐释。
如宋许顗在《彦周诗话》中所说:
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②许:《彦周诗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四一七(钦定四库全书,集部九),诗文评类,第908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古代的诗话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它会对诗歌中提到的一些名目,即名称和器物,进行考证。以《诗经》为例,清乾嘉时期,戴震作《毛诗补传》、《毛郑诗考正》、《果溪诗经补注》,通过考证名物字义来探讨诗之义,其名物训诂方面的成就,使之成为后人治诗绕不过的经典文献。若没有小学的根基,根本无法读懂《诗经》。诗话也常关涉一首诗的来龙去脉,对其本事进行考证。
诗话的重要内容还包括对诗句的身家或渊源,也即典故的追溯。以北宋词家周邦彦的《满庭芳》为例:
凤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开篇写春光已去,梅子借雨势长,即化用杜牧“风蒲燕雏老”(《赴京初入汴口》)及杜甫“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午阴嘉树清圆”,是用刘禹锡《昼居池上亭独吟》“日午树阴正”之意。紧接着,“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又与白居易《琵琶行》中“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心境与意境相呼应。读者不难联想到词人此时与白居易写作《琵琶行》时被贬江州之境遇的相仿。再看下片,“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化用杜甫“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绝句《漫兴》)和杜牧“身外任尘土,尊前极欢娱”(《张好好诗》)。“不堪听急管繁弦”又用到杜甫《陪王使君》“不须吹急管,衰老易悲伤”的典故。陈振孙说周邦彦“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第618页,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此言不虚。与前人诗句的互文关系,不仅仅体现在文字间的关联上,更体现在诗人对于前人境遇的理解和回应之中。周邦彦元祐二年离开汴京,先后流宦于庐州、荆南、溧水等偏远地,所作词中多有感时伤世之叹。若不是对于章句的上溯追寻,我们也许很难体会其隐藏在写景状物之中的伤感。清真词的婉约细腻,与其来有自的写作方式分不开,也使词句更为含蓄蕴藉,意味绵长。而点醒后来的读者,提供这些或是“呼应”或为“引文”的出处,是诗话词话的重要功能。
再举一例。清朝邓汉仪在《题息夫人庙》中写道:“楚宫慵扫眉黛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明要亡了,按照中国古人的惯例,忠臣不侍二主,前朝重臣理应自杀殉国,即便位阶不高的大臣,也应为葆守节操,不再出来做官。这首诗是邓汉仪后来一次游玩途中题写在息夫人庙中的,本意是将息夫人与投靠清廷的文人相提并论。息夫人庙中,有着类似感慨的题诗很多,若不了解息夫人的典故,和这些题诗人的现实境遇,恐怕很难理解诗人何以感慨。让人印象深刻的这后两句诗,内中暗藏玄机,包含着很多关于本事的考证。
一首简单的诗,其中包含着许多文本以外的内容。我将这些阅读准备称为前理解。假如没有前理解作为阅读准备,一首好诗很有可能成为费解的、封闭的、不值一文的文字游戏。
诗话传统是中国古典文论最悠久最主要的传统。我们甚至能够在钱锺书这一代学人身上,感受到它的深远影响。他为《管锥篇》所作的序,就是以中国传统批评的方式,在谈笑中引经据典,不断铺垫,从某个词,某句话生发开来,引申出去,这样的方式在今天几乎已经失传了。与此相对,五四以来中国学者刻意学习和秉承的西方文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政治理论。
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经历了非理性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两次重大的变故,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其背景都是文学的科学化需求。直到今天,文学研究逐渐演变成一种科学。原本文学批评的目的是祛魅,即消解文学作品的神秘性,使文学作品能够被解读。但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论在祛魅的同时又制造了新的神秘性,造成了文学批评比文学本身更为费解的反向效果。文学理论的门槛也因此越来越高,衍生出许多专业术语和专属范畴。批评终于成为让普通读者望而生畏的专门知识,在大学学科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同时也与真正的阅读完全脱节,违背了文学批评阐释文本的初衷。而体制化导致模式化、工业化的知识生产,科学化的规范变成文学研究的标准,既无法增进对文学的理解,也无益于真正的文学创作。
此时再来反观中国古代的“诗话”传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文学理论也未必具有绝对的权威。而中西之别以外,西方文明也并非铁板一块,其文学、哲学、思想史内部还有所谓的“古今之变”。后结构主义的大家福柯、德里达等人都对西方思想史的发展变化有过深刻的反省和追问。在此过程中,尼采可谓始作俑者。且不论内容上的革命性与反科学化,仅就其表面的形式来看,《快乐的科学》、《瞧,这个人》等著作完全置所谓的科学体系、学术规范于不顾,以语录的形式写就。
我非常欣赏的另一位西方理论家本亚明,对当代文学批评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如果按照现今的学术规范要求之,他连取得硕士学位的资格都没有。他最重要的文章几乎都是随笔和散论。所以,所谓的专门化知识其实未必像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神圣,高校的体制和规范也未见得是好事。中国的传统文论在此意义上是否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充满趣味和旁征博引的批评方式在今天也许更值得我们重新回顾,重新关注。
除了正规的诗话理论,小说中还有例话,尤其晚清以后,评论小说的文人逐渐增多,例话于是应运而生。现代文学史上,孙楷第、周振甫等人在一些著作中延续了例话式的批评方式,摘录小说中的人物或场景描写,进行随笔式的评论,或是考证。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例话并不多。常见的是小说评点。它既没有采取纯粹的理论式的阐述,也没有采取“话”的方式。它以“准文本”的形式出现,依附于正式文本,并被编织进正式文本中。具体来说,有眉批、夹批、旁批等许多样式。小说评点之所以在中国古代特别发达,在我看来,是由于注经传统的影响。按照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的说法:
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书则孔安国传。诗则毛苌传郑玄笺。周礼仪礼记则郑玄注。公羊则何休学。孟子则赵歧注。皆汉人。易则王弼注。魏人。系辞韩康伯注。晋人。论语则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则杜预注。尔雅则郭璞注。谷梁则范甯集解。皆晋人。孝经则唐明皇御注。其后儒辨释之书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①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清乾隆刻本,第353页。
古代的经书年深日久,渐渐无法读懂,因此需要解释;此类解释被称为笺、解、学,后人统称其“注”。一家的解释出来之后,必然面临着后人的质疑与考辨。对于已有解释的进一步辩证、集解,是为正义,也即“疏”。关于儒家经典著作的解释与传承,形成了经学的传统。
孔子曾说,“述而不作”。与创造新的观点相比,中国古人似乎更乐于依附于前人的著作,通过对前人的注释述评,提出自己的观点。众所周知,一部《春秋》有春秋三传——《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作解,这还不算早在汉朝就已失传的邹氏、夹氏两家。《春秋》记事,文简义深,是为经,后人研读《春秋》,必须借重三传。到后来,《左传》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春秋》本身。
注疏比原书更为著名的事并非特例,注家的知名度也常常超过原作者。稍有古典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水经注》的作者是郦道元,但《水经》的著书年代和作者至今存疑;不仅如此,虽然宋以后通常认为是桑钦所做,知道桑钦的人却极少。
小说评点与经学的解经、辨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究其来源,很可能就是受到经学注疏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跟史传也有关联。司马迁作《史记》,每篇后面都有总评;我们不难由“太史公曰”联想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小说评点中将小说与史传相联系的评论更是不在少数,与《史记》、《春秋》、《左传》相媲美的评价很常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评点与史传文体有着密切的关联。
那么,小说评点到底有什么功能呢?评点者不仅会像现代批评家那样,对原作的修辞、叙事手法和结构安排作出评论性的意见——如“入画”、“如见”,“如画”、“传神”、“精妙”、“草蛇灰线”一类普通圈点,也会对作者隐含于文本中的许多奥秘和玄机加以揭示,从而引导读者的阅读。他们甚至会在批评过程中直接发表自己的感慨,如对世道人心表达评论性意见。更有甚者,评点者竟忽然插入与正文毫无关联的故事,使读者不得不中止对原文本的阅读,而进入评点者的故事。①比如脂砚斋在甲戌本《红楼梦》第三回的眉批中,忽然给读者讲起了一个乡下人进京的村俗笑话。评点者出于不同目的强行置入文本的内容,与作者的原创意图本无牵扯,但这些评点文字在原作的第一文本之外形成了第二文本,或次生文本,它对读者的影响不容低估。
举例来说,金圣叹评本的《水浒传》,其中一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雪正下得紧,写雪妙绝。”依照我的个人阅读经验,若不是金圣叹提示,读者未必能够意识到这雪妙在哪里。紧接着,“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写雪妙绝。”评点者的文字不断指涉原著的修辞或寓意,又强化了林冲逼不得已,雪夜上梁山的凄惶处境。
我们今天所讲的评点,或者说批评,在古代有着更为细致的划分,批、评、点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从字面考证,以打耳光为例,所谓“批耳光”,“自批耳光”,是指下手不那么重的耳光,如果打得很重,就要用“掴”。所以“批”的意思就是“薄切”。小说评点中,用小字写在正文旁边,这句话写得如何,有什么来源,可谓轻描淡写。所谓“评”,再细分下去,又有总评、回末评,旁边还常有眉评。“点”即为圈点,评点者用圈和点这样的符号在正文的文字上做标记,常常同时伴随着几句简单的评论,比如很好,或者妙。王熙凤在《红楼梦》中只写过一句诗,“一夜北风紧”,一个不会写诗的人能够写出这样一句诗,真是妙极了。我若评点,一定会在这句诗上面做圈点。
评点也是点化、提点。对于不易被领会或发现的细节,评点者试图以此引导读者,提醒读者,进而指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讲究伏笔,尤其是《三国演义》、《金瓶梅》、《水浒传》等。伏笔本身文字寥寥,常常作为重要的线索埋藏在小说中,普通的读者很容易忽略它。可是好的评点者会在这些文字底下密密地圈点,然后写上一个“伏”字,告诉读者此处有埋伏,阅读时要特别留心。《金瓶梅》中尤其多。我读过许多遍,但若不是借重张竹坡的评点,仍然会忽略其中的一些埋伏。
中国古典小说特殊的美学追求和叙事方式,使阅读变得费力,它要求细心的读者用心去发现。张爱玲曾经说中国总有一天读不懂小说了。她晚年随手翻书时突然发现一个重要的细节,吓了一跳,感慨自己原来根本就没读懂。因为线埋得很深,评点家的提醒就显得尤为必要。
除指点以外,评点中表达评点者赞叹的文字也很常见。仍以金圣叹评《水浒传》为例:杨志为梁中书押送生辰纲,途中为吴用等人设计,生辰纲在黄泥岗被取。杨志正要自寻死路,转身又忽然醒悟。回身望望一并随从的十四个下人,之后,“树根头拿了朴刀,挂了腰刀,周围看时,别无物件”。金圣叹此处作评:“止有满地枣子,写来绝倒。”②施耐庵:《水浒传》,第十六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青面兽双夺宝珠寺》,第182页,金圣叹评本,长沙,岳麓书社,2005。巧妙点出了杨志又一次功败垂成后的意境和心境。评价的赞叹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还有一类,是评点人对于小说中重要的词、写作的本事的说明与考证。甲戌本《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荣国府一节:
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
脂砚斋在“半旧”旁边圈了一个点,作侧批:
三字有神。此处则一色旧的,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笑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则曰商彝周鼎、绣幕珠帘、孔雀屏、芙蓉褥等样字眼。
又作眉批:
近闻一俗笑语云:一庄农人进京回家,众人问曰:“你进京去可见些个世面否?”庄人曰:“连皇帝老爷都见了。”众罕然问曰:“皇帝如何景况?”庄人曰:“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马上稍着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一时要屙屎了,连擦屁股都用的是鹅黄缎子,所以京中掏茅厕的人都富贵无比。”试思凡稗官写富贵字眼者,悉皆庄农进京之一流也。盖此时彼实未身经目睹,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又如人嘲作诗者亦往往爱说富丽语,故有“胫骨变成金玳瑁,眼睛嵌作碧璃琉”之诮。余自是评《石头记》,非鄙弃前人也。
脂砚斋通过此处的故事,说明正是经历过荣华富贵的人,才敢于写“旧”。打个比方,如果一个阿拉伯人写阿拉伯,也许从头至尾都不会出现骆驼,不会出现沙漠,因为这些对他来说太平常了。但如果有人冒充去写,可以想见,骆驼和沙漠是一定会反复出现的。
评点中还包括很多议论。即如“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中那个众所周知的公案所昭示的,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是文本意图,而评点者则披露了被作者删改掉的原始动机。秦可卿是《红楼梦》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曹雪芹对她的描写可谓煞费苦心,但却听从了评点者的劝告,最终修改了原先的文字。评点者在文本后又写到评点人与曹雪芹出游、交往的经历,以及更改这一段文字的始末。这也足以证明《红楼梦》跟曹雪芹之间的关系,后来成为红学作者考证的重要凭证。
仍以脂评本为例。晴雯死时,作者忽然悲从中来,不能继续,半夜跑进院子里,看到月亮在天上,地上降过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看到评点人的评点,同时还可能看到某位作者发出的议论。附着在文本之内的准文本使读者在阅读一个文本的时候,也看到了其他不同的文本,这包括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也包括一部作品成书的漫漫历程,都在评点中呈现出来。读者不仅会为晴雯的死感到伤心,同时还能看到若干年前也有人为她伤心,并置的方式使不同时空的读者得以用同一个文本为基础进行交流。评点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在中国古典小说评点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评点的丰富性还不仅限于此。古代的评点者甚至会参与到创作过程中,对作品内容进行修改、调整,甚至大面积地删改。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往往是集体创作,也即经历不同的朝代,由不同的作者增进,补益,因此所谓的“作者”身份并不清晰,现代版权法的观念更无从谈起。晚近的研究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有五十七人之多。评点者在这一集体创作过程中,亦功不可没。明末清初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改,即是一例。明万历年末杨定见序的《水浒传》有一百二十回,金圣叹将其“腰斩”,砍掉二十余回,删去了受招安、征方腊等回目,又加续“惊噩梦”作为结尾,形成七十回本。这七十回本,与一百回的天都外臣序本和荣与堂本,以及杨定见序的一百二十回本,成为《水浒》最为通行的几个版本。
金圣叹的修改十分微妙,至今无法确证七十回本中具体哪些文字经过了修改。比如他本人对宋江非常反感,但却从未在正文中直接评述,但最终在读者看来,宋江这个人真的坏透了。这不能不说是作为小说家的金圣叹技艺高超所致。金圣叹评本第三十五回至三十六回,宋江因杀婆惜被通缉归案,由两位公人押解前往江州,途遇吴用、花荣:
下马叙礼罢,花荣便道:如何不与兄长开了枷?宋江道: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①施耐庵:《水浒传》,第409、419页,金圣叹评本,长沙,岳麓书社,2005。
可是后来宋江与公人夜半投宿生人庄院,两个公人道:“押司,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快活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说得是。当时去了行枷。金圣叹此处作批:“写宋江答公人,偏不答别句,偏答出此三个字,便显出前文‘国家法度’之语之诈。”②施耐庵:《水浒传》,第409、419页,金圣叹评本,长沙,岳麓书社,2005。
中国传统小说中批评人物时的隐晦和含蓄,由此可见一斑。就金圣叹版的《水浒》而言,他不仅做了大量删改,甚至还假托原作者施耐庵之名,为全书重新作序,并且作了评点。金圣叹是不是作者呢?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实质上参与了创作。
晚明心学大家李贽据说也曾评点过《水浒》,从他本人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切实的依据。但在流传至今的《水浒》评点本中,有两部都署名为李贽评点,而两个版本完全不同,我们只能推断它们之中一为真,一为假,当然,也有可能都是假托,或是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的评点。研究者考证认为真正的评点人是叶昼,他需要假借李贽的文名,也可能是李贽确曾作过一些评点,但叶昼又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假托”使创作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也使“作者”藏匿于历史的晦暗之中,难以辨认。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作者”的概念确实非常复杂。一部经典作品可能经过近百人、上千人介入其间。至于《水浒传》这样有故事原型,经历了无数民间艺人加工创作的作品,情况就更为复杂。以今天的写作术语来表述,我们很难说施耐庵是“编纂”者,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作者。在过去的年代,相对于作者来说,作品更为重要。而现代版权制度的确立也建构了所谓“抄袭”的说法。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如我们所知,司马迁的《史记》借鉴了《国语》、《左传》等重要前代史书,《金瓶梅》中有大段文字直接挪用自《水浒传》,但作者并不讳言。
“作者”概念的复杂性还表现为“作者”身份的古今差异。清末民初以一部《老残游记》流传后世的刘鹗,其主要成就并不仅仅是文学。他做官、行医、经商,甚至曾经参与治理黄河。又介入矿产开采,成为最早与外商合资的买办。八国联军入侵时,他向联军购米赈济灾民,因此获罪,被清政府发配新疆,死于乌鲁木齐。刘鹗收藏金石甲骨,其《铁云藏龟》一书,最早将甲骨卜辞公布于世,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些后来的甲骨文研究专家。我们今天看到的《刘鹗集》中,算学、水利、医学、音乐、金石之学的分量远远超过了文学。他之所以成为文学家,只是因为写了一部小说。
张爱玲曾说,中国古典小说中,只有三部是好的。这三部是《水浒传》、《金瓶梅》与《红楼梦》。《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不在其中。我的看法与她相同。这三部小说经历了许多文人不断的修改,才最终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在此过程中,评点的功能不仅仅在于指导读者,它本身也是作品的一部分,作为准文本依附在正式的文本之中,读者无法将之剔除。
由于“评点”这一特殊文本的存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与西方叙事学意义上严格的作者-批评者-读者之间的关系相比,中国传统小说中三者的界限并不那么明确。评点者既是读者,也是批评者,同时就像我们刚才所论述的那样,甚至兼有作者的功能。读者在阅读时,他所面对的文本不仅是作者的正文、评点者的次文本,还有许多无名作者阅读过程中留下的痕迹。这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对话关系。
古代的评点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金圣叹、张竹坡这样的大家。第二类是刻印者。这类人受到商业利益驱使,需要完整的作品印行销售,于是请文人来续。还有一类是普通读者。由于喜爱收藏、喜爱批点,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信手涂鸦,在书的眉页之间留下自己的阅读痕迹。如果假设此人拥有的本子恰好是孤本或善本,那么这位无名读者随手写下的意见也会随着本子的传抄、影印与过录一并流传。而且读者在传抄过程中,也常有随手篡改文字的“恶习”,使得衍文与错讹不断,有时甚至难以通过考辨加以还原。我们不妨略举一例,以说明之。《红楼梦》第八回写到宝钗、宝玉比通灵玉之时,黛玉从外面进来,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犹未了,林黛玉摇摇地走了进来。
其中“摇摇”两字,传神刻画出林黛玉的弱不禁风,脂砚斋特地加以圈点,评价为“两字画出身”。可是在另一些《红楼梦》的通行本中,“摇摇”变成了“摇摇摆摆”。按照俞平伯的解释,这很有可能是某个无名读者总觉得“摇摇”两字不通,遂径自加入“摆摆”两字,以至于显出大腹便便的轻浮之态。评点中不乏这样格调低下,或类似封建卫道士、令人生厌的口吻,当然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让我们为之叹服。
小说评点的方式至今仍有人在使用。我并不主张完全恢复它,但它其中所包含的作者、批评者、读者之间特殊的互动关系值得我们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准文本,它与正式文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值得我们重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