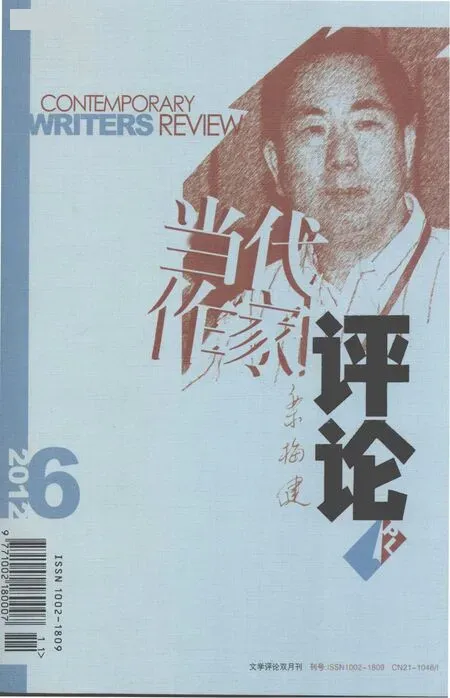提速时代的历史反刍——略论王彬彬及其文学批评
2012-12-17王侃
王 侃
一
二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这二十年,人类社会的快车正以加速度的方式撞向尚不知处的未来之门,时光也在刹那间被重重压缩。这时,一个词就会拨开眼帘闪身而入:提速。“提速”,大约也体现着这二十年中国人现代性焦虑的典型症候。经济发展要提速,政治进步要提速,教育改革要提速,文化建设要提速,生活质量的改善要提速,物质的、精神的都在提速。相应地,人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通讯电子化,办公自动化,饮食快餐化,连男女关系也在速配闪婚的理念下快马加鞭一日千里。
火车也三番五次地提速。如今的动车组或高铁,跑一趟沪宁线,最快时不到一个钟头。对于像我这样睡眠脆弱、入睡困难的人来说,一个小时连打个盹的工夫都不够。记不得是哪个作家说的:疯狂的提速,其实是对人的时间的强行剥夺。诚哉其言。表面上,“提速”在为我们争取和节省时间,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提速”则扫荡着我们的从容,扫荡着我们沿途播撒目光的余裕心境。我们的生活与记忆正在“提速”中失去质感,它们流于平面,它们被抽空,被缩略了无限多的感性细节,被删除了可供咂味的历史内容。一切,只为快速抵达一个实现或谋取功利的终点。乘坐动车在沪宁线上跑一趟,除了那些被印刷在寡趣乏味的列车时刻表上的站名,我们还记住了什么?
“提速”不只是经济社会的一种内在要求,它同时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化逻辑,并进一步衍化为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准则,一种直奔主题罔顾手段、只求结果不计过程的普遍心态。如果不是一些刻意的提醒,那些曾在沪宁线上缓慢推进的历史风云,就会在“提速”的今天被遗忘。譬如,同样是关于睡觉,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夜十一时,陈独秀在上海被押解上开往南京的列车,不俟多久便恬然入眠,酣睡达旦。他时间裕如,心境从容,以至鼾声大作。若在提速的今天,这酣睡、这鼾声都将成为难题。但无论对于现代以降的中国,还是对于陈独秀本人,这沿途的酣睡与鼾声却足以构成一个历史事件。同时,作为历史符号,这酣睡与鼾声也直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操守的生动表现与刚性标尺。这标尺,形式幽默,内容严肃,并能迅捷地考量出每个知识分子个体的最终的精神高度。
王彬彬在《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①王彬彬:《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钟山》2002年第3期。一文中所作的钩沉,为我们描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情节与关键细节。王彬彬的文章有他的刻意。这是他为这个“提速”时代提供的一个历史反刍的范例。不用说,他还同时坚持认定进行这种反刍的现实必要。他轻松行文,凝而不发,但表达的却是关乎生死的沉重命题。毕竟,无论提速与否,赴死的旅途不会让太多的人“若平居无事者然”地轻松滑进酣睡的悠游之境,相反,大多数人会在被羁捕、被押解之前就选择一种规避,选择一种只求生不问死的活命哲学,选择一种不与生死判决提前遭遇的生存路径,或者,在投机的举动被识破、机会主义路途被堵死之后,面临严酷的生死考验之前就不假思索地做出避害趋利的本能之举。若非执著于一种严肃的立场,这些选择或许无可厚非,不劳指摘。但是,当这些选择被宣扬为是一种公共认同、一种普适价值、一种随时随地可以放肆凭借的基本伦理时,我们面临的危机将是丧失对于羞耻的最低敏感,高尚成墓志铭、卑鄙当通行证的悖谬就不会只是独属于政治专制年代的流行现象。非惟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在王彬彬简洁透彻的思想认定里,对于应当视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而言,应有更为苛刻的举止约束与对于信仰、对于节义的伦理自律。在写于同一时间的另一篇文章《瞿秋白的“名誉”》②王彬彬:《瞿秋白的“名誉”》,《南方文坛》2003年第3期。里,王彬彬就再次试图说明,舍生取义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是孤例,而且,瞿秋白之所操持的“义”,甚至只是当代人不屑一顾的此微名节。我愿意倾向于认为,王彬彬的文章有他的私人原因。差不多二十年前,当他指斥中国作家过于发达的生存智慧时,这“真的恶声”便招来了铺天盖地的恶诬与羞辱。由之,若干曾经的文化精英在高喊“躲避崇高”的同时正呼吁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放低甚至放弃伦理底线;“牺牲”、“殉道”已沦为笑柄,与“革命”、与“崇高”一道在备受嘲讽后被当作脏水一股脑儿泼掉,与此同时,犬儒主义及其践行者则俨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与精英。我相信,王彬彬在那场论战之后十年写下这些文章,当是孤愤中的回击。十年的世道体悟,十年的思想磨砺,他已一洗当初的稚拙与朴钝,但他偏至为文、激越发言的姿势一如既往,只不过其战斗身形已脱去当年的单薄。此时的他,已身怀利器,如漆的黑夜里也能看见他剑口的寒光。虽是回击的文章,但行文中已无视具体的对手。虽是起于私人原因,最终却通过对一种知识分子形象的揭橥来垂范于这个只讲究“提速”的时代。那一路视死如归的鼾声,那一个在法庭上为自己的政治立场“不思悔悟”的自我辩护者,以及那一张临刑前一声“此地甚好”的淡定笑靥,在王彬彬叙议相间的文字里统统奔向了道义的大命题。陈独秀、瞿秋白的历史地位与身世命途的复杂性、丰富性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示范性,岂是后来自命聪明的文化精英所能比附。下笔之时,破题之际,取意已定;那些看似严正实为聒噪的低级辩论,已在文章中被远远甩到身后。王彬彬所做的,就是指认一种不证自明的价值存在,一种在提速时代被有意无意丢弃的历史形象,从而让那些仍然试图急于辩白的声音陷于喑哑。对于王彬彬来说,他“姑活”①所谓“姑活”,由“苟活”这一义项训得。王彬彬如此注疏:“苟活,便是随随便便地活,对怎样活着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而看重的是活着这一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姑活,是对死持随随便便的态度,而怎样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姑活者,随时准备不活,但只要仍旧活着,那就每一天都要活得认认真真,都要坚守某些原则,都要活出人的价值,活出人性的光辉。”见王彬彬《鲁迅的晚年情怀》,第1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十年的回击,只是为了等待一个由历史提供的、历史为其自身除尘祛蔽的时机。
如今回想二十年前的论战,或许我们仍然有理由批评一匹“黑驹”的青涩,批评他的见事未明与省事不深,批评他的片面与冥顽,但如今又有谁能否认,当年由他执笔挑开铁幕,敲裂冰面,让世人看清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不可弭合的巨大断裂与不易辨识的种种暗流,难道不是一种不逞多让的恰当吗?
掩卷时曾暗自想象,经常往来于沪宁线上的王彬彬,每每面色端凝,敛神动容之间常似若有所思。陈独秀的鼾声应该是他这段旅途中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怀想。只是,大多数人并不知晓,他同时还是陈独秀的乡党。当他不吝辞色地直呼陈独秀为“真豪杰”、“真英雄”时,其实是为知识分子群体、同时也为自己进行了归类。诚然,相比于那些复杂繁缛且弹性十足的生存智慧,王彬彬的归类标准看上去失之简单。就像他在《周作人是特殊的汉奸吗》②王彬彬:《周作人是特殊的汉奸吗》,《钟山》2003年第6期。一文中批判汉奸周作人时所下的论断一样,他只以一种终极的道义尺度来划分知识分子形象的类型,并且黑白两立,阴阳两隔,泾渭分明,在这个终极尺度面前,任何强调灰色中间地带的企图和努力都会被他视为诡辩与失德,挥斥之后再一并烙上他轻蔑的斜睨。而他之所以习惯性地喜欢将人推进这个极富张力的终极境地来进行测度,是因为道义的利刃只需轻轻一划便能分出灵魂的清浊和精神的昏晓,尤其是,在他看来,在生死道义面前,人与人之间比试的不是智慧的高下,而是气质的优劣。成败难论英雄;是战士还是伪士,最后能验出真章的,惟在气质。不用说,明知万难幸免却仍然挺身为光明世界掮住铁闸的,一定不会是气血亏弱的灵魂孱头,也一定不会是“躲避崇高”的精神侏儒。高下原来很容易分辨——何况,退一万步讲,以陈独秀、瞿秋白辈的水平,即便单以智慧论,如今自命精英的“智识阶层”又何曾胜出过哪怕半筹?
质之于文学,相同的决断延续着王彬彬对气质的尊崇。他相信,是“情怀”而非“才华”才最终决定着文学品质的分野。③王彬彬:《才华与情怀》,《北方大学》1996年第4期。同样是习惯性地设置一个二元撕缠,他相信,在“功利”与“唯美”之间,惟有气质者因其“情怀”便一步迈入游刃有余的自由之境,出乎技而进乎道,一出手、一落笔便可能是震古烁今、百世流芳的华美篇章。有关于此,随手可引为一例的,是他于一九九七年仲春写毕的专著《鲁迅的晚年情怀》。我在翻阅王彬彬的这部著作时,不必费神绕弯就能清晰地看出他立意的苦心孤诣。多年以来,围绕着鲁迅的种种榨取或攻讦,已完全彻底地掘毁了知人论世的学术路基。王彬彬所做,是在毁败处重新出发,为鲁迅晚年的文学与人格写下别具一格的判词。只“情怀”一词,举重若轻又掷地有声,点石成金又击中肯綮,诸般争讼,似可迎刃而解。思忖之余,不禁黯然:混迹鲁界者众也,但这般带着体恤与体温的捍卫,如王彬彬者,微斯人也。
毋庸讳言,王彬彬是个片面者,虽然深刻。因其深刻,他的局限和偏颇也愈发彰显。他的片面,是气质使然;更大的原因,是世道,是环境,是人心,是形格势禁,使他在愤怒中断然将自己抛向孤绝。老实说,这个时代并不时常有人有此胆色。如今的秦淮河,正在接续桨声灯影的风流,彻夜飘荡着醉生梦死的香软酬唱,更多的人只想纵身一跃,变水变浪,但求融入其中。但总会有人选择做一只蹲踞于黑夜深处的怪鸱,不屑于低吟浅唱的粉腻,震悚一叫。这异端的声调,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种命定,别无选择。王彬彬的片面自不待言,我相信这也是一种命定。他的片面,是作为异端的片面。同时,他的片面,有一种可爱的不加矫饰的透彻,有一种刻意为之的偏执和谑意,因此,实际上,片面或褊狭并不对他的自省能力造成不可跨越的障碍。这在他对同道先驱之局限性的种种评价中可窥一斑。不过,从一个更为超拔的层面来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价值选择,是他对自己在当下历史的角色定位,是他对自己的群体归属的认定,这使他即便在困境中也仍然自信和强大。他是个生活在历史中的人;较之现世的朋辈,他显然更看重被他引为同道的历史人物。不用说,置身历史,他并不孤独,相反,他有理由因此骄傲。在总结陈、鲁等先驱者的得失之后,他援引以赛亚·伯林的话写道:“他们也许太褊狭,对人类的经验事实往往也会判断失误,但是他们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们试图把中国的老百姓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反残忍,反压迫。他们跟迷信无知以及许许多多败坏人们生活的勾当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并且取得了可观的胜利。因此,我们站在他们一边。”①王彬彬等:《略论启蒙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此文所引以赛亚·伯林的原文,出自〔伊朗〕贾汉贝格《伯林谈话录》,第66页,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这已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明志。此时,我继续倾向于认为,这些年写下的铁血文章之于王彬彬有着深刻的私人原因。这些文章,不仅是思想前行的屐痕,不仅是荷戟彷徨的心迹,同时也是他一个阶段的生命总结。经由这样的总结,他完成了一个私人仪式,从此将自己融入那些在气质中傲然行世的历史形象。
二
我不知道,也不曾征询,是不是二十年前的那次论战最后铸定了王彬彬如今的问学方式。他著述颇丰,风格朴野;笔锋所至,常留下论战的焦土。但他激越地讲“义”,又结实地释“理”,所谓“文质彬彬”。这是他四面出击却又从不担心腹背受敌的原因之根本。不过,这还不是我想说的王彬彬的问学方式——只是为了取其形象,不妨一借,我且把王彬彬的问学方式称为“知识考古学”。
由于对“义”的激烈偏倚,王彬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大部分落在了“美学意识形态”的论域,落在了对思想的萃取与对思想史的勾勒。这使他的研究在大的层面上被理所当然地归入“文史互证”的范畴。互证者,先辨真伪,以发现历史与文学(文本)之间何处互相印证,何处莫名错位。不过,“文史互证”本身不是目的,辨识真伪也只不过是学术的低端。“文史互证”的最终意义,还是在别求新声,在于豁人耳目的思想发现,从而提供对历史、对文学新的理解契机与新的阐发向度,并提高我们的视线。这其中,当充满对意识形态化历史的不懈警惕,对各种已知结论的持续不满,以及对文学“文本性”所持意识形态修辞术的深刻怀疑。这些年我们遭遇过太多这样的文章:它们在看似循从“学术规范”的形式外表下,用整饬光滑的史料堆砌与拾人牙慧的话语拼贴,煞有介事地论证着已知的结论;思想的命题自非此等庸辈可堪承托。水平的分野,关键处真是天壤之遥。
就方法的一般层面而言,王彬彬所操持者可谓老旧,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扎实的史料考据是不可或缺的,推理的每一步都必须约束于缜密的用心。但即便如此也还远远不够。对于一种其论断旨在试图偏离既定历史的思想研究来说,还必须有“知识考古”的方法与洞见,以求得重新建构历史的思想材料,以使文史互证可以产生新的思想取向。在偏离/重构的双重操作中,历史被祛魅,思想被甄别,启蒙的意义方得落实。当然,一种方法是否得心应手,窥其堂奥,还在于操持者对“义”、对价值理想的选择和预设,由此才可使人文学术一开始就摆脱科学主义的所谓“客观”,使有洞见力的人文学者最终能摆脱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的窠臼,使一种看似老旧的方法论摆脱画地为牢的种姓限囿,成为普适,并焕发出新的阐释能量。
兹举一例,以初步说明王彬彬问学时的“知识考古”。在《林道静、刘世吾、江玫与露沙——当代文学对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叙述》①王彬彬:《林道静、刘世吾、江玫与露沙——当代文学对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叙述》,《文艺争鸣》2002年第2期。一文中,题中所列四个人物在当代小说中依次出现。其中,露沙直到晚近的一九九四年才出现。依着“考古”的习惯,我把露沙的出现称为新近“出土”。对露沙的研究,使其他三个原来散在的人物迅速形成了谱系,构成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历史序列。王彬彬提问的切口不大:这些人,同是知识分子身份,在大致相仿的时期,都以林道静式的单纯和热烈投身革命,结果,最终都变成了刘世吾式的世故与冷漠,是谓何故?露沙的出现,弥补了在林道静和刘世吾之间存在的形象断裂,而露沙投身革命后的身世遭遇也意外地同时说明了断裂发生的必然。这篇论文使一种原本滞涩、含混的历史叙事在紧要处续上了逻辑,变得通畅、顺当和贴近真相。切口虽小,但因为击中命门,它也可能让意识形态化历史因此痛彻全身。在我们不经意的地方,王彬彬早早地埋下了他的疑问,然后开始难以限期的考掘、披阅和等待。也许,他最后掘到的只是一块细屑的历史碎片,但恰恰因为这块碎片的补缀,使历史最后呈现出迥异的面貌。
王彬彬的研究,长时间地聚焦在知识分子人格形象及其种种变体。发动“文学革命”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倡导“革命文学”的瞿秋白、胡风、郭沫若,左翼的丁玲、何其芳,非左的朱自清、闻一多,“十七年”的邓拓,“文化大革命”的浩然,以及当下的“文坛三户”,都是题中应有之人。研究知识分子,是因为知识分子是思想的载体与塑形。他就此写下的一批论文,以雄辩的粗粝之气,用力修订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谱系,揭示了曾被遮蔽的思想史线索,同时,还隐隐然勾勒出一种样式别致的文学史形态。
王彬彬所论,涉及文本内外的知识分子人格形象。很大程度上,他更看重对文本之外的文学家或作家人格的辨析。除了对“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的批判,以及由此自然引发的对陈独秀等舍生取义之壮举的赞许,另一些正本清源的甄别在他看来也事关重大。比如对邓拓的评判。流行的文学史著述,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为彼一时期文学成就的高峰,视邓拓为专事批评政治专制与个人崇拜的时代良知的体现。这样的结论源自国内外学界对邓拓的“书生”气质的刻意肯定,源自对这种“书生”气质之不合时宜性的正面强调。但王彬彬不客气地撕碎了邓拓所谓“书生”的人格形象。还是通过“知识考古”,历史的现场感被尽量复原,同时被尽量还原的还有当时的“政治气候与文化氛围”,以及对主要文本的初始阅读①王彬彬:《邓拓的本来面目》,《粤海风》2004年第6期。。他行文周致,述与论都丝丝入扣,丰饶厚实的史料考据、鞭辟入里的精神分析以及诚实用功的文本阅读,在“互证”中找到了结论的出口——王彬彬不得不严肃地指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提倡的,往往也是其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提倡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反对的,也正是其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反对的”,“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邓拓是乐于写‘遵命文学’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应作‘遵命文学’来看”。王彬彬甚至抑制不住地语带讥讽:“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并无什么锋芒,或者说,都离‘政治’很远……这类看起来远离‘政治’的文章,能够弥合和安定人心,能够不知不觉间消除人们心中的火气,所以,实际上又能十分巧妙地为现实政治服务。邓拓们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主要目的是要向读者传授知识。他们写下的绝大多数文章,也的确像是中小学教师的讲义。面对饥肠辘辘的读者大谈养牛养狗养猫养蚕一类知识,似乎有意在以‘精神食粮’代替窝窝头与糠菜团——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多少起了‘帮闲’的作用,不知是否有些过分?”
对邓拓的“考古学”分析,会导致其他一些更具深意的结论的涌现。彼一时期,政治专制下的作家人格,论其大体,都是政治人格,与邓拓相比只是程度不一。与邓拓一样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他们“基本的知识结构和精神视野”,是他们人格的资源性要素。因此,他们的文学大致都可归入“遵命文学”的范畴。当代表了彼一时期文学高峰的邓拓的文学都被否定了,余者怎能幸免?如果不苛责他的极端,至少我们应该承认,王彬彬坚实的研究,使我们相信,果真是“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而“欺”和“瞒”的时代便只有“欺”和“瞒”的文学。他对“十七年文学”的激烈否定,是有其学术上的清晰理路的,是有扎根于“考古”的思想支撑的。这在他的《政治全能时代的文学:〈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论评》②王彬彬:《政治全能时代的文学:〈十七年文学:“人”与自然的失落〉论评》,《南方文坛》2000第1期。中有过总结性的陈述。进一步地,当一种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论调出现时,王彬彬的激烈反应就完全不会出乎你我的意料。
考古的目的在于为历史去蔽,而启蒙的要义在于为思想去蔽。某种意义上,“考古”与“启蒙”是同一构件的不同侧面。区别于那些自私为人、光鲜为文的“纯学者”与“纯学术”,王彬彬其人其文以对一种文化使命的自觉承担,以果敢、率直、粗粝、不矫饰、不妥协的姿势,表达着启蒙对于当下文化和文学的现实意义。这种使命感驱使他不断进行从一种去蔽(考古)到另一种去蔽(启蒙)的双重劳作。他是批评者,也是解构者。他的学术意图,在于不断地要将意识形态化历史奋力拉回到叙事起点,指出历史叙事的其他可能性,指出意识形态化历史叙事在话语合法性上并不具有天然的优先权,指出意识形态化历史叙事对事实真相的恶意偏离、篡改、歪曲以及意识形态修辞术在历史叙事中的整容功能。于是,如果说,在前述对王彬彬之“知识考古”的“初步说明”中,我已提示“知识考古的初步”还只是“在追寻落在时间之外,今天又归于沉寂的印迹”,以补缀某种历史断裂,那么,在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上,王彬彬的“知识考古”则是在不断揭示、刮开历史内部的断裂,以使通体美观的历史露出整容的秘密刀痕。的确,如果不是因为一个精辟的发现,我们未必能如此透彻地认识到“新启蒙运动”与“《讲话》精神”以及“毛泽东思想”之间直接的渊源关系,认识到以否定和“踏倒”五四为前提的“新启蒙”其实只是党争的策略与需要。①王彬彬:《〈八一宣言〉、“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结论自然是断裂性的:我们发现,其实五四传统从来就不曾在延安之后的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及其文学中被有效地继承过,启蒙的意志也一直在起跑线上原地待命。往深处说,这就是我们已然度过的种种历史悲剧的思想根源,也是我们进入下一个悲剧的思想入口。这就是为什么“重回五四起跑线”会成为当下时代的思想吁求,这就是今天重申启蒙的历史缘由。
相似的篇什,如《“皆起于此夜之会”——陈独秀为何离开北京大学》、《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一九三六年的“双簧戏”》、《一九三六年的“救国会”与“民族魂”》等,让我们在刮开的一道又一道断裂处陷入沉思。我们因此能更为清楚地听到,在历史的背后,知识与权力的枪戟交鸣,启蒙与“蒙启”的殊死较量。不得不承认,无论文章体量的丰瘦,也无论问题切口的大小,王彬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大命题的追索。就我个人而言,披阅这些文章之时,与我的思路撞个满怀的,有温故知新的欣然,有别开生面的讶异,有破题解惑的开悟,更有重估历史的举意,它们补充和拓宽着我的思路,也在紧要处提醒我推敲和调整思想的路向。
年轻的王彬彬因一场论战而“暴得大名”。那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还能走多远。如今,一个不需自命的“精神界战士”,一个治学厚谨的严肃学者,已无须应对那些无聊的证明。你不认识他不要紧,读他的文章就行。他以气质取人;有尊严过敏症;不能免俗时,会点起香烟愧怍地踱步。他的为人与为文,有着难能可贵的统一。需要说明的是,正是这种统一,使他的人和文都异常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