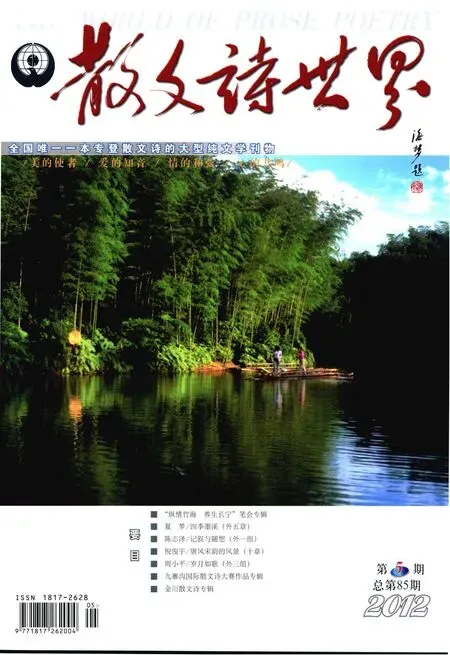水生明月,笔底烟霞—读蔓琳散文诗集《穿越河流的月光》
2012-11-24巴芒
巴芒
一
关注蔓琳的散文诗,始于去年进入四川天府论坛《诗临天下》。彼时,蔓琳有些许作品发在那个板块。但就是那些短小精美、灵动无限的文字,像粒粒晶莹透彻的水晶,滴落我心,一直不曾离去;随后,进入她的新浪博客,得以较为完整、系统的阅读她的作品,感受她的心灵文字和诗意世界;再后,意外得知她在去年底将出版散文诗集《穿越河流的月光》,欣喜若狂,忙打电话托成都朋友为我购得一本,寄与我。近期日日捧读,在蔓琳或是轻灵绰约的或是感伤悲悯的而又充满质感的文字里游走,在她或是委婉倾诉或是深切呼唤的情感世界里停留。品着她的文字和心情故事,如与作者对话。
我注意到,蔓琳是近两年才冒出的散文诗作者。但她的起点之高,对诗意文字的非凡驾驭功力,对情感世界瞬间爆发的捕捉能力,都让人惊叹。对于散文诗的认识,我总认为“诗”的成分是要占主导地位的,它是用诗歌语言写就的散文,是用散文形式写就的诗歌,诗蕴、诗情和诗心应成为这种体裁的主体、核心。因此,优秀的散文诗者他一定具备诗人的气质和品性,能用诗性的语言和诗化的情感来成就自己的文字语言,用形象跳跃可感的文字来架构看似散漫的诗行。在这个意义上说,蔓琳的这部作品,是具有代表性的。通过仔细阅读蔓琳的这些文字,我发现,蔓琳首先是一个诗人,是一个在诗意世界生活的人,是一个在诗意世界上下求索的行吟者。诗者,悲悯者也。蔓琳用自己的诗韵情怀,通过神形兼备、文心统一的深情诉说,来让我们感受她所感知的世界:喜怒哀乐,如歌似泣;水声月色,如梦似幻;一路风景,如音似画。运用个个可感的文字意象,把心情记录向我们一一道来,让人情不自禁地随之走进她所营造的诗意世界,任她游走的文字涤荡自己的灵魂,欲罢不能。
二
作为一个读者,反复阅读蔓琳散文诗集的过程,就是与诗者反复交流的过程,在这种反反复复的交流中,总会有些心得。散文诗集的题目为《穿越河流的月光》,“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朱光潜语)”我想,这部作品的文字一定和水有关,和月色有关;和水质情怀有关,和月质境界有关;和流水一样的人生岁月有关,和月光一般澄澈的心灵感悟有关。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通过贾宝玉之口赞美说女子是水做的,水有着着洁净、甘冽、温软、纯美的品性,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赋予到女子身上便是温柔多思、善良慈爱,敏感而知性的情怀,这是我说的水质情怀;而月亮作为美的象征,代表着安宁,静谧、空灵、永恒的精神境界。在这部散文诗集里,与水和月相关联的意象比比皆是。我们先看水:开篇《茶关》中的茶,是一杯很“单纯”,却饱含深情的香茗,意境悠远,诗意绵长;紧随着是《鸳鸯江》的“一湾澄蓝”“一湾浑浊”的一脉江水,通过简洁形象的可感文字,表达自己勇敢、纯净、坚定的情感追求,练达世情而又掷地有声;《带泪的曼陀罗》中的“泪”水,“滴在我紫色的高跟鞋上”,是因为“是因为怎样交错的前世今生”,“是怎样花开彼岸的不甘心”!高贵而矜持的曼陀罗,也有着如“珍珠”“露水”的“泪”,一下真如“寒夜星辰”,有了灼灼光辉。其他诸如《约会海水》《浪与沙》中的海水,《秦淮河怀古》中滴落台阶的细雨,《与雪山的距离》中洁白的雪,《木格措》中一闪一闪的浪花……等等。我们再看月:“我一览无余的月亮,我沉沉的思念(引自蔓琳《月亮,时光的镜子》)”,这是时光记忆中存留的月;“玉兰记得那些它们彼此相拥的夜晚,记得月光无限的柔情(蔓琳《玉兰与月光》)”,这是深情无限的月;“……笛声悠扬,那一捧皎洁的月光是你前世送我的花束(蔓琳《爱有来生》)”,这是如爱情“花束”一样珍贵的月;“而我醒来,月光潮湿,模糊了我的双目(蔓琳:《母亲又入梦境》”,这是带着思念感伤的月;“此刻,我依然携着那轮朗月前来,为你的生日,也为我曾经的承诺赴约(蔓琳:《祝你生日快乐》)”,这是可以作为生日特别礼物的月;“我以一种放手的方式拥抱你,而你,用广博的心怀,包容与我有关的所有黑暗(蔓琳《开江望月》)”,这是如至亲爱人值得“放手拥抱”的月……等等。蔓琳对“水”和“月”如此钟爱,为何?我想,作为诗者的蔓琳,同时也是在物华天宝、风光秀丽、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天府之国成长起来的现代女性,是巴山蜀水赋予了她如梦似幻的诗人气质。她的思想通过文字溢出,自然而然地会把女性的温柔、感伤、细腻、敏感、慈爱等特质表现出来,情感真,性格善,境界美,如流水一样干净,如月光一样透彻。
我们知道,“流水”和“月亮”作为诗歌意象的使用,地位早已相当稳固。“流水”古典诗词的意象使用一般是象征时光流逝、岁月短暂、愁苦绵长。如李煜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如李嘉祜的“黄卷清琴总为累,落花流水共添悲”,如韦庄的“百年流水尽,万事落花空”等等;而“月亮”作为一个心灵相通、精神团聚的象征性意象被很早纳入古典范畴。早见于《诗经》:“月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这和思念有关,后来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白居易的“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相兴五处同”莫不如此,而突出这一范畴达到哲学高度的当首推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这里的月亮已是世事变迁的永恒见证者。蔓琳散文诗对流水和月亮意象的使用,是有着和古典的坚定传承的。诗歌写作传承古典没有什么不妥或不好之处,“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他和过往诗人和艺术家只见的关系的评价”,“不仅他作品中最好的部分,而且最有个性的部分,和可能正是过往的诗人和艺术家们,也就是它的前辈们,最有力地表现了他们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叶芝语)”。尤其是这种赋予传统意象新的感悟、含义和精神的时候。月光穿越河流,水面生出明月,就形成了我眼前的华美篇章。我为此感到无比振奋。
三
在“水”和“月”的交融里,我再试着一窥作者的心灵感悟是怎样如月光一般澄澈的。“风和雨匆匆传达着春天的信息,却将一些随意散落的回忆重重地打在我的躯干上,抓紧泥土的根须在暗地里瑟瑟发抖,我的寒冷我的悲伤你永远无法看到!(蔓琳:《版纳的三角梅》”,对于蔓琳,我并不熟悉,她的情感于我就像像晨雾萦绕的绿色沼泽,她有着怎样的人生历程,写着这些文字时她是一种什么精神状态我无法感知,只能从作品本身去探索。我不知道,她究竟是什么样灵感促使她把一枚“开不出花”的三角梅写成了一首感伤而优美的散文诗歌,或许,世间开放的花朵太多了,她只能留住其中和自己思想最为融合的一朵,哪怕这花并非是花,但也一样会如花朵在她的诗心里疼痛绽放,让诗者在诗意重新创造的苦役中品尝造物主一般的快乐。“曼陀罗开了,带着一如既往的微笑”,“神秘而忧伤”,这是诗者的主管感受,清丽而凄美。我想,蔓琳想告诉我们的并非这个,“许多心事,袒露在浅浅的月光下,如寒夜星辰在闪耀灼灼的光芒”,“是怎样的交错的前世今生,是怎样携手而来的约定,是怎样装饰黄泉路的指引,是怎样花开彼岸的不甘心(蔓琳:《带泪的曼陀罗》)”在蔓琳的笔下,精神境界里,这传说中的来自西方极乐世界的极为芬芳美丽的花,早已降临人间,和人一样是具有记忆、情爱的高贵生命,和人一样有着坚韧的品性,和人一样有着满怀失望和希冀的情感,成为信念的忠诚守候和执行者。像这一类心灵絮语,在她这本诗集里不时绽放,成一朵朵开在我们心房里惹人怜爱的山花:“都说格桑花大片大片地开放,草原的牛羊就会饥饿,绿草就会衰弱,可我真的无法割舍我的花季,那美丽的八瓣花朵,只是我想呈给你的最完整的花容(蔓琳:《高原格桑花》)”;“随意摘下路边的一朵野花送给你,无需探问缘由。山间的清风,林间的飞鸟,谁又知晓她们来去的方向。就将我的爱别再你的胸襟吧,走这一条通往心灵深处的道路,她是你今生可以一路前行的证明(蔓琳:《写意温江绿道》)”等等,不一而足。我总在想,是什么让蔓琳的目光总能从这些无意识的生命中品出无穷的意味,并把它们珍藏于心中?
在蔓琳的目光里,情感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坚韧和纯粹,这种纯粹逐渐占领她灵魂的制高点。在《浪与沙》中,她得以迸发:
在夕阳下,你是水边涤衣的女子,缳着发髻,伸着玉臂,柔柔缓缓地将水面荡起一层层涟漪。
入夜,风高浪急,你是狂傲的勇士,披肝裂胆将时光一次次击穿”!
至柔至刚,惊世骇俗,诗意澎湃!
我心上的泪珠是你从深海走来的明证,是你遗落于这世界唯一的纪念,我是你心里最柔软的肋骨,是你在风起云涌的惊骇中那一抹不堪回首的痛”。
柔情似水深似海,意蕴绵绵何久长!
在这里,蔓琳通过情感寄托物(“浪”与“沙”),把似水的柔情和奔放的情感有机结合,造就这种掷地有声的爱情宣言。“谁说简单的生命注定平淡?谁说纷繁的经历注定复杂?我在简单中寻得绚烂,在复杂中留得单纯,于是,一沙一天堂的世界中,我看到我全部的梦想,那么绮丽那么缤纷的闪着光亮(蔓琳:《希望》)”或许,正是蔓琳用单纯的眼光去看待梦想,用平凡的感悟来提炼诗情,用简单的心境来容纳纷繁的灵魂,从而把自己的思想提升到了“月质”的境界。“君掌盛无边,刹那含用劫(引自勃莱克的诗)”;“诗的境界是理想境界,是从时间与空间中执着一微点而加以永恒化与普遍化……诗的境界在刹那间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引自《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诚如是,我们就不难在蔓琳的散文诗里,寻到她总能在无意识的生命中悟出无限寓意的根源,这些“微尘”以“诗”的形式进入她的生活和生命,一直涤荡着她的灵魂,让她的魂魄逐渐干净透明,如一轮悬挂天上的月亮,在她心里生长出了洁净的光华。
我也在想,蔓琳精神世界一定和所有的诗人一样,常常充满孤独,在孤独中不断进入充实世界。她在“千山万水的跋涉中,感知岁月的心跳”,倾听“那些低声的吟唱(引自蔓琳散文诗集)”,她在这不断跋涉的情绪空间里,以双足游走四方,以一双慧眼处处发现风景,以诗心不停浅唱低吟。行吟的过程,即为诗意发现的过程,也是寻找自我的过程,赫拉克利特说:“我寻找过自己”,普罗塔哥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说:“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一提”。在人生不断的找寻和发现之旅中,一草一木,一叶一花,一山一水,一缕阳光一滴细雨,一粒黄沙一弯明月,一道茶关一片海水尽入诗心,生长成为具有感知能力和人类情怀的生命个体。它们,和蔓琳的情感撞击出灿烂的火花,再相溶成不可分离的整体,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理想情景,成为蔓琳散文诗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她的文字常常“弥漫着极浓的月光意境,历史纵深和驿站情绪,有很强的穿透力(引自牛放:《洁白的月光》——蔓琳散文诗创作及其散文诗集《穿越河流的月光》窥管)”!很难说,是它们的精魄成就了蔓琳,还是蔓琳赋予了它们灵魂;正如流水之于月光,月光之于流水——究竟是是月光穿越了河流,还是河流长出了月光?还真值得我们仔细回味。
四
如果说,月光和流水还是属于个人感官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话,作为诗者的蔓琳,她的视觉决不会仅仅在个人感官上作永久停留,现实社会很多东西常常会吸引她敏锐的目光。虽然在这部散文诗集里出现得不是很多,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却有着不平凡的代表性。
蔓琳是“单纯”的“幸福”记录者:“在无人的山坡上,听风的声音”,“只需要一块长满花朵的草地,一根线一张纸就可以飞上天空(蔓琳:《城里孩子的幸福》)”;蔓琳是用“生命”“呵护”亲情的执行者:“我的女儿,我用心灵爱着的女儿啊!我承认我是自私的,我给你所有的祝愿,都像生铁浇铸的碑石一样(蔓琳:《致女儿》”;蔓琳是丑恶现象的鞭挞者:“听吧,理想和现实在撞击,他们含糊其辞;友情和金钱在勾兑,他们纠缠不清;灵魂和肉体在推杯换盏,他们达成了协议。”“唉!这黑色的混乱!”“我用一首诗,删除这个邪恶的词语(蔓琳:《冲击》”;蔓琳是弱势群体的同情者:“这世界疯了,上天宠坏了无心的女人,而我,伏在思想的背脊上哭泣。”“下雨了,请将这个狂乱的黑夜洗净(蔓琳:《美丽,被装进笼子》”;蔓琳是永远的自由追随者:“低飞是一种曼妙的舞姿,翱翔更有一种冲云的姿态(蔓琳:《被禁锢的自由》”……凡此种种,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作者的精神世界,使她的写作更具有了强烈的质地感和锋芒。蔓琳通过一些具有时代标志性特征的语言嵌入散文诗写作,用这些语言来触及时代和现实,在时代文本中留下了真切而又微妙、感性而又婉转的痕迹,善莫大焉。
这些文字,常让我感到某种强烈的象征意味,这不在于它们表现出了多么让人称道的才情,不在于它们有多么高深的终极思考,而在于它们为我提供了另一种欣赏作品的角度。这些文字隐藏或暗示着蔓琳的另一种情趣和风格。如果说“水质的写作”和“月质的思想”暗含古典情调的话,那么这些东西所提供的空间感就更为开阔,我们在欣赏作品细腻笔触的同时,常常会有种失重感,因为它们太接近我们生活和时代的质核部分。
五
我注意到,散文诗界的泰斗海梦老师在这部诗集序里这样写:“蔓琳的散文诗文笔朴素优美,语言含蓄精练,形成一种温柔淡远的艺术风格。意境独特,浅出深入,内涵十分丰富,既有阴柔之美,又具阳刚之气,字行里间闪烁着作者的智慧和奇思。”对此,我深以为然。
蔓琳在这部散文诗集后记里说“我不知道这本散文诗集里的作品能够有多少人喜欢,也不知道它有多少文学高度,但是我是用心书写我的故事,用心回望来路,用诗清洁灵魂,可以说问心无愧”。至少,我是喜欢它的,我也相信,认真阅读它的人也会喜欢它的,一定也会有更多的人发现它的价值,“我知道我永远成不了莎士比亚,成不了歌德,但是我宁愿永远不读他们的传世名作,也不愿轻易放弃瞬间灵感而不去写下我易朽的诗句。别人的书再伟大,再卓越,也只是别人生命世界的痕迹。他也许会触发我的生命世界,但只有我才能刻下我生命世界的痕迹(引自周国平《写作》)”。“我的主,我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泰戈尔诗句)”。其实说到底,文字,无非就是写作者自己的心灵产物,是写作者自己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寄托,这是每个写作者最初也是最后的追求。而当这种追求上升到某个高度,能用自己的诗心去影响他人,去净化他人灵魂的时候,作者自己的行吟价值和情感历练也就得到了升华。我总觉得蔓琳在散文诗创作上,心里已生长出明月,笔底自然而然就会氲氤出烟霞。在很短时间内创作出这么多有质地的散文诗,并被人们喜欢和称道,就不足为奇了。
漫游蔓琳在这部散文诗里营造的“水质”和“月质”的诗意世界里,如在她笔底的烟霞中穿行,我是有福的。在这幸福的感召下,我愿把这些文字分享给别人,自己也会无比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