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战时云南文教图景
2012-11-20段福君
○段福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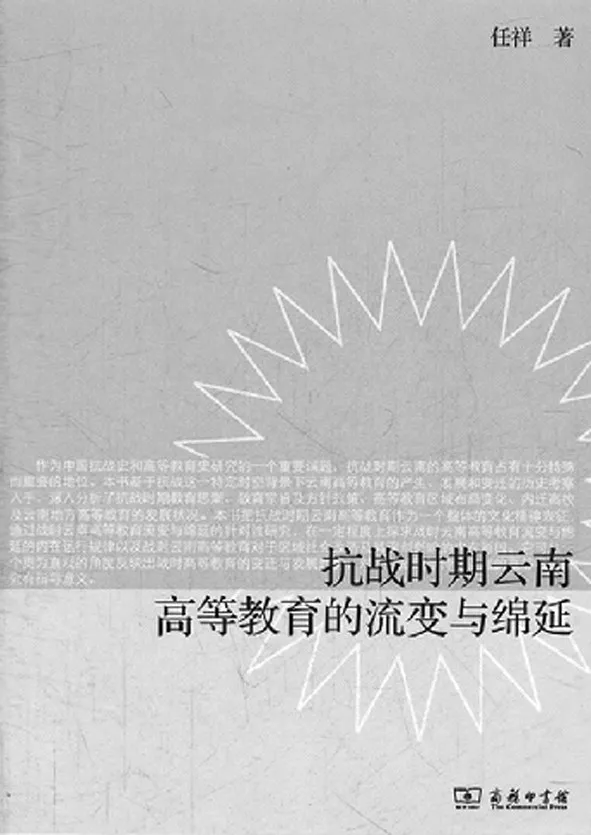
《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任祥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5月版,36.00元。
云南虽有170万年前“元谋猿人”这一人类先祖,有秦汉时期的“古滇国”文明,有唐宋盛世时的拱卫疆土的妙香国“大理”,也有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学术重镇、文化要地、民主堡垒”,亦有今天的“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然而,“交通闭塞、民智未开,荒蛮边夷”仍是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的“云南标签”。在这些与事实有所出入的外界认识中,折射的是云南本土文化,尤其是文教事业被淹没、被掩埋的现实。
今天,提起云南的文教事业,浮入人们脑海的更多是战时的内迁高校,尤其是国立西南联大,而很少有人会想到早在晚清便创立的“云南蚕桑学堂”,以及一度与“黄埔军校”齐名的“陆军讲武堂”,也很少会想到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收录的中国15所著名大学里的东陆大学(云南大学),更很少会想到国立艺专、国立中山大学、私立武昌华昌大学、私立中法大学等其他内迁高校。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内迁高校的光辉掩盖了云南文教的辉煌,而西南联大的光辉又笼罩了内迁高校的辉煌。
人们常说,历史是属于过去,然而梳理和评述历史的人,是属于现在,属于未来的,因为他们能拨开历史的云雾,为我们再现曾经的历史,因为他们可因循史料的经验得失,启示未来的发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云南师范大学任祥所著的《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一书,以详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推论将内迁高校的风采从西南联大的光环笼罩中透射出来,将云南本土文教事业的本真面貌从内迁高校的光环中离析出来,以知识的理性为我们再现云南文教事业的历史图景。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作为边陲的云南,不仅有长期偏安一隅的处世姿态,还有着历久弥坚且璀璨多姿的地域文明,更有从未间断的中华文化延续和中华文明传承;它使我们知道,“学校教育”并非域外文明的独有产物,“睁眼看世界”的近代风潮也曾席卷云南这片广袤的土地;它使我们意识到,抗战后方的民主堡垒并非仅有西南联大的支撑,其后还有无数内迁高校的身影;助推民主的“一二·一运动”,不仅有诸如闻一多的斗士身影,有联大学子的风采,还有南箐中学不屈的脊梁。它使我们关注到,与西南联大一道进步不仅是内迁高校,还有云南本土高等学校生生不息向上的内生发展。
战时云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是一部内迁高校与云南本土高校、云南本土文明以及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史。正如云南省商会联合会、昆明商会《公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归复校序》中所述:“自联合大学南来,集诸科多数之专家,得悠长之岁月,或以修志躬莅其地,或受委精研其事,其已结集成书者既不少成书,其待编行者层出不穷。凡兹所为,均可谓之类通方,开物成务,有关国计民生大者。于是滇之为滇,始一扫阴霾,以真面显示于天下,后者有董事开发之者,其必以为是借镜矣。”可以说,从内迁高校逐步融入云南经济社会开始,就使云南高等教育呈现出接纳性、嵌入性的发展态势,从中小学的师资养成,到高校间的协作发展,云南文教事业的发展无不深深地烙上内迁高校的印记。客观而言,一方面,勤劳的云南人民以自己的无私哺育着内迁高校;另一方面,内迁高校也以知识的教化无声地浸润着云南人民质朴的心灵。与此同时,内迁高校既在竞争中挤占了云南本土文教事业的资源,同时也在协作中促动了本土文教事业的飞跃。战时云南的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精神表征,从某种角度看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然而它对云南开发这一历史功绩,实际上已深刻地体现于中国20世纪战时大学迁变所引发的促进西部落后地区发展的总体特征之中。
“夫然后教育事业之神圣,学术思想之尊严,乃有所丽,而可久维而不蔽。如是熏习而楷模焉,久与俱化,他日士气民风,奂然丕变,溯厥从来,知必有所由矣”。回顾历史,我们很难给战时云南高等教育的那段流金岁月下一个完整的结论。究竟是内迁高校助推了云南的文明进程,还是云南的固有文明成就了内迁高校的辉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内迁高校的到来,云南得以成为战时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民主堡垒,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想得以在此开枝散叶,云南的经济社会、民智民风、社会风尚都得到了更新与进步。在内迁高校的促动和本土文化的自觉下,云南有识之士或奔走于“教育救国、保存民族精神文化血脉”的最前线,或远走异国他乡寻求智识增进,以献身国家和区域事业改造。这期间,云南的高等学校数、中小学校数以及相应各类学校的受教育者人数明显、持续增长;各种进修班、讲习班、培训班、扫盲班、妇女先修班遍地开花;云南籍旅美、旅日、旅法留学生人数急速增长;乡绅宦士捐资助学、出资办学的渐次升温。从龙云统辖的云南省政府到龚自知执掌的教育厅,从登大雅之堂的顾映秋(龙云夫人)到籍籍无名的乡里市侩,从文化学人济济一堂的昆明到民智初开的大山深处,一股“尊师重道、兴文教化”的风气悄然刮起并持续回荡。据作者任祥统计:联大在昆明八年,所培养的8000余名学生近半数留在后方工作,成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支撑;华中大学在大理八年,共培养了300多名滇籍学生,为边疆开发提供了必要的人力支持和技术保证;受内迁高校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1944年初,昆明市工业从业妇女达6296人,占是年妇女总人数的17%,商业妇女从业者达4858人,占是年妇女总人数的13%,交通运输妇女从业者3129人,占是年妇女总人数的9%,公务员妇女从业者2698人,占是年妇女总人数的7%。妇女就业面的扩大、就业率的上升,反映了云南社会对妇女的歧视现象有所改变,也说明妇女摆脱家庭依附关系、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体性意识正在觉醒;从1935—1945年10年间,昆明的公立中学由战前9校63班增加至10校85班,私立中学由2校6班增至19校98班,总体增长近10倍;仅1942年一年,云南籍高等教育受教育在校学生1113人,而从1911—1938年的27年时间里,云南籍毕业生仅为2575人,直接反映出云南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剧增……如上种种,既是云南文教事业发展的缩影,更是战时云南高等教育流变绵延的真实写照。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忘记在历史中的不断自我省思。在内迁高校复员70余年后的今天,云南的文教事业虽然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很难说其还保有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个中原由,值得我们深思!内迁高校对云南文教事业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但透过历史,我们更希望在这种深远的影响中,有一批本土的高等学校,能够支撑起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为云南建成中国西南面向东南亚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提供更为丰富的智力支持,为历史文化的传承与社会文化的繁荣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