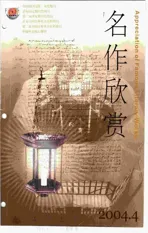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暴风骤雨》:从周立波到蒋樾、段锦川
2012-10-13河北
/ 河北_邢 进
一
那天,朋友邀请我去看纪录片《暴风骤雨》。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是名著,得过斯大林文学奖。被改编的故事影片《暴风骤雨》半个世纪以来也一直被当做经典影片放映着。现在怎么又出来一个纪录片?原来,这是对电影《暴风骤雨》中人物原型的一次采访。听着老人们追忆当年土改时的“暴风骤雨”,你会感到,历史有另一番景象,并不是传说。
这些当年参加元宝村土改的年轻人,如今已是年过八十的老人了。他们谈论往事,并没有因成为电影中的原型兴致勃勃,而是在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中,带我们走近了土改时的真人、真事、真情景。
“韩保长”韩老六,在电影中奸猾、贪婪、凶残的恶霸,是“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但高凤桐老人说,“他是外来户,在这村里干了六年,也是群众选的”,他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给小学生做点校衣”。吕克胜老人说:“韩家有那么三间小草房,高矮有棚。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窗。”谈到当年的地主,不同的被采访人还说: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只能说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东北地广,老实巴交,苦劳苦做的人家,一般人都有几十亩地。就是所谓贫穷人家也有十几亩。只有好吃懒做,二流子,把家底都折腾光了的,不得已给人扛活,才是赤贫。”刘志国老人对地主“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仍记忆深刻。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他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折着棉裤,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在采访中抱怨:“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还有人回忆:“人家到铲地铲得最累的时候,割地割得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他们的回忆,和小说、电影里的地主老财完全两样。

对当年斗地主、分财产的做法,刘福德老人这样看:“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电影《暴风骤雨》的主要演员于洋也接受了采访,他说: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工作队来了,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把他当成积极分子,这种情况也有。”对这样的人,他引用了当地流行的称呼:“二流子”。纪录片中也回放了故事片《暴风骤雨》中的情景,发动者对着一群表情迷惘的听众说:“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十四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一个接一个的诉苦者,越来越激动的表情和动作。最后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当时,许多地主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高凤桐补充道:“咱也不知道后来能枪毙那么多人啊。”“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说完,他陷入沉默。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七百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七十三人。
没收地主和富农财产的热浪掀起,也会危及到一些生活不宽裕的中农家庭。如果有哪个村的“砍挖运动”不彻底,其他村的人也可以去挖,“谁挖归谁”,这被老人们称为“扫堂子运动”。于是,那时候,赶着大车,赶着爬犁半夜去别的村挖浮财,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观。到后来,农村被清扫一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那年冬天,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爬犁”。
这样重现土改,不能不让人深思。
二
这部让人深思的纪录片是怎样拍出来的呢?
原来,地处黑龙江的元宝村要建设“《暴风骤雨》纪念馆”,把这里开发成红色旅游景点,需要拍一部专题资料片。蒋樾、段锦川接受了这项业务,按照纪念馆的意图,完成了正面宣传的影片。但他们在采访过程中有意识地搜集了大量相关素材,于是又按照自己对历史的理解,重新剪辑了这部反思精神贯穿始终的独立纪录片。
蒋樾是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重要人物,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文学编剧专业,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跟随黄建中拍摄过故事片《龙年警官》《过年》。受吴文光、小川绅介的纪录片启发,开始关注身边的现实生活,拍摄了纪录片《彼岸》《静止的河》《幸福生活》等。1995年,他参加了《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团队,“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拍摄了《东方三侠》《票友》《上班》《矿工》等短片,开创了国内电视纪录短片的新模式。1998年他和段锦川、康建宁组建了“年年三畅影像工作室”,专事纪录片拍摄。他们制作的《大国崛起》《我们的土地》《法门寺》《大秦岭》《公司的力量》等在央视播放,都引起较大反响。独立制作的纪录片作品《幸福生活》《拎起大舌头》《当兵》亦进入国外市场。蒋樾说,为电视台拍片子,是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
段锦川也是纪录片领域的著名导演,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在西藏电视台工作多年,曾自己执导或与他人合作《青稞》《青朴——苦修者的圣地》《广场》《八廓南街16号》《天边》《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等作品,多次获国际奖项。他说,真正认识到纪录片的本质是在1993年去日本山形电影节看了怀斯曼的作品之后。他还说,和张元拍《广场》时找到一种“直接电影”的方法,其理念核心就是创作者就是旁观者,像墙上的苍蝇一样,在那儿不动声色,尽可能地不干预拍摄对象。
段锦川说:“新纪录片”在中国出现至今已有十多年了,但观众仍有一个误读,似乎“新纪录片”与过去的“宣传片”的最大区别就是把关注的焦点从大而无当的概念或者英雄人物转移到普通平民,甚至是弱势群体、边缘人群。实际上,这只是关注对象的转变,而不是“新纪录片”的实质。作为一个纪录片作者,我的看法是,“新纪录片”的出现,只有一个核心的、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讲真话,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事实的真相。
那几年,蒋樾一直在东北农村行走,熟悉当地的生活,为自己的片子寻找拍摄点,找到元宝村,是一次机会,也是一种眼光。元宝村就是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里的元宝屯。这个村现在是东北有名的亿元村。走进村子,蒋樾发现村里老人的故事很精彩,五个亲历过土改的八十多岁的老人对那段历史在心里保留得很完整。许多的历史痕迹将会随着亲历者的消失而追寻不到了,他必须抓紧时间。《暴风骤雨》用了十天的时间拍摄完毕。
蒋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漫画家丁聪在临死前不久接受了《南方周末》的采访。丁聪在沉吟片刻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画漫画有个屁用。’当我看到这句话时,我突然就悟出丁聪的那份心情。这句话充分代表了他对自己漫画生涯的觉悟。我也想引用他那句话,‘拍纪录片有个屁用’,但是对于我来说,即使它是个屁,我也觉得它有它的作用。”
三
实际上,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三个元宝屯土改。一个是当地农民感受和记忆的土改,一个是周立波讲述的土改,一个是蒋樾、段锦川再现的土改。哪个更重要,哪个更可信,这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的确,周立波不但是历史的再现者,也是历史的当事人。他是实践土改在前,讲述土改在后。1946年冬,他来元宝屯发动土地改革运动时,已经是有着十多年党龄的革命干部。暴力土改不是元宝屯的孤立现象,几乎普遍存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早在左联时期,周立波就翻译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心仪苏联的土改实践。他是湖南人,对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相当熟悉的。当时在东北进行的土改,党有一整套方针、政策、方法。作为老共产党员的周立波,不但在理论上真诚地信仰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方法,在行动上也坚决实践党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在实践中,如果农民跟不上这些理念,他会归结为农民觉悟太低。在创作中,如果生活原型跟不上这些理念,他就自觉地运用典型化方式来弥补。他的《暴风骤雨》就这样建构起来,成为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样板。
蒋樾、段锦川走进元宝村时,虽然与当年的周立波年龄相仿,但时间已跨越了五十多年。重要的是,他们的知识背景与周立波大为不同。资料表明,他们不但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暴力土改,同时也很关注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和平主义乡村建设,台湾的和平土改可能也在他们的视野之中。有了这些参照,他们就有了不同于周立波的观念框架,产生了重新寻找元宝屯农民对土改的真实感受的心理动力。
如果回归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就应当承认当地农民对土改的感受是第一位的,外来的作家、导演的看法是第二位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地农民感受和记忆的土改和蒋樾、段锦川再现的土改达到了一致,他们比周立波更加接近历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