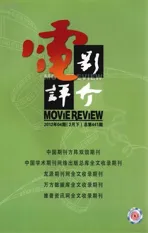冷漠与温情: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迷失之物》中的艺术真实
2012-09-28曹汝平
在历届奥斯卡获奖动画短片中,部分影片以刻画人性之美丑见长,如《平衡》(1989)、《老人与海》(1999)、《回忆积木小屋》(2008),获第83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的《迷失之物》(The Lost Thing,2011)也不例外。这部来源于作者少年时代生活体验的动画短片,其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与“善”和“美”共生的现实性主题,其实就是以虚拟性的“艺术真实”向观众讲述一个存在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情感历程故事。

图片来源:第83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迷失之物》视频截图
一、以动画艺术来表现冷漠的现实主题
《迷失之物》根据陈志勇(Shaun Tan)的同名绘本改编而来,讲述的是“在很多个夏天以前”发生的故事:还是个少年的主人公喜欢搜集瓶盖,有一天在沙滩上发现了一个没人愿意理睬的“东西”,一个表情悲伤而迷茫的奇怪生命体。虽然这个“无名物体”生性友善、好奇、胆小且又顽性十足,但是没有人“留意”它,更少有人愿意帮助它,就连主人公的父母也不能接纳它。在另外一个奇怪生物的指引下,主人公终于把“迷失之物”送到了属于它们自己的乌有之乡。
很明显,这部动画短片反映出人在成长过程中,由于世事的繁复与忙碌,导致原本友善、童真的自然本性日益消褪,对周围的事物已不再有新奇感,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亦趋于冷漠,甚至是隔阂。应该说,采用动画艺术来表现这样令人压抑的现实主题,的确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因为动画向来以幽默与欢乐为自身的艺术特征,因此欲在动画影片中添加真实的伤痛环节,实属不易,更别说将影片的情感基调定位在忧郁、低沉和冷漠等这些“不太愉悦”的主题之上了。在这里,陈志勇等创作者们是想尝试一种带有悖论基调的风格:“虚拟”中的真情实感。他们要以批判的态度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冷漠,同时对人性的复杂性给予反省,并期待短片能够唤醒现代社会迷失已久的良知与温情。
细软的沙滩上,有人躺着享受日光浴,有人在翻看报纸,有些人则扎堆聊天,当然也有人在四处拾掇垃圾,而正在兴致勃勃收集瓶盖的“我”发现了坐在沙滩上“无所事事”的“那个东西”——一个砖红色的大“玩具”。由短片中呈现的沙滩景象,我们便走进了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人性场域。与正“忙着别的事”的人们形成对比,处于一个隔膜的现实世界之中的迷失之物没有“迷失”自我,“我”的一句“HELLO”,便立即唤醒了它昏睡已久的心灵,让它重新恢复了往昔的活力,从庞大而怪异的身躯中迸发出的那个调皮劲儿,让人在顷刻间就喜欢上了这个“被人遗忘”的“东西”。没有比这个更让人怜爱的东西了。“这个东西”表面看起来是想远离人群,但实际上正观望着人群,虽然处在喧嚣而冷漠的社会里,但却在等待着温暖的阳光。“我”给了迷失之物无私而真诚的帮助。这种帮助,按照大机器工业社会的法则,其实是不应给予“流浪者”的,因为他们的迷失或许是竞争失败,或许是因为懒惰、不安分守己、老弱病残等因素造成的,但主人公还是伸出了援手。现在看来,迷失的不是这个“东西”自身,迷失的是人的友爱之情和怜悯之心,人与机械的结合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象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同情反倒成为一种可遇不可求的东西。这种互为本末的现实说明,人的孤独与冷漠,即是现代人类文明酿就的苦果,也是人越来越忧郁的主因。
但是,在与这个东西玩耍的过程中,“我不知为何觉得有些不对劲”。乍看起来,“不对劲”的原因似乎是“不大可能会有人带着这东西回家”,不过,从短片给出的情形看,真正的原因应该来自“我”周围的环境。当大喇叭响起时,穿着印有编号制服的人们像听到了“收工”的命令,收起遮阳伞,关掉机器,拔起插在沙子里的人造海鸥,然后纷纷离开了沙滩,原本热闹的景象只不过是一场有计划的“伪装”。显然,这里的沙滩和人已经成为一种工业社会的象征,个体的人已不再需要很多属于自己的色彩,他们只是资本社会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在面对一个关乎其他人的前途命运的时刻,他们无需做出努力或选择——制度和规则已经安排妥了每一个生命体的归宿。尽管这个社会还有善良与同情的成分,“我”和这个“迷失了”的东西之所以玩得“非常开心”,就是因为有“真心”的介入,很多时候,个人的能力和美好的愿望无法平衡这个世界,金钱才是命运的领导者和主宰者。在这个机器轰鸣的环境中,“迷失之物”拥有人的童心,但它同时拥有孤独和悲伤,“我”也是一样。并且“我”还生活在一个充满成见和老于世故的家庭里,母亲嫌弃迷失之物的脏,父亲则担心它会带来“各种奇怪的疾病”,“他们俩只想让我把它带回当初发现它的地方”去。正在成长中的“我”不可能不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潜意识里已经滋生出一点社会习气与偏见,虽然这还不足以让“我”丧失“真心”,但也成为“不对劲”的原因之一。
让人倍感冷漠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来自于联邦什物部门。当“我”正在为如何处理这个东西而“进退两难”的时候,电视上播放的联邦什物部门服务广告让“我”决定把它送到那里去。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这个社会公职部门应该是一个公益性的收容与养护场所。如果顺利的话,迷失之物将得到庇护而不再“迷失”,它因此也可以获得世界的合理性存在,与人们的正常沟通才成为可能。可是,一个让人几乎窒息的“没有窗户的灰色大楼”摆在我们面前,黑魆魆的大楼里面还充斥着“消毒剂的味道”,生性胆小的这个东西虽然亦步亦趋的跟着“我”,但仍然被一路泯灭的小灯所制造的黑暗吓得够呛。在长长的过道尽头,随着最后一个小灯的熄灭,一盏刺眼的聚光灯在我们的头顶上亮起。站在高高的柜台下,“我”和这个仍然迷失的东西显得是如此的渺小,以至于“我”仰起头说话时,只能看到接待员的头和手!高高在上的接待员面无表情的拖长语调说了句“填好表格”之后转身就走了,等“我”双手接过厚厚一摞表格时,头顶上的聚光灯也被关闭了,只留下在黑暗中寻找桌子准备填表格的“我们”。阵阵冷风吹走几张可有可无的表格,“迷失之物”的情绪也跌落到了冰点。社会服务广告的欺骗性让人心痛,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所处的真实情境!如果说“痛并快乐着”表明人还有希望的话,这里的“痛”已经让人没有了目标感,这是一种彻底透心凉的痛。正如法国剧场人阿尔托(Artaud)所说,神话故事“不是个人的,而是超越的,目的不是娱乐,而是表现一个民族心理、文化中最实在、最急切的真实。”[1]《迷失之物》也是如此,其中的无助和冷漠构成了今天人类社会真实的存在样式,并存在于“一切向钱看”的意识之中,时时绞割着尚存良知的人,也正因为如此,社会才有了分裂感和不完整性。影片中的社会公职部门反而成了“遗忘与抛弃之地”,这正是《迷失之物》的现实性批判之所在。
二、冷漠的机器世界掩盖不了真诚之心
《迷失之物》也为观众塑造了一个奇怪的机械世界:灰色的大街小巷和房子里到处都是锈迹斑斑的金属管道、仪表、电线,以及各式各样的烟囱、路标、红绿灯、告示牌;行驶在铁轨上的电车车顶上还装有蒸汽机式的排气管;甚至连大街上的人也是机械式的冰冷面孔与姿态,能拒人千里之外。“迷失之物”自然也是一个奇怪的合成物,它巨大的壶状金属外壳里除了柔软而灵活的触手与触脚外,还包裹有金属齿轮、风扇、仪表等一套蒸汽机装置。不过,迷失之物纯正的砖红色外表让它与影片中灰蒙蒙的城市“格格不入”——故事的伏笔正是通过这一抹亮色被巧妙地穿插进来——冷漠的机器世界掩盖不了真诚之心。
在向一些人询问无果后,“我带着这迷失的东西去了皮特家”。他向“我们”伸出了热情之手。皮特开门见到“我”时的微笑让人颇感慰藉,他本人也是影片中最“真实”的人物,有自己的信念和想法,爱探究未知的事物,理性中带有一点迂腐。皮特搬出参考书和各种实验仪器,想“通过细心观察,精准的测量,以及良好控制的实验”来“辨认”这个东西是什么。很遗憾,皮特终究没有搞清楚“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他的实证方法失败了。问题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但皮特一如既往的和“我”坐在他家的屋顶上喝咖啡聊天,而迷失之物则站在屋顶上兴奋地观望着这个城市。身在“高处”,“我”和皮特的友谊因此不会“迷失”。人要掌握这世界,也应该有相互间的真诚帮助与理解作为一种维度,这样的人类世界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真切的家园,才能以本来的面目无拘无束、毫无遮掩地交流,并快乐的生活。
回到家里,因为父母不能接受“这个东西”,“我”不得不“把它藏在后面的小屋里”。“不能就把它丢到大街上晃悠”是“我”对迷失之物最真诚的态度,这里面没有掺杂任何人世间的虚伪,一方面,“我”只是出于一个青少年朦胧的责任感而坚持着这样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有着令人难忘的可爱劲儿,顽皮与懂事远远胜过了它怪异的外表,这种可爱劲儿来自于创作者细腻的刻画。比如“我”和父母还有“这个东西”一起看电视,屋外火车经过时的震动让墙上的镜框歪斜了,这个东西轻轻地将它扶正;它又对台灯很感兴趣,观察了一会儿后伸“手”去碰灯罩,结果让灯罩歪斜着掉了下来,自己也吓了一跳。在这里,创作者将细节安排得流畅而有起伏,自然之中的过渡是那样的巧妙而不突兀,不落窠臼又有个性,而且在性格描写中又有一种活泼与幽默,但幽默一定不是那种有意的逗笑,而是“这个东西”的本性。这种本性不是任何人都能具备的,它来自一种心无隔阂的真诚。与之相应,“我”的坚持就显得顺其自然,因为迷失之物是那么的单纯与天真无邪,而“我”不懂得去远离肮脏的东西,不懂嫌弃,不会势利,在这个东西的眼里,“我”是一个可以信任和依赖的朋友,这个朋友不会抛弃它,他会义无反顾地帮助自己寻找那一片乐土。因此,还是少年的“我”和迷失之物的故事,就让影片集“真、善、美”于一身,在不知不觉中让人体会到了影片纯真的魅力。
还是在联邦什物部门,虽然“我们”受到了冷遇,但却意外得到了一个奇怪生物的帮助。这是个带着平顶帽、长着一条蛇形尾巴和两条触手的生物,是联邦什物部门的清洁工。它给“我”一张印有“路标”的小卡片,在离开的时候,这个奇怪的清洁工重复着前面说过的话:“你不应该把它留在这。”语气中带着些许的责备,很显然,清洁工在直白地告诫“我”,这里不是广告所说的能够解决“困扰”和“麻烦”的地方,“如果你真的在乎那东西”,就应该按照这张路标去寻找真正属于“它”的地方。看来清洁工常年在此工作,对那些被送到这里的迷失之物深感同情,因此在影片中扮演着向导的角色,并一次次揭露了人的冷漠与自私行径。在轻声细语中,清洁工展示出它的真诚与不惑,这使得它在短片中显得分外醒目,成为平衡这个世界的重要角色。而且这个几乎看不见头的奇怪生物还充满了绝妙的反讽意味:有头有脑的人类对迷失之物一脸冷漠,更不愿知道它从哪里来;看似“无头”的怪物却心明眼亮,真诚的给“我们”指明了寻找的方向。
最终,在走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后,“我”将这个迷失之物送回了属于它的乌托邦,在这一时刻,“我们”相视而笑,心灵在瞬间都获得了解放。短片最后体现出地这种真诚之心成为故事的灵魂,它建构起整个影片的情感,这就是故事“迷失”后“回归”的主题。影片以超乎寻常的想象力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梦幻般的乐土:明媚的阳光,玩耍嬉戏并互相打招呼的大大小小的“玩具”,它们自由而欢畅,它们抛弃了人类的虚伪,纯真与帮助成为一种默契。这片乐土也是一种象征,一个与人性并存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比人类世界可爱多了。生活在其中的“东西”是那样地接近人性的真诚,善良与同情的心灵被开启,然后自由地飞翔,任由飞翔的天空没有边界,即使迷失了,也要不停歇地寻找,坚持与真诚成为这个世界的情感主线。人们在这样的情感中获得了真实感,并由此可能成为那些“迷失”的东西获得拯救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三、回忆中的虚拟性真实
动画艺术的真实还需要通过可知可见的视像表现出来。相对而言,这些视像的虚拟性真实,比超现实主义绘画中的梦呓、电影文艺片中的假定性,显得更真实可信,因为动画艺术能够把有机或无机的对象变成知觉意识中的人类世界,因此动画中的虚拟,既是表现有个性特点的具体而个别的角色,在性格描写和个性揭示中,又必须和必然地要反映出现实生活的真情实感。《迷失之物》以第一称“我”的回忆为基础,这就给予了影片强烈的真实感,并且其中的“真实”又遵循着动画本身的艺术逻辑,以“虚拟性”的表现方式为人们呈现出人世间真实的冷与暖。
《迷失之物》中的虚拟性真实,首先是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这就摆脱了时间与空间概念的桎梏,扩展了动画艺术中可见情境的范围,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满幻想的无距离的世界。这样的“虚拟”世界无形中延展了人们的精神空间,使我们能够对真实的生活做更深层次的理解,虚拟性因而可以成为继时间之后艺术中的“第五维坐标轴”,它也因此成就了动画艺术中超乎想象的灵活性。《迷失之物》中就频繁地运用了第五维坐标轴:无处不在的管道加深了观众对影片背景的印象;红绿灯只是城市的标记物,并没有实际功能;庞大的迷失之物能够进出只有小门的房子,而且还能与“我们”一起“爬”上皮特家的尖屋顶;看不见头的奇怪生物已经让人诧异,它居然还能指引“我们”去寻找那片乐土。由于所表现的“迷失之物”具有知觉上梦幻般的想象性,由于影片具有观众所需要的生活原型,以及由于具有直接表现自然形态随意变化的技术可能性,因此便有了处理并实现这种形态变化的第五维坐标轴,即虚拟性的存在。这就为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们心中的梦想、接近现实生活中实在的矛盾与冲突提供了可能。这是虚拟性带来的好处。因此可以说,具有第五维坐标轴性质的虚拟性是动画艺术最好的同盟者。
其次,相框式的背景为“我”的回忆提供了“真实”的依据,也为虚拟性的表现带来蒙太奇式的便利。短片极力还原了绘本的视觉效果,将其中印有电力学和机械学图案的背景转换为短片中的相框,新颖而别致。这些手工制作的相框不时出现,既奠定了短片的叙事风格与情感基调,也串联起“我”记忆中的往事,同时还让人们能够从“第一人称”的感官知觉到发生的一切,从而获得直接而理想的真实性。相框所诉求的这种内在的独特的视像感,是短片中所有要素和内在的超逻辑的叙事结构的综合显现。当“相框”这一虚拟的视像进入影片的蒙太奇结构之中,并成为具有特殊构成性的叙事要素时,它本身就已经成为既是表现的客体,又是表现的主体,还成为一种表现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这种虚拟的视像元素使观众与短片所营造的“虚拟实境”巧妙地联动起来,让观众产生了创造性的想象力。可以想象,如果是以生活本身为故事蓝本出现在观众的知觉中的,那么,不管是创作者还是观众,都希望这种为了真实而虚拟的表现手段多多益善。
最后,有意做旧的材质与贴图效果让短片浸染着浓厚的历史感,“回忆”的色彩很浓厚。墙体斑驳,管道等金属物锈迹斑斑,书籍和电视也是陈旧的,就连生活在乐土中的形形色色的“玩具”都是如此。从时间维度看,这样的处理是还原历史真面貌的需要,是同环境、精神和审美心理紧密联系的,烙印出时代痕迹;最关键的是,“由历史性所带来的确定性是实在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确定性,就没有人类文化的根基,就没有现实性的力量和普遍性的法则”[2]。当然,《迷失之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有历史感的艺术载体,材质与贴图还发挥出重要的情境揭示和隐喻功能。如短片中的标记贴图,除了联邦什物部门的清洁工给的那张“看起来无足轻重”的路标外,其实其它众多的指示标记实际上没有一个能够指示方向,在“我们”走出联邦什物部门的大楼后,影片甚至直接贴出“SIGN NOT IN USE”的字样,这样的贴图设定显然增强了“迷失”的主题性意味。如此来说,恰当的材质与贴图设定应该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创造性,如能通过这样的设计激发人们对生活本质的思考,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就是艺术的真实。
结语
综上所述,在叙事主题与艺术的现实性批判方面,《迷失之物》客观而冷静地讲述了“迷失”的东西“回归”家园的故事。从前文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影片中的“迷失之物”实际上象征着现代工业社会的人们在成长过程中那颗趋于迷失的心灵,孟子的“人性本善”论在这部短片中再一次得到了精彩的演绎。创作者不仅赋予世界不同的象征寓意,把人性中的善与恶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赋予短片以“心灵拯救”的人文内涵,使这一简短的动画影片充满了“走出埃及”般的宗教意味。作为动画艺术中的佼佼者,在视像表达与符号指向方面,《迷失之物》也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期待,为人们营造出具有显著时代性的“真实”的视觉艺术样式,并为“迷失”与“回归”的主题呈现塑造出充满温情的真实情境。这些成就让我们知道,动画也能从人性角度更好地表述艺术的真实,这就是短片的艺术魅力所在。
注释
[1]刘俐.在焱焱柴堆中呼救——阿尔托和他的《残酷剧场》[EB/OL].广西话剧团.http://www.gxhjt.com/gxhjt/sys/html/2009/1/128.htm,2011年9月访问.
[2]黄其洪.德里达论艺术[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7:55.
[1]《迷失之物》官方网站,www.thelostthing.com.2011-7访问
[2](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M](2版).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3](美)S.普林斯.真实的谎言:感觉上的真实性、数字成像与电影理论[J].世界电影.1997(1):209-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