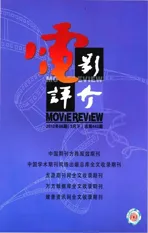农村留守儿童的等待:电影《小等》的思考
2012-09-28贺祝平
根据贵州青年女作家肖勤创作的小说《暖》改编,由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朱一民执导的数字电影《小等》,正在进行后期制作,预计6月初即将上映。这是由贵州省文联、湄潭县委宣传部、秦皇岛汇中承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贵州省电影家协会、北京雨墨春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贵州省第一部反映农村留守儿童题材的电影。
电影《小等》故事讲述了一个孤独却坚强的留守儿童、十岁的山村女孩小等与年迈患着怪诞病症的奶奶相依为命的故事。小等的父母为偷生男孩而外出打工,小等和奶奶独自留在山村。小等在家不仅要照顾奶奶,还要支撑起一个家的活计。在农村,有许多很小就肩负起家庭劳作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农村去外地打工,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六年……
不能忽略的社会现状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用勤劳获取家庭收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但却把孩子留在了农村家里,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这些本应是父母掌上明珠的儿童集中起来便成了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
2011年4月28 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发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在全国人口中,0-14岁的人口2.27亿[1]。根据权威调查,中国农村目前“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5800万人。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据调查显示,父母外出打工后,与留守儿童聚少离多,沟通少,远远达不到其作为监护人的角色要求,由于监护不力,九年义务教育难以保证,而占绝对大比例的隔代教育又有诸多不尽人意处,这种状况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亲情饥渴”,他们缺乏抚慰,身心健康令人担忧,疏于照顾,他们的人身安全不容忽视,由此导致他们的心理、性格等方面出现偏差,学习受到影响,社会给予他们的关爱不足问题
电影《小等》主人公“小等”名字是父母为了续香火加在她身上的符号。也因为续香火,父母走了,丢下小等与奶奶相依为命,不到10岁的小等没有等来弟弟,等来的却是爸爸的死和母爱的沦丧,等来的是过早的为生计奔命,等来的是奶奶因患“怪诞病”而“静静睡去”,等来的是自己险些毁灭。
小等是现实生活中留守儿童的一个典型,不乏留守儿童共同的境遇。

肖勤与小说《暖》
肖勤一反当下乡村留守儿童题材小说的传统叙述方式,打破从一个“病孩子”入手的“潜规则”,塑造了一个聪颖、懂事、早熟的好孩子。文笔细腻,语言质朴、发人深思,该小说获第二届“茅台杯”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创作小说《暖》的时候,肖勤还是贵州省湄潭县的一位乡长女作家,她用不一样的方式领导和关怀着乡村以及乡村的命运。她工作在基层,“三关”工作是她到乡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关爱留守儿童、关心外出务工人员、关怀空巢老人。她的作品尤其关注老人、儿童和妇女等弱势人群。在小说《暖》中,出色地表现了偏僻山乡生存的艰辛和人性的尊严。这不能不令人惊异和称赏,这与她的长期深入底层有关,与她的艺术天赋有关。可以说,正是现实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忧思,为肖勤的创作提供了灵感与素材,而她的小说也以艺术化与典型化的方式,引起了更多人对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
拍摄电影的初衷
随着打工族的增多,“三关”工作成为农村工作一项重要内容——关爱留守儿童、关心外出务工人员、关怀空巢老人。这三类人员名单,一年年总在增加。走进村寨,田野显得那么空落,偶尔听到一声劳作后的咳嗽,那声音也是空洞而年迈的。青年们都离开了,农村的肋骨被抽走,只留下虚弱的老人和孩子,在孤独中无力地彼此支撑、无助地彼此温暖。
对于这些老人和孩子来说,他们真正缺乏的是爱与关照,但是“三关”工作能给予的只能是极少的温度,因为真正的温暖,是油盐酱醋琐琐碎碎到极至与分秒的参与,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关照与搀扶。旁人只能走进、走近,却不能融入、停驻。
电影中的庆生老师对周幺爷这样说道:“小等这孩子太可怜啊!她父亲躲计划生育客死他乡,妈妈又在南方打工不回。奶奶常年害怪病。屋里的事都压在她一个小姑娘身上。白天一个人在田里、土里苦巴苦做,晚来还睡不上一个安神觉。10岁的姑娘,正是要拱在娘怀里耍娇的,可是小等,连个讲话的人都没得,她孤独啊!就是狗也要钻个热乎窝,小等她也要有人疼她啊!”
而主人公小等发自肺腑的呼叫:“不!我不要当大姑娘!我不要长大!因为长大了就没人疼,没人要!长大了就要当家!小等不要长大,不要当大姑娘。小等就要当小等。小等要妈妈,要奶奶,要睡觉!要像同村的小朋友们一样,上学读书!可是,谁都说我长大了,什么都推给我做,我做不了。我害怕!庆生叔,我,我不要长大!……”
剧本中这两段台词,就是拍摄电影的初衷!
电影《小等》不是一部商业片,是一部呼唤爱心的的艺术片,它展示出了政府提倡的“三关行动”“关心农民工,关爱留守儿,关怀留守老人”,为此唤醒广大群众的爱心。其主旨在于:从更深层次去思考三农问题,怎样让农民守着家门致富,不用抛家弃子;让更多的人关心和关爱留守女童这一特殊群体。因为,事实上,在当下的农村,留守女童的心理健康和安全已经到了必须关注的时候!
敬业的摄制组
该影片全部镜头都在湄潭县天成乡李家堰、兴隆镇天平村等农村拍摄,正值2011年的盛夏,剧组同志们白天顶着烈日战高温斗酷暑,晒掉一层皮“坚守阵地”,夜晚忍着蚊虫叮咬拍夜戏,浑身上下起脓包坚持“轻伤不下火线”。每一天的拍摄都有感人的故事,每一个镜头都饱含大家的辛苦和奉献。最值得敬佩的是一老一小:年过6旬的导演朱一民和未满10岁的演员郭春艳(小等扮演者)。


朱一民是一位艺术造诣精湛、创作态度非常认真的导演,获过无数国家级电影、电视剧奖项的他却没有轻视这么一部儿童影片,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投入艺术创作,仍然是用“出精品”的态度投入影片拍摄。从一开始的小演员培训,到剧组班子的组建,以及摄影机器设备的挑选,每一步都亲自操作,绝不马虎。到了拍摄现场,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旺盛的精力、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敏锐的头脑。在拍摄过程中,他对每一个镜头都严格要求,严格把关。朱导演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全剧组,也凝聚了大家的艺术创造力,大家合力将影片每一个镜头按照高质量完成。
小等扮演者郭春艳是在贵阳地区近400名9—12岁的女孩中筛选出来的,经过4轮的筛选与培训,未满10岁的小女孩郭春艳脱颖而出,战胜了所有的女孩,在片中担任女一号小等。最巧的郭春艳就是农民工的女儿,是一名山村的留守儿童,他的父母为了生计长期在重庆、贵阳打工,她是农村的外公外婆一手带大。角色确定之后,导演及工作人员们才知道郭春艳就是农民工的女儿,这正是本片所需要的。从未进行过艺术培养的郭春艳幸运地得到这个角色,她自己告诉导演,说她在试演前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扮演了这个角色,没想到真的能梦想成真。
毕竟小春艳还是个孩子,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真正到现场拍摄,还是需要指导和帮助,但是小小年纪的春艳非常敬业,电影中有很多顶着太阳在三十多度高温下拍摄的镜头,田间地头,厨房猪圈,摘了辣椒掰玉米,做了饭菜剁猪食,一遍又一遍,一条又一条。许多成人都无法坚持,可是小春艳却极其认真完成了拍摄,大家开玩笑称她为“小能干婆、小麻利”。
最感人的是拍摄夜雨的戏,立秋后的晚上,气温骤降,剧组拍摄“小等奶奶死后的戏”。小等的奶奶死了,无助的她在庆生老师拒绝后,无望地在山里河边奔跑,最后到了压桥石边,看到因雷击倒在岩石旁纵横交错的电线时,误认为是电话线,为了能听到妈妈的声音,伸出双手要把断掉的电线接起来,被赶来的庆生老师推开,而庆生老师却因触电倒地——这场戏需要在“狂风骤雨”中完成。小春艳被雨浇得直发抖,大家真怕她瘦小的身体扛不住,最终,导演提出停下拍摄,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寒冷中静静地等候着,等她上车暖和后再继续开工,在这样的情况下,小春艳依旧坚持完成了拍摄。
年近80岁的宋可兼老师扮演小等的奶奶,精彩的表演和顽强的精神给剧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等的奶奶由于身患特殊的病,白天昏睡不起,晚上舞刀捉鬼,这样的角色给演员创作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可是宋老师从未耽误一点拍摄。活跃在贵阳舞台上的卜小贵老师又一次触电,扮演留守村委会主任周幺爷,在镜头前不适应中进行调整,最后一场在村委会坝子上耍枪弄棒中完成了角色创造。扮演影片中男一号庆生老师的演员杨斌,毕业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表演专业,这是他三十而立之年第一部主演的作品,并且经过四次竞选最终获得的角色,所扮演的庆生老师得到全剧组的认可。
电影人的思考
电影《小等》没有扣人心弦的紧张悬念,没有大起大落的情感波澜,没有城市的灯红酒绿,没有世俗的喧嚣繁华,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有的只是绵延的大山,弯曲的山路,简陋的木屋;有的是沉甸的生活,写实的风格,简单的剧情,不复杂的人物关系,朴实的表演;有的是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现状的思考,有的是对农村留守女童的心理健康和安全的关注,这些留守儿童在翘首等待,等待父母早日回来团聚一堂,等待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等待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幸福快乐。
希望电影《小等》能引起人们的思考,希望留守女童小等的命运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希望关心留守儿童的朋友们都来为他们做一点贡献,让他们真的能有人守,有人爱、有人疼,能和其他孩子一样有一个欢乐的童年!
参考资料
[1]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来源:统计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