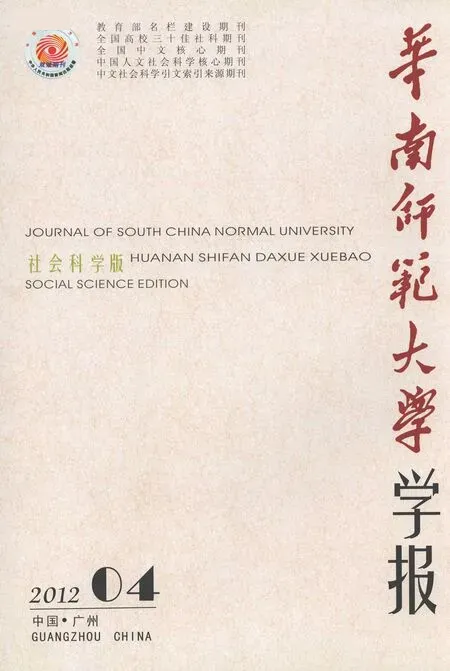唐代虐婢故事的宗教观念发展与女性声音发露
2012-09-11谢健
谢健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中国香港)
唐代虐婢故事的宗教观念发展与女性声音发露
谢健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中国香港)
唐代虐婢故事中的宗教观念经历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婢女强魂难抑,执意对施虐者索命,体现出中古时期的厉鬼信仰。这些亡婢魂魄在他界喊出了女性的声音,这样的女性声音在南北朝时期遭到佛教救赎的消解后一度处于失语的境地。入唐以后虐婢故事极力否定了佛教的救赎功能,很大程度受了统治阶级在民间层面大肆打击佛教的影响。与此同时,超越一切宗教救赎的主宰“上帝”在虐婢故事中出现。“上帝”的出现首先与唐代郊祀仪式之争中昊天上帝成为主神有关;另一方面,“上帝”出现使得亡魂索报否定佛教向施虐者索命有了合法的理由。女性声音是妇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中国历史中,与女性有关的材料为数不多,若有女性自身之声音已属可贵,但是女性声音也并非尽然是心声之流露,这为妇女史的研究带来了限制。唐代虐婢故事是女性声音在他界发露的一个例子,女性本有的发声诉求经历了短暂的失语过程后,却发出了更加响亮的声音,这只能在他界的层面上得到释放。
唐代 虐婢故事 宗教观念 女性声音
一、引 言
妇女史是新史学洪流中的一个支流。①“新史学”学派始于法国年鉴学派于1929年创刊之《经济及社会史年鉴》为阵地,后遂成欧美史学之主流。哥特布鲁(Gertude Himmelfarb)认为,新史学的关注点在于社会史、心态史,与传统史学对政治制度史和思想史的关注大相径庭。新史学对历史中的寻常人寻常事更为感兴趣,排斥宏大叙事,以事件为单元细微关注历史的“深层结构”。[1]在新史学思潮下展开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多集中于明清、民初等近古、近代时段[2],盖因为这些时段资料较为丰富,亦处于社会转折期,西方思潮逐渐渗入,女性境况亦较前有所不同,故而最能吸引学者的注意。上古妇女研究虽然也面临着传世文献不足的局面,但出土文献的增多,也为上古妇女史研究带来新气象。中古妇女研究似乎一直处于较为尴尬的局面。唐代是中古时期的重要朝代,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鼎盛使得这个时期的女性面临的环境较为宽松。对唐代妇女之研究也多从法律、家庭等角度切入;②郑显文《律令制下的唐代妇女法律地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认为唐代妇女法律地位较为低下,政治上无参与国家管理和接受教育之权利;经济上无受田资格,财产继承和交易受法律限制;生活中无婚姻自主权及离婚权;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梁敏的《从(唐律)规定性及社会实践看唐代妇女地位》(《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则从婚姻礼制、法定夫妻关系、财产继承权、“婢女”四个方面着手研究,认为唐代女性现实地位较高,与低下之法律地位形成对比。对唐代女性社会地位之探讨成果还有陈丽、门珥然《唐代上层社会妇女婚姻地位探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等。对唐代妇女社会生活也有学者进行研究,③勾利军、吴淑娟《略论唐代妇女的经商活动》(《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认为唐代妇女在社会中占据一定的经济地位,但不是主要地位。周平远、何世剑《唐代诗词视野中的妇女文化观》(《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指出唐代文教普及和社会风气开放为妇女参文化活动提供了平台。此外有焦杰《从墓志看唐代妇女崇道的原因》(《东南文化》2008年第3期)等研究成果。大多认为唐代妇女之社会地位相比前朝有所提升,社会活动之参与度也较高,所使用的文献数据主要为《唐律》、《唐律疏议》等。
学术界关于唐代婢女的研究源于对中国古代社会奴婢阶层的关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奴婢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学界对奴婢问题亦有着浓厚的兴趣,多从政治制度、社会矛盾、政治斗争的角度对奴婢进行研究。如褚生《奴婢史》[3],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4],刘伟民《中国古代奴婢制度史》[5]、《两晋南北朝的奴婢制度》[6],韩大成《明代的奴婢》[7],韦庆远等编著《清代奴婢制度》[8],戴玄之《清代的奴婢》等[9]。这些著述的最大特点是将古代社会中的奴婢视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从类别、名色、来源、役使、地位、待遇、反抗等多个方面探讨奴婢的生存境况。总体而言,奴婢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处于被支配被玩弄的地位,同时具有受压迫与反抗的属性。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为唐代奴婢研究的领纲之作,以阶级观点探讨奴婢的来源、功能和社会地位。这部著述虽然认为女性奴婢因为其性别特征使然往往比男性奴婢承受更多苦难(如男主人的玩弄凌辱等),但是浅尝辄止,并未从性别差异角度对唐代奴婢这一群体做更多的关注。因婢女的历史文献不多,专门探讨唐代女婢的专著并不多见,只有部分论文成果。隋唐以前奴婢多来源于战俘,素质较差,身份也较低,多从事粗重的体力劳动;隋唐以后奴婢多来源于破产农民之典卖和商人贩卖,素质较高,身份也较高,主要在官府机构和私人府邸中从事服务性质的工作。[10]
高世瑜《唐代的妇女》[11]一书把婢女作为唐代女性的组成部分,分官奴婢和私奴婢两类略述唐婢女的情况。她同时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妇女史应当以女性的立场去书写,在女性研究中应当听到女性自己的声音。这个观点诚然对中国妇女史研究方向极具指导意义,然而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中国古代社会男权语境下,女性发声之机会甚少。相比前朝而言,唐代奴婢研究非常幸运,唐传奇大量存在,并多以婢女入书,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婢女的鲜活形象。
然而唐传奇中“有意为之”的问题需要在研究中谨慎对待。唐代传奇文的整理发端于鲁迅与陈寅恪。鲁迅《唐宋传奇集》从《文苑英华》、《太平广记》、《青锁高议》等著作选出单篇唐宋传奇45篇,包括《离魂记》、《李娃传》等[12],后人对唐传奇之研究多以鲁迅的45篇书目为基础开展。对唐奴婢的研究所选篇目多为《莺莺传》、《飞烟传》等,在《太平广记》中被收入传奇一类,当中婢女形象大多聪明美丽、言语得体、才思敏捷、精通乐器,活色生香并不逊色于大家闺秀。如鲁迅所云:“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趁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则始有意为小说。”[13]69在鲁迅看来,“有意为之”乃是中国小说具有文体自觉性、走向成熟的标志。
既然是“有意为之”,则其意何在呢?《云麓漫钞》卷八论道:“唐之举人先籍当世现人,以姓名达于主司,然后以所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因为行卷是赴考举人自荐之重要途径,这些传奇作者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之才能”[14]335。因此,以文学虚构为特征的唐传奇能在多大程度上流露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值得商榷。
如此一来,对唐代奴婢之妇女史研究似乎已经无从下手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唐代婢女研究仍有部分材料未受到足够重视,其中大多是《太平广记》中所搜集的虐婢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是婢女,其主人皆有明确的姓名与官职,多为朝廷命官或者皇室贵族,其出处多为《朝野佥载》等社会札记,朝野轶闻,属于时人记时事之列。其所述指涉官员家庭琐事,“皆琐尾擿裂,且多媟语”[15]358,卷12。同时,这类故事大多情节单薄,人物简略,语言平实,崇尚简古,带有六朝志怪“实录”风格。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虐婢故事基本涉及了婢女被虐杀致死后以亡灵索报的故事情节,其宗教内涵仍然有待发掘。从妇女史史料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女性发声的场合并不多,这为妇女史研究发展带来了瓶颈。然而在宗教领域,妇女的声音所占比例并不低于男性。①在《太平广记》中收录了神仙传共五十五卷,为男性神仙故事;另外收录了十五卷女仙传,全部为女性神仙故事。若我们将视野从社会经济制度史转向宗教史,从现实世界转向他界描述,我们或许可以听到更多女性的声音。
二、强魂难抑:女性声音的发露
《太平广记》②《太平广记》成书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由李昉、扈蒙等八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而成。全书500卷,目录10卷,共510卷。共分为神、女仙、定数、畜兽、草木、再生、异僧、报应等92大类。《太平广记》搜自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文后皆附有引用书目,共计475种。中共收录了514则报应故事,下又细分为金刚经、法华经、观音经、崇经像、阴德、异类、冤报、婢妾八个细目。前面七个细目中的故事主人公多为男性,遍布平民、官员、皇室贵族、僧道多个阶层;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故事仅数例,其角色身份主要为母亲与妻子,故事出处主要有《法苑珠林》、《报应记》、《冥祥记》等。卷129与卷130两卷为婢妾故事,共21篇,内容多为虐杀报应,出处为《还冤记》、《朝野佥载》等。
“强魂难抑”是唐虐婢故事的重要宗教特色之一。在《梁仁裕婢》[16]916,卷129中,婢女虽然被李氏虐待致死,然而在其死后的一个多月后,亡魂时常叫唤李氏,致使她头疼哀嚎,脓疮流遍,在痛苦中死去。《玉堂闲话》中的《马全节婢》[16]923卷130也讲述类似的故事:“魏帅侍中马全节,尝有侍婢,偶不惬意,自击杀之。后累年,染重病,忽见其婢立于前”,亡魂但“索命而已”,马全节“不旬日而卒”。唐虐婢故事中这类亡魂亲自复仇故事源自先秦。北齐颜之推所编撰的《还冤记》①《还冤记》是北朝颜之推集录的志怪小说集。在最早的著录中被称为《冤魂志》,宋以后改称《还冤志》,后代始通称为《还冤记》。现从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版称为《还冤记》。有一则《燕臣庄子仪》[16]831,卷119,记录庄子仪被燕简公无辜杀害后亡魂报仇的故事:
燕臣庄子仪,无罪而简公杀之,子仪曰:“死者无知则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当使君见之。”明年,简公将祀于祖泽。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太祀也,男女观之。子仪起于道左,荷朱杖击公。公死于车上。
此事原载于《墨子·明鬼下》:
日中,燕简公方将驰于祖涂,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着在燕之春秋。诸侯传而语之曰:“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其憯速也!”[17]117-118
墨子对于整个亡魂索报事件的描述基本与颜之推一致,并无出现鬼神字样。但是在事件描述完之后,却特意强调了这个索报事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强调了亡魂之可感、可听、可见,栩栩如生,整个索报世界仿佛没有生死异路之隔。《马全节婢》中“忽见其婢立于前”,《张景先婢》[16]911,卷129中其妻子听到婢女的呼喊,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亡魂的真实可感性。唐虐婢故事并不仅仅简单讲述亡魂向施虐者索命的过程,还突出了亡魂强烈执着的索报意志,暗示报应来临的必然性。马全节病重乃是因为被杀的婢女冤魂不散,无论马全节如何苦苦哀求,都不为所动,执意要其偿命。张景先得知妻子杀婢导致重病,欲到弃尸之茅厕内“取其骸骨,香汤浴之,厚加殡葬”,但是亡婢“不肯放,月余日而卒”。婢女绿翘被鱼玄机笞杀前也大声发出:“谁能抑我强魂”[16]922-923,卷130的宣言。
婢女亡魂具有神秘不可思议的索命能力,似循南北朝时虐婢故事之窠臼。《后周女子》[16]913-914,卷129记录北周宣帝在虐杀婢女之后患病丧命的故事。据《周书》记载,周宣帝讳赟,字干伯,是北周高祖武帝的长子。宣帝还在东宫当太子时,武帝“虑其不堪承嗣,遇之甚严”,还遣东宫官记录宣帝的语言动作,“每月奏闻”。宣帝在武帝面前战战兢兢,待武帝一死,“嗣位之初,方逞其欲”,“才及踰年,便恣声乐,采择天下子女,以充后宫。”[18]92,卷7宣帝疑心重,对群臣“密伺察之,动止所为,莫不钞录,小有乘违,辄加其罪”,“宫内妃嫔,虽被宠嬖,亦多被杖”[18]93,卷7。《后周女子》以宣帝暴虐成性、虐打宫女的史实作为原型展开。根据《后周女子》所述,左皇后陈氏有一位侍婢伸懒腰打呵欠被揭发罪行,被宣帝下令责打。这个婢女被腰斩后,在斩杀地点一直出现人形般的黑晕。宣帝以为是血迹,命人反复洗刷,但“旋复如故”,即使挖走原来的土,用新土填充,还是“一宿之间如故”。宫婢亡魂重复出现,洗刷不掉,暗示亡魂强烈坚定的心志。但在这里,亡魂的形象变成血迹一般的黑晕,轮廓状貌非常模糊,与先秦时期可感可见的亡魂形象已经有所不同。但是亡魂的行迹飘渺,却有不可思议力量。宣帝死后,“及初下尸,诸局脚床,牢不可脱,唯此女子所引之床,独是直脚,遂以供用”。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表明此时的亡魂形象与先秦已大有不同。在亡魂的表达上,唐虐婢故事与南北朝时期实乃一脉相承。唐代虐婢故事中的亡魂形象继承了自先秦以来亡魂索报的故事框架,其执意索报的坚定心志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唐代虐婢故事也继承了南北朝时期对被虐女之亡魂行踪飘渺、能量惊人的认知,再度强调了亡魂的模糊性和神秘性;并对这些亡魂的可见性做了差异性处理,只有施虐者能见其形,听其音;旁人不能见之、闻之、感之。如马全节婢索命的时候,只有马全节一人看到婢女亡魂,且与她交谈。马家人皆以为马喃喃自语。这种亡魂观的处理表明,在唐虐婢故事中报应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私密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亡魂的神秘色彩。
《太平广记》中收集了大量冤报故事,多以男性为主。只有两例男性奴婢被主人杀死的故事,施暴者全为男性,且其善行被大肆渲染,其施虐恶行则被轻描淡写。如王简易[16]873-874,卷124第一次梦游城隍冥府时门人便议论:“王君在世,颇闻修善,未合身亡,何得遽至此耶”,表明王简易平素为人甚好,品行良纯。王简易第二次梦游冥府向妻子述说责打僮仆旧事时,其妻诘问道:“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王简易回答道:“世间即有贵贱,冥司一般也”,暗示在阳间虐死一名奴婢只是小事,丝毫不影响王简易的善行。在《王济婢》中,王济枉杀僮仆基于他认为侍者犯下奸淫罪的前提下做出,并非因为残暴而虐待奴婢致死,文本并未对王的品格做负面评价。反观唐虐婢故事,施虐者多为主妇,而且文本叙事中也着意强调施虐妇人内心之歹毒,用“甚妒”、“嫉”等词汇形容之,对于施虐过程中之残忍与暴虐也毫不掩饰,如“截双指”、“灼烙双目”等血腥场景皆让读者身临其景,不寒而栗。这大约是男权社会语境下针对“妒妇”所做的批判。
同时,行文中也并没有突出男奴的角色。《王简易》以唐洪州司马王简易腹中患有肿瘤展开叙述。这一“腹中生物如块大,随气上下,攻击脏腑,伏枕余月”,让王简易疼痛苦恼不已。有一天,这个肿瘤忽然攻往心脏位置,王简易在疼痛中晕死过去,梦见手执符牒的城隍鬼吏丁郢带他前往城隍庙受审,得知性命尚有五年,其后被放回阳间。五年后,腹中肿瘤再度攻心,王简易再度昏睡,梦游冥府,才知到这个顽疾是“被小奴所讼,辞气不可解”。整个故事仅通过王的疾病与冥府差吏转述还原僮仆在妙龄时被主人责打致死然后诉诸冥府的经过。《王济婢》[16]911,卷129中,王济听信了谗言,误以为侍从要奸污女婢,故将侍者处死。侍者再三申辩,王济仍然不信,侍者临死前说道“枉不可受,要当讼府君于天”。王济病重之时,忽然看到死去的侍者魂魄,向他说道:“前具告实,既不见理,便应去。”王济于数日后死去。纵观全文,这名侍从生前死后都执意于道理争辩,亡魂相告的时候也用冷静理性的态度阐明王济生病与殉命缘由,未像被虐之女婢一样发出“谁能抑我强魂”的呼声。
“强魂”更多见于其他男性冤报故事中。江融[16]851,卷121“耿介正直”,被酷吏周兴等人网罗罪名诬陷。问斩前江融大声呵斥“吾无罪枉戮,死不舍汝”。被斩之后,尸体不倒,反而“激扬而起,蹭蹬十余步”。行刑者再三将尸体踢倒,但尸体每次都起立再走,“如此者三,乃绝”。不久周兴死去。江融“虽断其头,似怒不息”,让人印象深刻,与后周女子的亡魂有相似之处。再如被唐昌令王悦无辜杀死的李之,死后冤魂附身于长子身上说道:“王悦不道,枉杀予,予必报”,声音严厉,表明索报之强烈意愿。数日后,李之魂魄痛击王悦要害,并言明痛杀仇人快意恩仇之心志,王悦终于右肾溃烂而死。李魂意向坚定强烈,恰似女婢之“执意索命”。
从宗教观念之变化历史来看,唐代虐婢故事中的报应观与先秦时期的鬼神观有渊源。在先秦时期,鬼神所指向的乃是冤死的亡魂本身。关于燕简公杀庄子仪一事的记述中,墨子这样写道:“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是证明鬼神存在的有力证据。在对庄子仪的亡魂绘声绘色地描述后,篇后还强调了“鬼神之诛,若此其憯速也!”在整个索报事件中,诛杀燕简公的唯有庄子仪可见可闻的亡魂。此时的鬼神,当指冤死亡魂。
在汉代,先秦时期单纯的亡魂索报故事发生了变化,以《还冤记》中《游敦》[16]831-832,卷119为例:
游敦,字幼齐,汉世为羽林中郎将。先与司隶校尉胡轸有隙,遂诬敦杀之。敦死月余,轸病,目睛遂脱,但言伏罪,游幼齐将鬼来,于是遂死。
校尉胡轸因为矛盾诬陷游敦并将其杀死,游敦带群鬼来索命。在这里,冤魂索报的主题非常明确,报应仍然被简单理解为杀人偿命。但整个索报过程中,游幼齐的亡魂并不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将鬼”而来。“鬼”为一种与亡魂不同的超自然力量出现,与庄子仪孤身索报呈现的宗教观又有所不同。
南北朝虐婢故事《宋宫人》[16]911,卷129中,亡魂反复出现暗示了报应作为超现实的必然存在,人为的力量无法撤销。但是施行报应者是谁呢?从上文的叙述看,似乎是奴婢亡魂本身;然而在故事结尾处,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进行了猜测:“盖亦鬼神之意焉。”这个猜测反映出时人认为在亡魂之外还有一种更超然的力量在主导报应的发生,这力量就是鬼神。此时,鬼神逐渐变成了超越于亡魂之上的、索报完成的主导力量,而亡魂的形象已不如先秦时期般具体可感,而是变成了模糊的影子。亡魂与鬼神二者逐渐分离:亡魂的形象逐渐模糊,鬼神的主导者的角色越来越分明,是先秦至南北朝以来虐杀报应故事中宗教观念发展的主要脉络。
唐虐婢故事中的“强魂难抑”实为古代中国之厉鬼信仰。厉鬼也被认为是横死、被杀、冤死之鬼。这些婢女、男奴以及被冤杀的忠臣良将都应当属于厉鬼之列。这些厉鬼若无宗教安抚,会为生人带来困厄灾难。根据《礼记·祭法》,王要为群姓立“七祀”,其中有“泰厉”;诸侯要为国立“五祀”,其中有“公厉”;大夫要立“三祀”,其中有“族厉”。[19]1305,卷46
被虐杀的婢女、男奴与冤杀的忠臣、在战争中死去的兵士皆属于厉鬼之列。唐王朝对阵亡兵士动用了大量佛教力量进行镇抚,以保国泰民安。贞观三年,太宗下诏,年三月六普断屠杀,行阵之所皆置佛寺;[20]建义以来交兵处立寺七处,并官造,又给家人车牛田庄,召僧徒为战亡人设斋行道。然而从唐虐婢故事来看,这些婢女仅仅因为主妇的嫉恨或者主人的残忍而殉命,死后尸骨仍不得善待。《张景先婢》中,婢女被杀死后置于厕所里,其他的虐婢故事则未曾交代被虐杀之婢女如何被安葬。施虐者一般是在时日降至才想到要做种种仪式镇抚这些女厉,但为时已晚,故而冤魂为厉格外凶猛。六朝时期江南地区出现祭祀“女性人鬼”的现象。这些“女性人鬼”多为生前受虐打之女性,地位卑微;死后却法术灵验,凭着附身巫者说出预言,并施展法术惩恶扬善,眷顾妇女,成为民间信仰体系中的女神,受人敬拜。例如丁姑从一位被役使致死的女性变成了一位庇佑妇女法术高明的神明。虽然她被虐致死,且无后,为厉鬼之属,但是却用略施法术、小惩大诫这种温和的方式被时人所接受。[21]61-62,卷5相比之下,唐虐婢故事更多地保存了女厉的本色,正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声音发露之体现。
三、佛教忏悔:女性声音的失语
在佛教中,忏悔主要用于消除个人过去无始劫以前到现在身口意所作下的种种业障,“远离十恶,修行十善”[22]337下,避免沉沦苦海。从敦煌礼忏文看,最早有年代信息的礼忏文是大统十七年(551),即西魏文帝时期。其中10世纪的礼忏文特别多,正是晚唐五代时期。[23]可见从南北朝后期至有唐一代,佛教之忏法都非常盛行。众多忏法中以“梁皇宝忏”最为流行,又称为《慈悲道场忏法》。这部忏法的目的是“欲守护三宝,令魔隐蔽。摧伏自大增上慢者。未种善根者,今当令种。已种善根者,今令增长。若计有所得住诸见者,皆悉令发舍离之心”[24]922下。《梁皇宝忏》集众经文之大成,所引有《决定毗尼经》、《分别功德经》、《观药王药上菩萨经》等。
南北朝时期佛教忏法的盛行影响了虐婢故事的形成,以《金荆》[16]912,卷129为例。后魏末年,嵩阳杜昌的妻子柳氏嫉妒婢女歌喉动听,将她的舌头割掉,自己的舌头眼看也要溃烂。柳氏柳氏凭着为期七天的“顶礼求哀”使得禅师发出咒语,使得蛇从口出,免遭烂舌报应。整个故事讲述了两个结局不同的虐婢事件:
柳氏嫉恨——婢女失去双指——柳氏失去双指
柳氏嫉恨——婢女失去舌头——柳氏向禅师忏悔——禅师念咒语——柳氏吐蛇——柳氏免失舌头
佛教忏罪有两种形式:其一为事忏,其二为理忏。唐宗密在《圆觉经修证仪》第十六卷中对事忏和理忏两者做了区分:
夫忏悔者,非惟灭恶生善,而乃翻染为净,去妄归真——故不但事忏,须靠理忏;事忏除罪,理忏除疑。然欲忏时,必先于事忏门中,披肝露胆,决见极应之义,如指掌中,悚惧恐惶,战灼流汗;口陈罪状,心彻罪根。根拔苗枯,全成善性,然后理忏,以契真源。[25]496下
柳氏所做应是事忏。这则虐婢故事中还刻意强调了咒语的灵验:“禅师大张口咒之,有二蛇从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复。”在佛教之忏罪仪式中,咒语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极大威力。《梁皇宝忏》中多次出现“主善罚恶、守护持咒”的语段,并有“赞佛咒愿”,也本为拯救妒妇所作,①据序言,此忏法是梁武帝为郗皇后忏悔罪孽所集。郗皇后生前因为嫉恨,死后变作蟒蛇,经此忏法后得生天人。或可推断“柳氏顶礼求哀,经七日”所做的应该是梁皇宝忏,其后罪得消除。爱德华(Mark Edward Lewis)认为,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状态发生了改变。尽管汉译佛经的工作始于东汉,然而只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译佛经才达到了形而上学的高度,被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认可。部份上层贵族扩大了与僧人的交往,甚至出家研习佛教之智慧与辩才学。[26]204南北朝时期至有唐一代,普罗大众已经将佛教忏悔和诵念经咒作为为自己、家人乃至死去的祖先寻求福祉与阴德的重要途径。[26]188这些虐婢故事也佐证了爱德华的观点,显示在南北朝时期咒语和忏悔被认为具有灭罪功能而为信众所接受。与此同时,报应的绝对性和必然性被削弱。在《金荆》中,婢女失去舌头,彰显报应的烂舌之疾也被佛教之忏悔仪式和咒语所消解,折射出女性声音在社会环境的包裹下事实上处于“失语”的境地。
有唐一代,佛教忏悔仪式逐渐完备,佛教各宗派也各出忏法,可谓百花齐放。净源简明扼要描述了汉以来忏法的发展流程:“汉魏以来,崇兹忏法,未闻有其人者,实以教源初流,经论未备。西晋弥天(道安)法师,尝着四时礼文;观其严供五悔之辞,尊经尚义,多摭其要。故天下学者,悦而习焉。陈、隋之际,天台智者撰《法华忏法》、《光明》、《百录》,具彰逆顺十心。规式颇详,而盛行乎江左矣”。[27]512下入唐以后,忏法逐渐从自我修行转向了追荐亡人,其目的也从“忏悔清修、远离尘垢”的自证自修转向为逝去的先人忏悔,帮助先人脱离轮回之苦的“助他”、“觉他”形式。因此唐代逐渐出现以追荐亡者为目的的寺院,唐后期更出现了为先人做长期礼忏追荐、公私忏院并起的现象。这些寺院多数以“忏”命名,如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80)吴兴郡乌程县惠觉寺所建“观音忏院”[28]4749下-4750上,卷5。唐代虐婢故事中施虐者多数提出为婢女亡魂“铸造经像”等佛教功德,也是社会风气使然。
然虽有唐一代佛教之忏法日盛,虐婢故事却背道而驰,对佛教的忏悔仪式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在《马全节婢》中,无论马全节向亡婢许诺“与尔钱财”还是“为尔造像书经”,婢女都漠然视之,执意索命,表明佛教忏罪功德的无力。《胡亮妾》[16]915-916,卷129故事再次强调了这种态度。①在唐代社会中,妾与婢在家庭中同样容易招致正妻的嫉恨而被虐杀,因此援引一个唐朝虐妾故事说明之。唐代广州化蒙县丞胡亮的妻子贺氏趁着胡亮外出时将小妾“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后贺氏有娠。产一蛇两目无睛”。贺氏向禅师求问缘故。禅师明确道出此蛇乃是被烙伤的女妇转世,只要“好养此蛇”,则可以免受灾祸。但胡亮无意看到这条蛇后非常惊异,立即”以刀斫杀之”。报应马上临到,贺氏“两目俱枯,不复见物”。整个叙事结构可以表现为:
主妇嫉妾——烙妾双目——主妇有孕——蛇无双目——禅师点名原因——主妇养蛇——男主人斩蛇——主妇失去双目
蛇的出生很大程度上呼应了佛教的六道轮回理念。禅师点破缘由使得这个故事中的佛教色彩非常浓厚。但从故事的结局来看,贺氏双目从此不再复见,也充分说明贺氏虐妇的报应并未撤销,甚至连受报应的程度也并未因贺氏悉心照料蛇两年而有所减轻。若将蛇这一中介从故事中取走,可以发现这篇故事仍旧遵循了整齐的倒影结构构思,再次维护报应的对等原则——“虽有延迟,却分毫不差”:
主妇嫉恨——妾失双目——主妇有孕——主妇失双目——主妇懊悔②故事结尾提到了“悔无及焉”的懊悔情绪,然而懊悔之人是谁却并未言明。如果懊悔之人是胡亮,其应当懊悔不该斩蛇,以致妻子遭受报应,双目失明。但若懊悔之人是贺氏,其懊悔的內容应当是当初因为嫉妒而烙妾的双目,以致今日身受其苦。
如此这般是否可以视为入唐以后女性的声音较之南北朝时期更加富有独立性呢?唐代虐婢故事主要集中于初唐与中唐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佛教的发展也多次经历了起伏。开元年间对民间层面的佛教就进行了极重的打击。开元二年(714年),玄宗禁创建佛寺,并敕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还颁布《断书经及铸佛敕》,禁民间铸像写经。[29]539,卷113开元三年(715)玄宗下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闭,公私望风,凡大屋大像亦被残毁”[30]374上,卷40。唐中期朝廷在民间层面上对佛教的大肆打击,让我们不难理解这些虐婢故事中何以会出现对佛教之忏悔、造经像等荐亡活动嗤之以鼻的态度,因这些虐婢故事本来就来自于民间,至中唐已经是士大夫们“征其异说”,于“方舟沿流,昼宴夜话”[31]44时的谈资了。因此,唐代虐婢故事对于佛教忏悔仪式之否定,或许更多地体现出外部处境对于女性声音的影响力所在。
四、超然主宰:被改变的女性声音
在否定佛教的救赎功能的同时,唐代虐婢故事进一步探索了超越宗教救赎的超然主宰——上帝。《严武盗妾》[16]920-922,卷130便是其中一例:
中唐西川节度使严武看中邻居军使的女儿,将其引诱带走。严武因此事被追捕,惊惶之下将其用琵琶弦勒死,尸沉河底,躲过了追查。数十年后严武病重,被女子冤魂寻至,不久命终。
这个故事尤其强调了道教和佛教的救赎企图。在女子上门之前,一位峨眉山道士预言严武“灾厄至重,冤家在侧”,如“自悔咎,以香火陈谢”,或可免于劫难。在严武将死之前,这名道士向女子冤魂求情。而严武自知死期将至,“悔谢良久,兼欲厚以佛经纸缗祈免”。但女子在这种宗教救赎面前不为所动,执意索命。在否定道教与佛教的救赎功能的同时,“上帝”在亡魂施行报应中的超然地位得到了肯定。冤死女子前往严武住所时就已经向道士申明:“上帝有命,为公所冤杀,已得请矣。”道士遂无奈让路,并让她亲自见严武。当道士为严武求情时,女子也严词拒绝,说道“不可。某为公手杀,上诉于帝,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道士也无计可施。在严武提出烧纸钱给枉死女子时,女子也奉“上帝”之命断然拒绝。在这个虐杀故事中,“上帝”为亡魂的索报行为提供了超然的合法认可,各种宗教救赎试图撤销或者减轻报应,都是徒然。这点在男奴被虐的故事中略有体现,在虐婢故事中则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调。
唐代虐婢故事中出现了“上帝”这一超然主宰,或与唐代郊祭主神的更迭有关。郊祀是皇家大典,主要祭祀天地系统,君主需以“天子”自称,以印证君权神授之合法性与至高性,是体现君主对国家有掌控权威的最重要仪式。[32]4-8唐王朝向来重视郊祀对于巩固政权、树立国家权威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盖春秋之大事,莫先乎祀;王者之盛礼,莫重于郊”[33]98,卷5。因此隋唐时期关于礼制之争也主要集中在郊祀主祭神之安排上。[34]44-49有唐一代,郊祀大多以昊天上帝为主祭神。显庆年间,朝廷就认为昊天上帝“不属穹苍”[35]823,卷21,肯定了昊天上帝凌驾众星辰之上,涵括万有之地位,这显然是受了王肃(195-256)说的影响。在礼仪实践中,《显庆礼》一年举行四次祭天礼,均以昊天上帝为主神。[36]14,卷1昊天上帝的地位在唐王朝得到初步的肯定。永昌元年(689),朝廷再次下诏,称“天无二称,帝是通名,……自今郊之礼,唯昊天上帝称天,自余五帝皆称帝”,直斥过往将昊天上帝与五帝并列祭祀是“假名实未尝,称号不别,尊卑相混”[30]342,卷67。开元二十年(732)起居舍人王仲邱等撰成《大唐开元礼》150卷,遂成后世郊祀典范,昊天上帝的至高地位在国家祭祀系统中最终完全确立。这也是唐虐婢故事着意强调昊天上帝超越众神众星之上的原因。①《窦凝妾》中有“妾以贱品,十五余年,诉诸岳渎,怨气上达,闻于帝庭”,从中凸显了上帝超越五岳天神之上的超然地位。
但是昊天上帝并非一直是唐朝郊祀的主神。唐王朝建立初期(太宗时期至贞观年间)一直在郊祀中沿用郑玄(127-200)礼制,所祭天神为六位,一年祭祀九次,即:冬至祭祀昊天上帝,立春、立夏、季夏土王日、立秋、立冬、夏正、四月雩祀、季秋明堂均祭祀五帝 。[19]154-155,卷5昊天上帝与五帝并列为六位天神之一,只在冬至祭祀;五帝则享有八次的祭祀,体现出五德终始说对唐初期郊祀的影响,昊天上帝的地位并不突出,甚至较五帝低微。干封元年(666)郑说重新抬头,朝廷“祭五天帝,其雩及明堂”[37]825-826,卷21,昊天上帝的地位再次下降。昊天上帝在唐王朝中的地位沉降过程也解释了为何在较早期的虐婢故事中并没有看到“上帝”主宰的现象。
“上帝”出现也反映了婢女自身的诉求。唐朝在战争过后经历了长期的安定繁荣,奴婢数量激增,开创了中国历史中大规模蓄奴的先河。多数朝廷官员府中奴仆数量惊人,如王宗 “僮奴万指”[36]2358,卷182。唐朝社会存在大量奴婢,但是奴婢的地位却比前朝要低下。②根据《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其时京兆尹赵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执魏丞相,欲求脱罪而不听。复使人胁恐魏丞相夫人贼杀侍婢事而私独奏请验之,发吏卒至丞相府,捕奴婢笞击问之,实不以兵刃杀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赵君迫胁丞相,诬以夫人贼杀婢,发吏卒围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骑士事,赵京兆坐腰斩。可见在汉代,即使对于高级官员而言,家眷杀死侍婢也是十分严重的罪行,对其政治生涯也有莫大的影响。汉代位极人臣的高官杀戮奴婢也要受严厉惩治。与唐代杀奴不加追究的情形形成对比。《唐律疏议》明文规定:“其良人殴伤杀他人,部曲者减凡人一等,奴婢又减一等。若故杀部曲者,绞;奴婢,流三千里。”[37]404,卷22“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37]405,卷22因无须抵命,唐代主人虐杀奴婢的事情并不少见。房孺复妻子崔氏因为嫉妒婢女浓妆高髻,将婢女眼睛烫伤,美其名曰“汝好妆耶,我为汝妆”[16]2145-2146,卷272。濮阳范略妻任氏因为丈夫宠幸一名婢女用刀把她的鼻子和耳朵截掉[16]915,卷129。主人虐杀奴婢受到的处罚极其轻微,而奴婢若伤害主人,则需以性命相抵,“诸部曲殴伤良人者,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38]403,卷22。因此婢女在生时处于社会的底层,对任何苦难只能逆来顺受。面对现实中力量的悬殊,只能以弱势个体的死亡暂时缓解这一冲突。然而奴婢杀死主人,在现实法律中并不具有合法性。因此,这些婢女尽管化为索报的鬼魂向施暴者讨回公道,是对公平正义的一种寻求,但是也需要合法性的认同,“上帝”正是扮演了这一角色。这在《窦凝妾》[16]919-920,卷130中借着被杀死的小妾的口明确道出。唐开元年间窦凝为了娶新妾,将原有的小妾和小妾的两个女儿杀死。旧妾亡魂上门索报时申明被杀后“怨气上达,闻于帝庭。上帝降鉴,许妾复仇”,用“上帝”的允许彰显此举的合法性。这与唐王朝在郊祀中把昊天上帝视为超越众星辰的苍穹之神,并且以祭祀昊天上帝来证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有相通之处。
唐代郊祀礼制之变化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唐代虐婢故事的发展路向,使得女性基于自身诉求发出更强的声音。以《窦凝妾》故事为例,当新妇问是否可以用佛教功德为窦凝赎罪时,旧妾断然拒绝:“凝以命还命足矣,何功德而当命也?杀娘子,岂以功德可计乎!”明确表示佛教功德根本不能抵消窦凝所犯的过错,必须以命偿命。其后窦凝请来高僧昙亮与内阁置坛念咒以驱赶旧妾亡魂。旧妾怒斥佛教罔顾正义真理,庇护恶人,让冤屈者永远沉冤不得血:“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义隐贼。且凝非理杀妾,妾岂干人乎?上命照临,许妾仇凝,金刚岂私杀负冤者耶?”故事以窦凝身中鬼毒,自咬肢体而死,其两个女儿出嫁后双双死去告终。这段话体现出女性复仇的强烈愿望,又用佛教诵经念咒的“不正义”反衬“上帝”的正义。早在旧妾上门之前,窦凝父亲就在书信中告知他有大祸将至,“近在暮月,宜疾理家事”,并且在信中指示“长女可嫁汴州参军崔延,幼女嫁前开封尉李驲,并良偶也”,以此避祸。最后新妇生的两个女儿成功出嫁,但仍难逃一死。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儒家教义中所谓祖先庇佑(祖荫),面对报应一事也无法阻止,无能为力。“上帝”的超越各种救赎的主宰地位再次得到肯定。在这些充满着“上帝主宰”的虐婢故事中,可以听到女性发自内心的强烈诉求。这种诉求巧妙地利用了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自己的声音更加振聋发聩。
五、结 语
在唐代虐婢故事中我们看到宗教观念经历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婢女强魂难抑,执意对施虐者索命,而这种强烈的复仇情绪并未在男奴被虐杀的故事中出现,可以视为女婢因为性别差异而导致的结果。然而,这样的宗教观却在忠臣良将被冤杀故事中有所体现。强魂难抑体现的是中古时期的厉鬼信仰。她们在生的时候无力发声,只能以死后之魂魄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说,这些亡婢魂魄在他界中喊出了女性的声音。然而,这样的女性声音在南北朝时期遭到了佛教救赎的消解,使得这些被虐杀的女性无论生前死后都处于失语的境地。这种失语与南北朝时期佛教以自我修行为目的的忏法兴盛有关,故而施虐者可以通过忏法消除罪业,复种善根,免受惩罚。进入唐代,寺院中追荐亡魂的忏法日益兴盛,出现大量公共与私家忏院。但虐婢故事极力否定了佛教的救赎功能,很大程度受了统治阶级在民间层面大肆打击佛教的影响。
唐代虐婢故事否定了佛教的救赎功能,却不可能回到单纯的亡灵索报结构中。超越一切宗教救赎的超验主宰——“上帝”开始出现。“上帝”的出现首先与唐中期及以前郊祀仪式之争有关。经过反复废立,王学战胜了郑学,昊天上帝在郊祀中超越中星辰大帝,宇宙苍穹化身之超然地位得到了确认,这在虐婢故事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另一方面,虐婢故事需要一个合法授权抵挡佛教对自身固有报应观的消解,“上帝”正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当“上帝”参与到亡魂索报的过程时,婢女的亡魂有了更加合法的理由向施虐者索命。这种女性声音混和了外部压力后显得更加嘹亮,振聋发聩。
妇女史的研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时至今日,已经摆脱了单性别的妇女历史研究,建立了两性比照的理论体系。[2]15-76与此同时,对妇女史研究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女性声音的发露已经成为妇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中国历史中,与女性有关的材料实在为数不多,若有女性自身之声音已属可贵,但是女性声音也并非尽然自我心声的流露。如女犯人的供词,可视为女性亲口所言,然若结合犯人所在处境考量,又难免让人怀疑这些画押的供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女性的心声?是否有刑讯逼供或者女性为自身开脱之嫌疑?唐代虐婢故事是女性声音在他界想象中发露的一个典型例子。从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历史中的女性原本有发声的诉求,虽然也有短暂的失语过程,但是总能在曲折与幽深中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而这种声音只有在他界层面上得到释放,这或许能让我们在妇女史研究的女性声音这一议题中有更多思考。
(本文修改过程中得到陕西师范大学焦杰老师的指导建议,特表感谢)

附录《太平广记》婢(妾)报应故事目录
[1]Gertude Himmelfarb.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2]叶汉明.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
[4]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刘伟民.中国古代奴婢制度史:由殷代至两晋南北朝.香港:龙门书店,1975.
[6]刘伟民.两晋南北朝的奴婢制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学报,1965(4).
[7]韩大成.明代的奴婢∥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韦庆远,吴奇衍,鲁素.清代奴婢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9]戴玄之.清代的奴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74 (4).
[10]赵云旗.论隋唐奴婢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变化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7(2).
[11]高世瑜.唐代的妇女.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12]鲁迅.唐宋传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7.
[13]鲁迅.唐传奇文(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北新书局,1927.
[14]鲁迅.且介亭二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5](南宋)洪迈.容斋续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6](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
[17](春秋战国)墨翟.墨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
[18](唐)令狐德棻.周书.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19](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0](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东京:大藏经刊行会,1924-1935.
[21](晋)干宝.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
[22]金光明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册.东京:大藏经刊行会,1924-1935.
[23]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24]慈悲道场忏法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东京:大藏经刊行会,1924-1935.
[25](唐)宗密.圆觉道场修证礼忏广文卷∥大正新修大藏经续藏经:第74册.东京:大藏经刊行会,1924-1935.
[26]Mark Edward Lewis.ChinabetweenEmpires: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27](宋)净源.圆觉经道场略本修证仪∥大正新修大藏经:第74册.东京:大藏经刊行会,1924-1935.
[28](宋)李景和.嘉泰吴兴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
[29](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30](宋)志磐.佛祖统纪∥大正新修大藏经续藏经:第49册.东京:大藏经刊行会,1924-1935.
[31]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
[32][日]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06.
[33](唐)张九龄.曲江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4]Howard J.Wechsler.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35](五代)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36](唐)萧嵩,等.大唐开元礼.东京:古典研究会,1972.
[37](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赵小华】
Religious Ideas in Stories of Slaughtered Maidservants in Tang Dynasty and Female Voice
(By XIE Jian)
Religious ideas in stories about slaughtered maidservants in Tang Dynasty have gone through a lot of changes.In the early stories,the strong soul of maidservant insisted on killing the abusers.The soul of people killed were considered to be devil deities in the Medieval China.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strong souls of the dead slave girls embodied a type of female voice.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the female voices got faded because of the digestion of the Buddhist salvation.Influenced by Against Buddhist Movement in the civil level,stories about slaughtered maidservants were written to deny Buddhist's salvation.At the same time,“Shang Di”who was the highest among deities of Buddhism and Taoism,appeared in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Jiao Si(suburban ceremony).Female Voice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study of women's history.There were few materials related with women in Chinese history.Female voice was valuable,but its authenticity should be questioned.Stories about slaughtered maidservants in Tang Dynasty offer us a typical example of surreal Female Voice.
Tang Dynasty;religious ideas;female voice.
谢 健(1983—),女,广西梧州人,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2012-05-10
K242;C913.68
A
1000-5455(2012)04-0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