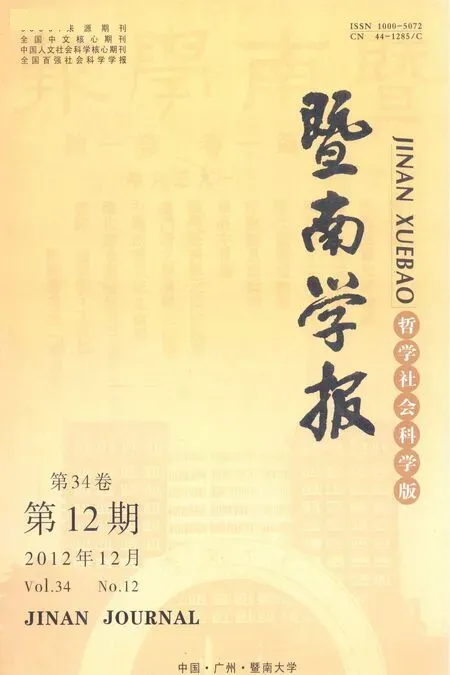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及策略取向
2012-09-03陈莹
陈 莹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广州 510632)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向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约2000个援助项目;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快速增长,2004年至2009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9.4%;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1]。可以说,新中国60多年的对外援助,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推动南南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从提升国家对外软实力这一视角来观察,对外援助在塑造民族形象、提高国家声望、宣扬社会价值和传播生活方式等方面还未充分发挥作用。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外援助金额和援助项目的增长与中国在该国家或地区软实力的提升并未成绝对的正比关系,个别甚至出现被受援国政府拒绝或民众排斥等极端事件,如缅甸叫停中国援建的密松水电站大坝。问题出在哪里?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Eddy Sadeli(李祥胜)一语中的:“中国有些援助没有获得当地人的心”。如何使对外援助更有效?如何让援助赢得政府和民众的心?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于2012年2月在印尼雅加达和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市、三口洋市,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研和访谈,访谈的对象包括政界、传媒界、华社界和普通民众。以下将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一、中国对印尼援助的现状和效果
近十多年以来,中印关系一路向好。自2001年起,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年均增速超过20%,2008年达到315亿美元的高峰。与此同时,中国对印尼的援助力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美国国防大学亨利·耶普的一项调查显示,2002年中国对印尼的援助已达美国的两倍[2];在2004年印度洋地震海啸中,印尼受灾最为严重,中国政府向受灾国家提供了各种援助共计7亿多元人民币,这是迄今中国对外援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紧急救援行动。目前,印尼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重要市场,中国与印尼两国企业使用中国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在印尼实施了包括巨港电站、芝拉扎电站、风港电站、泗马大桥和加蒂格迪大坝在内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之相对应,中国对印尼的援助也集中在发电站和大桥等基建设施的成套项目①成套项目援助是指中国通过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等援助资金帮助受援国建设生产和民用领域的工程项目。中方负责项目考察、勘察、设计和施工的全部或部分过程,提供全部或部分设备、建筑材料,派遣工程技术人员组织和指导施工、安装和试生产。项目竣工后,移交受援国使用。上。
印尼人如何看待中国的援助?精英层、普通民众和传媒界的反应不尽相同。印尼国会议员Albert Yaputra(叶锦标)“非常感谢和欢迎中国对印尼的无私援助。”他认为,与美国、日本、韩国对印尼有条件的援助相比,中国对印尼的援助是无条件的。印尼国会议员Eddy Sadeli(李祥胜)则认为,中国对印尼的援助是中国政府向印尼政府和民众展现了一个友好的态度。而普通民众对此则知之不多,笔者就“请您讲出几个您所知道的中国援助项目”这一问题随机访问了近30名普通民众,受访者介于25~70岁之间,有一定的受教育水平(能读懂印尼文和中文报纸),绝大多数人回答“不知道”,仅有3人回答“志愿者老师”,2人回答“海啸援助”,1人回答“发电厂”,1人回答“大桥”。笔者采访的普通民众均为华人,并且均有阅读中文报纸和观看中央台国际频道的习惯,比较关注与中国相关的新闻,由此笔者可以推断,印尼华人以外的其他族群对中国援助情况的了解会更少。印尼一份中文报纸的记者道出了个中原因:“中文报报道中国援助项目的篇幅会比较多,放在较重要的版面,有时还会配有彩色图片;但是印尼文和英文的报纸则报道得比较少,有时也没有详细地宣传援助项目的背景资料,读者可能只知道有一座桥建成,但不一定知道是中国援助的。目前印尼文报的受众较中文报多,所以一般群众获知中国援助信息的渠道很窄,有的民众甚至将援建项目误解成当地政府的工作业绩,当地政府有时也很喜欢这种美丽的误会。”
印尼人认为中国的援助存在哪些问题?印尼国会议员Eddy Sadeli(李祥胜)指出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目前中国对印尼的援助大部分为工程项目,这些项目例如发电厂很多都涉及到征地和拆迁,当地老百姓得不到太多的好处,对当地老百姓来说,首先是他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一些他们熟悉的环境,有些甚至可能会损害他们的眼前利益;第二,没有积极地宣传援助工程会给当地人带来的好处,也没有真正给附近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第三,工程队大多躲在工地里固步自封,不敢主动与当地人交往,与当地政府、警察界、新闻界和民众都没有建立正常的沟通交流渠道。他建议工程队应更主动地与当地人打交道,做一些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例如:帮助附近村庄修缮学校和道路;招聘当地失业人员工作,增加就业,传授工程技术;还可以参加村民的节庆和婚庆活动等。印尼国会议员Albert Yaputra(叶锦标)则强调,中国在印尼的投资基本上都是基础设施建设或与资源有关的项目,例如,开矿、采油等,与当地老百姓没有什么联系,相反还有可能影响他们的生活,如造成污染等。他还建议,中国对印尼的援助不要都集中在大城市,要关注边远的落后的地区,例如,西加里曼丹许多人一个月的收入还不足20美元,这些穷人,包括许多华人,他们更加需要援助。与叶议员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三口洋市议长蔡翠媚和三口洋市教师联合会的黄锦陵主席,蔡翠媚希望援助能淡化官方色彩,加强对农村地区农业技术、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援助;从事印尼华语教育近20年黄老师则认为,援助应该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现在印尼学习华语的风气很浓,很多基层一线的中小学缺华语老师,而目前印尼华文教育志愿者老师均集中在孔子学院,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志愿者老师支援到中心城市以外的中小学。坤甸邮报集团CEO Untung Sukarti则认为,中国援助的项目多为发电厂等基建工程,建成后喜欢举行盛大的仪式,但是当地权威媒体对此类新闻都不感兴趣,一般不会报道,因为离民生太远,读者的关注度不高。
二、软实力与软性援助
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S.Nye)将权力划分为“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①学界对“soft power”的翻译包括“软实力”、“软力量”、“软权力”、“软国力”、“柔性国力”等。本文统一采用“软实力”的译法。,所谓“硬实力”,是指以军事、经济等传统权力资源为主的,建立在强制和引诱基础之上的命令性权力(command power)[3];而“软实力”是一个国家运用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实现目标的能力,并使其他国家按照与它的偏好和利益相一致的方式界定自身的偏好和利益[4],这是一种建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基础之上的同化性权力(Co -optive power)[5]。
对外援助(Foreign Aid)是提升国家影响力,建设对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对外援助是一种可能对受援国施加影响的工具,其主要职能是争取受援国的人心”[6],他把对外援助划分为六种类型,其中一种是“为提高自身威望的援助”,他认为对外援助可以提高援助国的威望,从而可以提升一国的软实力。
对外援助国家内部因素的外化理论认为,在一个沟通渠道日益畅通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和社会文化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表现出来,向外部释放。对外援助是这种国内因素外部化的一个主要渠道。因此,对外援助至少有三个主要目的:(1)追求救援国的既得利益,包括短期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但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战略和安全利益;(2)谋求救援国广义的国家利益,包括塑造民族形象、提高国家声望、宣扬社会价值(如民主、法制、人权和社会团结)以及传播生活方式等;(3)关注人类共同的利益,包括环境的保护、缓解贫困和减灾救灾等,并通过这些活动营造救援国的国家形象[7]。后两者就是“软实力”的体现,正如约瑟夫·奈所言:“某些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大于它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是因为这些国家在考虑国家利益时涵盖了一些具有吸引力的目标,诸如援助和维和等[8]。”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资金、技术、产品、观念和文化等各种要素从世界中心流向全球各个角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些流动有很多载体,对外援助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对外援助活动涉及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通过在这些领域里与受援国的各阶层进行合作,援助国的影响力可以渗透到受援国最边远的角落和社会的最深处[9]。”因此,借助对外援助,援助国的文化观念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提升援助国的软实力。
对外援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硬援助”和“软援助”的划分始见于官方,商务部对外援助司司长王世春曾撰文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应坚持“硬援助”与“软援助”相结合[10]。笔者也认为,按照对外援助的性质和内容,可划分为“硬性援助”和“软性援助”,武器等军事援助和基建工程等经济援助属“硬性援助”范畴,人道主义援助、教育援助、援外医疗队、援外志愿者、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属于“软性援助”范畴。硬性援助有助于带动资金、产品和劳务的流动,而软性援助则更有利于促进援助国内部的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等各种要素向受援国进行多层次的扩散和渗透。
目前,成套项目是中国最主要的对外援助方式,在对外援助支出中一直占有较大比例,2011年成套项目援助占对外援助财政支出的40%左右;而61%的优惠贷款援助投入到经济基础建设项目(如下图所示)。
官方将成套项目援助纳入硬性援助的范畴[10]。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对外援助结构中,硬性援助占绝对的优势。相比而言,冷战后美国的硬性援助则呈逐年下降的态势,军事援助从1990年的33.1%降到了2004年的23.2%,经济援助1990年28.6%降到2004年的26.1%[11]。无可否认,硬性援助在促进资金、产品和劳务的流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和冷战时期,硬性援助在打破外交困境、赢得受援国政治支持、帮助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硬性援助使我们赢得了政府,但未能真正赢得民众,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援助工程破坏当地资源、影响环保、涉及拆迁、工程质量差等批评的声音很多,在印尼甚至出现群众质疑中国援助亚齐的食品和矿泉水过期的极端事件。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发展,正如俄著名政治学家尼古拉·兹洛宾在《第二个世界新秩序》中所说的:“冷战后时代世界秩序的特征是无极和激烈竞争。而竞争不是与其他力量中心的竞争,而是要通过一个国家提高自身的吸引力来实现。争夺未来世界的一席是软实力。世界的重大变化,要求世界各国政府重新考虑本国的对外政策,花费更多的资源在世界上树立本国的形象和威望,通过软实力的方法树立正面威望[12]。”目前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要增进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信任,提升国家形象,营造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在这种新形势下,单纯的政府层面的硬性援助已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软性援助更贴近民生,更能深入到受援国的社会生活中,对受援国民众对援助国的认识和理解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软性援助对于塑造中国和平、合作和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增强国家对外软实力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
三、他山之石:美国的和平队
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国内对美国对外援助抱怨最多的就是“赢得了政府,但却失去了人民[13]”,因此肯尼迪希望打破传统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援助模式。1961年3月1日,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了建立和平队的特别法令,宣告了和平队(Peace Corps)的诞生。按照肯尼迪的构想,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增强美国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并以此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14]。实际上,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和平队,其建立的真正初衷是“赢得不结盟发展中国家中的人心和头脑[15]。”
截至2011年,已有20多万和平队志愿者为139个东道国提供了服务。和平队的项目划分为六个领域:农业、商业、教育、环境、卫生和艾滋病,以及青年发展,它们占志愿者项目的比例分别为:教育35%,环境14%,卫生和艾滋病21%,商业发展15%,农业5%,青年项目6%,其他4%[16]。据2009年美国一个关于和平队的调查显示:84%的东道国受帮助者和86%的全体东道国国民报告说,在与和平队志愿者工作后,他们关于美国人的观点发生了正面的变化[17]。学者刘国柱认为,和平队志愿者大多数是工作在东道国的基层社会,接触的都是受援国的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和平队成立以前美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即在对外援助中增加了直接面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因素,将关注焦点部分地转向了第三世界的公众,转向普通的老百姓,由美国公民直接向第三世界国家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从而避免重蹈以前“赢得了政府,但却失去了人民”的覆辙。这种“公众外交”正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4]。”学者周琪也认为,“和平队的项目同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和平队采用的是吸引和示范的方法”,所以“和平队从建立之日起,就如同美国对外援助一样,是被当作软实力资源来使用的[18]。”
奥巴马政府更加重视作为软实力资源的和平队。和平队在2010财政年度的预算达4亿美元,2011年更增加到4亿4615万美元,比2009年的预算增加大约1/3。同时,奥巴马重视把和平队的影响力引向东南亚地区,奥巴马的母亲安敦汉姆曾在印尼教英文,所以当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建议由美国的和平队来帮助提升东盟国家人民的英文水平时,奥巴马欣然接受,并于2011年在马来西亚重新启动和平队计划,首批派遣30名志愿者前往马来西亚的乡村教英文。奥巴马也向国会呼吁大幅增加志愿者人数,使和平队能够进入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新增加的20个国家。
和平队作为一种软性的援助手段,它不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和设备,因此没有直接作用于第三世界国家GDP的增长,他的影响力难以量化。但正如《响应世界的召唤:和平队及其最初五十年不为人知晓的故事》(When the World Calls:The Inside Story of the Peace Corps and Its First Fifty Years)一书作者史丹利·梅斯勒(Stanley Meissler)所说:“对于两个志愿者和一个贫穷的少年结为朋友,结果他长大后成为秘鲁总统,你如何衡量和平队的影响?当一名医疗志愿者向阿富汗护士显示对病人展现慈爱和关注是工作的一部份,你又如何衡量其影响?我从不怀疑和平队志愿者对当地人民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四、几点思考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逐步提高,中国已经摆脱以前那种勒紧腰带搞援助的困境,对外援助的资金也逐年增长,对外援助的重要性和独特作用日益凸显。但目前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国家对外援助的财政投入也是有限的,如何充分利用资金,提高对外援助的效果,使对外援助成为提升国家对外软实力的助推器,调整软硬性援助的结构比例,加大软性援助的投入迫在眉睫。
笔者认为,所谓“软性援助”,主要体现在软性内容、软性方式和软性机制三个方面。
(一)软性内容
软性内容主要指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以外的其他援助内容,包括农业、公共设施、教育、医疗卫生、清洁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
目前,中国硬性援助和软性援助的投入力度相距甚远。(如表1所示)。

表1 截止2009年,中国各类对外援助项目数据对比
当前国家决策层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开始注意援助内容的多样化,例如无偿为柬埔寨农村打了1000口民用水井,解决了20多万人的饮水问题;由袁隆平院士牵头的中菲农业技术中心,在帮助菲律宾发展推广杂交稻技术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0公顷示范田平均每公顷单产超过10吨,远远高于菲律宾水稻的全国平均每公顷单产3.4吨的水平[19]。截至2009年底,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在华举办各类培训班4000多期,培训人员12万人次;中国累计对外派遣21000多名援外医疗队员,经中国医生诊治的受援国患者达2.6亿人次。
但是,在软性援助的运用上仍有不少需改进之处。以对外教育援助为例,自2004年开始在海外设立的“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是国家近年来主要推动的内容,也在世界各国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据国家汉办统计,截至2012年3月,中国已经在世界五大洲104个国家建立了835所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派出汉语教师志愿者14000多人次,为2000多所学校200万名学生教授汉语。但是绝大部分的志愿者老师都集中在主要城市的大学中,真正派到广大偏远乡村的寥寥无几。正如笔者在印尼调研所了解到的情况,西加里曼丹是全印尼华人占比例最高的一个省份,全省600万人口,华人约占了20%。主要集中在山口洋、坤甸一带。在华人比例占50%的三口洋市,有20所华文学校,却只有1名志愿者老师。与之相比,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老师除少数是在城市教大学外,大多是在农村教中小学或职业学校,有些地区甚至连所在国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愿去[14]。
(二)软性方式
硬实力的“软运用”(soft use)也是一种软实力的表现。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中美国派出了16000名军事人员,20多艘舰只,100架飞机参与援救;201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队在印尼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救灾演练,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任务,为当地群众实施常见病诊治、疑难病会诊及中医技术展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和健康宣教。医疗队共接诊患者273人次,健康宣教300多人次,发放疾病防治手册1500余份,处理疑难病症5例。
硬性援助的“软运用”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援外工程队与当地民众的矛盾与冲突问题。工程队可以利用物质和技术上的便利条件,义务帮助附近村民修缮学校和道路等,使援助贴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增进中国援建人员与当地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例如援建老挝昆曼公路的工程人员看到当地居民生活比较贫困,很多年轻人无所事事,项目组负责人便主动找到驻地附近的村长,在村里招聘工人进行培训,这些村民学到技术,成了建筑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领到了工资,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20]。
(三)软性机制
目前我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是以政府唱主角的双边援助,而多边援助和非政府组织(NGO)等较为软性的援助方式则很少见。2007年多边援助仅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3.41%,而NGO在对外援助中参与的程度则更低。政府唱独角戏的援助方式,在对外援助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容易被扣上“政治化”的帽子,例如一些受援国的反对派与个别西方国家就曾攻击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破坏了良治,炒作中国的援助是一种“新殖民主义”。
在对外援助机制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国家,NGO的角色非常重要,参与度也非常活跃。2008年,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无偿援助资金高达236.55亿美元,比2003年的113.2亿美元增长了108.97%。与此同时,各发达国家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借助非政府组织渠道来提供官方发展援助,2008年这一金额达到25.08亿美元[21]。NGO参与对外援助可以淡化官方色彩和稀释政治性,可以进入很多政府援助无法触及的领域,这种方式更灵活多样,更能够深入基层,使援助直接惠及平民百姓,这种援助更容易被受援国民众接受,更容易在无形中构造国家的对外软实力。
伴随着新中国60多年建设和发展史的对外援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做出了不同的积极贡献,正如有专家所言:“对外援助推动了中国的海外投资,对外援助是中国分享全球战略资源的重要手段。”冷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赋予了对外援助新的历史使命,对外援助特别是软性援助,触及到受援国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援助国的影响力无形地渗透到受援国最边远的角落和社会最深处,对提升国家对外软实力、塑造中国良好国际形象有着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2011,04.
[2]陈显泗.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J].东南亚研究,2006,(6).
[3]Joseph S.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4]Joseph S.Nye.SoftPower[J].Foreign Policy.Issue 80,Fall 1990.
[5]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6]Hans Morgenthau.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6,No 2(January 1962).
[7]周弘.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9]周弘,张浚,张敏.外援与发展:以中国的受援经验为例[J].欧洲研究,2007,(2).
[10]王世春.提供无私援助促进共同发展[J].中国经贸,2009,(3).
[11]Foreign Aid:An Introductory Overview of U.S.Program s and Policy,p.8.
[12]中国需要更出色“推销自己”[N].参考消息,2010年3月4日,第13版.
[13]刘国柱.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4]刘国柱.和平队与美国对第三世界外交的软实力[J].浙江大学学报,2008,(1).
[15]The Peace Corps in a Turbulent World,Brookings Institution Governace Studies Program,working paper,October 2003,available at:http:∥www.brookings.edu/papers/2003/1015civilsociety_rieffel.aspx.
[16]Peace Corps,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Fiscal Year009,availableat:http:/multimedia.peacecorps.gov/multimedia/pdf/policies/annrept2009.pdf,p.2.
[17]Peace Corps,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Fiscal Year 2009.
[18]周琪.作为软实力资源的和平队重受美国政府重视[J].美国研究,2011,(2).
[19]王传军.中国杂交稻在菲实现突破[N].光明日报,2005-05-17.
[20]吴杰伟.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援助研究[J].东南亚研究,2010,(1).
[21]毛小菁.国际援助格局演变趋势与中国对外援助的定位[J].国际经济合作,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