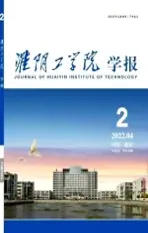近三十年肃“AB团”和“富田事变”研究
2012-08-15赵金平
赵金平
( 淮阴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江苏淮安 223003)
0 引言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江西出现过反共反人民的“AB团”,不久即被人民推毁,其“寿命仅三个月”。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却发生过一起由打“AB团”引发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的爆发,是肃反扩大化和严刑逼供及滥捕、滥杀“AB团”的结果。这一事变的发生,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其教训是十分沉重的。肃“AB团”和因此而来的“富田事变”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悲剧。时隔五十年,当事人回忆起来仍不堪回首。①由于该事件的复杂性,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发起整风运动,总结中共党史的过程中,就没有形成定论,建国以后很长时间里研究者也没有涉及,直到“文革”后沉默才逐渐被打破。
1 肃“AB团”及“富田事件”研究的重新评价
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肃“AB团”及“富田事变”进行研究。尽管当时可以引证的文献不多,同时研究者受政治的束缚,把原因主要归咎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部分有识之士基于肃“AB团”扩大化错误的视角,展现史实,揭露肃“AB团”和“富田事变”中的悲剧,有力地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坚持“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的传统观点。但随着更多资料的发掘和研究者思想的解放,这一观点很快失去市场,一种新观点的影响则不断扩大:肃“AB团”并非犯扩大化错误,而是根本错误,对其责任的追究也不再局限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李韶九等个人原因。
对肃“AB团”问题权威政治结论的突破始于“富田事变”的重新评价,戴向青是引领者。戴向青根据文献记述认为,红二十军在发动“富田事变”后没有投敌行为。事变后中央领导的态度也不一致。以代理书记项英为领导的苏区中央局根据调查研究发出通告,认为不能认定“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斗争,称“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但总前委的领导和任弼时等新的中央代表坚决主张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暴动。1932年1月,周恩来主持作出的《苏区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决议案》指出总前委领导时期对“AB团的认识与处置AB团的方法……种下了肃反工作的错误根基”,认为红二十军的“武装对抗”是迫不得已,虽然也是错误的,但绝对不能以这种反抗作为“AB团”的“反革命暴动”。其最终把“富田事变”的发生归因于总前委代表李韶九,以及王明路线推行者所犯的抓杀“AB团”扩大化错误恶性发展。[1]戴向青的研究说明最初中央对于该事件的态度演变,仍然强调肃“AB团”的扩大化错误,本身并未提出新的结论。但其思考的立足点显然是全新的,史料引用也着重在对红二十军的同情和对肃“AB团”悲剧的谴责。
选择“富田事变”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攻其一点,有利于引起共鸣。但事实证明,不从其源头即肃“AB团”本身分析,单独研究“富田事变”并不能将事实真正搞清,仅仅依据一些领导人的结论也不一定科学。戴文发表后,一些坚持“富田事变”是“反革命事变说”的人很快进行反驳,并提出了更多有关领导人和当事人的文献资料。
阎中恒就提出,“富田事变”是1930年12月上旬,红军第二十军独立营营长刘敌“煽动全营指战员首先由东固发难的反革命暴动事件”。其根据曾山回忆和朱德的回忆,认定军队和地方党内“AB团”存在的真实性,及肃“AB团”的必要性。其同样引用1931年1月16日《苏区中央局通告第2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记述,段良弼等反革命分子在永阳成立所谓“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通缉曾山、陈正人等,并“捏造假信,企图挑拨朱、毛、彭、黄的恶感,来分裂革命势力”等。阎中恒的结论是:总之,“‘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但在最后作者又认为:当然,除了为首分子外,绝大多数参与者不是反革命,至于所谓是“AB团”领导的说法,证据也是不足的。[2]
这一结论前后矛盾,“AB团”领导“富田事变”的证据既然不足,则李韶九抓“AB团”就是错误的。结合其此前大规模的捕杀行为,被冤枉的红二十军成员予以反对是否合理?何以肯定其仍然是“反革命暴动”。不加分析地引用一些回忆资料,乃至带着一些预设的结论去看待和寻找历史文献,就导致这一研究中逻辑的混乱。
此后,愈来愈多的研究者认为,从源头厘清“AB团”是解决“富田事变”问题争论的根本。戴向青根据台湾学者王健民的研究和国内有关文献揭示“AB团”的来龙去脉,认定1927年江西的“四·二”大暴动已经摧毁了“AB团”。对前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事变的观点,戴向青通过文献的广泛发掘和细致梳理,进行了驳斥。作者认为,当年有关“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决议,仅是政治表态,不能作为段良弼等加入“AB团”凭证,其中没有任何确切证据。显而易见,中共1930年3月开始的党内军内捕杀“AB团”及此后的“富田事变”是冤假错案。[3]这是对肃“AB团”全盘否定的开始。
在此基础上,戴向青、罗惠兰等研究者进一步根据有关档案阐述肃“AB团”和“富田事变”冤案产生经过。他们认为,1930年赣西南苏区“AB团”纯粹是逼供信的产物。资料表明,由于当时的主事者认定“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故“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正是刑讯逼供使得捕杀“AB团”之风愈演愈盛,最终导致“富田事变”的爆发。“富田事变”爆发后红二十军的矛头所向是毛泽东,而非中央局。参加事变的领导人在按照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开会时被一网打尽。因此,应该纠正“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错误结论。[4]
2 对肃“AB团”和“富田事变”的细节考证
在“AB团”和“富田事变”主要经过基本清楚后,研究者对肃“AB团”和“富田事变”中一些细节进行考证。细节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针对“AB团”在1927年“四·二暴动”中被彻底摧毁的观点。根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王阿寿证明,1928年初“AB团”仍然存在,但并无反对共产党的内容,此时的“AB团”是和改组派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组织。[5]这一观点因对文献的释读不同而引起了意见纷争,杨宏、戴向青根据原始文献说明,所谓“AB团”都是朱培德强加的,如呈文中所说“搜获AB团重要决议案印刷品多张”、“此次呈送AB团第四次会议议决案”等都是朱培德的话,而所谓的“AB团第四次会议决议案”中根本没有“AB团”字样。朱培德之所以把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定为“AB团”上报国民政府,实因党务指导委员会是蒋介石派到江西省和朱培德支持的改组派进行夺权的组织,朱培德不敢公开和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对抗,于是冠之以“AB团”而进行打击。这些都说明,“AB团”被摧毁后没有重建。[6][7]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AB团”是如何引入党内斗争的?研究者对有关原始文献进行解读,认为这些材料中所谓“AB团”分子都是从反地主斗争中破获的,“AB团改组派多为富农与小商人”,“这些分子有十分之九是地主富农出身”。其实,这些资料中没有证据说明这些人就是“AB团”,而只是把地主富农打为“AB团”而已。[8]
二是,李文林被捕原因的探讨。李文林是江西省行委书记,刘晓农根据朱德回忆,李文林的被捕是因为“AB团”文件中发现李文林的地主父亲亲笔签字的“AB团活动经费收条”,怀疑李文林与“AB团”有关系。李父签收“AB团活动经费收条”这一说法受到戴向青的质疑。李文林被捕的根本原因在江西省行委和总前委间的矛盾,但直接的原因显然与“AB团”有关。②
三是,任弼时等“以毛代项”的建议也是在肃“AB团”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事件。章学新根据有关文献分析,1931年10月任弼时等建议“推毛为书记事”,即是“以毛代项”。根据中央决定,1931年1月15日,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即着手处理“富田事变”。作出“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改组派的暴动”,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处理的意见。但任弼时领导的中央代表团被授命“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任弼时等批评项英,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该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同时,对毛泽东予以肯定。1931年10月,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决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文字依据,中央复电同意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取代了项英的领导。[9]
3 肃“AB团”和“富田事变”的原因和责任
随着这些细节讨论的深入,研究者开始直面肃“AB团”和“富田事变”的原因和责任问题。
单人麟详细分析肃“AB团”的悲剧产生原因:赣西南党组织内部左倾的发展;红军总前委和赣南特委的矛盾;党内对知识分子干部的蔑视;土客籍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终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单人麟总结并发展了前述研究者观点。
一是,“AB团”在1927年“四·二暴动”中已被摧毁。江西中共组织原先也一直把“AB团”作为反动势力内部冲突对待。但1930年5月赣西南特委文件,开始声称发现有“AB团”组织在党内活动,由于对“AB团”知之甚少,因此捕风捉影,“把一切反对分子,一切不满分子,一切犯了错误的人都当作AB团看待”,相信“赣西南的AB团已成立了临时总团部,各路设有办事处”。这就使问题严重地复杂化了。
二是,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党组织矛盾激化。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通过一年内争取江西的左倾计划,对与此意见不同的赣西南党组织产生了错误估计。1930年2月吉安陂头会议,江汉波、李文林等省委、行委领导人和毛泽东在土地分配、政权建设等问题上产生矛盾。李文林1930年5月到上海参加会议,接受了“立三路线”,否定了“二·七”会议方针,撤销了前委派来的特委书记刘士奇,引起总前委的不满,导致双方矛盾激化。
三是,该事件的发生,也同党内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有关。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认为“党在组织上无产阶级基础的削弱,干部分子停顿在知识分子成份上……足以成为右倾思想发展的组织来源”。当时江西省委也接受了这样的思想,红四军前委把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混为一谈。李文林、李白芳、谢汉昌、王怀等学生出身的干部,在事件中均未能幸免于难。
四是,用对敌斗争方法解决当时党内和红军内存在的地方主义、土客籍间、地方党与红军间的矛盾等,也是酿成事变的不可忽略因素。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误传获得了“AB团”文件中李文林父亲签字的收条,怀疑李文林与“AB团”有关系。罗坊会议指责“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要“改造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总前委遂于1930年12月软禁了李文林,派李韶九带兵到省行委抓人,最终酿成了“富田事变”。[10]
刘晓农则进一步把当时地方党和红军之间的矛盾作为肃“AB团”的主要原因研究,探讨地方党和红军党之间矛盾的渊源。作者根据一些访谈和回忆资料以及一些档案探究这起事件的发生原因。但其中不少结论带有主观性,如提及刘真妻子被杀,刘真“迁怒于宛希先,责怪宛希先没有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从此恨结心头”。宛希先被杀后,“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感到痛心,也非常气愤”等,[11]简单地以个人恩怨为主线,解释地方党和红军间的矛盾,以及肃“AB团”和“富田事变”,这样的分析失之于简单。
以毛泽东为中心,探讨其肃“AB团”的原因,开始于戴向青、罗惠兰的著作《AB团与富田事变》。其结论是,赣西南特委肃“AB团”的报告误导了毛,“年轻的总前委领导人看到这些令人吃惊的材料,信以为真,认定赣西南党和苏维埃政府中都充满了AB团”。毛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对比“二七会议”和赣西南特委的“二全会”,指出,“二全会仅是AB团取消派的操纵呢,还是正式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恐怕操纵两字,还不能代表内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献,毛派到富田肃“AB团”的李韶九对参加赣西南特委“二全会”的代表一概冠以“AB团”,显然是依据了毛的认识。[12]但这样的分析也有疑问,毕竟毛是个一贯重视调查研究的人,为何轻信在他的眼皮底下突然间出现如此多的反革命?高华的研究则把肃“AB团”和毛直接联系起来,主要根据许多回忆资料和档案文献的梳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世界,认为其要成为中央苏区的列宁,对挑战他权威的赣西南地方党组织采取极端措施,导致肃“AB团”和“富田事变”的爆发。通过分析毛的性格因素及其把肃“AB团”引入党内斗争的过程,高华认为毛此举既有翦灭离心势力,扫清党内障碍的现实目的,也有建立新社会的理想考虑。③
与高华认定毛发动肃“AB团”的动机不同,绝大多数研究者显然还是认为毛泽东是受地方的误导,并且进一步分析其对肃反的认识和反省。凌步机认为,1931年12月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反省并认识肃AB团的错误,“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毛泽东等人意识到中央苏区肃AB团斗争确实存在许多错误,认识到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开始采取措施使肃AB团降温”。毛泽东为纠正肃“AB团”扩大化的错误也作出很大贡献,“不能因周恩来纠正苏区乱肃AB团错误有巨大功绩,而抹煞毛泽东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13]
4 余论
回顾肃“AB团”事件和“富田事变”的研究过程,由于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在其中的责任因而牵扯到对毛泽东在其中的评价问题,使得研究复杂化。这一问题在“文革”期间的特殊政治背景下显得尤为敏感,截至八十年代许多领导人的回顾中仍然坚持“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同时又否定事变是由“AB团”领导,并把事变领导人和广大下层官兵区分的矛盾做法反映了这一点,这对研究者也是很大的压力,因此一些研究采取的迂回策略是无可厚非的。如从开始阶段否定“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但承认其反对中央的方式错误,到后来对事变的发动持同情和理解;由开始阶段认定总前委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到后来的肃“AB团”是根本错误;由开始阶段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李韶九等个人品质问题到逐步强调总前委以及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也有对毛泽东的批评。研究中通过文献资料的发掘,对事变的详细经过以及项英、任弼时、周恩来等在肃“AB团”事件中的表现都有反映,推动了研究的发展。
肃“AB团”事件中的毛泽东研究显然还不够深入,另外如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红军领导人以及曾山、李文林等的表现也没有专门研究,这是肃“AB团”和“富田事变”研究需要延伸的地方,当然这些都需要文献的进一步发掘。
注释:
①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中的《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
②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调查认为,李文林原名周郁文,他的父亲周作人,既非地主,亦无文化,不可能有签收字据。但以此否定朱德回忆并不合理,因为可能是朱德事后回忆有误,但也可能是当初为抓李文林而制造的谣言,或者是“误传”。见刘晓农《论肃AB团导致的严重后果》(江西党史研究,1989)、单人麟《试析肃“AB团”的复杂原因》(争鸣,199)、戴向青《必须以严肃态度对待AB团问题——评刘晓农的四篇文章》(中共党史研究,1990)。
③高华:对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J].二十一世纪,1999(54).转引自"高华个人网站",网址为: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ztlw/yjzs/000021.htm,2008 -3-25.
[1]戴向青.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J].江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3):15-20.
[2]阎中恒.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J].江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4):49-57.
[3]戴向青.富田事变考[J].江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4):53-56.
[4]戴向青.论AB团和富田事变[M]//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18,119.
[5]王阿寿.从历史档案看AB团组织存在的时间[J].近代史研究,1984(5):254-258.
[6]杨宏.论肃“AB团”的根本错误[J].江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86(3):40-43.
[7]戴向青:论AB团和富田事变[J].中共党史研究,1989(2):10-17.
[8]武国有.论肃“AB团”误区的形成[J].中共党史研究,1994(6):22-27.
[9]章学新.任弼时等提出“以毛代项”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始末[J].中共党史研究,1993(1).
[10]单人麟.试析肃“AB团”的复杂原因[J].争鸣,1990(6):54-57.
[11]刘晓农.红四军前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赣西南党内肃“AB团”的缘由[J].争鸣,1992(3):76-80.
[12]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72,173.
[13]凌步机.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为纠正肃AB团错误所作的努力[J].中共党史研究,2002(4):6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