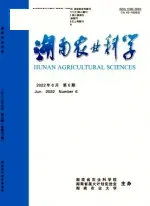环洞庭湖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2012-08-15邝奕轩
杨 芳,邝奕轩
(1.湖南女子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2.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洞庭湖是中国重要的湖泊,由大通湖、东洞庭湖、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4个较大的湖泊水系组成。洞庭湖区水产丰富、航运便利,作为重要的湿地,洞庭湖发挥着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的作用,湖区丰富的水土资源及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在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绿色湖南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1]。然而,近年来人类对洞庭湖的开发、利用的强度超过了湖泊生态系统阈值,导致了一系列生态问题。2011年11月,洞庭湖主要控制站城陵矶水文站水位一度降至21.62 m,为1960年以来罕见的低水位。洞庭湖蓄水量的降低,间接影响到湖泊水质净化功能,水质型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湖区面临的新难题。环湖地区低生态型的经济增长以及湖区民众对洞庭湖生物资源掠夺式的采集加剧了洞庭湖区生态危机,2012年4月,洞庭湖水域出现的江豚群体性死亡事件就是例证。
为了保护洞庭湖生态系统,政府采取了建立保护区等措施来维持洞庭湖的生态平衡。而单纯通过建立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来实现生态系统的维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环洞庭湖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洞庭湖在区域生态平衡中所起的作用才能得到全民认识和根本保护。但是,如果一味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生态的破坏,则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同时洞庭湖生态系统彻底被破坏。因此,寻找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平衡点,选择能实现环洞庭湖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1 环洞庭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要克服“外部不经济”和“市场失灵”,实现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模式就成为了环洞庭湖区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2]。循环经济模式是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来改造传统的社会经济增长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3R原则(减量化、再使用、资源化)。循环经济模式要求在生态大系统中,协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内部各要素,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物质交换,最大限度地利用系统输入的物质和能量,降低系统的物质和能量使用废弃物的输出,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特有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特征,将经济活动构建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式流程,使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尽可能降低至微小的程度。
2 环洞庭湖区循环经济发展思路
环洞庭湖区经济结构中,农业循环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以农户、农业企业、工业企业、第三产业企业为微观主体,以生态园区为循环平台,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系统循环。树立系统的发展思路,在产业内部、产业间实现资源、能量的循环流动,提高资源效率,降低环境污染。环洞庭湖区域经济发展应实现第一、二、三产业有机对接和交融,既要实现产业内的循环,又要实现产业间的资源循环。
2.1 发展立体循环农业
立体循环农业是在土地管理单元上,实现种植的立体生产、种养的立体结合,形成横向延伸、农林牧渔副一体化生产格局。利用农业生产体系中各生物物种间的互利、相克,降低生产废弃物的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立体种植循环模式即综合运用土地利用和技术系统,在空间上合理组合多年生木本植物和栽培作物,诸如林药间作、农林间作和“农—林—药—菌”多作物间作等,形成多级生产、稳定高效的生物复合循环体系。在环湖农田推广稻田养鱼,利用鱼粪肥田、田泥肥稻,同时鱼类可以吃掉稻田中的有害虫类。这样既高效利用了多种可饲资源,又减少了农药的用量,降低了农药残留风险,有效减少了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在湖区退耕还林地区,实行林牧间作,在林区种植经济林,并在林区放养家禽,这样既可以利用家禽灭虫害、吃杂草,其排放的粪便又利于林木生长,减少了化肥与农药的使用,保护了生态环境。利用环湖区丰富的水土资源和基础设施,发展桑基鱼塘,形成“基面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肥桑”的循环生物链,在“桑基鱼塘”系统内实现物质的有机交换,协调发展有机桑、蚕、鱼、菜生产,有效保护农业生物资源。
2.2 以沼气为纽带的循环利用
随着环洞庭湖区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卫生设施的改进和消费行为的变化,绿肥、沤肥等生态肥料的获取难度日益增加,这已成为环洞庭湖区绿色农业发展的瓶颈,而化肥的高密度使用则加剧了农业资源环境破坏的程度。为了解决农村“饲料、燃料、肥料”之间的矛盾,环洞庭湖区应大力发展以“畜沼果”、“畜沼菜”为主的循环模式,以沼气工程为纽带,把养殖业和种植业紧密联系起来,在农业内部形成“养殖→沼气、沼肥→种植→养殖”的循环经济链条,把农村沼气工程作为有效技术措施之一,大力实施有机品牌农业战略,以生态养殖业助推有机种植业。
沼气进入农业循环链条,整合了农业资源,提高了农业综合利用率,上游:畜禽粪便流入沼气池;中游:沼气源源不断供入农户,解决生活供能;下游:沼渣成为高效有机肥和绿色农药,促进有机农业发展。以沼气为纽带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实现了农业生产资源低消耗、经济高产出、污染低排放的良性循环,有利于环洞庭湖区农村的全面发展。
2.3 以秸秆为纽带的循环利用
环洞庭湖区是湖南粮食主产区,农作物秸秆以水稻、油菜类秸秆为主,资源丰富。环洞庭湖区应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因地制宜、多种措施并举、变废为宝,综合利用农作物秸秆资源。应大力推广秸秆还田,努力提高土壤肥力。当前秸秆还田是秸秆综合利用的主要途径,其方法有粉碎直接还田、快速腐熟还田、田间地窖沤肥还田等。秸秆还田简单、方便、易行,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以秸秆为纽带的食用菌生产再循环利用主要模式为“秸秆—牛粪—食用菌—菌渣—肥田”,基本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和废弃物零排放。利用农作物秸秆发展食用菌产业,不仅有效地利用了资源,而且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也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开发秸秆饲料,促进草食畜牧业的发展。环洞庭湖区可以采取青贮、氨化、微贮、揉搓丝化等处理方式,把秸秆转化为优质饲料,为湖区畜牧业发展提供原料。
积极发展秸秆能源。秸秆能源化利用应成为环洞庭湖区综合利用秸秆的新途径。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主要包括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秸秆发电、秸秆沼气(生物气化)、秸秆热解气化、秸秆干馏等。可以建设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站,以秸秆为主料制气,通过管道集中向农户供应炊事燃料。
此外,还能利用秸秆为原料生产多种产品。如木塑型材、人造板、轻型墙体材料、板材、生产活性炭以及秸秆造纸等。
3 环洞庭湖区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建议
3.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环洞庭湖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存在交通、通讯、水电供给等问题。环洞庭湖区发展循环经济,首先要改善基础设施,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应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做好洞庭湖流域的水土保持、退耕还林、退湖还林工作,控制水土流失;继续完善“三网”,构建信息网络服务系统,建设“循环经济信息网”,为从事循环型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农户提供准确及时的产品供求和配套服务信息。
3.2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政府在国债项目安排、资金投入、金融贷款等方面,政策应向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倾斜,引导循环产业发展的方向。在税收政策方面,应调整现有税制,实施变动税率,对无公害农产品实施低税率,开征生态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实现循环产业发展。深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在农村开展消费信贷、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小企业信用贷款,加大对实施资源综合利用和自主治污的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健全信用担保机制,降低信贷风险,创造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参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
3.3 构建完善的循环经济发展体系
3.3.1 构建循环经济发展的文化体系 首先要利用媒体进行宣传,举办大型文化宣传活动,普及循环型的文化理念,在理念上增强认识;其次是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这需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政府层面上构建国民经济生态核算体系,扣除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导致损失的经济价值,建立并实施生态统计体系,督促行业生产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行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二是在生产层面上树立循环管理理念,在实践中积极验证和推进实施。三是在社区居民这个微观层面上,提倡生态消费,将环保理念嵌入消费行为,提倡勤俭节约,杜绝奢侈浪费。
3.3.2 构建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体系[3]加强循环科技队伍建设,应用先进的循环生产技术。建立循环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培训、引进技术推广员,为从事循环产业的农户和生产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构建循环产业新品种、新成果、新技术的实验基地和示范基地,多路径推广、普及循环生产技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和政策环境,促进循环技术的创新。
3.3.3 构建循环经济发展的人才体系 环洞庭湖区要发展循环经济,可针对性地引进专业人才。对于外地的优秀人才,要给予优惠政策,对于急需的专门人才,要特事特办,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大力支持。
3.3.4 构建循环经济发展的区域法规体系 结合环洞庭湖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制定符合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完善规制、鼓励循环经济发展的区域法规体系,为循环经济的高效、有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3.3.5 构建循环经济发展的政府服务体系 政府要提高工作效率,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优良服务。政府职能在管理过程中应实现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创造转变,政府统揽一切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转变,依赖于行政手段运用的行政管理向依赖于经济、法律手段运用的公共管理转变,构建高效运行的基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府服务体系[4]。
[1] 朱 翔.环洞庭湖经济圈建设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 欧阳涛,蒋 勇.洞庭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61-63.
[3] 尚红云,周生军.循环经济发展评价与政策设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4] 邝奕轩.基于社区参与的海口市旅游业循环经济发展[J].特区经济,2010,(11):165-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