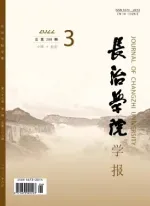电子传媒时代的口头诗学
2012-08-15崔国清杨振岗
崔国清,杨振岗
(兰州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电子传媒时代的口头诗学
崔国清,杨振岗
(兰州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初的口语文化是思维的启蒙时代,具有强烈的“现场感”、“真实性”。人类社会的变迁是从口语文化走向书面文化再到电子文化,但发展并非呈线性特征,文字的出现只是多了一种交流的工具,随之带来了很多“言而无信”的内容。因此口头诗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并没有消失,而是淋漓尽致地结合到现今的多媒体电子传媒时代。
口头诗学;次生口语文化;活态文化;原生口语文化
一、口头诗学的提出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口语作为一种天然的交流方式一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口语是一切语言交流的基础。但是自从文字出现之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把文字当做语言基本形态的顽固偏向。直到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浑然不知文字为何物的文化与深受文字影响的文化迥然有别。伟大的荷马史诗,就是口语时代的巅峰之作。诗人在掌握了丰富的史诗歌唱技巧之后不断歌唱,以至形成了现代无法超越的口头文学的丰碑。甚至在文字产生之后很久,口头诗学并没有丧失它的魅力。他们可以并行不悖的存在于同一个地域之中,而且,书面文学传统并不高于口头传承。在历史上,文字的出现只是意味着多了一种交流的工具。不能把其他的交流形式都代替了。
文字带有天然的反思性,但口头诗学却带有更加丰富的现场感,因为它所要表达的内容都在具体的情境之中,所以更加真实可信。在《易·系辞》中,提出了“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观点。可以设想存在这样一个表意等级结构,语言特别是口头的语言更接近所要表达最为核心的“意”。相对于文字产生以来的若干世纪,口头传承作为最主要的交流方式存在的时间要更为漫长一些。当我们追溯我们的文化之根的时候我们最远的行程只能到达文字产生的“轴心时代”。东西方在那个伟大时代都产生了至今仍然无法超越的文化奇葩。显然是由于两种交流媒介的碰撞所引发的,口头诗学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再往前追溯,那将是一个人类还未完全了解的神秘领地,口头传承在那时独领风骚。
弗雷泽到达那里停靠在美丽的瓦尔登湖畔试图解开人类的最初的心灵密码。一直发展到现在,由最古老的“荷马问题”所引发的讨论直接促发了“口头诗学”的提出。口头诗学是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及其合作者艾伯特·洛德,通过对史诗的实证研究和比较方法而创立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决定性地改变了传统的以书写和文本理解传统的方式。荷马史诗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主要源头,但是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纠结于这样一些问题:荷马是一个人还是一些人?如果有一位叫做荷马的行吟诗人,他是不是盲人?他如何能够创作,记住并且歌咏数以万计韵律整齐,生动感人,语言优美的史诗?他难道是天生的“诗才横溢”还是“死记硬背”?或者“缪斯附体”还是“神经错乱”?“口头诗学”的“程式”概念为我们解开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在没有书面文字可供利用的时代,诗人凭借什么来构筑自己的诗行,数万行一首的长篇史诗又是如何传唱下去的?米尔曼·帕里是“口头程式理论”的奠基者,他的发现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荷马史诗的每一种特征都是口头创作的产物,是其精简原则强制作用的产物。”[1]
帕里深入到南斯拉夫地区,并且做了大量的田野作业。认为“口头诗歌是活态的有机体,以程式和主题来构建,他强调歌的每一次表演,即表演中的诗歌创作。口头诗人属于传统,同时他们又是创造性的艺术家个体。”帕里通过对荷马史诗文本的语言学分析,发现了程式、跨行接句、程式系统以及“俭省的”荷马修辞法。此外,他在文本背后的口头传统研究中又引入了“叙事单元”的概念。“程式”是口头诗学的核心概念,帕里认为“程式是在相同的步格条件下,常常用来表达一个基本观念的词组。程式是具有重复性和稳定性的词组。”[2]1935年,帕里的突然逝世,使得生前的研究计划无法继续。艾伯特·洛德既是帕里的学生又是他最为得力的助手,帕里逝世后,洛德继续老师的事业,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帕里生前的研究计划,还在口头理论领域立下不朽功勋。洛德的著作《故事的歌手》被誉为口头理论的“圣经”。他从表演这一角度出发,研究了程式、主题、故事模式等口头传统叙事单元,对帕里的学术成就形成有益的补充和突破。洛德虽然沿用了帕里对“程式”的概念的界定,但他又补充道:“(程式是)思想和被唱出的诗句彼此密切结合的产物。”[3]口头传统中“程式”的基本特征便是重复性,重复的意义在于构成稳定的诗行,形成一种延续传统的、具有固定意义和固定韵律的表达形式。我们说“程式”的表达、传承不是创作者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的结果,它的传承是时代沉淀的结果,其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字本身,传达着某一个时代的文化内涵。“每一个或大或小的主题,甚至于每一个程式,都充满了意义的光环,这是它们过去产生的语境所赋予的,当这些主题或程式产生之时,传统便赋予了它们以意义……要想理解这种超常的意义,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接触传统的材料或者一定的传统。[4]”
二、电子传媒时代的口头诗学
如果把荷马时代的口传身受的口语文化看做口头诗学的滥觞,那么现在以电子传媒为主要载体的口语文化则是口头诗学的延续和再生。我们可以把第一个时期称作“原生口语文化”,把第二个时期称作“次生口语文化”,“次生口语文化指的是当前正在“讲述的文化”。原生活态文化指的是不知文字为何物时“讲述过的文化”。作为人们体验过经历过的文化,它并非只是简单的作为历史古迹被放置在博物馆或者退回到底层直至消失。按照本雅明的《传统的发明》中来理解:当前“正在讲述的文化”可以通过“传统的选择性”而使其部分地“活跃起来”。因此口语文化包括“讲述过的文化”和“正在讲述的文化”以及二者之间的对话协商。“正在讲述的文化”激活“讲述过的文化”,“讲述过的文化”中的文化基因在“正在讲述的文化”中延续;“讲述过的”文化不仅与“正在讲述的”文化在文化流传的意义上相关联,而且,“讲述过的文化”也是“正在讲述的”文化有选择地创造构成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口语文化实质上涵盖了时间维度上曾经讲述过的文化和正在讲述的文化及其间协商关系所产生的新质。
电子传媒的时代正是“次生口语文化”的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产生的文化是次生口语文化。“次生口语文化也产生强烈的群体感,因为听人说话的过程是聆听者形成群体的过程……但次生口语文化产生的群体比原生口语文化产生的群体大得多,甚至于难以估量——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5]每个人可以利用手机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发送信息,微博上的粉丝可以跨越大江大洋实现亲密沟通。“次生口语文化”恢复了原生口语文化的一些特征,它模拟“现场感”和“真实性”。但“次生口语文化”不是真实的会话,它只是虚拟的仿真会话。这是因为“次生口语文化”的产生是在文字之后,任何一种文化一旦与文字联姻,必然会受到文字的影响,因为文字天然地带有反思性,一旦内化在人们的心里,就会与传统的声音的神奇世界相剥离。
历史证明:每一次大的媒介转型都会带来文明的巨大碰撞,雅思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指的是原生口语文化向书面文化的转换,那么次生口语文化的产生即是发生在书面文化和多媒体电子技术的碰撞之后。新的媒介塑造新的文学样式,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是信息。文字借助手机这个载体发展成为短信段子,手机短信几乎彻底改变了我们日常交流的方式。人们借助于搞笑的、整人的、诙谐的、调侃的信息内容,插科打诨,实现亲昵的接触,因此手机段子不能归入严肃的书面文学范畴,而应该归入新生代的电子文化中的口语诗学。
短信在创作时,可以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包括声音、图像、动画,因而也更接近于口语。图形主要是一些特殊的符号、标点和数字,如“(*^__^*)”代表笑脸,“7758521”代表的意思是“亲亲我吧我爱你”,“88”代表再见,“O”代表的意思是“同意”,就如同人在表示同意应答时的“哦”的口型,而“OO”代表的意思是“惊讶”,这和表演诗学也存在很大程度的关联。手机短信善用修辞,比如:戏仿、铺垫、抖包袱、谐音、方言读法,这些都生动地体现了口头诗学的魅力。“而且手机短信凭借无线光缆,实现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多的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沟通。多在熟人之间,信息的交流性强,反馈直接、快速、集中。传、受双方可以现场把握信息的流向、流量和清晰度等,传者和受者机会均等,可随时交换传播角色。”[6]同时,一些精彩的手机段子大多是来自底层的声音,是压制之后的反抗,比如:“听说你最近很牛逼,普京扶你下飞机,布什给你当司机,麦当娜陪你上楼梯,金喜善给你烧烤鸡,刘德华给你倒垃圾,连我都要给你发信息。”这则信息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的名人聚拢在一起,以戏谑的口吻对他们进行降格处理。从而为发送信息者进行加冕。这类短信凝聚着民间大众的智慧,无情地嘲讽了当权者的权威,现实的规约被轻易颠覆。从而使人们获得一种“狂欢化”的快乐,十分精准地体现了一种贴近人生世界的,带有对抗性色彩的口头诗学的风格。
繁复抽象的书面文化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隔绝了鲜活的生活经验。在审美范畴中表现为一种“静观”式的、“陌生化”的审美风格,把领袖人物和社会名流的名字制作成抽象的清单。而口语文化里没有这样的限制,当我们利用口语表达思想时总会多多少少的贴近人生世界,以便使陌生的客观世界变成人们熟知的人际互动的世界,政治人物和娱乐明星总是时不时地被人们拿来幽上一默。短信可以对社会生活做全方位的景象书写,于方寸之间完成对芸芸众生的形象勾勒。
短信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几种程式化的表述,比如:对于社会的批判以及对于情感的宣泄,短信是我们的“日用品”就如同我们每天要说话一样。正如德赛托所讲的:“我们尽管各不相同,但都必须服从于日常语言,我们如同被赶上了满是疯子的大船,无法逃脱亦无法叠加。”[7]短信就是这样一种日常语言,它勾连起人们的情感,如同一道烛光照亮了文字和印刷术建立的悬置大厦,短信温暖而熨帖的扎根于实在的生活琐碎之中,以上所述均说明短信作为电子时代的产物和口头诗学内在底蕴有深度契合。
口头传承不光作为活态文化存在于偏远落后地区,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融入到了现代传媒之中。“在人类文明的今天,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众多的人群,他们的生存心理和思维方式还滞留在一个口头传统的文化里,我们民族从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时空观或许仍然循环在我们本原的文化河床里。”[8]因此作为一种最持久最纵深的人类表达之根必然沉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从而与电子传媒时代的各种新生媒介产生良性互动。因此电子传媒时代中口头诗学的兴盛并不是要回到“原生口语文化”,“而是试图恢复被文字和印刷术的线条型和单一性所压制的社会丰富性。”[9]我们身处电子传媒的时代,之所以要重新发现自己的口头传统,并不是要天真的回到过去,而是依靠当今时代赋予我们的特殊视阈来发掘口头诗学所蕴含的深刻的生态意识。
三、口头诗学所体现出的生态意识
生态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人们所关注,显然是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遭遇到了巨大的麻烦,从美学角度来看,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范式都是围绕书面文化展开的,而忽视了口头诗学的美学价值,从而使得当今的文化陷入了多方面的危机之中。比如: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技术投机,哲学丧失了本土根基,思想的原生土壤已经流失。追踪其产生的本源在于将知识和文化从其产生的具体情境中分化出来了,进而固定在书本之中。“当代的生态美学强调应该强调文化知识的‘连续性(continuity)’。”[10]环境的延续性引导我们应当将个人的经验和社会的经验相联系,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经验相联系,不断扩展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它强调整体性,主体的介入,而不是静观式的审视。口头诗学既是这样一种在时间维度上是“活过的”和“活着的”诗学体验,在空间维度上是浑然一体的思维方式。它在本质上是移情和参与式的,而不是与认识对象疏离的。对口语文化而言,学习或认知的意思是贴近认识对象、达到与其共鸣和产生认同的境界。口头诗学强调真正说出口的语词总是出现在人类生存的整个环境之中。语词的意义不断地从当下的环境中涌现出来,它把手势动作,面部表情,语音语调以及人类生存的整个环境一网打尽。电子传媒时代为文学的存在刚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活态的可能性,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口语文化的诗学品格。
[1]弗里.口头诗学:帕里 - 洛德理论[M].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
[2]郑培凯.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桂[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
[3]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05.
[4]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213.
[5]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4.
[6]蒋述卓,李凤亮.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72.
[7]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实践的艺术[M].方琳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37.
[8]乔晓光.活态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初探·自序[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8.
[9]张进.活态文化转向与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134.
[10]伯林特.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M].陈盼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05.
Abstract:In the long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the earliest oral culture has enlightened the thoughtof human-being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has very strong“sense at scene”and“realness”.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the human society's culture is generally as follows:starting froMoral culture,enduring long period ofwritten culture and finally reaching the age of electronic culture,however,this process is not as simple as other linear one we are accustomed to,the emergency and use of written language do provide one more tool of communications for human society butat the same time it has produced many“descriptionswithout any realmeaning”.As amode of thought the oral poetics is far froMdisappearing,on the contrary it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sent age of electronic culture after incorporating itself into themulti-media environment.
Keywords:oral poetics;secondary oral culture;live culture;original oral culture
(责任编辑 史素芬)
The Oral Poetics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Media
CuiGuo-qing,Yang Zhen-ga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cademy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20)
G04
A
1673-2014(2012)04-0044-04
2012—05—18
崔国清(1987— ),女,山西朔州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诗学研究。
杨振岗(1974— ),男,甘肃永登县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