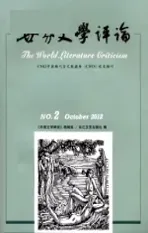关于海外华文文学批评的思考
2012-08-15江少川
江少川
(江少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中文系主任。Email:jiangsc2011@163.com)(责任编辑:张琼)
在谈海外华文文学批评之前,先说说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指中国、台港澳地区以外的他国与地区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这里不包括移民作家用华文以外的语言(如英语、法语等)创作的文学作品。我这里主要探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移居海外的新移民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即通常说的新移民文学,以与早期的海外华文文学与台湾的留学生文学区别开来。同时新移民作家在当今世界也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
新移民文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移民海外的移民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它是在与母国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发展、繁荣起来的新兴的文学品种,它既与中国当代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又受到作家所在的移居国很大的影响。
新移民文学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初也称之为留学生文学,九十年代初,随着《北京人在纽约》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两部长篇问世及改编成电视剧的热播,新移民文学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新世纪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新移民文学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涌现出像严歌苓、张翎、虹影等一批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频频在海内外获得各种文学大奖、在主流文学刊物发表,并改编为影视剧,产生了广泛而热烈的影响。近十年全国优秀小说排行榜的名单中,(从1999-2008年度9年的排行榜),海外作家(全是新移民作家)共9人12篇作品入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项到全项,从末位到榜首的过程。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获2009年长篇小说排行榜首,说明海外华语文学写作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已举办两届,评出了多部优秀新移民作家的佳作。
新移民文学的发展引发、刺激、拉动了国内的海外华文文学文学批评。这些年来,新移民文学批评取得的实绩也值得大力肯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立以来,在近30年中召开了16次华文文学的国际研讨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有口皆碑。国内有两家专门研究华文文学的刊物《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与《华文文学》,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近30年来出版了多本研究华文文学的论文集、专著、教材,一些高校培养了一批研究华文文学的博士生、硕士生。
但是,海外华文文学批评的现状也不容乐观,令人担忧。海外华文文学的双重边缘性必然导致海外华文文学批评的边缘性。新移民文学具有双重的边缘性。就新移民文学而言,它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边缘,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延伸与变异;对移居国而言,它又隶属于该国的少数族裔文学,也处于边缘化状态。海外华文文学的这种边缘性导致它的学科研究的边缘性,迄今,海外华文文学还只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远未形成一个独立、成熟的学科,这就导致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队伍的边缘,这支研究队伍相对比较零星、分散,它来自于文学研究的其他学科领域、如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外语等多种学科,专门从事海外华文文学批评的学者人数还有限。不如其他文学门类那么集中、专门化,都拥有一支较为整齐、庞大的“集团军”。有些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做过一些研究,毕业后,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也不做了。
海外华文文学批评相对滞后,跟不上新移民文学蓬勃发展的走势,对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华文文学的关注与批评也不均衡。对北美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关注就较少,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时、空的隔离,国内的批评家与海外移民作家缺乏了解,缺少沟通、交流与互动。旅美评论家陈瑞琳早就指出:由于时空的阻隔,大陆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达不到宏观的掌控,又容易造成局部的夸张。由于新移民作家身居海外,他们的作品不一定都在国内发表或出版,所以有的作品在国内不能及时读到,有的作家散居海外也不为国内批评家所熟知,批评也就无从说起了。
海外华文文学批评还未形成大气候,缺少理论上的突破与建树,华文文学批评的视野、方法有待扩展。在海内外有影响的批评家还很少,权威的论著还较少见,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反思。
一、构建全球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批评体系
把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来研究,摆脱政治话语的影响,疏离意识形态的约束,构建世界华人都认同的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这是值得华文文学批评界认真思考的课题。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有这么一个小的情节,女儿安慰母亲不要为失去故居而难过时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已成全球人了,妈妈。如果我们和某一具体的地点断了联系,我们不就属于整个世界了吗?妈妈,你明白吗?现在我们无论在哪儿,脚下的土地都属于我们和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区别。”(汤亭亭:《女勇士》,李剑波,肖锁章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98页)实际上她说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语境。旅居海外的诗人瘂弦就提出:构建全球华文文学大格局。我想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应该是这样的。
在对新移民华文文学价值的判断上,评论家杨匡汉的观点值得思索。他说:“对于海内外作家应该有同一的标准,即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标准来判断,在这样的标准面前,不分海内外,不分老少,不能一味地棒杀或吹捧。一部优秀的作品,大致应具有四个维度,即历史文化维度、生命体验维度、艺术创造维度和神性维度,是天地人神四重奏”(金涛:“方块字架起文化的桥梁——海内外作家、评论家聚焦新移民创作”,《中国艺术报》2011年12月7日)。
只要建立了这种全球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批评标准,才能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出比较公允、准确的审美评价与历史判断,而不为在过去“单维”,固有的批评模式所局限、所束缚。
二、要在方法和视角上有所拓展和更新
在构建全球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批评体系下,要在方法和视角上有所拓展和更新。新移民作家移居海外以后,在已有的母国生活经验基础上,又融入了海外的生命体验、他民族的文化因子,获得了开阔的双重文化视野,获得了观察生活的新鲜角度,新的参照。新移民作家前半身生活在母国,中国文化为他们打下了深厚的人文基础,移民后,又直接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创作方法上也有新的借鉴与拓展。新移民作家的文化“身份”与生存现状,都对华文文学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文学批评的对象发生了变化,移植于异域的文学毕竟不同于产生在本土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不能固守已有的批评路子与方法,当然要寻求新的学术视角与更新,寻求新的突破,用多种批评样式与方法进行研究,诸如文化身份、地域文化、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伦理学批评、生态主义批评等等。如“文化身份”就是我们切入研究极为重要的角度。
以写文革为例,海外新移民作家写文革题材,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视野上有新拓展,早些年严歌苓的《天浴》曾经激起读者巨大的震撼。近两年,旅美作家陈谦写文革的小说《流氓犯特蕾莎》、《下楼》,提供了迥异于当代中国作家的新视野,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旅加作家陈河的《布偶》,同样是以中国与西方生活的双重经验,用一种别样的视角写文革,充满神秘主义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这就要求批评者要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去解读、评论海外移民作家的作品,而不能只是因袭老套路去评论海外华文文学作品。
三、宏观研究与文本解读相结合
对新移民文学的批评,既要有宏观的整体观照与梳理,如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格局、文学思潮、文化身份、文学史线索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又离不开作家作品研究,而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这里特别提出研究文本,回到文本本身,仍是文学批评者的重任。认真、细致的解读文本、挖掘文本的内涵,对作家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索,仍要放在重要的位置。海外华文作家有不同的经历和背景,生活在不同的时空及语境中,有不同的创作心理与个性,对他们的研究同样不能用一种标尺,也要因人因作品而异,是非常细致、深入的劳作。作家作品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事实上,当下对新移民作家作品的研究还很不够,作家作品的论文集、评论专著、作家论的出版还较少。对一些理论观念,当然有必要界定、阐释,但过多地纠缠在这些概念上,有时会遮蔽对文学文本缜密的评析。如果缺少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宏观观照就会失去基础与依托。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是文学批评的根本,它也是海外华文文学批评的根基。
四、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
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存在天然的血缘关系、从发生学上看,新移民文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移民潮流中产生的,新移民作家都有着中国背景,其中有些作家出国前已开始文学创作,并有作品问世,他们当时就属于中国当代作家之列。如严歌苓出国前已出版三部长篇,有些作家虽然是移民以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出国前虽未在国内发表作品,但他们的基础教育、大部分人的高等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尤其是自幼所接受的文学启蒙与教育都来自中国文学,承继的是丰厚的中华文化传统。新移民文学与当代文学关系密切,互相影响。研究二者的互补、差异及相互的对接、整合,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刘俊将“海外华文小说”对当代小说的补充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中国人在封闭后重新走向世界时的心态和身影,使中国当代小说获得了开放、外望的补充;提供了在题材的新鲜之外更具“深度”的丰富。刘俊特别强调,“海外华文小说”从整体上对“当代小说”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就是“只有当作家老实地面对文学,还文学以尊严时,才能创作出杰出的作品”。(华文:“从乡愁情结走向文化思考——文学评论家谈海外华文新格局”,《文艺报》,2010年7月8日)我很赞同他的观点。
本土文学批评与海外海外华文文学批评的互动,参照,对话,交流,消除偏见非常重要。这里除了立场、观念外,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第二,文学批评的视野;第三是文学批评的方法。
格非说:“要突破资本——国家——民族三位一体圆环的循环”(格非:“现代文学的终结”,《东吴学术》2010年第1期,第75页),海外华文文学批评要走出粘滞社会现实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局限,构建世界华人都认同的文学价值尺度。东西方意识形态不一样,然而优秀的文学文本,尤其是文学经典都会找到共同、相通的批评尺度。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互为参照,进行比较研究,用汉语这一民族的语言作交流、互动的工具,用文学批评搭建华文文学的桥梁,促进世界华文文学的繁荣,是文学批评者应承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