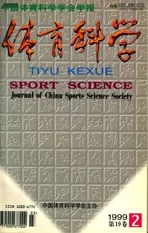论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调查关系
2012-08-15杨海晨沈柳红
杨海晨,王 斌,沈柳红,赵 芳
论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调查关系
杨海晨1、2,王 斌1,沈柳红3,赵 芳4
采用文献资料调研与逻辑分析法,就某学者提出的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应“分离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文化处境”这一观点,从田野调查的目的,调查点的选取与介入,资料的获取与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1)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异邦到本土的过程,而中国的体育人类学一开始便立足于解决本土民族体育的“残存”问题;2)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保持与研究对象的适度张力,“摇摆人”的研究视角较为客观与完整;3)对于田野资料的收集,应该适时地把“现场”与“文献”相结合并加以甄别与印证;4)对于田野资料的客观陈述是阐释的基础。
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田野调查;异邦与本土;局内与局外;现场与文献;陈述与阐释
1 问题的缘起
2011年12月,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在上海体育学院举行的第九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与会期间,笔者在聆听了“体育文化研究”、“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等专题的众多专家、学者的报告后受益匪浅,但就笔者感兴趣的体育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点滴问题存在些许疑惑,如清华大学仇军教授在其“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一文中,提到“体育人类学的实证主义强调亲身的参与和体验获取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基础……,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的体育活动,以及人的体育活动所体现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生活意义,因此,观察人的体育活动必须做到客观准确,这种客观准确通常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其一是分离观察者(研究者)与被观察者(被研究者)的文化处境;其二是在观察中有意识地避免偏见和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尽量获取完整的资料……[19]”。学界对于“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应该做到客观准确”应当不存在异议,但就“分离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文化处境”,笔者认为可能会存在争议,其原因有二:1)如果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文化处境分离得太过清晰,必然导致研究者有意识地避免融入被研究者的文化中,由此便可能会产生对被研究者文化的认同障碍,这样又如何能够做到有意识地避免自身认识的局限性?2)在无法克服自身认识局限的情况下,研究者如何能够做到客观准确地看待被研究者的文化?
2 体育人类学及其研究范式
2.1 体育人类学的沿革
“体育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port或Anthropology of 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是由人类学衍生出来的,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人类与体育有关的文化活动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6]。体育人类学在国外的研究较早,最先见于人类学在竞技体育领域中的运用,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BurnettTaylor)著书《竞赛的历史》(1879)、《论美洲的运气竞赛是前哥伦布时代与亚洲交流的证据》(1896),德国的伍勒(Von Karl Weule)著书《竞技运动的民族学》(1925)等。到20世纪中叶,有关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在北美兴起,学界普遍认为,美国人类学者布兰查德(Kendall Blanchard)和切斯卡(Alyce Cheska)的《体育人类学介绍》(TheAnthro-pologyofSportAnIntroduction)(1985)一书,在体育人类学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地位。随后,日本学者寒川恒夫于1988年翻译了该书,并于1991年到中国与体育人类学者进行交流,又数次对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田野考察。国内学者对于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最早见于1986年谭华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体育与人类学”一文,随后,席焕久、胡小明、倪依克、饶远、陈斌、王跃等专家学者所著的关于“体育人类学”的专著、论文相继面世。2009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在云南召开,我国体育学者经过努力,承办了“发展中的中国体育人类学”和“体育人类学的国际视野”两个专题会议,标志着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开始步入世界最高级别的学术殿堂。
2.2 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是某个学科团体遵守着共同的承诺,接受相似的学科训练,吸收同样的文献,有着共同的直觉和发布研究成果的方式[17]。从人类学研究传统来看,主要关注部落、部族这类非现代的或曰传统的文化。而运用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民族、民间、民俗的原生态体育时,需要从民族的起源、生存、进化和发展的宏观意义上去认识人类体育活动,以此来探讨体育运动文化在人类整个文化制度中的功能及它与文化制度中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学界把之称为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Culture)。要想达到这一目的,采用个案的方式以某一体育文化现象为研究切入点,采用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小样本量的深入访谈(Depth Interview),获得翔实的调查资料,以此来研究这类孤立、罕见、奇特的“小众文化”或“微众文化”,然后由点及面,探讨民族、民间、民俗体育的缘起动力、传承脉络、嬗变原因及发展方向等有着不可比拟的方法论上的优势,人类学把这种方法称为田野调查或田野作业(Field Work)。在确立了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采用文化整体观分析的理论基础及田野调查的搜集资料方法后,则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对一种“小众文化”或“微众文化”进行解释的问题。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被研究者相对于研究者一般都属于异文化(Different Cultures),因此,要想对研究对象做出中肯的评价,运用跨文化比较的视角(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r Perspective)则成为研究的必需。由此,“文化的整体观、田野调查及跨文化视角”构成了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其中,作为民族志的方法——“田野方法”,以长时间的实地考察为基础,建立了学科的基本知识框架[6],因而成为了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而文化的整体观及跨文化视角都是基于田野调查法之上进行的。因此,回到“问题的缘起”这一话题,笔者认为,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探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应当处在一个怎样的关系处境问题上,应该从田野调查的目的,调查点的选取与介入,资料的获取与分析等方面进行研究。为此冒昧成文,就教与仇军教授,同时也希望各位专家不吝赐教,以便把处在发展完善阶段中的中国体育人类学推向更高的理论层次。
3 田野调查研究中的诸问题之辨析
田野调查对于人类学来说,已然超出了研究方法论的范畴,大部分人类学家都认为,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惟一特征。笔者虽然不敢苟同这样的观点,但很赞同英籍人类学家塞利格曼(G.G.Seligman)的观点,他认为,田野调查之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不啻于“殉教者的鲜血对于教会”。田野调查是“与人们所熟悉的死与再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28],在学术成长中,一个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死了,一个职业的人类学者诞生了[27]”,是成为人类学者必须通过的成人礼。虽然所有研究者都认为田野调查对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但对于“何处是田野”[7],研究者是作为“局内人还是局外人”进行研究、研究者在资料的获取过程中应该如何看待“现场与文献的关系”、对于所得资料应该进行“陈述还是阐释”等却一直是人类学界争论的诸多焦点。之于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同样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
3.1 田野调查点的选取——异邦与本土
3.1.1 异邦与本土问题之争
在体育人类学学科体系萌芽之初,无论是从莫尼(James Mooney)关于彻罗基族(Cherokee)人的拍球竞技研究(1890),还是科林(Stewart Culin)的《中国人的骰子游戏》(1889)、《朝鲜人的游戏及中国和日本相应游戏的注解》(1895)、《北美洲印第安人的竞技》(1895),到之后的贝斯特(Elsdon Best)的《毛利人》(1924)中关于新西兰土著民族的游戏活动,再到后来具有学科创建意义的美国人类学者布兰查德和切斯卡的《体育人类学介绍》(1985),及寒川恒夫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的长期调查等,都显示了主要把“异邦”或“异域”的、尚未被开化的、在少数民族之间出现过的体育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迹象,而关于“本土”或“家乡”的研究成果极少。因此,大部分学者则从一开始认为,体育人类学研究对象应当为“异邦”或“异域”的那些“被压抑和被忽略的非主流的[3]”体育文化现象。
3.1.2 异邦与本土问题之辨
当初的人类学家和体育人类学家为何要选择远离自己熟悉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呢?笔者认为,这或许可从早期人类学的研究目的中寻找答案。早期人类学者把调查的异域看成是让他们做梦的地方,在他们眼里,那些新西兰的毛利人、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国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等,都是不开化的野蛮人,那里存在着没有被工业文明摧毁的原始文明和田园精神,他们期望通过对这样的田园精神的探究,恢复本民族文化的久远历史,改进西方文化的自我认识。于是,后人所见到的人类学的主要概念都来自于异邦部落社会[1]。但由于早期研究者的文化局限性,他们免不了以西方文化为制高点的殖民主义倾向来俯视被研究者的文化,研究的结果是对“野蛮人”的文化歧视[19]。随着人类学家对田野作业研究的反思深入,后来推动他们去调查的原因,是因为担心原住民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或在帝国主义政治的控制下,会迅速的改变或消亡,为此,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反对文化的霸权上来,期望通过将主流文化(研究者自己所处的文化)与非主流文化(被研究者所处的文化)的比较,还原一个真实的、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于读者面前,但无论从哈登(Haddon)对新几内亚东南岸的原住民文化(1898—1899)的研究,还是博厄斯(Franz Boas)对爱斯基摩人文化(1883)及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1897)的研究来看,这一时期的人类学者们依然固守着对异域的调查理念。
在人类学科已然成熟的西方国度中,学者们难以避免地因受既已形成的体系、结构、观念的制约,而易于流于众口一词,而在一个学科疆界尚未勘定的国度中,学者们有更多的自由去创造[22],因此,缘起于西方文明社会的人类学传到中国后,这样的“异邦”研究情结则有所改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且民族、民俗众多,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让人类学者可资选取研究的“自然环境”素材丰富,因此,与西方国家的人类学者把更多的焦点放在异邦不同,国内人类学者一开始便把目光锁定在了本土的研究上。如费孝通先生1935年前便开始对广西大瑶山进行田野调查,后来返乡到当时的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江村)进行调查,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的建议下,于1938年完成“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的博士论文,该文首次研究了本土的、文明社会的人类活动,改变了之前人类学只研究异邦的、原始文化的历史,在人类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的体育人类学家的研究轨迹,同样在依循着中国人类学家的足迹前行。在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中,首要强调的是基于对“残存”体育文化形态的纵向研究,而其意义就在于旧有的“残存”体育形态,包涵的习俗和观念,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阶段后,或者将其从原来的社会引入到其他形态的社会中后,它并没有消失,仍具有原来的意义和机能,即作为前一个时代的遗制还顽强地继续存在着。这种体育文化形态的“残存”延续正是当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所必不可少的资料依据,而这一点与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及方法的利用是紧密相连的[2]。因此,无论从最开始的谭华先生的“体育与人类学”一文,还是到后来胡小明、饶远、席焕久等人的《体育人类学》专著,主要都是为了致力于如何解决中国本土民族体育的“残存”问题而进行的研究。于是,在渐成体系的中国体育人类学理论指导下,出现了大批以本土为研究个案的田野调查文章,如李志清的“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杨世如的“原始礼仪竞技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苗族独木龙舟竞技文化调查”、罗湘林的“对一个村落体育的考察与分析”、涂传飞的“一个村落舞龙活动的变迁”、郑国华的“禄村变迁中的传统体育流变研究”、杨海晨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变迁与传承研究——以广西南丹那地村板鞋运动为个案”等。
尽管国内学者的体育人类学研究主题已经本土化了,但不难发现,相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依然还处在传统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之内——对少数族群体育现象(异文化或称为他者文化)的研究。因此,从目前来看,体育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是应该在异邦还是本土的话题,早已经被中国多数从事体育人类学的学者所忽略,而他们大都则认为,在田野作业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问题,倒是更值得引起关注。于是,笔者接下来提出了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应当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的探讨,这也是笔者对仇军教授提出的“分离观察者(研究者)与被观察者(被研究者)的文化处境”的思考之核心。
3.2 田野调查的介入——局内与局外
3.2.1 局内人与局外人问题之争
美国斯坦福大学汉学人类学家沃尔夫(Arthur Wolf)早年曾到台湾三峡镇的一个村落做调查。他发现该地区闽南系统的汉族家庭中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间,其童养媳成婚比例高达40%以上(1968、1970、1981)。童养媳婚姻对西方人而言,是一种很特殊的婚姻类型,经他对该地长达数年的研究后,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其中一条认为“童养媳婚姻是乱伦禁忌的来源之一”。沃尔夫的重大发现,对中国人来说实属不易,因为人们很难把这种自三国时代就有记载①《三国志》:至十岁,婿家即迎之长养为媳。的童养媳婚姻与乱伦禁忌联系在一起。从这一事实来看,作为局外人来研究异文化似乎有更强的敏锐性。而在更早的20世纪初期,英国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ourt Haddon)在答普里查德(E.E.Evans Prichard)提出的“如何做田野调查”时指出,“调查者的举动应像绅士一样[5]”。笔者显然对这样的观点不敢苟同,因为,如果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保持这样疏离的关系,田野调查肯定将无法得到很全面的、客观的资料。但笔者同时认为,如果研究者仅仅是就自己土生土长家乡的一些民俗仪式及其衍生出来的民族传统体育进行调查,而没有以局外人的眼光进行审视,必然会缺乏一种对本身从小习得的约定成规的乡风习俗的自然张力,从而使调查者处于“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境地。由此,便在体育人类学界产生了“调查者应该是局外人(outsider)还是局内人(insider)”的争论。
3.2.2 局内人与局外人问题之辨
前面已经提到,无论是人类学还是体育人类学,在自发轫之初,便以研究异文化或少数族群文化为着力点。那时候的人类学著作,大多是根据游客、航海家、传教士以及殖民地官员的口述或记录写成的。再到后来,即有一些有志于世界民族志的学者乘船到遥远的国家去,但是到达目的地之后,他们几乎都不下船,只找一些本地人了解情况而已[21],可以说,这个时代的田野调查者,是完全意义上的局外人,如很多学者把早期德国的科尔曼(G.Klemm)和斯宾塞(H.Spencer)称为坐在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正是缘于此。这种人类学的学术研究陋习直到本世纪初才有所改观,代表性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对新几内亚东北的特步兰岛(Trobriand Islands)的田野考察,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他才被迫得以长时间地居住在当地,学习当地人的语言,询问有关他们的生活风俗,直接观察当地人社会生活的全部面貌,并于1922年撰写成了人类学历史上划时代的巨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oftheWestern Pacific)。因为这样的机遇,马林诺夫斯基发明出来一套新的田野考察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并被后人冠之以田野调查的功能论。尽管马林诺夫斯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强调“三同”生活(同食、同住、同劳动),但他依然认为“访问者应该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他不能研究自身的文化”[4]。依据他的观点来看,田野工作者的身份本应属于局外人,只有局外人才能看到“异文化的模式”[8],只有在别的社会文化体系中,人类学者的观点才能充分的客观化,才能避免由社会制约造成的偏见。但随后他的学生——日本人类学者柳田国男对老师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只有局内人才能理解被研究的文化,因为,如果作为局外人进行研究,那么,研究者很难了解和体会仪式的内涵,更无法对那些微众文化做出客观的评判。这一观点与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1955)一书中强调的“你不是‘他者’,你怎么能够研究‘他者’”及《庄子·秋水篇》中惠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观点相似。只是,在柳田国男之后的一代学者把这种观点扩展至“东亚共同圈”,视自己为中国和朝鲜的文化局内人,可见,这里的局内人与局外人并没有客观的分界线。
人类学辗转至中国之后,对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争论似乎有所中庸。李亦园和乔健等人结合自身的田野工作实践,提出局外人和局内人相结合的看法[11]。随后,李亦园进一步阐述了在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应该有四种不同程度的参与性观察:1)局外的观察(complete obser-vation)。这是比较客观的,其分离度也高,但卷入田野的程度最低;2)观察者的参与(observer-as-par-ticipant)。参与到田野中,参与其中的程度适中,仅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同时保持了客观的立场,这种参与观察最难做到;3)参与者的观察(participant-as-observer),已经深深地参与进去了,但还能够有一些观察,有一点客观;4)完全参与者(complete participant),很多的是完全的主观参与,只能形成主观价值判断[10]。
从中国现有的体育人类学研究个案成果来看,这四种田野调查程度都有所涉及,而笔者认为,其中以“观察者的参与”和“参与者的观察”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如涂传飞与罗湘林两人的博士学位论文执行的均是参与者的观察,他们的研究对象均为自己的原籍江西的涂村和湖南的刘村;而以胡小明为代表的华南师范大学与以杨世如为代表的贵州民族学院众多学者共同对黔东南苗人的独木龙舟进行了多次调查,则包含了较多成分的观察者的参与。但细心的学者们应该从他们的著作中发现,无论以何方式进行的研究,他们的参与性调查均在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进行了摇摆:前面两位依循的是从局内人到局外人的路径,而后面两位依循的是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路径。
笔者很赞同这样的观点: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研究者既是观察者,又是“土著”的一部分。只有既能进入到被研究者的立场,又能从研究者立场考虑,努力把握参与观察的参与程度,保持与调查对象之间的适度张力状态,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所研究文化的内在逻辑和运行规则[14]。因此,笔者认为,在运用体育人类学基本原理对民族、民间、民俗体育活动进行研究时,单一的作为局内人或是局外人进行研究是很难做到客观全面的,最妥当的方式应当是局内人能够“出得来”,而局外人能够“进得去”。于是,这种作为“摇摆人”的田野调查,便可以回答仇军教授提出的“分离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文化处境”的观点妥当与否的问题了。
但如果问题讨论到此就戛然而止的话,笔者认为,这仍然无法较好的回答仇军教授提出的“观察中有意识地避免偏见和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尽量获取完整的资料”的问题。于是,笔者继续提出了,在田野调查资料获取时研究者应该如何处理现场资料与文献资料关系的讨论。
3.3 田野调查资料的获取——现场与文献
3.3.1 现场与文献问题之争
从当今人类学界的研究焦点来看,关于“田野与文献”是在诸多矛盾中讨论较为激烈的问题之一。自人类学萌芽之初始的殖民时期,如前面提到的科尔曼和斯宾塞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大都并不是基于现场到文本的过程,而是依循从文献到文本或从听说到文本的路径。于是出现了“表面上研究印度的人类学家坐在英国的档案馆里,研究巴西的却被发现在葡萄牙,研究印度尼西亚的在荷兰[18]”等现象。但自殖民扩张和学者们眼界的开阔后,他们发现以前用文献证明文本或用文献对接历史的研究,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特别是在研究无文献记载的原住民文化时,仅靠一些星星点点的文献或从传教士口头表达出来的主观化的信息来进行研究,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马林诺夫斯基通过长期在特步兰岛的参与性观察著成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后,适时地为人类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指出了新的道路。于是,这一时期很多人类学者开始把“现场”视为圭臬和法典,更有甚者走向了资料搜集的另一端——无视历史文献的存在,而意图从现场发现全新的意义。只是,通过这样长期的参与性观察来获取完整的资料并不是所有人类学者都有条件做到的,马林诺夫斯基仅仅是这样个案中的特例。由此便引出了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资料获取过程中,要想获得完整的资料,文献是否也属于田野,现场与文献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的讨论。
3.3.2 现场与文献问题之辨
在人类学研究的历程中,像布鲁思·特利格(Bruce Trigger)一样的人类学家曾经严厉地批判了在使用文本文献资料和口头文献性证据时的研究范式,“他们孤立地看待文献资料,全然不顾当时的场景,也不去判断记录者与口译者的偏见和能力,于是导致了文献资料使用过程中的傲慢与无知”(1976),其结果是在这个时代的人类学者研究异文化时,自我标榜并断章取义地以“文明”载体——基于文本或口头文献的文字,来书写别人的历史。如现今的非洲印象,很大程度上便因此而来,而至今在很多西方人心目中保持的“神秘、落后”中国印象,大抵也是受这种西方文献偏见的影响。其实,早期很多学者之所以以文本文献或口头文献为依据,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自觉尚未达到现今的高度。另外,还有可能是基于文献研究难以胡编乱造,因为书本、报章俱在,别人可以覆按,而田野作业有类似的领地特征,某一地域往往就是某一研究者或某一团队的天下,有时候胡编乱造也多是无从籍考。此外,还有学者往往将田野作业简化为“搜集第一手资料”或者加上“参与观察”,但随着实践的进行,发现这样的研究范式并不完美,有时候在费时费力之后,得到的却是与以往文本文献或口头文献相似的结论,于是,学者们开始审视文献在田野调查中的意义。
由于中国史料和传说丰富,因此,在人类学及体育人类学研究历史成果中,有很多主要依靠文本文献和口头文献进行研究的例子,如定宜庄博士的《最后的记忆》中,在16位生于20世纪初的旗人老年妇女田野访谈基础上,再以文献辅以人物实物、书信、民歌民谣、家谱摘抄等进行的研究;韦晓康撰写的《壮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王岗和王铁新合著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朱国权的《云南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等,均采用了文本文献的研究范式,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审视。但从体育人类学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发现,很多所引用的文本文献均来自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那两次对民族、民俗、民间体育的抢救性挖掘,部分研究者采用的是拿来主义,而没有辩证地吸收。为此,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期刊部主任李晓宪教授总结多年的审稿经验后认为,现有很多体育人类学、体育民俗研究成果等缺少实实在在的现场田野,并在众多场合呼吁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应该加强参与性观察。
笔者也认为,进行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时,现场参与性观察的田野作业应该是研究的基础。但是,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之下,许多民族传统体育业已势微,她们存在的文化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已经消失,这时候学者们如果全部依靠现场的田野进行研究,势必很难探究该微众体育文化的传承脉络及流变过程,更无从谈起研究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因此,此时的学者应该适时地把“现场”与“文献”相结合,毕竟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民间体育搜集整理工作已经汇集了大量的文本。当然,体育人类学者应该意识到,这当中也不乏有 “格式化”①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以马克思民族理论为惟一指导思想的,调查与研究材料中存在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的文本,因为以前的文献对民族、民俗和民间体育的详细记载很少,且所采取的史笔角度,也与现代体育人类学的视角有区别,这个时候就要求研究者对文献就行甄别了。而如何进行甄别呢?笔者认为,辨别应该基于现场,因为“文献的精神、文化的历史本身是叠合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25]。为此,笔者认为,体育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中应该包含参与性观察和对田野的文本文献的研究,“田野”并不仅局限于“野外”。从田野研究的立场来看,就要求研究者要从现场与本文献两个维度来高度关注体育人类学意义上的“证据提供”(documentation)[12],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体育人类学资料收集过程,才能获得翔实的、可进行比较研究的田野调查资料。
从前人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人类学者关注更多的是如何选取田野调查点、如何与当地人保持适当的人际关系来获取资料,而对所获田野调查资料在回归书房之后的分析,则较少有涉及。笔者认为,无论是田野调查点的选取,还是田野调查的介入角度及资料的获取来源等,都只能算是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调查基础部分,要想让所研究的文化现象真实、客观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最终还得落实到田野报告的撰写上来。因此,对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方式、角度及所借用的理论支撑等,都是决定了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准确地看待被研究者的文化”的又一重要环节。
3.4 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陈述与阐释
3.4.1 陈述与阐释问题之争
现代人类学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要想客观准确地看待被研究者的文化,那么,在对文化现象进行表述时应尽量地采用“当地人的观点”,极力避免用“我看到了什么”,而应用“单纯的、自白式的话语”进行描述;1936年费孝通在江村进行调查时,还主张调查者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的事实自动地在上投影。但吉国秀认为,这种话语与行为的表述方式,表面上给予研究对象以较大的话语空间,表面是较为客观的陈述了研究对象的真实文化生活,但实质上是将人类学者的话语混同于当地的非学术声音,目的是为了强调人类学者作为陈述者的地位,因而在其著述中听不到来自研究对象的声音[8]。针对这样的弊病,有人类学者提出,在对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上,不应是把田野作为既定的实事进行陈述,而是要自觉地把自己和对方都纳入到研究,以达到使自己的文化理解对方文化的地步[3]。因此,为了便于揭示研究对象背后的文化意义,田野工作者必需把自己和研究对象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叠合”,在资料分析基础上识别每个人的每一段访谈资料的关键特征和主题,然后打破田野调查时空的限制,进行资料的整理和归类,最后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故事文本[15]。即如格尔茨所说的,在对异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中,不只是对原始实事进行捕捉之后,将之化为面具或雕塑带回家呈现在读者眼前,而是应该对意义的推测以及从推测中得出的解释性结论。因此,对于研究对象的文化进行阐释是非常有必要的[16]。
3.4.2 陈述与阐释问题之辨
其实,人类学者们之所以对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是应该以陈述为主,还是以阐释为主存在争议,主要出发点都是基于“如何才能尽量客观呈现研究对象的文化现象”上。而笔者认为学者们的争论,是因为陈述与阐释本身在方法论上都存在的不完善所致。
田野工作者所从事的是一种“阅读”他人兼“阅读”自己的阅读工作,田野工作者已成为制造叙述文化意义的主体,而意义则是田野工作者对以往的专业理论、田野实践和人生阅历的消化理解,是对现实田野生活的体味能力和对它的内容与形式的把握能力的集中展示。只是,在这样的集中展示中,研究者不论从哪个角度来呈现研究对象,都是用学者自己既定的标准来看待所研究的文化。而这些标准,是研究者通过自认为客观的“技术的”观点,来构造社会文化的样式。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导致以物质器具为基础的功能论,最后把所有宗教的、伦理的和哲学的术语的变化,都予以实用主义的合理化,解释成社会演进的结果,构造研究者所认为的文化进化模式[3]。但在现有田野调查研究范式下,对田野生活的集中展示又是进行阐释的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田野资料的分析主旨,首先应是尽量恢复田野工作者从事资料搜集工作时的生活化语境,恢复这些资料赖以生存的独特文化环境,使后来的阅读者同样能获得理解田野工作者叙述田野资料时的特殊意识,尽量减少对田野资料文本的模糊认识。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他的晚年提出人类学是“文化的翻译”这一概念,即人类学家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贴近所研究的对象人群的群体思维,把异族观点“翻译”成自己文化中等同的观点[23]。笔者同时认为,在对资料进行展示时,为了避免产生主观影响,应该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自己的调查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信息是怎么收集的,哪些材料是报道人陈述的,哪些是研究者从中整理和领悟出来的等等,这些都是构成田野调查研究的重要部分[13]。其次,学者在参与研究对象的行为实践时,应兼备局内与局外两种意识,在经过反复地比较研究以后,得出概括性的结论,这时学者对民众知识的解释,既不是学者原来的书斋解释,也不是被调查者的具体解释,而是能体现民众文化逻辑和整体文化脉络的理论解释。通过这一解释,学者不但可以了解民众知识的重要性,而且能够认识民众知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构架和工具作用[3]。这种局内与局外意识,用格尔茨在其《文化的阐释》中的观点即是“好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应是由详尽的、多样化的阐释组成的多样性作品,应该透视嵌入在一个特定文化中各个层面,用对多层面的描述来揭示它们”[26]。
现阶段运用体育人类学视角来进行研究时,主要是从民族的起源、生存、进化和发展的宏观意义上去认识民族、民间、民俗体育活动,以此来探讨体育运动文化在人类整个文化制度中的功能及它与文化制度中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个案的研究形式,因此,研究者总是希望看到个案在当地文化的原始面貌,获得最质朴的真实[11]。基于这样的原则,从前人关于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个案来看,很多学者都力图展示研究对象的客观事实,如杨海晨在对广西南丹那地村板鞋运动的缘起观点进行展示时,针对是何人发明板鞋的问题举例了4种不同版本的田野调查资料[24],以求让研究更具客观性,这样的撰写方式也让阅读者“更能理解田野工作者叙述田野资料时的特殊意识”。但事实上,多数学者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笔者认为,无论研究者花多么长的时间去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研究者最终只能是触到的能让我们理解的那一小部分文化现象,而更多的文化现象则被研究者所遗漏;此外,无论多么力求做到客观的研究者,但都始终无法超脱于自己的文化自发,于是或多或少会带着个人化的知识结构背景与先天的情感体验(特别是现代体育的情结)去描述他所研究的文化现象。
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让田野调查资料更具客观性,为了克服分析方法本身的先天不足,采用陈述与阐释相结合的思想是较为妥当的,此二者在方法论上能够起到相互纠缠的、重叠的、交叉且印证的作用。应该说,未来人类学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将是多种方法的混合[23]。
4 结语
体育人类学脱胎于人类学,而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因调适而形成的众多流派,导致了人类学者们对田野调查各环节的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在人类学及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调查关系中,无论是田野调查点的选取与介入,还是田野资料的收集与分析,都不会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屡试不爽的、万能的理论范式。可以预见,关于本研究因“分离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文化处境;如何能够做到客观准确地看待被研究者的文化”等所引起的争论仍将继续,而体育人类学也正需要这样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与百花齐放的学术机遇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1]艾伦·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M].王建民,刘源,许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73.
[2]崔乐泉.体育人类学的又一新作——《体育人类学》评介[J].体育文化导刊,2006,(10):84-85.
[3]董晓萍.田野民俗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杜博思.从“局外人”到“局内人”[N].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10-11-15.
[5]何星亮.关于如何进行田野调查的若干问题[D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29a82e010088e5.html.
[6]胡小明.体育人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3,37.
[7]黄剑波.何处是田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若干反思[J].广西民族研究,2007,(3):66-71.
[8]吉国秀.发展与论争:人类学视野中的田野工作[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2(4):21-24.
[9]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56.
[10]库恩.必要的张力[M].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5.
[11]李亦园.关于人类学的方法[A].乔健.我的人类学研究的经历和体会[A].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8.
[12]李亦园.田野图像[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103.
[13]李志清,虞重干.专题研究与田野调查——少数民族体育研究的途径[J].体育科研,2004,25(4):23-26.
[14]廖明君,巴莫曲布嫫.田野研究的“五个在场”──巴莫曲布嫫访谈录[DB/OL].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forum/viewthread.php?tid=81&extra=page%3D10:2006-08-01.
[15]刘朝晖.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J].民族研究,2005,(3):101.
[16]刘海涛.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诸对矛盾与“主客位”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08,28(3):46-51.
[17]刘中一.田野工作资料收集的若干问题[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4(5):25-29.
[18]玛丽·德舍纳.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之“定位过去”[M].骆建建,袁同凯,郭立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81.
[19]仇军.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融合[C].上海:第九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2011.
[20]容观夐.关于田野调查工作——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研究之七[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1(4):39-43.
[21]王铭铭.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2]徐杰舜.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王铭铭答徐杰舜问)[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33.
[23]杨海晨.民族传统体育的变迁与传承研究[J].体育科学,2010,30(12):34-41.
[24]尤金·科恩,爱德华·埃姆斯.文化人类学基础[M].李富强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15.
[25]朱炳祥.“文化叠合”与“文化还原”[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2(6):2-7.
[26]GREERTZ,CLIFFORD.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M].New York,Basic Book,1973:3-30.
[27]R F ELLEN.Ethnographic:A guide to general coduct[M].London:Harcourt Brace Company Publishers,1998.
[28]WALLTER GOLD SCHMIDT.Anthropology and the coming grisi:Autoethnographic appraisal[J].Am Anthropol,1977,79:293-308.
Relationship of Field Work i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Sport Anthropology
YANG Hai-chen1、2,WANG Bin1,SHEN Liu-hong3,ZHAO Fang4
With a notion that we should separate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observer and the observed locate being the guidance of the research,we are trying to analyze the objective of field work,the research place and the approach to collect information by using the method of both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The result shows that 1)while,from the big picture,the anthropology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the foreign to the indigenous,the anthropology of sport in China was at first focusing on the remedy to the remaining problem of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2)the researcher should keep the tens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swing man”should be objective and complete;3)we need to combine the“scene”and the“document”during the collection of filed information,and also we should identify them to make confirmation;4)the objective statement of the filed inform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illustration.
anthropologyofsport;researchparadigm;fieldwork;theforeignandtheindigenous;insideandoutside;sceneanddocument;statementandillustration
G80-05
A
1000-677X(2012)02-0081-07
2011-11-11;
2012-01-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TY022)。
杨海晨(1977-),男,回族,湖南武冈人,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与组织行为,E-mail:yhaichen@guet.edu.cn;王斌(1971-),男,甘肃兰州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Tel:(027)67868159,E-mail:bwang@mail.ccnu.edu.com;沈柳红(1977-),女,湖南武冈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与传播,E-mail:284275487@qq.com;赵芳(1975-),女,广西桂林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法学、体育社会学,E-mail:zhaofang75@sina.com。
1.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9;2.桂林
电子科技大学体育部,广西桂林541004;3.玉林师范学院体育系,广西玉林537000;4.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4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Guilin 541004,China;3.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Yulin Normal University,Yulin 537000,China;4.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