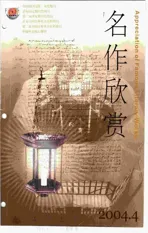文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探索实验:宁肯长篇小说《天·藏》
2012-08-15山西王春林
/ 山西_王春林
2010年,中国小说界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如同《天·藏》《身体课》这样一批具有突出的现代主义文体特色的长篇小说的异军崛起。如果说《身体课》的文体突破,还可以简洁地表述为秦巴子以心理精神分析为文本叙事核心的方式取代了传统意义上以故事情节为叙事核心的艺术表现方式的话,那么,宁肯的《天·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在文体叙事方面的表现就无疑是更其炫目耀眼更其令人倍感难以捉摸把握的。面对无论是精神内涵抑或是形式表现都极其深奥繁复且具有强烈文体创造性的《天·藏》,我最直接的阅读感受,就是一方面充分地意识到了小说文本的思想艺术魔力所在,另一方面却又有一种强烈的无所适从难以进入的感觉。如果说宁肯此前的几部长篇小说比如《蒙面之城》《环形女人》等作品,已经在小说的文体上有所探索,那么,他的这一部《天·藏》,无疑标志着作家在小说的文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探索实验方面已经走向了某种极致的状态。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如同《天·藏》与《身体课》这样一类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坛的联袂出现,乃在根本上标志着当下中国现代主义长篇小说的写作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天·藏》在叙事层面上的双重结构与情节层面上的双重故事,如同坛城的布局一般相互缠绕纠结在一起所构成的立体艺术图景,可以被看做是这部极具探索性的长篇小说文体上最根本的特征所在。应该注意到,在《天·藏》的第11章“坛城”的开头部分,曾对坛城进行过一种不失生动有序的描述:“坛城,一个复杂而深奥的意象”,“‘坛城’在梵语有‘圆圈’的意思,藏语中还有‘中心与边缘’的意思。坛城有圆的,方的,有二维的,三维的,但无论二维还是三维,‘中心与边缘’的原则一定存在。坛城的四面代表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由中心和四边组成一个汇集宇宙能量的地方”。小说中的双重结构与双重故事相互缠绕,互为“中心与边缘”,最后形成的自然就是一个类似于“坛城”的艺术空间。宁肯借助于叙述者的叙事话语所特别强调的“坛城”是“一个复杂而深奥的意象”这句话,对于我们更深入地切入理解小说文本,我以为,确实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在这里,叙事层面上的双重结构,主要指的就是小说中的正文部分与注释部分以相互交叉的方式逐步推进故事情节。与一般的小说中注释只是作为正文的补充性说明不同,在宁肯的《天·藏》中,就直观的感觉而言,注释部分占据了相当大的一个篇幅。如此之大篇幅的占据,就使得注释部分已经不复是一般意义上的注释,而是远远地超越了所谓补充说明的价值层面,极为有效且有机地参与到了小说的整体叙事过程之中。
必须指出的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如同《天·藏》这样采取如此一种叙事结构方式的小说,两条不同的结构线索会以一种可谓是泾渭分明的方式分别推进各自的情节故事,然后,在某一个交叉点上发生碰撞交汇,再进一步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天·藏》的情形却绝不相同,正文部分与注释部分不断地相互交叉碰撞,不断地离离合合,二者实际上是以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携手前行,以此来推动小说的叙事不断向事物的纵深处发展演进。这样看来,注释部分的实际功能其实已经不再是注释,而是作家宁肯一种带有极大创造性的有效叙事手段。同样不容忽视的另外一点是,在小说所采用的双重叙事结构之外,也还有对于感性和智性双重叙事话语的混杂运用。具体到小说文本中,所谓的感性叙事话语,就是指那些主要讲述人物故事的叙事部分,而所谓的智性叙事话语,指的就是感性话语之外那些以哲学、文化等为主要谈论内容的理论性叙事部分。如果说《身体课》在文体上的一大创新之处,就在于秦巴子主要以一种对人物身体及心理精神性的剖析彻底取代了小说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中心,如果说智性叙事已经构成了《身体课》的主体艺术形态的话,那么,到了《天·藏》中,实际上占有相当大比重的智性叙事则是化零为整地如盐入水般融入到了小说的整体叙事历程之中。以至于,你甚至很难简单地把智性叙事与感性叙事的成分有效地区分开来。这样一来,《身体课》的艺术形态当然就显得相对单一一些,而《天·藏》的艺术形态则无疑要丰富和驳杂得多。我们之所以在面对《天·藏》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无所适从的感觉,其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实际上,与感性叙事相对应的,正是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情节层面上的双重故事中的人物故事部分,而与智性叙事相对应的,则是双重故事中那些引经据典的关乎藏传佛教、德里达、弗洛伊德等哲学、文化的讨论部分。当然,宁肯的睿智之处在于,他并没有让这些智性叙事的成分漂浮在人物故事的层面之上,而是让这些成分以有机的方式彻底地融入到了人物的故事之中。二者之间分裂感的消弭,一方面使得《天·藏》的文体具有了一种特别的创新意味,另一方面却也给读者的阅读进入,制造了不小的接受障碍。很显然,秦巴子的《身体课》也罢,还是宁肯的《天·藏》也罢,这类在文体上有着突出新意的长篇小说文本,从根本上说,只能是一种不可读性的文本。缺乏一定知识储备的读者,缺乏浓烈文学兴趣的读者,恐怕大多都会望而却步的。然而,一旦真正地进入《天·藏》所营构的艺术世界之中,真正地得以一窥其精妙的艺术堂奥,自然就会充分感受到文本所散发出的艺术魅力。虽然不能说宁肯与秦巴子他们的小说创作缺乏感性的色彩,但某种更高层次上的理性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读他们的小说作品,之所以往往会感觉到有某种浓烈异常的哲学意味存在,其主要原因盖在于此。然而,在一味分析强调《天·藏》文体创新性的同时,我们也得注意到,长篇小说某些传统的基本要素依然在小说中有着突出的表现。比如,对于诸如马丁格、格维尔、于右燕、教练、诗人等若干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同样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然了,相比较而言,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刻者,无疑还是王摩诘与维格这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形象。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辨析一下宁肯对于西藏文化的强烈探索兴趣与其小说诗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毫无疑问,不只是这一部《天·藏》,从宁肯的写作历史看,应该承认,西藏文化对他的思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以小说艺术的形式对于复杂精深的西藏文化作出积极的探索,始终是宁肯内心世界中一种无法摆脱的情结。固执地把自己重要长篇小说的故事背景放置到西藏,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对西藏文化作深入的不厌其烦的探究,都可以被看做是其西藏情结的现实表现。既然如此,那么,宁肯此种不无顽固的西藏情结对其小说的精神内涵,甚至于对活跃于其笔端的人物形象的影响,也就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即如王摩诘与维格这两位人物,西藏文化在他们身上所留下的印痕就是特别鲜明的,但是,他又必须让自己的西藏情结最终服从于小说诗学的要求。比如说,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就是小说诗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让自己无比服膺的西藏文化在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又不妨害到人物性格的完整有机性,对于宁肯这样一个西藏文化的极端热爱者来说,正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方面。实际上,如果从小说诗学的角度来看,《天·藏》一个十分突出的艺术成就,就在于宁肯充分地潜入王摩诘与维格的人性世界深处,对其人性的复杂性进行了格外深入的探究与表现。
即如王摩诘,他之所以从内地来到在一般人看来是偏远异常的西藏,其社会身份显然是一位志愿支教者,所以,他自然会进入学校,成为一名教师。但真正促使他远赴西藏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他内心中对于西藏文化的真心热爱。不难看出,王摩诘是一位对于哲学与文化(不仅仅是关乎于西藏的哲学与文化,而是总体意义上的一种哲学与文化)有着相当透辟理解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设若不具备如此精深的文化知识储备,他就无法与马丁格、格维尔进行高层次的精神思想对话。须知,他们之间高层次的精神思想对话,对于《天·藏》这一小说文本整体叙事的成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就是这样一位可谓智慧超群的现代知识分子,却居然是一位虐恋者。在与女性的交往过程中,王摩诘必须依恋于来自于女性的鞭打折磨才能获致某种高潮体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曾经刻意地强调过王摩诘对于“制服”的迷恋。“制服”是什么?如果联系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我们就不难明白,所谓的“制服”,其实与国家机器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至于,一说到“制服”,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警察(巧合的是,王摩诘远在内地的前妻,身份就是一位警官),联想到暴力。王摩诘为什么如此迷恋暴力?在他的虐恋习性形成的背后,具有强烈的暴力特征的现代国家机器究竟发生了多么大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思考,我以为,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王摩诘实际上早已被扭曲了的人性世界,进入宁肯在《天·藏》中所精心营构出的那个不无诡异神秘色彩的艺术世界。我们所谓的人性深度云云,事实上也正体现在宁肯对于王摩诘如此深邃的内心秘密的洞悉、触摸与表达上。
再如维格,如宁肯自己所说:“她在寻找自己,她是特别开放的,她站在三种文化的交接点上,哪个方向都可以去,她始终在寻找确认自己的身份,藏族、汉族、西方,在接纳、开放中,她的身份一度出现过迷失,她感到好困惑。”(《存在与言说——王德领与宁肯的对话》,《天·藏》代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应该承认,宁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维格的心灵困惑所在,辗转于多种文化之间而最终无所适从,正可看做是维格的精神与生存困境之所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还得注意到维格与王摩诘之间的情感关系。很显然,如果王摩诘不是一个无法正常进入爱情世界缺乏了爱的能力的虐恋者,那么,他毫无疑问就会是维格情感上的上佳依托。但很遗憾,王摩诘不幸正是这样一位被扭曲者。维格最后疏远王摩诘,应该说与此有极大的关系。读完《天·藏》,我个人觉得有一点需要与宁肯兄讨论的是,在他看来,维格之最后成为博物馆的解说员,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表达了维格最终解决了自己文化身份的疑虑,最终还是回归认可了西藏文化。我知道,宁肯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充分体现出了他自己刻骨热爱西藏文化的一种文化理想。但就我个人的理解认识,我却觉得其中恐怕更多地还是体现着宁肯自己一相情愿的文化意志。怎么样才能够安妥维格那颗躁动不安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灵魂,我以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对于维格最后对西藏文化的回归认可,我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我以为,如果宁肯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没有定论的结尾方式,或许要更加切合生活与艺术的规律一些。那样的话,在文化与情感上最后都无所皈依的维格,事实上就更加具有了悲剧性的色彩。而悲剧,则毫无疑问是一种更加切合于宁肯审美理想的艺术形式。我们注意到,在小说的注释部分,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句叙述话语:“一场成功的对话与一场失败的同居——大致是可以对这部小说作结论的。”某种意义上,这句话其实精辟地概括了宁肯《天·藏》的基本故事构架。能够把这样的一句话演绎成《天·藏》这样一部艺术上非常成熟的带有强烈文体探索性的长篇小说佳构,所充分说明的,当然就是宁肯一种超乎寻常的艺术创造能力的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