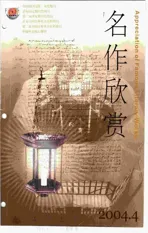李清照词中的“焚香”意象
2012-08-15吉林伏涛李晓絮
/ 吉林_伏涛 李晓絮
李清照才华横溢,宋代王灼称其“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宋〕王灼:《碧鸡漫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8页),套用其词可谓之:“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下引李词,均自本书,只注明词名)李清照被称为婉约词宗,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书写内心最本真的情感,以优美的言辞发露深刻的人生启示。“焚香”在李清照词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一意象,我们可以探析女词人内心深藏着的柔情和浪漫,寻绎其心魂悸动与美好希冀。
作为艺术符号的“焚香”
语词的选择出于表达的需要,同时亦是词人的一种偏好,而从惯用语词中可以探究词人的心灵节律与微妙情思。在李清照词作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即是“焚香”,现把相关词句援引如下:
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小髻鬟松。(《浣溪沙·莫许杯深琥珀浓》)
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忆秦娥·临高阁》)
薄雾浓雰愁永昼。瑞脑销金兽。(《醉花阴·薄雾浓雰愁永昼》)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
玉鸭熏炉闲瑞脑,朱樱斗帐掩流苏。(《浣溪沙·髻子伤春慵更梳》)
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念奴娇·萧条庭院》)
沉水香消人悄悄,楼上朝来寒料峭。(《木兰花令·沉睡香消人悄悄》)
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鹧鸪天·寒日萧萧上锁窗》)
归鸿声断残云碧,背窗雪落炉烟直。(《菩萨蛮·归鸿声断残云碧》)
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满庭芳·小阁藏春》)
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袅残烟。(《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
记得玉钗斜拨火,宝篆成空。(《浪淘沙·帘外五更风》)
沉香烟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
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
诗、词等文学作品都是由艺术符号构成的,符号学的奠基人卡西尔就认为“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或“符号体系”(〔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艺术符号与日常言语符号的差别不在手段而在目的,前者表现美感,后者表现概念。艺术符号是艺术化了的语言符号,比一般的语言符号要更具体、更生动、更具有灵活性。质而言之,艺术符号就是借对一种客观事物的描绘对情感加以象征性表现,给情感形式找到一种客观同构物(异质同构)。“焚香”就是这样的艺术符号,我们不妨先审视一下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意象——“香炉”。“女性生殖器则以一切有空间性和容纳性的事物为其象征,例如坑和穴,罐和瓶,各种大箱小盒及橱柜、保险箱、口袋等。船艇也属于此类。有许多象征是指子宫,而不是指其他生殖器官,例如碗柜、火炉,尤其是房间。”(〔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7页)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火炉是女性器官的象征,我们同样可以在这种意义上对“香炉”加以解读。“焚香”即使香炉保持一种温热状态,作为艺术符号,它的隐含意义可以理解为使女人有男人的陪伴。进而,“焚香”这种行为可看做爱欲宣泄的一种象征性表现,它给独居女性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
细看上面所引用的词句,三首《浣溪沙》皆为李清照前期词作,都是典型的描写“闺情”之作。而《醉花阴·薄雾浓雰愁永昼》更是世人皆知的名篇,抒发的同样是闺中思情。这些作品的主题大致可以理解为“闺中思人”,都是李清照在与丈夫分别时所作。在那些离别的日子里,以及丈夫亡故后李清照独自滞留南方的岁月中,孤独和哀愁始终萦绕在词人心头。夫君不在,香炉犹存;夫君亡去,“焚香”继之。词人仿佛在用焚香这种行为来填充内心的空虚与落寞,它可以改变闺中气味,让人感到温馨,甚至还是一种性心理的代偿。在李清照的词作中,除了“焚香”外,还出现“梦”、“床”这样的艺术符号,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些都是被压抑的力比多的象征,代表一种原始冲动。
翻看其他词人的作品,温庭筠《菩萨蛮》云“夜来皓月才当午,重帘悄悄无人语。深处麝烟长,卧时留薄妆”,这是对美人半夜独睡的描写;其《更漏子》又云“玉炉香,红烛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则是描写一个孤独的少妇,不梳理,少粉黛,在空寂的房子里对雨难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男性词人笔下的“焚香”常常和无所事事的女人形象联系在一起,她们不用为生计操心,其全部心思就是等待某个男人,或者满怀幽怨地思念他,或为他的负心而痛苦。李清照似乎也不能免俗,但她并没有停留在空空的思念和无望的等待中。李清照既非失意嫔妃,也非风流艺伎,更非小家碧玉,这就意味着“焚香”在其词作世界中呈现出更深刻的意味。
作为文化仪式的“焚香”
我国焚香习俗起源甚早,古人为了驱逐蚊虫,去除生活环境中的浊气,便将一些带有特殊气味或芳香气味的植物放在火焰中烟熏火燎,这就是最初的焚香。随着社会的发展,焚香逐渐被神化,从一般生活需要发展到宫廷、宗教、圣事、圣地需要,变得既庄严又神圣。真正的焚香膜拜起源于春秋时期,最早服务于诸侯王的朝仪,宫室、朝堂、议事厅必焚香。还有一种说法,焚香膜拜起源于道教,除表达敬意外,焚香亦被视为与神明直接沟通的方法。
换一个角度来看,“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9—70页)这样的思维就是互渗,也就是两者存在一种认同关系,或者说异质同构。例如波罗罗人自夸是金钢鹦哥,这不是说他们死后会变成金钢鹦哥,而是他们认为自己是长着羽毛的鸟。“存在物和现象的出现,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发生,也是在一定的神秘性质的条件下由一个存在物或客体传给另一个的神秘作用的结果。它们取决于被原始人以最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想象的‘互渗’,如接触、转移、感应、远距离作用,等等。”(〔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0—71页)无疑,“焚香”也可以看做“互渗”的方式之一,成为原始社会及至文明社会的一种膜拜仪式,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如前所述,李清照的“焚香”在艺术符号的意义上是一种爱欲的象征和宣泄。进一步来看,在词人对爱欲的宣泄与“焚香”之间也形成一种互渗关系。“焚香”成为词人自己的一种文化仪式,其中包含着她的怨恨和不满、苦痛和辛酸。通过这种仪式,其内心得到一种暂时的满足,能够排遣掉一点对丈夫的思念,还能成为她默默叨念的“咒语”——命令丈夫快点回家,“唯有归来是”(《青玉案·一年春事都来几》)。
如果说爱欲的宣泄是对等待的被动接受,那么这种文化仪式就是对等待的主动还击。这正是李清照的“焚香”不同于他人之处,流露出其独特的个性。在其前期创作中,她与丈夫只是暂时分别,恩爱夫妻即使小别也会思肠百结、充满期盼,希望丈夫能尽快回到自己身边。本应缠绵的夫妻由于各种原因不能长相厮守,这对于写下“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丑奴儿·晚来一阵风兼雨》)这种词句的李清照来说,该是多么的痛苦。因此,我们对于李清照前期词作中“焚香”的理解可以偏向于爱欲的象征。李清照后期创作的基本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她已经失去了丈夫并且背井离乡,在这样的情况下,“焚香”更应该在文化仪式的意义上被理解。后期词作中,“床”、“梦”这样的艺术符号也已经被“酒”所代替。随着社会时局的变迁、人生境遇的变化,词人的心境也由希望和思念变为愁苦和凄凉。“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寻寻觅觅》)此中之愁,已经不仅仅是闺怨的离别之愁,更兼有国恨与家愁,是乱世离人难耐的孤独、无穷的落寞。《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云: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烟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一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据《金石录后序》,赵明诚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八月十八日卒于建康。这是一首悼念亡夫之词,结合李清照当时的心境,我们对词中“香断”、“玉炉寒”的含义理解得会更加深刻。夫亡国破,天涯孤旅,颠沛流离,此时的处境与昔日的快乐时光相比,可谓天上人间。曾经好强的女性在生活的多重磨难的打击下,心灰意冷,了无生趣。“玉炉寒”说明女词人的心已经死了,烟断香消,一切皆成过眼云烟,再怎么期盼,人也不会回来。爱火不再,心香怎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