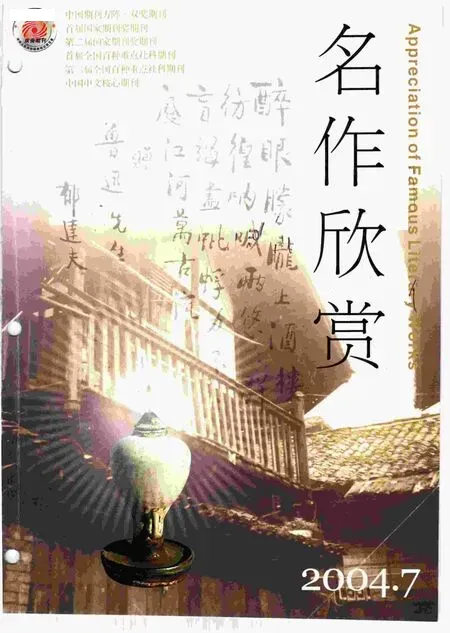诗人的黄昏
2012-08-15/欧南
/ 欧 南
克尔凯郭尔在那本描写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痛苦地抉择的《恐惧与颤栗》中说过:“每当个人由于进入普遍性而感到无力将自己作为个体来维护的时候,他就是处于一种精神磨难之中。”亚伯拉罕被深深地围困在一个悖论之中,他无法在信仰和伦理中求得一种平衡,他被一种深沉的悲剧牢牢地控制住了,现实和精神世界那种无法调和的紧张和令人窒息的恐惧,使他不自觉地成了一个悲剧英雄。克尔凯郭尔写道:“悲剧英雄因他的道德德行而伟大,亚伯拉罕则纯然因他个人的德行而伟大。”
个人的德行是克尔凯郭尔对亚伯拉罕悲剧的一个注脚。显然,它不是那种纯粹放弃自己而进行膜拜的一种仪式。宗教的真正力量产生于人的内心,否则,悲剧将缺乏足够的内涵来验证它的悲剧性。人们可以苟且在一种普遍的荒诞和欺骗中寻欢作乐,无所用心,而一旦想反抗这种荒诞,那么他必将被一层无形的力量逼入险境。个人在普遍性的世界中只能保持一种持续的力,而这种徒劳的力反观出这个世界在本质上的不完美。对于诗人来说,这种力来自于从古至今诗人内心的一股神秘的暗流,它不断地出现,成为超越时间的一种心灵存在。
善与恶只是一个庸常的概念,它无法在更深的意义上接近人的本质状态。人的内心其实隐藏着一种普遍的混乱,诗人大多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而日常生活表现得更多的只是一种形态;一种在特定时刻所反映出来的心境,就像一棵摇曳的树一样,它的静止只是由于风平浪静,而狂怒就取决于风暴的力度。
对于读者来说,也许并不在乎一种经典性的诗文本,屈原和荷马不是每一个时代的人必须去阅读的。阅读有它的时间性和区域性,随着年代的流逝,审美的主体或许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对表现方式的感受性却大不相同,尤其是在现代,严肃意义上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沉湎在一种近乎封闭性的写作状态中,希尼所说的“内心流浪”正在被更多的作家所体验着。而这种相对的“封闭性写作”正在以失去绝大部分读者的兴趣作为代价,写作成了一种噩梦,一种存在的,或者抵抗死亡的方式,虽然这种封闭性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但它却难以激起大众的兴趣。
布罗茨基曾经说过:“如果艺术(首先是对艺术家)有所教益,这便是人类的单独状态。艺术是最古老同时亦是最名副其实的个体的事业,无论人自觉与否,它在人的身上培养出独特性、个体、分离性的意识——于是使人从一个社会动物转化为可感的‘我’。”张曙光的诗便具有这种封闭性的个人性特征,这首先取决于他并不试图为大众写作。在他的诗中,面对的不是一般的读者,或许可以说,他对真正意义上的读者的兴趣要比数量上读者的兴趣要大得多。这种写作意味着一种不幸,一种背离,甚至会遭到忽视和冷淡。诗人和读者虽然是相互选择的,但诗人并没有培养读者的能力,读者的阅读能力取决于整个社会中人文修养的一个基本的层次,取决于人们是否会安静地倾听,而读者的数量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但过于嘈杂的人群却以忽视诗人的存在来验证这种封闭性写作的合理性,如果一个诗人没有意识到大众必然的冷漠,那么,这种写作本身会遭到质疑。清醒的写作是可怕的,他会使写作者经受无休止的痛苦和折磨。
诗人经历了这种荒诞,他的意识使他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他要选择的不是那些平常意义上的人,他要对话的或许是一道风景,一条弯弯曲曲、阴暗的街道,或许只是一杯酒中的倒影,他沉湎在这种话语中,感受到虚无的压力。
让我们沉思死亡,并且记住
那一串长长的名字——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亲友
或一切先于我们死去的人
这是我们唯一的能够从事的工作
除了祈祷,除了在树木凋零的风景中
和冬天寒冷的夜晚
写下我们的诗句
(《四季·冬》)
在张曙光的诗中,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浓重的虚无色彩和颓唐的心境,但这种虚无并不是建立在否定一切、否定生命意义上的一种姿态。诗人可以以一种面貌出现进而博得一片掌声,事实上,这种诗人相当多,而大多数的先锋诗人多以这种姿态出现在诗舞台上,他们可以给人们以新颖奇特的感觉,但并不一定会引起更大的兴趣。对于我来说,最吸引我的诗是能够被反复阅读、反复解释、反复激起我内心冲动的诗,而它又是无法言说的一种直观的入迷。
诗人的感知是微妙的,而他区别于哲学家的工作就在于,他并不试图去寻找答案(事实上很难找到甚至根本就没有答案),他用哲学家寻找答案所花费的时间来营造一种气氛,一种给读者千人千面的神奇的阅读效果,像李商隐著名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种奇妙的句子迫使读者不自觉地进入到神游的幻觉中,并剥离现实世界所谓的真实,谁能证明现实世界不是一个梦,不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空洞的虚无呢?
张曙光明确地感受到了这种虚无,它没有时间性,也没有地域性,它是人类内心的一种感觉,一种沉思后下意识的空白,就像一个棋手在紧张的思考后常常会有的意识空白一样,以至于根本就不知道棋应该下在哪里,这是一个高手才会有的经验。
张曙光的虚无是一场被苦难的泪水冲刷之后遗留下的阵痛,他的很多诗都在反复地吟诵他的童年、家人和友人,在他的心境中既有感动,也有长期被寂寞压抑后的冷漠。但他诗的特征却是温暖的,这种冷漠掩盖不了诗人本质上的善良和良知的触动。一个阅读者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虚无才能发现文字背后的真实感情,正像但丁《神曲》的背后,不是按照自己的好恶将人打入地狱,而是对人性弱点的同情。
苦难既然是人间常态,诗人就应该去面对它。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罪恶史,没有一种动物比人类更无耻却又更智慧了,诗人鄙视无耻甚至放弃那些邪恶的智慧,这是一个具有良知的诗人的品格,他由于同情而痛苦,虚无仅仅是对一种没有结局的反复而表现出来的惘然。
这一行必须重新做起
学会活着,或怎样写诗
还要保持一种高傲的孤寂,面对
读者的赞美,挑剔,或者恶意攻击
写诗如同活着,只是为了
责任,或灵魂的高贵而美丽
一如我们伟大的先人,在狂风中怒吼
或经历地狱烈焰的洗礼
然而,一次又一次,我这样说了
也试图这样去做,但有什么意义
当面对着心灵的荒漠
和时间巨大的废墟(《责任》)
怀疑使得诗人的心灵变得沉重和阴郁,甚至阻碍了他行动的步伐。诗人在现实中可怜的处境并不像哈姆雷特说的“这个时代是脱了节的,却偏偏我有责任去拯救它”。诗人的无奈是痛彻心扉的,命运使他充当着一个感知者的角色,却没有能力使感知转换成一种力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的全部的信仰和崇高只对自己负责,他的命运只能完成一次悲剧的撞击。
诗人已经无法再回到拜伦的年代,也无法回到唐朝盛世去经历那种灵魂勃发的激情,一个剑客,或者一个歌舞伎都能使庸常的生活爆发出一种神性的光芒。但诗人依然存在,他面对着与他一样孤独的酒杯,已经没有了幻想。
我们向往着永远逝去的美好时光?或者
它们不过是一场幻梦,或我们在痛苦中进行的构想?
也许,我们只是些时间的见证,像这些旧照片
发黄,变脆,却包含着一些事件,人们
一度称之为历史,然而并不真实(《岁月的遗照》)
在张曙光的诗中,他提炼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经验,并以一种平静的咏叹来揭露生命的悲剧性意义,而他凝重的叙事性风格常常将读者带入到一种情绪中,这是他诗歌的一个基本的特征。相比于那些鼓动性,或者呐喊性的诗来说,他的悲剧显得更为沉重和痛苦,我们感觉诗人已经不自觉地被一种恶劣的情绪所控制,他去寻找、去苦苦地追寻生命的真实意义,但迎来的却是一个更大的虚无、一个没有梦的梦想和一种没有命题的活着。诗人甚至不愿去欺骗一下自己那颗易感的心,使得诗流露出一种假象中的快乐。诗人的世界是破碎的,他对苦难显得更为敏感,对不幸有着强烈的共鸣。
每天,几乎每天,我在这条街上
匆匆走过。僻静而肮脏
旧式俄罗斯建筑和黝黑的树木,以及
一间间新开的美容厅和小吃店
挂着漂亮的招牌和冷清的生意
一本没人翻阅的旧杂志——
历史,逝去的繁华和悲哀
在白昼和变化的街景中沉积
如果你愿意,那些老人会告诉你
流亡的白俄贵族和穷音乐家的轶事
但现在衰老了,他们和这条街
在初冬麻痹的阳光中
像中了魔法的石头,坐着
沉默,孤独,而且忧郁
(《一条旧时的街:外国街,1989,11》)
这些苦难的流亡贵族,难说不是你将来的影子。张曙光从人类的苦难中感受到生命的不幸、悲剧和孤独,他写下了这一切,也疏远了喜欢理想的读者。在张曙光的世界中,理想的虚幻性也许比客观的事实更可怕,人们从一条街上走来,从一个天真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伤感的大人,从希望变成虚无。人总是要长大的,而长大的成人却再也找不到那条他曾经熟悉的路。
大众常常只是一个徒具符号意义的生命个体,他们像一块块碎石一样铺洒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诗人便是一个捡石头的人,他发现了活着的荒诞,发现了生命无始无终的徒劳延续,他想改变这种无意义的重复,这促使了理想主义的产生。但可悲的是这种仅存的理想主义也被现实碾得粉碎。现代诗人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们很多都是躲在家中的先知,诗人的舞台早已被现实挤压到一间狭小的屋宇中,而那些徒劳无益的诗朗诵会已经越来越像一种小圈子里相互安慰式的“沙龙聚会”,诗人们在里面声嘶力竭地倾泻着剩余的激情,而门外的路灯依然不屑地睁大着昏暗的眼睛。
张曙光选择了一种沉思冥想式的生活,选择了一种叙事性的语言来诉说他的故事和对世界的感悟,他领受了一份清醒的圣餐,他的困惑是每一个诗人都能感受到的那种无形的命运之网,他太清醒了,而清醒对一个诗人来说多少是一种不幸。
没有人相信我说的一切
没有人。在我说话的时候,人们
只是在笑,谈论着天气,或漫不经心地
注视着广场的鸽子,它们在啄食
或发出咕咕的求偶声,没有人相信
我说出的一切。孩子们跟在我的后面
投掷石子,像当初对待年老的塞尚
当黄昏收拢起橄榄树的叶子
城墙上的石头陷入对历史的沉思
牧人们细数归来的羊群,酒吧里
弥漫着浓烈的烟草气味,但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