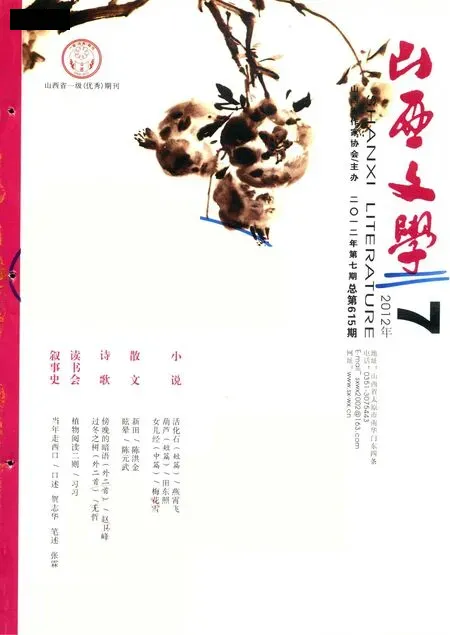植物阅读二则
2012-07-26习习
习 习
卢梭这个老头儿讲给我的——读卢梭《植物学通信》
奇怪的是,印象中,卢梭从没年轻过,他仿佛一直是个博学固执又忧悒的老头儿。他的忧悒会随时从文字中跳将出来——琐琐屑屑真实的怨愤、怀疑、忧伤,叫我觉得,卢梭这个老头儿其实非常单纯可爱。忧悒浓雾一样拉扯在他通常的日子中,他个人情趣的十分孤单的快乐被浓雾重重包裹,这叫人有些悲伤,因为他传达快乐时,你会在想,或许是竭力逃避时的强颜欢笑。读《植物学通信》时,在感受这本书中的老卢梭的时候,总让人想起《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中的那个老卢梭。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我购于1986年,那时的我,除了能读出老卢梭一些散步的情节及碎散的想法外,一定无法更深地理解那本书,后来,扉页上有了这句话:“2009年3月重读,颇得益”。2012年,为了对应正读的他的《植物学通信》一书,我又重读了《遐想》中的“散步之七”,书目录的要目这样勾勒这节的内容:“植物学畅想——并非人迹未至的地方——旧日的重现”,再读这一节,我发现老卢梭在这节文字中谈植物很少,大部分内容依旧在抒发忧悒之情和忧悒之思,他不停地强调寄情植物的释然,可是,一个已然超脱的人怎么会不断强调这种情绪呢?这一节中有个叫人玩味的情节,老头儿散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非常静,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陡峭的断岩,也有很多稀奇的植物,一种狂喜攫住了他,他暗自认为他前所无人地深入到了这个偏僻之地,像“哥伦布第二”,“我来到了一个就连迫害我的那些人大概也找不到的无人知晓的隐蔽所了,一种高傲的情思立刻涌进了我的遐想。”这时,他忽然听到一种似曾熟悉的撞击声,原来,离他几十步之遥,是一个工场。此刻,他先是生出了回归人群的惊喜,继而惊喜被痛苦取代,他认为即使自己躲进阿尔卑斯山的洞穴中,也逃脱不了那些执意加害于他的那些人的魔掌。在这段稍显荒诞的情节中,卢梭非常细致地描写了自己的心理变化,让我深刻而清晰地感受到,老头儿在孤独散步、遐想时内心密布的忧伤和脆弱。
这本小书正文前有一张黑白插图:生长着树木花草的山野间,老卢梭身着燕尾服长筒袜戴着波浪银白假发套拄着木棍(看不清究竟是否是木棍,也许是很考究的文明棍,但我觉得一个落魄的人,又那样喜爱山野和植物,就算是西装革履,拄一根粗糙的木棍也不过分),仔细端详着手里的一株植物,画下配了《遐想》中的几句话“每遇见一株新草,我就得意地自言自语,‘瞧,又多了一种植物’”。从看到这幅画起,我脑海中的卢梭便一直是这个样子,直到读到《植物学通信》这本书。这本书正文前还是有幅图,正是《遐想》中那幅图里的老卢梭,只是那幅黑白画被改成了版画,周遭环境被滤去,老卢梭成了一个正凝视着手中植物的黑色剪影。
《植物学通信》的写信时间先于《遐想》四年,读这本书时,我意外地看到,老卢梭是一个那么温情细腻体贴他人的人,虽然每封信中,他都重点传授一个方面的植物学知识,但言语之间,时时充盈着十分深情的关切,有时,甚至让人感觉他仿佛一个热恋中的情人。
此时,这个思想茁壮的天才,已经被几十年追踪和迫害搞得心力交瘁,但这些信件非常妩媚温暖。其实,对植物的热衷在他26岁成书的《忏悔录》中已有表达:“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哪项研究比植物学研究更适合我天然的品味”,再之后,因为他作品的思想锋利和激进,他被迫四处流徙,到他再一次定睛于植物学时,已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者。
1770年,这位满腹忧伤虚弱不堪的老头儿重新回到巴黎——警方已经仁慈地暗示将忽视他的存在。惊弓之鸟的他选择完全寄情于植物。1771年到1773年间,他与年轻的勤学好问的艾蒂安·德莱赛尔夫人通信,交流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应德莱赛尔夫人的请求,卢梭教她四岁的女儿玛格丽特·马德莱娜学习植物学。面对两个温柔美丽的女性,与她们讲解那些同样温柔美丽的植物,对这位内心伤痕累累的老人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的慰藉了。
信件与读者总有奇怪的感觉,它让文字可亲可近,那种娓娓而谈,春雨般润物无声。《植物学通信》,实在太适合我这样对植物颇有兴趣和感情,但又缺乏植物学知识的人。读完这些信件,我方知,我对植物诸多感性的认识大都偏颇而且盲目。
其实,也只有像卢梭这样的非专业植物学家,才能旁观者清地说出这样的话:
植物学最大的不幸,是一开始就被视为草药学的分支,结果导致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发现或想象植物的药性上,而忽视了有关植物学本身的知识。
恰恰这正是泱泱东方大国的中国对植物研究的层面,在中国古代,几乎鲜有植物学的专著,和植物相关的,大部分都是实用性极强的药草学书籍。
让人饶有兴致的是,在《植物学通信》中,这位不辞辛劳的教导者,在每封信里,对植物知识的引入总显得那么自然舒服,老卢梭仿佛一个极有素养的教师,掌握着极好的以情动人的教学方法,他随时能设身处地的想到读信人的会在哪里疑惑和扭结,从而更加形象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之外,他绝不囿于植物学知识的传导,他不停地将自己对植物的理解和情感传达给读信的人:
“我希望你获得的不是一种鹦鹉学舌式的给植物命名的能力,而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是能陶冶我们情操的、最令人愉悦的学问之一。”
“我亲爱的朋友,你一定不要把植物学看得比它本身更重要,这是一门纯粹出于好奇的学问,除了一个热爱思考、心性敏感的人在对大自然和宇宙奥秘的观察中所得到的快乐之外,它别无现实的用处。”
老卢梭深怕表妹成为一个只会满口拉丁语植物名词的植物呆子。
以前三封信为例,来看看老卢梭讲了些什么,是怎样讲的。
第一封信写于1771年的8月22日,巴黎时值秋末,许多花儿开败了,但又有许多花儿迎来了最好的季节。信里,老卢梭首先赞扬了“表妹”让她的孩子学植物学这一行为:“不管对哪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探究自然奥秘,都能使人避免沉迷于肤浅的娱乐,并平息激情引起的骚动,用一种最值得灵魂沉思的东西来充实灵魂。”然后,进入正题,老卢梭以百合花为例,讲述了一株植物的主要构成,以及一朵花的哪些部位是“花冠”,怎样的花是“离瓣花冠”,怎样的是“合瓣花冠”,什么是“雌蕊”、“子房”、“花柱”、“柱头”、“雄蕊”、“果皮”、“花萼”。老卢梭的讲解极为亲切,而且他非常体贴地告诉表妹,所以选择百合花,是因为它正处在花期。这样的话,表妹可以随处摘到一朵百合,一边看着手中的百合,一边对照老卢梭的谆谆教导。
第二封信写于1771年10月18日(大概已经到了深秋或者初冬,不知为何,我很在意写信的日期)。这封信里,老卢梭的植物学讲解从百合科过渡到了十字花科,并以桂竹香为例,给表妹讲了花瓣的具体构成,比如“瓣爪”、“檐部”,以及“雄蕊”的奇特之处。之外,老卢梭耐心地引出了极其繁多的有关十字花科的必备知识,他唯恐表妹失去耐心,话语间时时引导表妹要安心。当这封信里的植物学知识终于讲完后,老卢梭用这段话对他假设的表妹的认真和专心给予了表彰:“我美丽的表妹正忙着用放大镜观察一堆美丽的花儿,而她本人比那些花儿还要鲜艳、明媚和美丽一百倍呢”。呵呵,老卢梭的文字鲜有幽默,所以,这些貌似幽默的话,看起来真的几乎有些可爱的谄媚了。
不知为何,写第三封信时,已是第二年的5月16日了。看得出这是他给表妹的回信,也许是表妹回信很晚的缘故。老卢梭先在信里对表妹来信中提到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给予了交代,然后,进入了正题。这封信继续了前两封信的内容:关于植物的科。前两封信讲了百合科和十字花科,在进入一个新的科之前,老卢梭很怕其他植物学书本上庞大的命名系统会搅乱表妹的认知、让她走很多弯路,同时也担心她只满足于肤浅地知道一些植物的言词知识。老卢梭希望传授给表妹的是自己苦苦钻研后得到的最简洁明了的植物学知识,这样她便可以事半功倍地走一条轻盈的捷径,“你要有耐心,要满足于仅仅阅读自然这本大书,并且只以我的通信为指导”,老卢梭这话真是可爱至极。老卢梭以豌豆花为例,讲了植物中数目最多、用处最大的豆科植物神奇的结构。老卢梭讲述得非常精致,就仿佛这个科的精致微妙的结构一样,他从小心翼翼地解剖开一朵豌豆花开始,讲到豌豆科蝶形花的“旗瓣”、“翼瓣”、“龙骨瓣”,“龙骨”,当讲到解剖到蝶形花的龙骨这个部位时,不知“表妹”的感受如何,我也跟着老卢梭在惊叹:“当这最后一片花瓣被拽下来,被迫暴露出它的秘密时,我相信你一定会忍耐不住惊叹其构造之奇妙”。真的,从豌豆科的花儿,讲到果实,老卢梭带着那样痴迷的感情,几乎达到了忘我,令你不能不动情。
“至高的创造者关照着一切生灵的存在,他花费大量心血,在植物结实的整个过程中提供保护,使其免受种种可能袭来的危险;不过,他似乎对那些能为人类和动物提供食物的植物,比如豆科的大多数植物给予了加倍的爱护。”
——这样的理解在通常的植物学教科书中是绝不会有的。
八封信外,还有三篇通信续篇、一个挺长的序言,以及一大篇植物学术语词典注解。在我看来,词典注解和书中另外的内容一样珍贵,因为他似乎本该是卢梭想完成的一部植物学《词典》中的一部分。这些注解读起来依旧引人入胜,因为其中不乏老卢梭不自禁的情感和理解,所以这些注解完全迥异于那种干巴巴的解词。
植被(PLANTS【plante】):在地球表面蔓延扩张、覆盖并装饰着地球的植物性(vegetable)物质。没有什么景观比荒漠更令人伤感,也没有什么景观比树木葱茏的高山、夹岸烟柳的河流、绿荫如毯的田野和杂花纷乱的峡谷更令人欢欣。
作为植物学著作的必需,书中必然要出现大量植物插图(关于这个必需性,是个复杂的话题,比如植物学命名系统的混乱,还有国家的地域的风俗的等原因、导致不得不以确切的植物图样来做讲解)。国外植物学文字著作,成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植物花卉画家。这些图画与我国古代药理学著作中大而化之的线条白描大相径庭。
读这本《植物学通信》时,能够十分幸运地欣赏到很多幅非常美丽的植物绘图,它们出自法国“花卉图谱界的拉斐尔”——著名花卉图谱画家勒杜泰之手,这些植物绘图细腻无比,色彩样貌呼之欲出、触手可摸。对应着老卢梭的讲解,画家非常用心体贴地绘制了精细的花卉解剖步骤图和细部图,如序言所言,“对前缩法和阶调值的掌握,使他绘制出的植物绘画呈现出三维立体效果”,加上雕刻师和制版师的劳作,这些精美直观有强大说服效果的插图,让这本植物学通信集显得更加温暖缤纷。
那么,当我读完这本书,我到底知道了些什么?我知道了那些司空见惯的植物无与伦比的神奇,正如卢梭说的,也许在理论和知识方面,我不能很精确地掌握一些名词和概念,但卢梭给了我发现和领悟:比如豌豆花四瓣花的结构美妙在哪里?果花通常何以是五瓣?比如很多人所不知道、也想象不出的,那种普普通通的伞形科植物的奥妙:一朵雏菊和向日葵原来深藏那样壮观的秘密……还有,我知道了二百多年前,一个孤独的法国老人,对植物怀有那样深的感情。
《植物学通信》(法)卢梭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熊姣 译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法)卢梭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张弛 译
原来有这么庞大的一个故事——读《植物的故事》
读《植物的故事》之前,我几乎没想过这个问题:植物分类和命名体系的重要性。
有一年,在甘肃舟曲一个山林,当地朋友在野草中摘到一种金黄莹润满是小突起类似野生草莓的小果实让我吃,说它叫“mie子”,他家乡的人都不知这个“mie”字怎么写,小时候,她用狗尾草的草茎把“mie子”穿成一串,拿回去给爷爷奶奶吃。野生草莓,我们家乡叫“piao儿”,这个“piao”也不知怎样写。在西北,窗前院落常种一种开花时间很长的花儿,我们叫八瓣梅,八片舌形花瓣平整绽开,后来知道它的学名叫波斯菊,产自墨西哥。一次在拉萨的一家院落,有人指着波斯菊说,叫张大人花,因为这花的种子是内地一位姓张的官员带来的。植物和周遭的人那样亲近,自家小儿一样,可爱的花鸟草虫,人们总喜欢按着植物的样貌脾性颜色花期等给它们昵称,于是,鲜有往来或者彼此隔绝的地方,同样的植物便有了不同的名称,我猜测,古今中外,大抵如此。但这个小小的日常化问题,如果拉到植物学研究的层面上,就是巨大的混乱。
这是由《植物的故事》这本书想到的。
和另一本我非常喜爱的植物学书籍《植物的欲望》一样,这本书依旧不是一位专业研究植物的人所著。作者安娜·帕福德是英国《独立报》园艺版记者,还是《观察家》、《乡村生活》和《Elle装潢》等多家杂志的专栏作家。可以想见,对一个非植物专业的作家而言,具有史记性质地、将两千余年西方植物命名体系的历史条分缕析一遍,并加入自己的观察、记录、思考,写下这部被翻译成三十多万汉字的大书,需要多么庞大的知识积淀、何等多的资料积累,和对植物多么非凡的感情。对于国外这些自然人文的思想者、劳作者、书写者,我总是抱有无限尊重。如此浩繁且游移于学科边缘的工作,那些植物学家好像无暇或者不屑去做,势必要有些像安娜·帕福德或者迈克尔·波伦(著有《植物的欲望》(美))等看似非专业的人士怀着某种使命感和热忱感去完成。
《植物的故事》一书,清晰又血肉丰满地整理出了自有文字记载起到20世纪植物命名和分类体系的规律和历史,不过,大部分内容放置在公元17世纪以前,因为这段历史对植物学研究的各方面来说,是一段漫长廓清的历史,终于,到17世纪之前,植物的分类和命名体系面目清晰。关于植物分类和命名的重大意义,的确在我们未设身处地思考时,很难意识到。书是从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哲人狄奥弗拉斯图对植物的研究起笔的,从这一部分的阅读开始,我马上感受到了植物分类和命名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令人惊异的植物在它们到达远离家乡的异国他乡之后,又是怎样得到另外一种全新的、朗朗上口的当地通用名的呢?……虽然没有了老户籍,人们也必须为这些远道而来的娇客们安排新的身份。”
这是人们发现世界很大,并且可以来往很远时,纷至沓来的新鲜植物带给人们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如何称呼它们?面貌性情相似的植物们是否该有个合适的归类?
时空的开阔,见解和命名的不同,导致对植物认知的混乱,甚至确实到草药学上,对症下药时,对应经验中的草药,因为名称的不精准,会出现致命的错讹。仿佛群居的人没有各自的称呼一样,植物因没有各自确切和公认的名称而干扰了人们对它的交流和热爱,特别是那些外来的新异植物。在我国没有过的是,西方经历了一段对植物几乎宗教般迷狂的历史。没有名称,就没有指定,就没法深入系统的研究,而狄奥弗拉斯图凭他个人可贵的知识和认识,竭力要找出一个给植物分类的方法。狄奥弗拉斯图功不可没,至今,世界流行的很多植物的名称都源自这位作为哲学家和植物学家的研究和命名。叫人心生联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代,中国古典文学奠基之作的《离骚》和《诗经》,其中香草缭绕杂花纷呈,但这一时期,没有留下任何植物学研究的只言片语。
《植物的故事》,全书由狄奥弗拉斯图开始,然后,继续细致充实地按顺序叙述了对植物命名和分类系统的最后确立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世界各国的哲学家植物学家药草学家,还有画家的各自重大的贡献(鲜有亚洲国家),书的内容十分饱满,因为这条主线深深嵌入与植物相关的世界历史和具体的个人生活史中。
安娜·帕福德在做着十分繁冗的厘清归纳和结论性表达时,在书中呈现了很多可贵的原始记录,这些记录细碎地散布于全书,散发出浓郁的“故事”气味,之外,她还大胆地进行分析和评价,在她目睹了整个发展史后,她看出了一些清晰的破绽,发现了在植物命名和分类中,那些大人物身上的毛病:脱离植物本身,本本主义,不深入自然,盲目迷信,以讹传讹。
安娜好像对著有植物学重要著作《博物志》的普林尼就很没有好感。“普林尼非但没有提出任何结论性的东西,也没有指出传言与现实孰真孰假。”她精确指出,“普林尼的《博物志》‘参考’内容共计473处,其中146处选自罗马著作,327处选自希腊著作。”在《剽窃者普林尼》这一章,安娜对普利尼的意外去世用了一种有调侃意味的叙述,这种略带渲染的有情趣的笔触,在书中比较常见:
公元79年8月22日,大约中午时分,一朵形状酷似意大利松树的云彩从维苏威火山口处升腾而起。普林尼征用了一艘轻型船,打算近距离观察这一奇特现象,随后,地震了,火山爆发,熔岩喷涌,普林尼命令舰队继续前往,他一面观察着火山爆发,一边冷静地让惊惶不安的听写员速记他的观察口述,那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洗澡吃饭睡觉,第二天,黑云压城,不见天日,庞培城的居民们绝望地四处奔逃,普林尼在两个奴隶的搀扶下从躺椅上刚站起来,“一股硫磺烟扑面而来,最终倒地身亡。”“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庞培城查斯特拉夫花园里的苦艾、番樱桃、紫苑、石竹、锦葵、风铃草、剪秋罗、耳草和车前草等植物正在争相绽放。”
安娜是一个细心又耐心的女人,在一个巨大纠缠的线团中,她找出头绪然后把它重现绕成了一个浑圆的头尾井然的新线团。很神奇,在阅读这样一个大历史时,我时常会踟蹰于她的一个细节或者片段,甚至她一笔带过的某几句文字。的确,国外这类自然人文书籍,包含的能触类旁通的信息实在太多。
这本书里,除了引子部分能看到安娜写了在马儿上看到的中亚天山山脉的植物风光外,她通篇很少提到亚洲的植物学研究,书里没有任何中国植物、或者药草学研究的成绩。她看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对亚洲在植物的世界性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她的目光始终没有投向过中国,比如对我们国人影响甚大的《本草纲目》,她仿佛根本没有过听闻,如果抛开这本书的主题,我能感到,她完全在以一个西方人的视野和思维讲述植物的故事。
作为一名英国作家,安娜用一章的篇幅写了本国植物学家特纳在植物学方面的成就,当时的植物学研究,英国明显落后于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荷兰等国,但特纳奋起直追,让英国的植物学研究有了一席之地。写到特纳与教会的冲突以及研究和出版的艰辛,安娜以祖国女性特有的温情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比如写到特纳生活中的窘境,家庭和孩子等物质方面给他的研究带来的压力,安娜让叙述故事味十足——传教士特纳如此乞求英国教会的帮助:“我的几个孩子各个瘦骨嶙峋,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得到一个薪水更高的职务,好把我的孩子们养得白白胖胖的,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除了安娜本国的特纳,她还详尽讲述了生活在17世纪,对英国植物学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并给世界植物学研究产生了影响的约翰·雷,安娜说:“雷——一个农村铁匠的儿子,成为故事中最后登场的主角”,安娜在讲述这位性情高洁的植物学家时,语言间深含感情。用安娜的话说,约翰·雷大力推广了“双名法”这一新的植物命名法则,从而,对世界植物命名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与我在别的植物学著作中得到的认识不同,安娜把世界著名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放到了全书的《尾声》部分,这一部分似乎要通过对林奈成就的简要概括的讲述,调整人们认识中的偏误,即便如此,《尾声》依旧以约翰·雷开头:
约翰·雷为之后继承其事业的研究者们指引了方向,帮助后人渡过重重障碍,走出扑朔迷离的命名学迷宫。自他开始,人们学会如何使用科学的方法对植物进行分类、描述,他还为这项研究赋予了新的名字——植物学。
约翰·雷是最后一位让植物研究摆脱迷信,步入科学正轨的杰出人物。
于是,林奈仿佛成了一个坐享其成的投机者,安娜就他的重要著作《植物种志》,这样评价:“林奈只是把握住了机遇,在正确的时间发表了这部正确的著作,使其名利双收,名声大振。他如同一台非常有效率的计算机,为近六千种植物贴上了双名标签。”很明显,安娜对这位蹚过先知之河的集大成者,对他鲜有创造的成就颇有微词,似乎世人眼中他的过于强大的成就,得来实在太轻而易举。
书的封面是一张漂亮的彩图,也是书中的一幅插图,插图下有这段文字:
图48:问荆(俗称马尾,木贼属不开花植物),摘自意大利北部地区伦巴底的一手抄本(1440年)。图中标注为Jacintus的球茎植物。应该是当时在法国、德国境内发现的葡萄风信子,而我们现在所说的风信子那时还没有从土耳其传入西欧地区。
这是张非常有故事意味的插图,很仿佛我国的壁画,色彩鲜艳、画面情节生动。画的左面一片巨大的问荆叶子,右面一个巨大的球茎风信子,中间有两个穿着贵族礼服的人似在谈论植物,画面背景还有隐约的虚化的其他植物,画面后方一位妇人与一少儿对话,还是讲授的样子。
植物学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绘画艺术的密不可分,在这本书的引言中,我们得知,第一本热销于欧洲的植物畅销书《本草图谱》(1530年,奥托·布伦费尔斯著)所以畅销的原因,是因为书中一批木刻印版的精美植物图像,睡莲、荨麻、车前草、欧龙牙草、马鞭草、白屈菜、琉璃莒、白头瓮和麟凤兰花等。这些画中的植物在整个欧洲被一眼辨识出来了,绘画加速了植物命名和分类的系统化进程。
这本《植物的故事》中,共有157幅十分珍贵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插图,让我们能看到早到很久远的十分精致、有的甚至带着人类童年气味的植物插图,它们着实令人遐想和着迷。这些缤纷美丽的植物穿插于文字中,使这个长长的植物故事更加曼妙生动。
事实上,安娜把不少篇幅给了那些给植物学研究给予了重大贡献的画家们,她不但讲述了植物绘画的简要历史,还由点及面地论述到许多生动细腻的绘画细节。特别讲到了意大利大画家达·芬奇、德国画家丢勒等人在植物绘画方面的功绩。书中有一幅丢勒1503年绘制的驰名后世的写实水彩画《青草地》。安娜对《青草地》给了这样诗情画意的描述:
丢勒在绘制时,采用了蚯蚓的视角,画面给人以仰视的感觉,画中的青草几乎和实物一样大,牧草、婆婆纳、蒲公英、狗舌草、野茅、雏菊、大车前草、康穗草、欧菁草、仿佛刚刚从土里钻出来。
之外,安娜还将整整一章的内容,留给了德国植物学家植物绘画家富克斯。
《植物的故事》起于古希腊哲人,中间经历在欧洲各国的交流糅合和促进,最后连线美洲。这使我们看出,植物学研究,特别是植物分类和命名体系任何细小的一点进程,都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和很多人的艰苦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故事。
关于书作者安娜·帕福德,我得知,这个多产的人文作家,在写作之余,她还是英国古迹保护组织成员、古代园林及建筑修缮工作的负责人。她曾耗时近三十年参与重新修复了原属该地区首席神父的花园。近年来,她又开始了另一处花园的修缮。她是一个令人尊重的女性。
《植物的故事》一书,装帧印刷排版十分精美,纸质柔韧色调优雅,这些,也体现了对书中庞大植物故事和那些风云际会的植物界精英们的卓绝努力的极大尊重。
《植物的故事》三联书店 (英)安娜·帕福德 著 2008年6月北京第1版 周继枫 刘路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