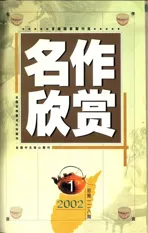散文在21世纪——对话和独白
2012-07-18山西毕星星
/ 山西_毕星星
作 者: 毕星星,山西临猗人,著名作家,曾任《山西文学》副主编。
有一段在北京小住的时光,于是想找几个高人谈谈散文。
到昌平找到丁东住处,已近中午。他搬到山脚下,住在一个乡村小区。虽说偏远,这里却是文化名人聚集落户的地方,大概大家都相中了心远地也偏的安闲宁静。尽管每个人的心海里依然搅动着风云变幻。
房子很宽大,如不然,如何盛得下主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思维?丁东一如以前的不修边幅,听邢小群嘟囔过多少次了。有一次还抬出我的衣着比对。我其实也不是一个衣着得体的人。当然,这会儿,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平常的布料里,装裹一幢巨型的思想仓储。
案头有一本《中国在梁庄》,这是最近上榜的畅销书,各地书店卖得正火。此前我也知道作者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只是从来没有联想到,她和邢小群同事。从丁东所谈得知,她们同校同系,平时就有交流。鉴于多年来文学评论言不及义,梁鸿对自己的写作甚至产生了羞耻之心。她要寻找更直接的言说方式。于是她选择了散文,选择了纪实。大量的采访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能不能表现中国农民的真实存在?就在前一年,还在忧虑,为寻找成功之路纠结。转过年,一本《中国在梁庄》就爆响了。
《中国在梁庄》成功的原因,丁东归结为思想和材料的占有反应。用他的话说:上面的眼光和底层的史实,一碰就成功。这种田野考察式的写作占有两头,是成功之道。上头有理念,没材料;下边有材料,却没有眼光,材料也就没用。文学圈常说“作家的眼睛”,是指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没有眼光,任材料从眼前溜过也不会留意。有好多材料,看似寻常,思想的光芒一旦照亮,就有了价值。
这个意思,邢小群表达得更加准确,更加理论化。用她的话说,与农村保持密切联系的人,往往缺少宏观的社会文化意识,有宏观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又很难接通与中国乡土的血肉联系。二者的完美结合,就是目前影响较大的文体:纪实性散文。
和纪实文学相联系,影响较大的另一种散文文体是人物传记。丁东阅读量很大,历数各路名家。内地不必说,一些不便言说的,港台这个窗口发挥了作用。比如近年出版的《李作鹏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内容都很丰富。李作鹏在山西,待遇好一些,写回忆录,力度差一些。邱会作在陕西,待遇不好,有气,回忆录动力很强。他在军队历来搞后勤供给,抓生产,对部队地方经济建设有想法,周恩来曾经想用邱做副总理,抓经济建设,可惜没有办成。邱会作的回忆录里,为各个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历史,提供了许多不同以往的解说,好些材料很宝贵。
散文的地位,标明当代一种阅读需求,对真相的需求。由我说故我在到他在故我说,这是认识世界方式的转向。
以小说为主打产品的作协系统,不太看重散文文体的强大影响。作协系统的小说,没有思想含量,面对现实软弱无力,已经没有过去的影响。中国作家协会还是那块招牌,若论文字的影响,远不及思想界。
纪实性散文的最高成就,当推章诒和先生的一系列著作。她的巅峰状态出现也不过十年,却产生了持久的强烈反响。对于体制内写作,冲击不可估量。
中国作协的顶尖产品是鲁迅文学奖。看“鲁奖”,越来越像政策、关系、实力的勾兑,有人成功获奖,实至名归。也有人获奖,作品不见得好。未获奖,也不见得不好。
章诒和先生在大陆在港台,获得多高评价。看看那些“鲁奖”、“茅奖”,有谁理会呢?
当今文学的地位,远不能和20世纪80年代比,这和文学自身的矮化有关。那时评奖,关系占比重很小,主要看作品。作品也确实有影响。现在评奖没有客观公正,即便有,文学普遍乏力,设想“文起八代之衰”也不可能了。
丁东所谈一个核心:散文代表当今汉语文学的高度。谈论总比较散乱,好在不久看到了他有一个经过整理的发言,条理化多了,在畅谈《背影书系》的编辑心得时,丁东说:
每一时代的文学,总有代表性的体裁,过去常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这个意思。上世纪8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体裁是小说,当时涌现出一大批小说家,看小说的不光是文学爱好者,一些搞经济工作、政治工作的跟文学根本不相干的人,都要看小说。小说在当时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当中成为一个最敏锐的触角。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千年以后,不能说没有好的小说,整个小说已经跌到了一个低谷。小说不行了,不等于中国的文学就不行了。这时中国的文学出现了两个亮点。通俗文学的亮点就是段子,那些手机短信里的段子颇有智慧。高雅文学的亮点就是散文,写人物命运的散文,像章诒和、野夫、徐晓、吴迪,以及旅居国外的赵越胜、沈睿,他们的散文,我觉得代表了当今汉语文学的高度。《背影书系》里大量的作者是学者,也有一部分作者是作家,或者作家兼学者,他们的文章,作为散文,艺术性也是比较高的。选文也是一次观察和评判文坛的机会。虽然只是个人眼光,不同于官方机构的评奖活动。但只要选得认真,照样可以引起良好的反馈。有一些出版社每年按照文学体裁出版年选,这是一种评价方式。我按内容专题选文,不知可否成为另一种评价方式。我想表达这样的想法:在主流体制文学走下坡路的时候,中国文学并没有死,真正的高手在别处,真正的佳作在别处。
散文原本就是中国人写作的文体源头,由诗、戏进入小说,完成了一个轮回。下一个轮回又要从散文开始吗?
这两年喜欢冯秋子的散文。尤其喜欢她的《荒原》《1962:不一样的人和鼠》。《荒原》六万多字的篇幅,很难把它理解成原来意义上的散文,但确实是。《荒原》讲述了一个名叫郭四清的农民几次钻进内蒙古草原深处“搂地毛”的经历(“地毛”即发菜)。艰难困苦,冒死,无奈,一种游民式的抢掠和生存。要在别人叙事,那是一般的纪实文学。冯秋子的精细描摹和游荡的笔墨,加上其他的文学元素比如方言的使用,让它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散文。
对于冯秋子,以前只闻其名,未见其人。《随笔》海帆说,她看了我的《谁还知道李希文》《书里书外:遇罗锦童话在小城》,向海帆打听作者,起码没有讨厌的意思。以文会友,我正好借机认识高人。
到《诗刊》找到冯秋子的办公室,她正在搬家,书本报刊堆满了脚底。客人远道而来,冯女士只好停下手里的活儿。一行一行书本曲里拐弯,将室内隔开条条细长的小道。隔着书山坐定,我听冯女士谈她的散文。
《荒原》一文,写得很苦。90年代的事,即便找到草场,现场早已破坏,不能复制。要恢复原来的写作现场,调查采访工夫大了。多年前的事,只能反复采访,采访多人。主人不明白,就周围了解,一点一点抠。农民没有文化,他做了那么多,断断续续说了不少,总说“没个甚”。你启发了半天,刚一开口,“没了”,“没个甚”。谈上半天,能用的也就一两句。《荒原》方言量大,与此有关。方言表现力很强,传达出的文化信息丰富极了。落笔时,我时时警戒自己不要用作家语言改造人家的土话,发现我自己的腔调立即恢复原状。曾经担心到南方看不懂,林贤治看了说,没问题,全能懂。
林贤治看了《荒原》,建议写成长篇,不是小说,还是散文,纪实散文。这个搂地毛,有人建议写长篇小说,我觉得,写长篇小说就把材料糟蹋了。新的集子里还有一个材料,收了一万多字,你们山西的吕新看了几千字,叫好,说,他能写一个三十万字的长篇,建议我写长篇,十五六万字也行。我写的只有一万六千字。
我欣赏用最少的翅膀飞翔。
这是我当时的一段现场记录。
《荒原》下了大工夫。我说,值,可传世。《1962:不一样的人和鼠》,也是这样。
散文常常是最能逼近真实的方式。“我坚持用散文,小心翼翼逼近事物原始面貌”,冯秋子说。
调查采访在前,写作在后。甚至,调查采访的工夫远远大于写作工夫,冯女士的写作,有点借鉴了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田野调查。文史哲,在纪实散文的写作中融会贯通了。思想性、历史感、艺术价值,使得散文植根于大地,和生活有着血肉相连的根脉,同时,艺术表达的精美也至关重要。冯女士特立独行,她的散文也区别于时下散文的虚脱,成为坚实精美纯粹的表达制作。
小说家坚持一种过时的观念,腐朽。冯秋子多次使用“腐朽”这个词,对一种固执又愚蠢的小说观念,表现出无比鄙视。我理解,这个观念,指小说家过于自信自己的表现力,忽视了现实世界对自身魅力的展现。其实不论哪个文体,对于表达,合适就是最好的。
冯女士又一次说得不客气了:
小说家轻视了散文随笔的存在,他们人多,他们可以写得长,但你五万字、十万字,能给读者多少东西呢?空洞,腐朽,没有内涵,常常读了几万字的小说,不如几千字的散文提供的东西多。我的阅读量很大,很杂,职业让我读了很多小说,结果,对小说的前途非常忧虑。你瞧不起人家散文,其实谁又瞧得起你。
我近年也写一些散文随笔,通过田野调查纪实,和冯女士的路子接近。在《随笔》发的几篇,得到冯女士激赏,有些意外。她说,什么时候我们合作一下,你要是下乡考察,我带一部摄像机追踪。你采访,我拍。你写别人,我拍你写别人。不影响你,怎样?知道这些年纪录片之风大盛,冯女士又写又拍,令人敬佩。我的制造,多以材料取胜,谈不上艺术记录。冯女士的散文,给我警策,我应当做得更精致,更像艺术品。
认真考究,冯女士的纪录片,不也是拷贝领域的散文随笔吗?
这次进京,约了章诒和先生,终究还是没有谈成,只好怅怅离开。她的《往事并不如烟》,好多篇章,多次反复看过,警言佳句,时有过目成诵者。她的经历,她的修养,肯定成为此行访谈的一段华彩。遗憾,只好长恨付诸阙如了。
先生最近出版了小说《刘氏女》,排行榜上名次也不错。但毕竟不比当年《往事并不如烟》的阅读风暴。先生还是钟情于纪实文体,但由于种种制约,不得已而写小说。这只能说明小说的乏力,我还是期待先生的散文。
北京之行,逼着我反省自己的散文。
我以前的散文随笔,多属于“作协体”,记人记事,议论抒情什么的。上世纪80年代初拨乱反正,文学的“写真实”口号再度响起,在新启蒙的大潮里,也写过一些反思历史的文字,有了零星的思考。认真注意散文的记录历史功能,应该到了本世纪之初。
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奈保尔赖以获奖,《印度三部曲》是闪光点。奈保尔宣布:长篇小说是19世纪的产物,21世纪是写实的世纪。他要把非虚构文体打磨成为一种利器,为人类书写记忆的权利而战。纪实,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学现象。2001年,也是“诺奖”设奖百年纪念,瑞典文学院以“见证的文学”为题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各路巨匠提出,希望文学起到为历史见证的作用,作家应该记录历史的真切感受,用自己的语言对抗以意识形态来叙述的历史和政治谎言。文学的天空响起强音,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奋,暗暗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此前此后,思想界正在热络“口述史”。抢救历史宜早不宜迟。一些蕴藏历史记忆的长者,年事已高,多年以来,他们的记忆不合主流史学的胃口,没有什么人理睬他们。他们自己书写记忆已经非常困难,只有任其自生自灭。思想界一些青年学者,或者组织,或者亲自撰写。一批口述史得以问世。这些边缘化的记述一旦出土,立刻看到了不同于主流记述的别一种姿态,别一种色彩。口述史不仅是讲述形式,可贵在对正史形成了挑战。思想界的动作,对我无疑是强大的推动。
再写散文,我逐渐把反思批判作为文章骨架。《拷问牺牲》批评“文革”时代的无谓奉献甚至献出生命,登上了当年的中国散文排行榜。随后的《毁誉参半说浩然》《最后的乡绅》《终身艺人》《寂寞雷锋》《谁还知道李希文》,都有一定影响。到了《书里书外:遇罗锦童话在小城》《不须放屁难倒全国人民》,反省历史的意识已经非常强烈了。
2008年,《特级教师南岩之死》荣获冰心奖。发表获奖感言时,我直言散文的功能在于记录。散文家石英很宽容,大会总结时吸收了我的说法。我知道一班“作协体”很不以为然,只要能说出来,还是有一种吐出自己标高自己的快意。
有人说我的写作接近政治书写。对不对?我管不了那么多。知名学者徐贲先生在叙述自己的写作道路时,解析他自己是由文学到文化,再到政治文化,我看这未必不是一条正路。
我已经这么写了,我决定这样写下去。
好在这几年,对历史的文学书写,已成为世界性的现象。从台湾传过来的《巨流河》《大江大海》让我们耳目一新。世界上还有另外一批人,用别一种眼光打量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辉煌,不过是他们的灾难。而这些人,恰恰还是我们身边的同胞。
广州最近推出了“在场主义散文”,强调写实精神、当下关怀、人文批判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评委们屡屡提醒获奖作品的诗化倾向,警惕由来已久的“伪抒情”。散文朝哪个方向走?不啻一声警策。
文学,写出真实的历史,不仅是能力,简直就是道德责任,简直就是见义勇为。
诗人说奥斯维辛以后没有了诗,接着说下去,20世纪的极权会消灭小说,苦难使得虚构毫无意义。虚构就是罪恶的帮凶,因为这个世界,真实的罪恶如此骇人,根本不需要虚构,虚构远不及它恐怖。21世纪最流行最给力的作品不是小说,是散文。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文体,如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现在,一种以文学方式记录生活、刻写历史的文体会引领潮流,21世纪,散文将会成为主流文体。
《人民文学》在2010年新开了一个“非虚构”栏目,这个国内文学刊物老大,表现出向纪实向散文示好的走向。2011年第6期,一个文体栏题赫然标明“非虚构小说”,这个转基因文体,让人思考。
写小说的人多。人多抵什么?
没有一个永远的主流文体。小说,请低下你高贵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