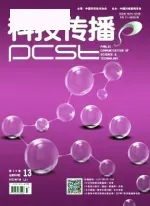蒙古族视觉传播形象特征与原因分析
2012-07-05郭倩
郭 倩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在当下社会中,少数民族的身份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蕴,即带有异域风情的、神奇而美丽的,蒙古族的形象展现就是其中典型的一支。
每每提及到蒙古族,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他们在广阔的大草原上骑着骏马自在地奔驰,居住在自己搭建的蒙古包里,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而蒙古族的男性形象是高大而强壮的,女性形象是身着长袍扎着头巾挤牛奶的阿妈,儿童则是骑在马背上放羊的牧童。可是在现实中,蒙古族的形象并不只是这样纯粹与单一,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蒙古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背上的民族”,现代与工业早已进入蒙古族地区,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充满着工业化元素,生活的环境高楼林立,着装也与普通城市的百姓相同。事实上,多数人看到或者想象到的蒙古族多是由视觉传播者赋予的外在,传播者给蒙古族限制的符号元素。
1 蒙古族形象含有以下几个特质
第一,关于蒙古族的形象定位始终保留在原始非现代的阶段。无论是不同媒体中的新闻报道,还是媒介中的广告宣传、电视剧电影的制作里,首先,大众媒介塑造的蒙古族人民形象里,蒙古族男性多是身着长袍、围腰和长靴,或者身着那达慕大会的骑马服与摔跤服,佩戴火镰、鼻烟盒等饰物,常见的形象多是在参加骑马射箭等民族特色活动;其次蒙古族的生存环境多是广袤无边的草原上自己搭建的蒙古包,交通工具是原始勒勒车;再次视觉传播中的蒙古族多依靠牧羊为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基本与现代生活相脱节。事实上工业化与现代化早已渗透到蒙古族的生活当中,但由于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越来越间接,我们自以为是真实的东西,只不过是利益群体利用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虚假环境,由于形象传播的片面,多数人认为蒙古族的生活还停留在原始非现代时期,从事畜牧、旅游等工作;
第二,他们往往是被观赏注视的对象,为接受者带来视觉上的享受。无论电视传播媒体还是平面传播媒体,蒙古族的外在总与鲜艳的色彩与华丽的蒙古袍与头饰相结合,从事的活动也是原始的畜牧手工劳作,不同媒介类似的表征实践,都将蒙古族这一群体推向更加边缘的位置,在蒙昧的被解救中,在被观赏中和在现代化及商业化过程中,蒙古族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其形象在“看/被看”之间,被放置在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上,被放置在强势民族权利的隐喻关系中,在被忽视和被误解中,被粗暴地以身体作为商业资本,为猎奇的世俗营造市场利润。虽然媒体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权力隐匿的书写从来都不曾消失过,偏见的本质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像在春节联欢晚会里,蒙古族歌曲《吉祥三宝》的表演在舞台背景、演员服饰、头饰装扮上都延续着一贯的风格;
第三,人们对于蒙古族形象的解读使他们服从于这样的印象,并在对外展示中依照这样的模式塑造自身形象。定式化的形象传播模式一方面成为满足了大众非功利的审美需要的产物,并迎合了人们对少数民族族群好奇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保护政策,其“牧民劳动者”的形象表征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政治的、政策的、形势的内容,这使得这类形象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话语主题服务,成为最“与时俱进”的形象表征。
2 蒙古族传播形象单一化的原因
第一,蒙古族形象的固化是由拟态环境带来的一种刻板印象。李普曼早在《舆论学》中就提出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不是先观察再感知,而是在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模板和对事物的定义,然后才带着一种固定的成见去观看事物。同样对于蒙古族形象的形成刻板印象是由大众传播造就的拟态环境而形成的,其中通过视觉传递的信息就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例如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里,蒙古族常常是身着色彩华美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以《吉祥三宝》(图1)为例,三位演唱者有着蒙古族始终如一的典型穿着与发型,伴随着歌曲出现的还有草原上的交通工具勒勒车、舞蹈演员扮演的羊群、电子屏幕上不变的绿色大草原。这样的传达符合了观众在接受之前的心理预设,在观众的理解中蒙古族就是这个样子,现实出现的画面也满足了他们之前的假象,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于蒙古族的刻板印象,二者不断处于相互作用之中。
此外,由于普通人的注意力、时间、社交圈子有限,他们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越过媒介直接认识世界,即使具备上述条件,也会因为人们用自己头脑中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去定义外界事物,从而无法获得真正的印象。于是,人们对于蒙古族特征印象最深的前三位分别是歌舞、风俗与服饰,认为蒙古族从事的行业前三位是旅游、文艺与游牧,而这些并不是实际的样子;

图1
第二,蒙古族形象的固化是被树立为他者的蒙古族确立身份的自我意识。牙买加裔英国文化批评家霍尔认为文化身份定位的方式之一就是着眼于异质,由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构成“现在的我们”。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之一的蒙古族,存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之中,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0.004%,在人口数量上蒙古族是一少部分;另一方面,蒙古族的文明与文化在多种文化竞相发展的现实环境下属于中华文化其中的一个支流,与其他少数民族文明并存,作为“全球后现代”和文化同质增长的结果,很多新的混杂身份正在取代着传统文化。蒙古族形象具有区别与其他民族形象的很大差异性,通过这样与众不同的特色点,确立有自身特点的外在形象是蒙古族信仰、态度、价值观向外界传播的一个部分,通过特殊的民族服饰、装饰、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以确立和巩固自己在众多文化中的自己独特的身份,所以形象单一化模式化的视觉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为他者的蒙古族地区的主动性选择。
蒙古族外在形象的单一模式化是建立“差异”的过程,是作为少数群体和边缘化的人宣泄对身份迷失的焦虑与对平等地位的诉求,但是与此同时,过分夸大“差异”的功能也容易导向一种消极或游戏心态,甚至陷入保守主义和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怪圈,因此蒙古族形象的表现不能够全面与多元;
第三,在商品社会里,蒙古族的单一的形象含有某种隐喻,承载着价值交换的资本,这在满足消费者审美需要的同时,也完成了潜在的商业表征,可以说,为了追求一定的目的,蒙古族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被固化。比如在某纯牛奶的广告(图二)里,主角小男孩生奔跑在广阔的草原上,他身着特色的蒙古服饰,皮肤黝黑,他有着一张朴实稚气的脸,还有深深的高原红,手持一只装着鲜浓牛奶的木碗,嘴唇上方还有厚厚的一层奶皮。广告商希望借此向公众传达自己的产品天然又健康,以这样的画面激发人们对产品的向往,树立产品在公众心中的美好形象。同时也不难发现,在内蒙古地区的广告宣传片中,多数也是对广袤草原的形象展示,以此来吸引游客前来,为地区创造经济效益。为商业发展塑造形象,形象服从于经济利益是蒙古族视觉形象固定化的又一原因。

[1]任悦著.视觉传播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王晓路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差异,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