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圣 我本来就一文不名
2012-06-25王与菡刘荔
王与菡 刘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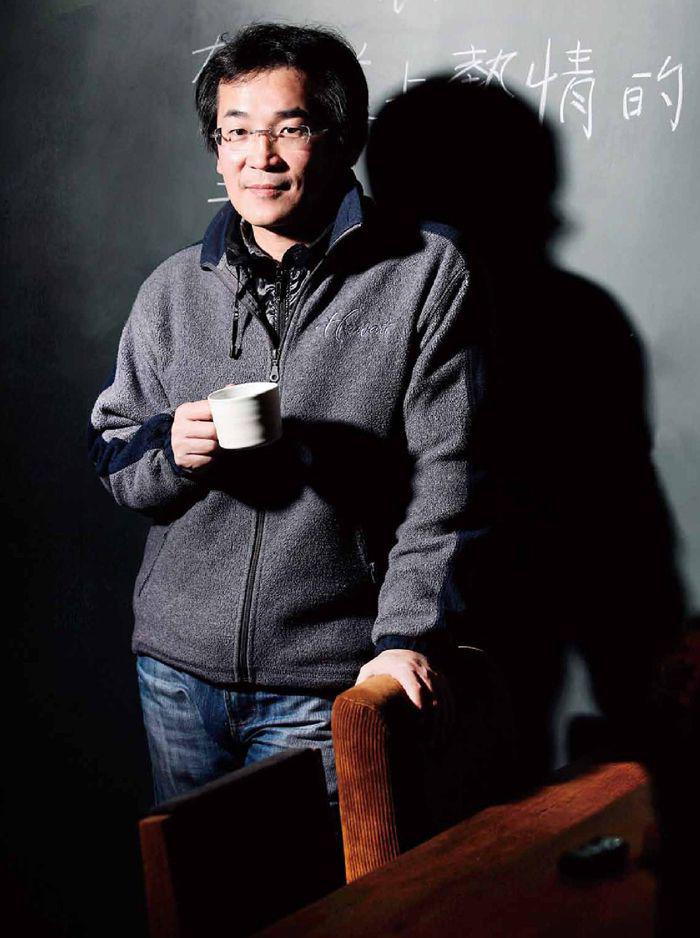
魏德圣很谦卑,甚至谦卑得有点手足无措。这个一度被誉为是台湾电影票房救世主的导演,没有他在《海角七号》中传递出的激情、渴望和冲动,而是极为默然,默然的神情,默然的话语,默然的身型。
这样的谦卑和默然让人很难想像他如何坚持了十二年,从无到有,从没有任何投资到借遍几百号身边人的钱,拍出了史诗巨作《赛德克·巴莱》。不言而明,《海角七号》的成功让他不是没有资本跻身“票房大导“。而这个清癯的男人,拒绝了唾手可得的地位、荣耀和辉煌,安贫乐道地践行着自己的信仰。就像他坚持把《赛德克·巴莱》在台湾公映的版本剪成四个小时,哪怕这样的时长让影片有难以上映的风险。
最卖座的救世主
魏德圣对《赛德克·巴莱》的信仰源于十二年前。刚离开杨德昌工作室的他开始独立创作剧本。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台湾原住民漫画作家邱若龙关于“雾社事件”的作品,便对那段历史大为触动。1930年,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岛发生了血腥的雾社事件。台湾雾社的赛德克族因不满台湾总督府与地方政府的压迫而激烈反抗。结果,除事件领导人莫那鲁道自杀外,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成为日本统治台湾期间最后一次激烈的民间反抗行動。魏德圣从来没有想过,这件在历史课本上只有两句话的历史事件竟然隐含着如此悲壮的过往。而最让他感动的地方,不是原住民对战争胜利的渴望,而是求死,求灵魂的自由。
魏德圣提笔写下了《赛德克·巴莱》的剧本,并开始酝酿把它拍成电影。几年时间里,魏德圣将剧本改了又改,当掉自己的房子,花250万台币拍了一个5分钟的宣传片挂上网,希望能通过这个短片寻到投资。可惜未果。无奈之下,他开始拍摄别的影片试水,也为《赛德克·巴莱》积累经验,就这样,《海角七号》诞生了。《海角七号》的出现给当时低迷的台湾本土电影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投资仅五千万台币,票房却突破四亿台币,远超了《色,戒》、《赤壁》等商业大片,还一举打破成龙主演的《警察故事》在台湾保持了16年之久的华语电影票房纪录,成为台湾史上最卖座的华语电影。
《海角七号》的成功,也让魏德圣成为台湾电影的“救世主”,各种投资纷沓而来,加码于海角八号和海角九号们的诞生。可是,这一切的金钱和荣誉并不是魏德圣的梦想,甚至他也没有为突如其来的追捧着迷和眩晕。《海角七号》不过是拍《赛德克·巴莱》的跳板,这一点,已经成了魏德圣的行为学。直到三年后,我们采访的这一刻,提到《海角七号》,魏德圣的神情中散发出来的是羞赧,而《赛德克·巴莱》几个字可以让他瞬间流光四溢。
赛德克·巴莱
从1999年开始,魏德圣带着《赛德克·巴莱》撞了六七年南墙。这一座山怎么闯都闯不过关,到最后,魏德圣只是一心想把它拍成。“我只知道《赛德克·巴莱》是我想了十几年要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否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它。我不希望它能赚多少钱,只希望能回本。所以,我也准备好在这部电影之后又回到一文不名的状态,反正我也不是没经历过。《海角七号》之前我本来就是一文不名。我的包袱没那么大。”
甚至,当导演对魏德圣来说已经称不上人生目标。在踽踽坚持的岁月里,魏德圣发现,讲自己想讲的话才是他的人生目的,当导演是工具,是他要讲话的一种工具。这让魏德圣越发执着,对他来说,拍出《赛德克·巴莱》这样的作品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而这一信仰已经剥离了利益的实质和外壳。对于近十余年来徘徊于“砸钱货”阶段的台湾电影而言,这样的选择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冒险。旁人愈加相劝,魏德圣愈加坚持。“我只想要诚实一点,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去做它,我有把握也有诚意去做。如果选择我不喜欢的,我做它只是为了赚钱,我放不了太多的心,做不了太多的思考,对结果也不会有太多的期待。”
魏德圣所做的事业不是为了生存。“如果只是为了生存,生存有那么难吗?如果不做电影这个行业还更好生存。人的一部分需求在于身体,衣食住行,可是我反而觉得心理需求更重要,心理需要是一种存在价值。存在价值跟存在是两个东西。只有真正经历过价值,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付出的东西产生的价值,有些人失去了时间,有些人失去了机会,而我一定不能失去我的坚持。”
魏德圣选择了坚持,2009年,他带着自己在筹拍期间绘制的重达五六公斤的分镜图手稿开始了新片的征途,带领着浩浩荡荡的摄制组在台湾深山里安营扎寨,正式投入了一个已经被人遗忘的史诗故事。
最厚脸皮的导演
魏德圣真正被钱吓怕,是《赛德克·巴莱》拍摄的过程中。
魏德圣的拍摄手记里,几乎通篇的矛盾都围绕着“钱”打转。没有钱,只能拉投资,邪门的是,那时候连矿泉水的赞助都拉不到。拉不到投资,只能借。魏德圣自诩是台湾电影史上脸皮最厚的导演,在长达十个多月的拍摄期,魏德圣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借钱,以至于,他对钱的感觉已经全然麻木。最开始小心翼翼地借几百万,最后眼睛都不眨地借几千万。不管认识不认识,先一通电话打去,直奔主题—借钱,以至于后来的台湾企业界集体封杀魏德圣,听到他的名字就挂电话。“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条落水狗,没人肯理我。”
魏德圣或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怕借钱的人之一。就凭“借”,《赛德克·巴莱》花费了创纪录的7亿台币成本。而拍摄的过程更是让魏德圣哭笑不得。每天要应付缺钱的状况,甚至几个月都发不出薪水,剧组差点在最关键的时刻停工。还听说他极钟意一件拼命三郎的T恤,而真相是,那是拍《海角七号》时马拉桑酒厂的赞助,他一直穿到了《赛德克·巴莱》。
拍《赛德克·巴莱》是魏德圣为自己的信仰写下的血泪史。支撑到杀青那天,他的眼泪不可遏制地流了下来,“我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男人。”魏德圣说。而在魏德圣的太太心中,这是一位有梦想的男人。拍摄前,魏德圣焦虑的是开工后有多少工作人员到场。2009年大年初五开工,三百多个工作人员,一个都没少。要知道,这些人很久没有拿到任何薪水,反而每个人都被魏德圣借过钱。《赛德克·巴莱》监制吴宇森也对着魏德圣感叹,“没有工资还死心塌地为你白干这样的事也许只会发生在台湾”。
魏德圣也不否认,这是一次属于台湾电影的奇迹。“因为相信所以做了,做了才知道没有那么容易。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生命体验在我身上会一再重复,我就是一直没有学乖!” 2011年9月,《赛德克·巴莱》在台湾上映后,魏德圣才过了一段摆脱负债的生活,终于“不再负债”让魏德圣异常满足,“现在生活至少是没有忧虑。吃喝穿和孩子的教育都没有问题。以前吃碗面要不要加卤蛋都要犹豫。”
与自己赛跑
《赛德克·巴莱》在台湾的表现异常好。席卷了8亿多新台币(约1.6亿元人民币)票房,还夺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这部长达四个小时的片子让台湾人沉溺于远去的史诗中疯狂了一把。而魏德圣还是继续马不停蹄地奔跑。
“其实电影里面有很多反思。英雄不是那么绝对,坏人也不是那么绝对,都是处在不同的立场,逼不得已的。日本人也是,原住民也是,他们要不没得选,要不只能二选一,却明明知道不会有好结果。其实人都这样可怜,总面对不同的选择,做也错,不做也错。就如同我知道很多观众总是抱着检验的心态来看电影,他们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不歌颂文明,而是要表现野蛮。” 魏德圣与时间赛跑,与金钱赛跑,与信仰和坚持赛跑,到了这一刻,他只剩下与自己赛跑。
如同《赛德克·巴莱》电影里原住民的信仰一样,魏德圣相信,总有一天,青翠的梧桐开出了嫩黄的花,云朵聚成了雨水,日头又射穿了云朵,山谷间架起了一座巍峨的彩虹之桥,而每个人心中都能有一座彩虹桥对端最美的猎场。
【对话魏德圣】
逼不得已的反击
记者:《赛德克·巴莱》这次在内地上映的两小时版本和台湾版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魏德圣:基本主题的讯息、想法都一样的。被剪掉的主要是结尾部分,它有历史的包袱在,有台湾本土文化的包袱在,所以常常被批评说结尾结了三次、四次这样子,在内地我们就结一次。
記者:像《海角七号》一样,《赛德克·巴莱》的音乐也是制作重点?
魏德圣:《海角七号》中音乐是诠释这部电影比较取巧的部分,因为我那时候觉得音乐是很有煽动性,特别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煽动观众的情绪,让他进入到电影的氛围里面,所以在《海角七号》中,音乐是绝对的主角。《赛德克·巴莱》中,音乐是体现气势磅礴的东西。开始想找到好莱坞大师做,但大师往往会把接到的计划交给团队去做,而不是自己做,收费还很贵。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我们还是做出了合适的音乐。
记者:对大陆票房有什么期待?
魏德圣:我现在很焦虑。片子的投入成本在台湾已经持平,在香港的票房表现不好。现在来大陆上映,前期要发行,要宣传,如果票房不够,那这些前期投入就会亏钱。《海角七号》在大陆的口碑很好,但票房惨淡。这次也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特殊的族群的生活美学。
记者:十二年的坚持完成了,现在感觉轻松吗?
魏德圣:很多的东西真的一开始是个很纯粹的东西。我喜欢这个故事,然后写出来以后,觉得也许它拍不出来,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念想要完成它,只是想把它写出来而已。可是当写出来了以后,发现好像可以完成,就有了更多的幻想,我就开始做一些动作创造机会给它。可是又没有什么机会,又放弃,过一阵子,又想把那个东西重新修一下,分镜头重新再划一下,会不会对投资者更有保障一些,所以再做一次,结果也是没有机会。现在拍了出来,只是想终于拍出来了。
记者:你有很重的英雄主义情结?
魏德圣:有一点,我特别欣赏那些逼不得已反击的人,就觉得那些人身上总是有激励人的行为和语言出现,让我觉得非常热血沸腾。特别是我在困境的时候就特别欣赏这些人,就给自己一些勇气,逼不得已的反击。
记者:为呈现“雾社事件” 努力了这么久,历史给你留下的是什么?
魏德圣:历史的辐射是多面的,有时候会让人越走越广,有时候会让人越走越窄,我宁可选择前者。我要原谅自己,就必须原谅我自己的历史,我不能让历史里面的伤害一直任它腐朽,任它腐烂,任它发臭,我要从历史的伤害中吸取养分,让自己成长。发生的伤害已经造成,如今就应该包容这个伤害,让自己成长。无意去妖魔化任意一方,无论谁,无论是行为是文明还是野蛮,都是呈现得比较中立,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观史者智商的一种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