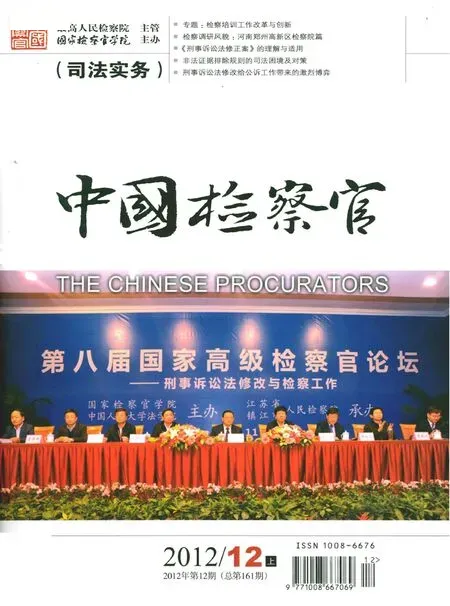论司法职务犯罪的体系化预防
2012-06-05文◎魏娜*
文◎魏 娜*
论司法职务犯罪的体系化预防
文◎魏 娜*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重庆市璧山县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402760]
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力,对保证法律实施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负有重要责任,因而其自身的公正与廉洁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司法腐败泛滥,司法公正萎靡,法律将形同虚设,社会机体也将丧失自我修复机能,最终陷于法律失灵的紊乱状态。因此,预防司法腐败理当成为构建我国反腐败策略的重要方面。
一、司法腐败的特征分析
据统计,1993年至2011年间,司法工作人员年度职务犯罪人数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其占全国职务犯罪总数的比例,最低为1997年的3.8%,最高为1999年的12.0%;自2000年以后,司法职务犯罪占全部职务犯罪的比重显著增加,法检系统年度职务犯罪呈上升态势,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相对高发领域 (详见表1)。相较其它领域,司法职务犯罪发案呈现滞后性,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具体特征。

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人数年度占比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9 2000 2001 2006 2008 2009 2010 9 2010总人数1804 2717 3792 4771 4130 4592 4626 4342 2987 2620 2761 2721总人数1804 2717 3792 4771 4130 4592 4626 4342 2987 2620 2761 2721检察院87 83 69 73 48 55 54 56 27 24 25 38 4 25 38法院53 47 72 59 145 73 46 85 109 105 137 113 37 113法检占比7.8%4.8%3.7%2.8%4.7%2.8%2.2%3.2%4.6%4.9%5.9%5.5%法检占比7.8%4.8%3.7%2.8%4.7%2.8%2.2%3.2%4.6%4.9%5.9%5.5%职务犯罪总人(案)数44540 67732 83685 82356 109039 38382 45113 49014 40041 41179 41531 44085职务犯罪总人(案)数44540 67732 83685 82356 109039 38382 45113 49014 40041 41179 41531 44085 4.1%4.0%4.5%5.8%3.8%12.0%10.3%8.9%7.5%6.4%6.6%6.2%4.1%4.0%4.5%5.8%3.8%12.0%10.3%8.9%7.5%6.4%6.6%6.2%
(一)犯罪形态渎职化
司法腐败的犯罪形态表现出以受贿为主,并与徇私枉法相伴生的渎职化特征。司法权纠正社会利益(或资源)错配,恢复利益配置的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司法权不像行政权那样积极和集中地分配社会资源,发生贪污挪用型犯罪空间较小1;但司法权却能够左右个案当事人的利益变动,具备以此向案件当事人寻租的客观条件。司法工作的隐蔽性、保密性、强制性和权威性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便利,当等价交换原则渗入司法领域,谋取经济利益成为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诱因和条件。相对贪污挪用型腐败,寻租型腐败更为隐蔽,又有司法自由裁量权作“挡箭牌”,发案风险低而寻租收益高,使得司法腐败的犯罪类型更倾向于以“个案寻租”为典型特征的渎职型受贿犯罪2。就个案寻租的分布来看,公安刑事侦查、法院民事执行和监狱管理是最易滋生司法腐败的高危领域,据有关统计,上述三个领域占政法系统贪污贿赂犯罪案发人数四成以上。
(二)犯罪主体高端化
据笔者统计,从2001年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因“远华”案锒铛入狱,到200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查处的最高级别司法官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案发免职,短短十年之间,被依法查处的正厅级以上司法高官多达15名,涉案金额愈加巨大。2010年5月,被判处死刑的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其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金额分别达1211万和1044万。事实表明,司法机关(及其内设机构)负责人已成为司法腐败的主要犯罪人群,司法腐败正逐渐向权力链条高端聚集,表现出高端化特征。
(三)犯罪模式组织化、经营化、长期化
司法权力的经营性、寻租性特征十分突出,并正由个人寻租发展演变为集体性、经营性的固定模式的长期寻租。如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原院长郭生贵,采用介绍案件给个别律师,从律师费中按比例收取回扣的手段,仅在1999年至2006年期间,就敛财高达367万元。站在“经济理性人”的立场上分析,案源是稀缺资源,出售案源谋取私利甚至以此长期经营,是典型的寻租行为。如果说郭生贵还只是兜售案源的“个体户”,那么相继发生的武汉中院13名法官、深圳中院5名执行人员、广东高院14名法官、重庆高院10名法官3集体腐败案就是渗透到从立案到执行的各个司法环节,通过机构化运作,演变为一条龙为腐败服务的寻租“企业”。从个体寻租到集体寻租,从偶然寻租到长期寻租,这是司法腐败向隐蔽性更强、权力寻租规模更大、司法不公受到更严重践踏的高级阶段发展的表现。
(四)腐败次生化
普通腐败案件进入诉讼领域后,继而又滋生出司法腐败的现象,可称之为腐败次生化,其中,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表现最为典型。所谓职务犯罪轻刑化,一般指职务犯罪案件在入罪标准、缓刑适用、减轻从轻、减刑假释四个环节相对它类案件惩罚过轻的现象。据统计,自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缓刑、免刑的共占68.7%,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免刑偏多,量刑普遍偏轻。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人情案、关系案认定减轻情节的总体比例也远高于其它案件类型,职务犯罪案件多减轻,非职务犯罪案件多从轻。
(五)犯罪分布阶梯化
在司法系统内部,职务犯罪发案状况呈梯级分布。据某市统计,该市近5年来查处的政法系统贪污贿赂犯罪中,审判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检察机关和国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发案数呈梯级依次递减趋势,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成为司法腐败的重灾区,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更是占据司法腐败总数的1/2。另从部门分布看,公安刑事侦查、法院民事执行和监狱管理领域属司法腐败行为的高发地带,三者约占司法系统贪污贿赂犯罪案发人数四成以上。
二、预防司法腐败的基本体系架构
通过上述对司法腐败特征的研判和分析,可以得出司法腐败呈现出职权愈重、寻租利益越大、行政干预越强,司法腐败则愈加严重的集中趋势。而为有效遏制司法腐败,也应当构建与其特征相对应的司法职务犯罪体系化预防机制,应当着重从司法制度、诉讼规则、内部监督和职业伦理四个方面着手,形成上述四个方面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整体预防体系。
(一)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体系
现代司法制度区别于传统司法制度的特征之一是运作的非行政化。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也是防范和抑制司法腐败的必要制度安排。与西方国家所谓“三权分立”式的政治结构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我国各级司法机关不能脱离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的立法监督而存在,在此语境下,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绝对独立。因此,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体系是我国实现司法职务犯罪体系化预防的基本制度诉求。首先,实现司法机关(机构)的财政独立。应当改革司法财务制度,变横向财政管理为纵向预算约束,使司法机关(机构)的财务收支摆脱地方财政约束,“将司法经费单列,列入国家预算,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国务院统一划拨,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支配和管理”;其次,实现司法人事独立。改革现行司法人事制度,实现司法官在人事任命、职业准入、晋职晋级、问责退出机制的自闭化和民主化,避免人事制度地方化诱发的利益板结与司法腐败。通过实施严格的司法职业准入制度,和司法干部任免的考查、公示、民主评议等人事程序,实行离任和就职审计,推行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使司法领导干部的权责之间实现有效平衡;再次,实现司法机关内部管理模式扁平化。积极推行“主审法官”、“主诉检察官”等管理体制改革措施,撤销司法机关中的行政性职务和行政性机构,打破行政化管理模式。同时,取消办案层级审批,以及重大案件经过审判委员会或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办案模式,赋予普通司法工作人员更大的办案独立性。
(二)程序优先的诉讼规则体系
从根本上抑制司法者偏执、偏袒、隐秘和肆意等主观因素所裹挟的腐败风险,有必要确立程序公正在司法理念中的核心地位,构建程序优先中立、公开、理性、公平的司法规则体系。
首先,应构建“抗辩式”诉讼架构,充分保障当事人(尤其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司法程序的主体为诉讼程序,诉讼模式的选择和诉讼结构的差异产生的腐败预防效果截然不同。实践证明,“纠问式”诉讼模式及其公检法“流水线”式的诉讼结构,存在自由裁量权过大、相互制约偏弱等固有缺陷,而“辩论式”诉讼模式使审判权回归消极裁判角色,诉讼双方得以平等、充分博弈,能够使自由裁量权在“审判权——公诉权——辩护权”三角结构中受到合理制约,更利于发掘个案公正和压缩司法腐败空间。我国目前的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律师同步介入、沉默权这三项制度的缺失,致使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结构畸弱,很难对侦方或控方形成有效对抗,诉讼地位始终处于弱势。弱势诉讼地位,往往是犯罪嫌疑人选择透过贿赂而非合法途径争取诉讼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原因。
其次,要建立现代司法公开制度。司法公开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基本的诉讼制度,成为保障司法独立、防止司法专横、保证程序公开的重要环节。而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确认了司法公开原则对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司法公开是原则,司法秘密是例外。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司法执行、强制措施等各个诉讼环节,除涉及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外,均应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相关信息。随着信息技术和新闻媒体的日益发达,重视和规范媒体监督,提高社会公众的案件参与度,是提升司法公开水平的重要途径。
(三)以检察权为核心的司法内部监督体系
司法机制具有救济性和封闭性的特点,这同时也限制了司法机关接受外部监督的空间。目前,司法机关主要的外部监督方式是立法监督与社会监督,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之于司法机关的立法监督缺乏经常性和程序性,以媒体监督为支点的社会监督又缺乏权力保障,外部监督乏力使得司法内部监督体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然而实践中,公、检、法三部门在诉讼进程中偏重职能配合,轻视相互制约,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制衡。公、检、法之间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定位不明、主次不分,是阻碍司法内部监督作用发挥的最大障碍。
因此,明确和突出检察机关的司法腐败监督者地位,建立以检察权为核心,横向约束侦、诉、审、执各环节的司法内部监督体系,有效压缩司法行为的腐败空间。首先,应强化侦查监督约束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权,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的司法审查权。其次,应强化执行监督、民事行政检察和刑事审判监督,约束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近年来,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的力度有所加强,民事判决抗诉率、改判率等关键指标均得以提升,民事审判和执行的外部监督正变得有力。再次,应明确检察权的诉讼监督定位,可考虑制定统一的《检察监督法》,依据《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权,整合三大诉讼法相关规定,对诉讼检察监督的概念、内容、种类以及监督的程序、方式、方法等进行全面、系统规定。同时,建立法律监督责任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不接受检察监督的介入调查权、责任追究权和提请惩戒权,确保检察机关能够随时介入、及时制裁,确保诉讼监督权的顺利行驶。
(四)廉洁自律的司法职业伦理体系
腐败行为的出现与司法者自身价值观念异化和司法职业伦理的缺失有着密切关联。法社会学创始人爱尔里说,“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在司法腐败惩治预防体系中,职业伦理体系是其坚固与否势将影响司法腐败惩治预防体系的整体功能。司法伦理职业教育的重心在于:培养司法者的职业尊崇感;培植司法者的法治观念和司法信仰;培育司法者的自律意识。首先,应将法治信仰教育、司法理念教育和职业伦理教育纳入法官、检察官、刑事警察等司法职业教育体系之中,着手建立司法职业伦理终生教育和督导评价机制,使职业伦理成为规范司法者执业行为的法律习惯。其次,应当建立司法职业伦理保障制度。司法职业风险高、责任重、压力大,如若无法获得与之相称的报酬,便会造成司法工作人员的心理失衡,从而促使其产生权钱交易,以便获取心理平衡的“代偿冲动”。对司法工作人员收入、职级等待遇加以特别保障,维护司法职业在社会阶层中的尊崇地位,有助于提高司法腐败的客观“门槛”,巩固司法职业伦理体系。
注释:
[1]主要以贪污、挪用或者私分罚没收入、诉讼费为主要表现形式,但数量相对行政部门的同类案件为少。
[2]据统计,贿赂犯罪占据某市检察机关查办的政法系统职务犯罪总数的82%。
[3]重庆法院“执行窝案”中被查处的10名法官被免去相关职务,其中包括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长乌小青及重庆市第一、五中级人民法院的8名庭长或者审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