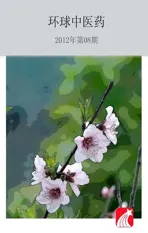从个体化技艺到标准化技术: 传染病辨证模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012-05-17聂凡周大桥聂广
聂凡 周大桥 聂广
早一段时间,笔者接连发表了一些关于传染病分期辨证的证候学调查和病因病机研究的文章[1-11],试图重新构建传染病的辨证体系。本文回顾了中医外感病不同辨证模式的发展脉络,通过梳理它们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进一步阐明了笔者在文献学研究、专家咨询和临床证候学调查基础上构建各种传染病分期辨证模式的新构想。
1 证候模型:“阶段论”与“随机论”
1.1 外感病的证候模型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教授Ronald Giere指出:科学知识的核心要素是模型,而不是规律。需要回答的经验性问题,不是理论是否为真(是否正确),而是模型对于特定的样例是否适用。[见《不谈规律之科学(Science without Law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9. ]这一理论被称之为“科学哲学的语义学派”。
自古以来,中医学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辨证思路。一是把疾病表现看成是纵向联系,如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等等;一是看成横向联系,如八纲、脏腑、气血津液等等[12-14]。笔者认为,外感疾病(对应西医的感染性疾病或传染病)有一个明确的发生发展过程,纵向辨证思路是在强调病因、病性、病位和病征的同时,更加注重疾病的演变过程,可以称之为“阶段论”(或称分期辨证);内伤杂病往往在强调例如病因、病性、病位和病征的同时,更加关注疾病的寒热、虚实、气血津液的消长变化,在临床上应用辨证论治的灵活性,证随机变更加符合个体化治疗,可以称之为“随机论”(或称分型辨证)。因此,在中医临床中一直有“外感宗六经,杂病宗脏腑”的说法。
1.2 临床表现的三个特征
当代医学门类越分越细的一个缺陷是,众多专家们在某一病种辛勤耕耘而缺乏整体观念。例如病毒性肝炎的临床诊断,目前分为急性肝炎、慢性肝炎、重型肝炎、淤胆型肝炎和肝炎肝硬化5类,急性肝炎又分黄疸型和无黄疸型,慢性肝炎分轻、中、重度(又分E抗原阳性和E抗原阴性),重型肝炎又分急性、亚急性和慢性(分早、中、晚期),淤胆型肝炎又分急性和慢性,肝炎肝硬化又根据炎症情况分活动期和静止期,根据机体状态分代偿期和失代偿期,根据肝脏储备功能分Child-Pugh A、B、C级。整体上看,这种分类有些杂乱无章,缺乏规律性。
如果借鉴一下中医的共性思维(根据各种外感病的传变规律,寻找某种一致的辨证方法,如卫气营血或三焦辨证),上升到传染病的总体框架进行整体梳理、逻辑分析,将其临床诊断从三个方面考虑,即发病类型(分型)、演变过程(分期)和病情轻重(分级)。那么,急性肝炎、慢性肝炎、重型肝炎、淤胆型肝炎和肝炎肝硬化5种类型为第一层次。第二层次一般有早、中、晚期的演变过程,但是疾病的不同发病类型有不同的区分,如急性肝炎有前驱期(相当于中医的表证期)、症状明显期和恢复期;慢性肝炎有静止期(无论是药物控制还是自然病程)和活动期;重型肝炎有急性坏死期、平台期和恢复期/终末期(笔者不同意传统的早、中、晚分期,因为“晚期”的规定里面不包括存活的患者,而不少康复患者还有一个恢复期的过程)[1]。第三层次即轻、中、重的分级,它只存在于疾病活动期或症状明显期,如急性肝炎的症状明显期,慢性肝炎、肝炎肝硬化的活动期(Child-Pugh A、B、C分级也可考虑改为轻、中、重的分级以便统一),以及重型肝炎。以上考量如果推广至每一种传染病,则可以执简驭繁,脉络清晰,具备科学美的特质。
通过以上共性思考,未来医学同样可以将流行性感冒进行分型、分期和分级,而不仅仅划为轻、重两型或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笔者设想,第一层次包括上呼吸道型、肺型和肺外型(暗合实践中卫生部专家组对于甲型H1N1流感轻型、重型和危重型的划分),第二层次上呼吸道型分为发病期(相当于中医的表证期)和恢复期;肺型分为表证期、里证期和恢复期;肺外型分为表证期、里证期和恢复期/终末期,不同时期还有轻、中、重的分级。当然,以上纯属于个人想法,仅为举例,有没有可操作性还得广泛征求意见。
2 传变模式:不辨菽麦的笼统学说
从技术层面讲,诊疗方案包括辨证模型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规范,而技术规范的进步都是经由个体化技艺向标准化技术发展的历程,“诊疗指南”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和修订即代表了这一趋势,也确实促进了临床疗效的提高。那么,为什么病毒性肝炎以及所有外感病的诊疗标准均采用分型辨证模式?这与当时“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初级的中西医结合价值取向(即“重实用、轻理论”的传统思维特征)有关,也与外感病传变模型的自身缺陷密切相关。搜罗中医学关于外感病的传变学说,试从现实需求剖析其内在不足。
2.1 外感病传变模式
2.1.1 “腠理→血脉→胃肠→骨髓”模式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闲,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这个传说没有说服力。
2.1.2 “腠理→络脉→经脉→腑脏”模式 《素问·皮部论》:“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客于络脉,络脉满则注入经脉,经脉满则入舍于腑脏也。”
2.1.3 “腠理→(阳明、太阳、少阳)→腑脏”模式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腠理开而中于邪,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于膺背两胁,亦中其经,……故中阳则溜入经,中阴则溜入腑。”
2.1.4 “皮毛→肌肤→经脉→六腑→五脏”模式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邪风之至,疾于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经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生半死也。”
2.1.5 “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模式 《素问·热论》对六经传变做了经典描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一古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言,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2.1.6 “九传”模式 《瘟疫论·统论疫有九传治法》:“夫疫之传有九,……盖瘟疫之来,邪自口鼻而入,感於膜原,伏而未发者,不知不觉,巳发之後,渐加发热,脉洪而数,此众人相同,宜达原饮疏之,继而邪气一离膜原,察其传变,众人不同者,以其表里各异耳,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於里者,有里胜於表者,有先表而後里者,有先里而後表者,识此九传,其去病一也。”
2.1.7 “卫→气→营→血”模式 《温热论》:“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玄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
2.1.8 “上焦→中焦→下焦”模式 《温病条辨·中焦篇》:“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
2.2 “寒温统一论”失败原因
随着温病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出现历经数百年的“寒温之争”。争论焦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伤寒可不可以包括温病;二是《伤寒论》方可不可以治疗温病。清代后期俞根初、吴坤安、杨栗山等开始尝试融汇伤寒与温病两种学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章巨膺、万友生等力推“寒温统一”(如专著《寒温纵横论》、《寒温统一论》、《热病学》等以及若干论文)。并进行了“应用寒温统一热病理论治疗急症的临床研究”,对流行性出血热、急性支气管炎、急性肺炎、急性菌痢、急性肠炎等多种传染性、感染性疾病按自行设计的寒温统一方案治疗。然而,尽管“寒温合流”的呼声很高,也完全符合历史潮流,但迟迟不能实现,甚至于至今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为什么呢?
2.2.1 难以协调的“统一纲领” 梳理“寒温统一论”失败的诸多原因,最主要的是看似学术繁荣、实际上莫衷一是的外感病统一纲领。
(1)以六经辨证统一:裘沛然[15]认为卫气营血只是六经病中部分症候而已,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可以统辖于六经之中。郭辉雄[16]提出以六经特定的结构层次和生理功能的特点及病理演变为依据,各型证候可在六经辨证的基础上调整充实,补充卫气营血、三焦体系中主要证候。黄松章[17]主张以六经机制为主体联结温病两机制的“两征六型方案”。孟庆云[18]认为伤寒六经辨证以三阴三阳等六个层次表述了热病过程的阶段性,模拟了病因、病位、正邪消长,包含了病程的传变转归。肖德馨[19]把整个人体和外感病过程分成六个子系统,根据六经的结构定位、功能定性、定量及发展规律定向来确定证型的归属,倡议用“六经系统”概念做理论框架,形成新的“六经系统辨证”方法和体系。杨麦青[20]结合实验医学知识,从血管神经反射学说来探讨六经本态,描绘出三阳病皮表内脏反射及三阴病内脏内脏反射图,得出以六经系统辨证方法来统一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的模式。
(2)以卫气营血辨证统一:姜建国[21]认为六经辨证并非单纯的外感病的辨证纲领。卫气营血辨证是由表及里横向层次,更能从本质上体现外感病的演变规律。邓铁涛[22]统计了2391例内科热病使用各种辨证方法的数字,适于卫气营血辨证者1896例,占79.2%,认为卫气营血辨证更适合外感热病诊疗。
(3)以八纲辨证统一:万友生[23]认为六经辨证体现了表里寒热虚实阴阳,三焦和卫气营血辨证纲领,仍以《伤寒论》的八纲为规范,用八纲来统一顺理成章。萧敏材[24]也认为,外感热病统一的辨证论治纲领也应当建立在八纲辨证的基础上。
(4)以分期辨证统一:胡仲翊总结出五期辨证法:恶寒表证期、表里同病期、入里化热期、入营动血动风期、阴阳损伤期,分别充实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证候[25]。吴银根等[26]根据外感热病过程中人体的机能和代谢改变可归为五期:发热前期、发热期、热盛期、邪盛正损期和虚衰期。黄梅林[27]根据现代医学,将外感病分为表寒期(属寒化阶段,以太阳病为主要代表证)、中期(热化阶段依病情轻重分为化热期、壮热期、热极期,化热期以卫分证或少阳病为主要代表证,壮热期以气分证(包括阳明病、中焦病为主要代表证,热极期以营血分证为主要代表证)后期(正虚期,属正虚阶段,以太阴病,少阴病及温病下焦病为主要代表证)进行辨证论治。
(5)以脏腑气血辨证统一:沈凤阁[28]认为,六经辨证充分体现了八纲的具体运用,卫气营血辨证是辨病邪之在气在血,三焦辨证突出了以脏腑为病变中心,三种辨证基本病机变化是脏腑气血的功能失常,倡导以脏腑为纲,以气血为辨,以八纲为用。
(6)以三维辨证统一:南京中医药大学等根据临床证候调查发现,外感热病的证候及其病理变化都是由病期、病位和病性三大基本要素组成,提出了三维辨证方案,即辨病期(表证期、气分期、营血期、正衰期、恢复期)、辨病位(邪在肌表、邪在半表半里、邪在脏腑)、辨病性(虚实、寒热、六淫、其他)等[29-30]。
(7)其他:如符友丰[31]认为西医的应激学说与中医外感病层次相似,六经中三阳病证,温病上中焦卫气形证颇似应激学说的反抗期;三阴病证、下焦营血证则颇似其衰竭期。也有人认为,伤寒与温病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疾病,辨证方法各异,不是统一在六经之下,也不是统一在三焦之下。凡热病而有三焦程序者就用三焦,有六经程序者则用六经,二者不必强合[32]。
2.2.2 不可回避的诊疗现状 科研的成功要素是直面问题,紧扣现实。那么,统一外感病(传染病)辨证模式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如何从现实与问题之间找到通路?
(1)传染病学的理论背景:在传染病医院和传染科的病房里,笼统称谓“外感病”(或“伤寒”、“温病”)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被现代传染病学分割成门类繁多的病毒感染、细菌感染、立克次体感染、螺旋体感染、原虫感染、蠕虫感染等等不同的疾病,医生不得不一种疾病一种疾病地研究它们的证候规律和辨证模型,因为每种疾病具有不同的发生发展过程和演变规律,企图简单化地建立一种辨证论治模型应对是不现实和不可靠的。医生不可能面临一个能够保持特色的纯中医氛围,也不可能抛弃西医的诊断、治疗而一味强调中医的一体化,更不可能遇到未经西医知识干预的“单纯病人”。
(2)循证医学的科技背景:当代中医药科研早已突破那种司外揣内、个案记录形式,尤其是循证医学、临床流行病学方法的建立,对中医学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果不面对现实、大胆突破,而继续在“自主创新”旗号下固守特色就可能寸步难行。事实上,所谓辨证体系不过是一种理论支撑下不断深化进步的技术模型,是一种从个体化技艺上升为标准化技术的可操作性强的诊疗路径。如果把《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温病学的卫气营血辨证看得过于神圣,变成不可更改的教条,就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因此,现代中医师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以证据为基础,制定精细、严格的操作规程。事实上,设计越严密、精细,参数越多,结果越可靠,模型的可操作性越强,规范化越容易;否则,设计得越粗糙,越简单,变异性越大,可操作性就越差。
(3)医院管理的人事背景:在现代医院管理背景下,传染病的分类管理,临床医师的分类使用已经用了规范的指导原则。目前的传染病医院和传染科已经不能接受中医专业的毕业生,中医专业的学生只能到中医科工作。而且,现代临床不能离开西医诊断,中西医传染病医生必须掌握传染病学理论,否则可能吃官司。如果一厢情愿地搞出来的“寒温统一”方案仍然要保持中医学的独立性,不与传染病学的知识更新、临床诊疗的现实需要、传染病诊疗的中西医并存格局接轨,闭门造车的设计难免不成为屠龙之术。
2.3 六经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的自身缺陷
传统中医学对于外感病辨证一直采用分期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但是当中西医结合采用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的临床模式后,所有的传染病均采用了分型辨证。这种退让的内在原因在于“寒温合流”时遇到的最大障碍——采用什么辨证方法?长期纷争局面的出现,是因为早期的辨证方法——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都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2.3.1 把握临床特征的欠缺 对于外感病临床特征的把握,古代医家有其内在的必然的缺陷,这是因为:(1)医师从业的方式,由于当时的专业分化不全和病种分类模糊而难以对某一疾病进行集中而深入地观察和研究;(2)资料的搜集方法,由于没有数理统计和临床流行病学的介入,个案分析往往导致结论偏倚;(3)理论移植的实用主义,由于受到笼统的自然哲学支配,可供选择的理论模型非常有限,如六经辨证的分期依据基本上来源于《素问·热论》的“一日巨阳……”,最后不得不忙碌于临床“变数”的应对。
2.3.2 分类病种的不确切性 由于病原学、病理学、发病学研究的欠缺,无法对外感病进行科学的疾病分类:(1)《伤寒论》虽然将外感病按六经分证,但基本上是对整个外感病笼统而言,而缺少病种的概念;(2)温病学虽然对四时温病进行了风温、春温、暑温、湿温、秋燥、伏暑等分类,但其模型的精细程度、可操作性与临床实际还有较大差距,难以高效指导当代传染病诊疗。
2.3.3 应对变数的处理方式及其不足 为了增加六经辨证的可操作性,虽然后世医家总结了“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循经传”,以及不以此序的 “越经传”(“越经传”中的表里两经相传者为“表里传”),来解释临床上复杂多变的演变特点:(1)太阳之邪可传诸经;(2)阳明之邪不再传经;(3)少阳之邪可传阳明、太阴;(4)太阴之邪可传少阴;(5)少阴之邪可传厥阴;(6)脏邪还腑,阴病出阳。针对“伤寒日传一经”,《伤寒论》亦进行了自身修正:“伤寒一日有传经者”,“伤寒二三日也有不传经者”。而且《伤寒论》中的本证、兼证、变证、类似证、坏证、复证、经证、腑证各有其内涵和意义,最终“要判断是否传经,欲传何经,要点在‘观其脉证’,有该经证,即知邪已传该经。” “六经辨证”为什么要添加这么多的附加条件,而且最后不得不“观其脉证,知犯何逆”?就是因为它没有具体研究每一种外感病的实际病程,笼统使用这一简单规律无法反映不同种类外感病的阶段性变化。
在卫气营血辨证中,尽管有“顺传”、“逆传”、“合病”、“并病”等对常规的卫气营血传变修饰,但仍然处于用一种简单的模型来解释种类繁多、表现各异的外感病临床过程。要提高临床辨证的准确性,必须根据每个病种或一类疾病的临床特征进行深入研究,以便获得高效、切实可行的辨证模型来指导临床。
不同疾病具有明确不同的临床经过,笼统辨证的结果是顾此失彼,增加变数。虽然辨证模型增加了“常”与“变”的概念,似乎能够通过灵活性与原则性来协调,从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辨证模型的粗糙和笼统。中医作为个体化技艺,缺乏众多的技术参数,就需要像庖丁解牛那样熟能生巧,难以进行规范化培训。每个人的掌握情况差异很大,后学者各以心悟,易于牵强附会,如“六经”的解释千奇百怪。
3 分型辨证:标准化浪潮下的实用理性
标准化是近二、三百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而发展起来的,也是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当前,各种诊疗常规、指南的诞生和不断修订,正是标准化浪潮席卷而下的结果。
“分型辨证”是“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的最初产物[33],也是标准化过程中的仓促选择。今天,当深入分析与评价“分型辨证”在传染病辨证体系应用过程中的功过得失的时候,就会发现它自身存在的一些深层问题:(1) 中医学有那么多的辨证方法,分型辨证是如何成为各科疾病包括传染病“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唯一选择,而一统天下的?(2) 分型辨证能否全面反映中医学的辨证论治优势,是否存在某些难以克服的理论困惑?(3) 能否根据不同疾病不同疾病类型探讨新的辨证论治模式?
3.1 违背古代训示
自古以来,在中医临床中一直有“外感宗六经(辨证,含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等),杂病宗脏腑(辨证)”的说法。为什么会有如此规定或训示?可能因为:(1) 外感病或传染病具有明确的外感病因(病原学)特征;(2) 发病具有一定的集聚性,便于人们认识其演变过程和传变规律;(3) 外感病一般病程较短,易于辨别不同时期的临床特征。但是,在标准化过程中对各科疾病都采取“分型辨证”的策略,虽然操作简单,易于举一反三,但是明显违背了古训。虽然将不同类型的外感病一律采取六经辨证,或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有“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笼统性缺陷,但是如果选择分型辨证则又有“削足适履”的嫌疑,恐怕会丢掉外感病一些自身的特色,而影响辨证论治的精髓。
3.2 抛弃病程研究
在标准化过程中对各科疾病都采取“分型辨证”的策略,虽然操作简单,易于举一反三,但是对于外感病(相当于西医感染性疾病或传染病),不仅要关注它的发病类型、病情轻重,往往更关注它的发生发展过程,以便针对不同阶段采用相应的措施,判断其预后转归。不同的辨证体系具有不同的临床价值,例如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是新感温病的辨证体系,六经辨证是伤寒的辨证体系,或者说三焦辨证比较符合消化道传染病的证治,卫气营血和六经辨证比较符合呼吸道传染病的证治,而血液传播性疾病易入难出,病程缠绵,演变复杂,则可能符合伏气温病的辨证规律。
3.3 忽视病机分析
采用分型辨证的弊端之一是忽视病机分析:(1) 例如慢性肝炎,从肝郁脾虚演变为肝胆湿热,又进展为肝肾阴虚,或瘀血阻络,毫无规律性可言,似乎是一些跳来跳去的疾病表象的排列组合,辨证论治是实际上的对症处理[34];(2) 从肝硬化看,无论肝气郁结、水湿内阻、湿热内蕴、肝肾阴虚或脾肾阳虚任何一个证型,都不能缺少“瘀血阻络”的临床表现,即“肝络瘀阻”是其本质特征,而所谓其他分型实际上是“肝络瘀阻证”的兼夹证,是“主”与“次”的关系,并非肝硬化本身能够区分为截然不同基本证型[35-36];(3) 在重型肝炎,一直未能拿出统一的“分型辨证”方案的根本原因在于局限于应用“中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传统模式,把重型肝炎当成了黄疸、鼓胀、出血、昏迷等四个病,每个病又分为若干型辨证论治[37],于是病机纷繁杂乱,莫衷一是,更难以获得多数专家的共识。
3.4 淡化理论思维
在分型辨证实施了20多年以后,它内在的“去理论化”的实用主义倾向就暴露了出来。记得在国家“十一五”重大科研专项的招标过程中,艾滋病、肺结核和病毒性肝炎等项目都把证候学研究放在了重要位置。又如病毒性肝炎研究中,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慢性重症肝炎等项目都包括了证候研究。而且仅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研究就有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北京佑安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深圳市中医院4家在做。如此重叠、重复的证候研究,基本思路都是“分型辨证”。在标准化的目标前提下,抽空了中医理论思维内核的辨证论治,遇到了现实中的难题:
首先是主、次症很难确定。例如,有的患者症状体征很少,特别是稳定期,常常会“无证可辨”,临床如何去通过主症多少、次症多少来确立证型?
其次是演变过程缺乏内在规律。例如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从携带者到活动期,通过治疗又可以从活动期转为稳定期,在分型辨证中体现的是从肝郁脾虚到肝胆湿热,治疗后又从肝胆湿热到肝郁脾虚。这样变来变去的机理何在?怎样用中医理论阐释?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三是证候之间难以区分。例如肝炎肝硬化,瘀血阻络是每个患者都包含的临床表现(实际上是基本证候),而肝气郁结、水湿内阻、湿热内蕴、肝肾阴虚、脾肾阳虚相当于兼夹证,临床上不能因为这些兼夹证而把它们截然区分成为不同的证型,因为任何一个证型具有“瘀血阻络”的本质特征,与所谓其他分型并不是并列关系,只能是主、次关系。
4 分期辨证:传染病证治的新构想
4.1 研究定位
一般而言,证候规范化包括四个方面:(1)证候概念规范化;(2)证候体系规范化;(3)证候命名规范化;(4)具体证候规范化。毫无疑问,本文的研究定位在证候体系规范化,属于证候规范化的范畴。
证候规范化的主要难点,是证候诊断标准的统一性与临床诊断的灵活性之间的矛盾[38],涉及到证候体系规范化也是如此。前面,我们分析了“寒温合一”失败的教训,其突出表现是制订出来的统一纲领五花八门,谁也说服不了谁,更谈不上诊断标准在临床上推广应用。笔者的想法是,尽量使统一诊断标准的产生程序各环节严格化、科学化,使之对临床多样化诊断标准的代表性更强[39]。
理论上讲,任何规范(标准)都具有约定性和真理性两种基本属性。约定性是指规范必须对概念的名(名称)与实(内涵和外延)的关系予以确定;真理性是指规范所确定的概念的名实关系必须合乎事物的客观规律。约定性使规范合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真理性在于保证规范具有实际意义。规范必须具备约定性,规范只要具备约定性就可成立。例如,我们根据各种传染病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统一采取分期辨证的模式,这就是约定性。而分期辨证是否符合临床实际,应用过程中是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能否获得大家的共识?则是个真理性问题。
4.2 预期目标
4.2.1 与现代诊疗实际接轨 鉴于现代传染病诊疗早已超出中医药独立干预的时代,新的辨证模式则必须考虑:(1)传染病学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模式对中医药干预的现实需要;(2)现代传染病的临床管理模式对中医药干预的制约性;(3)西医诊断、治疗措施对患者机体和心理的影响以及患者对中医药接受程度;(4)传染病医师(包括西医院校医疗系的毕业生)接受的简单性和可操作性(体现着两种医学临床和理论融合的程度)。
4.2.2 与中医理论思维接轨 在西医对传染病临床研究的基础上,体现出中医药的理论思维,而不是如“辨证分型”的“去理论化”,不分外感、内伤,千篇一律、大同小异的几个分型,甚至变来变去都没有足够的道理可讲。
4.2.3 与传染病分类体系接轨 尽管传染病多按按病原学分类,如病毒感染、立克次体感染、细菌感染、螺旋体感染、原虫感染、蠕虫感染、真菌感染等,但按传播途径分类与临床表现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关系更为密切一些。本研究拟按呼吸道传染病(如流行性感冒,肺结核,腮腺炎,麻疹,百日咳等,为空气传播)、消化道传染病(如蛔虫病,细菌性痢疾,甲型肝炎等,为水、饮食传播)、血液传染病(如乙型肝炎,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丝虫病等,为生物媒介等传播)、体表传染病(如血吸虫病,沙眼,狂犬病,破伤风,淋病等,为接触传播)等等划分。
4.2.4 与疾病临床特征接轨 根据临床表现的差异把出疹性疾病、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等等归类,可能更接近于临床实际。
4.2.5 与西医干预过程接轨 中医药治疗必须与病原学治疗、对症处理和支持疗法等步或先后而行,例如肺结核、乙型病毒性肝炎、细菌感染性疾病等的辨证必须考虑病原学治疗的证候变化规律,否则就会滞后而无法满足临床需要。
4.3 研究思路
关于“分期辨证”的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笔者已经进行甲型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肺结核、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慢性重症肝炎、肝硬化等,虽然每个病种样本量不大(302~2024例)[1-11]。基本思路是:(1)根据不同疾病类型的具体实际,确定其病程(分期),调查不同时期的症状体征发生频率;(2)采用证素分析(证素频率),确定其不同病期的主要病机、次要病机;(3)确定不同病期的基本证候和兼夹证候;(4)同时,按分型辨证的程序设置对照组,以观察两种辨证方法的得失优劣。当然,进一步的研究还包括治疗,如何确定主方及其加减应用?

图1 手足口病分期辨证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图1是对手足口病进行分期辨证研究的技术路线图,希望在文献学研究、专家咨询和临床证候学调查基础上探索构建各种传染病辨证模式。
参考文献
[1] 聂广. 重型肝炎的分型、分期与分级[J].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11,21(1):55-57.
[2] 聂广,林巧. 人禽流感中医病因病机的探讨[J]. 世界中医药,2008,3(3):131-133.
[3] 刘红,夏章,聂广,等.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证候学调查与分期辨证模式探讨[J]. 环球中医药,2011,4(2):109-113.
[4] 黄练秋,刘映霞,聂广,等. 472例新型甲型H1N1流感的分期辨证与病因病机规律探讨[J].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21 (2):72-76.
[5] 洪可,聂凡,聂广,等. 2024例手足口病患者分期辨证和病因病机的研究[J]. 环球中医药,2012,5(5):332-336.
[6] 聂广,洪可,聂凡,等. 手足口病“皮肤—经脉—脏腑”传变假说[J]. 环球中医药,2011,4(5):354-357.
[7] 李静,聂广,余卫业,等. 抗痨药干预过程的肺结核分期辨证的探讨[J]. 环球中医药,2011,4(3):174-177.
[8] 聂广,李静. 肺痨纳入外感病辨证体系的探讨[J]. 环球中医药,2010,3(6):442-445.
[9] 夏章,李秀惠,聂广,等. 新型甲型H1N1流感的分期辨证模式研究[J]. 湖北中医杂志,2010,(8):31-33.
[10] 袁虹,夏章,聂广,等. 慢性乙型重型肝炎分期辨证模式研究[J].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10,20(5):277-280.
[11] 袁虹,曹廷智,聂广, 等. 302例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中医证候学探讨[J].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09,19(6):346-349.
[12] 聂广. 中西医诊断的模型差异[J]. 医学与哲学,1990,10(3):8-10.
[13] 聂广. 证的探索[J]. 中医研究,1990,3(2):6-9.
[14] 聂广. 辨病与辨证的模型差异及其互补[J]. 医学与哲学,1992,12(7):6-8.
[15] 裘沛然.伤寒温病论争中的若干问题[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3,(4):5.
[16] 郭辉雄. 六经是寒温统一的基础[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3,(4):7.
[17] 黄松章. 伤寒六经为基础的寒温综合论[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3,(2):6.
[18] 孟庆云.从模型法看伤寒六经[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5,(1):19.
[19] 肖德馨.六经辨证纲要[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1,(3):1.
[20] 杨麦青.外感病辨证纲要之我见[J].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3,(4):9.
[21] 姜建国.论六经辨证与寒温统一[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24(1):10-12,15.
[22] 邓铁涛.外感病辨证统一小议[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3,(3):6.
[23] 万友生.八纲统一寒温证治建立热病学科体系[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3,(3):2.
[24] 萧敏材.论伤寒与温病学派之争[J].中医杂志,1962,(11):1-2.
[25] 金雪明,胡之璟.胡仲翊治疗外感热病的经验[J].江苏中医,1996,17(12):5-6.
[26] 吴银根,沈庆法.中医外感热病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38
[27] 黄梅林. 统一外感热病辨证纲领探索[J].中医药研究,1989,(5):8-11.
[28] 沈凤阁.关于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如何统一的探讨[J].新医药学杂志,1979,(4):7-9.
[29] 刘兰林,杨进,倪媛媛. 构建外感热病辨证体系的探讨[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05,20(1):18-20.
[30] 杨进.外感热病辨证的“三维观”[J].陕西中医,1988,(11):509-511.
[31] 符友丰.论外感病辨证中的层次特征[J].医学与哲学,1986,6(12):31-33.
[32] 姜春华.伤寒与温病[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64,(1):2.
[33] 中华医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科史[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67-168.
[34] 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 病毒性肝炎中医辨证标准. 第十一届全国中医肝胆病学术会议论文集,宜昌,2004. 北京:中华中医药学会, 2004:188-190
[35]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 肝硬化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草案)诊断[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24(10):869-871.
[36]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 肝硬化临床诊断、中医辨证和疗效评定标准(试行方案)[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4,14(4):237-239.
[37] 聂广,余绍勇,江福生, 等. 重型肝炎中医辨证分型标准的初步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01,8(3):172-176.
[38] 邓铁涛. 中医证候规范[M].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0.
[39] 于慎中. 诊断规范化与中医学发展[J]. 医学与哲学,1990,10(11):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