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世英主任医师学术思想探析*
2012-05-16于春泉马佐英王学岭吴世骥
何 山,于春泉,马佐英,王学岭,吴世骥
(1.天津市泰达医院,天津 300457;2.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0193)
何世英主任医师学术思想探析*
何 山1,于春泉2,马佐英2,王学岭2,吴世骥2
(1.天津市泰达医院,天津 300457;2.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0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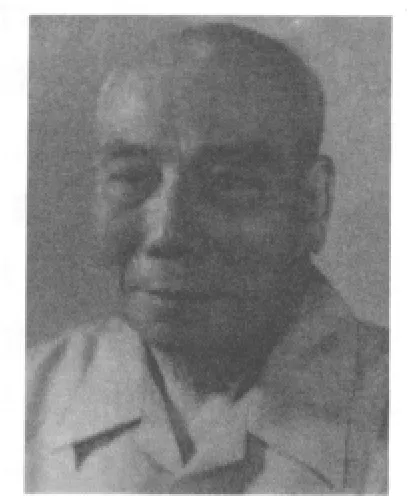
简 介:
何世英(1912-1990),男,主任医师,毕生致力于中医临床、教学,尤其在儿科及脑病的研究上颇有建树,曾任天津市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天津市卫生职工医学院行政领导组成员兼中医部主任、天津市中医院总顾问兼脑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天津分会副会长,天津市中医学会会长,《天津中医》杂志主编,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府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兼中医组组长,天津市卫生局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兼中医专业组组长,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常委等职,主编《历代儿科医案集成》、《增订幼科类萃》,指导编写《何世英儿科医案》等书,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中医;学术思想;何世英
作为名家辈出的北平华北国医学院第2届学员、施今墨等医学名家之后学,何世英主任医师可谓师出名门,学有根柢,他行医五十八载,医绩斐然,在内科、妇科、儿科等领域均有建树。何老根据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总结有效方剂,调整剂型便于服用,无私地将自己治疗儿科疾病的验方全部贡献给天津市儿童医院,临床应用至今,其中疏表灵、清降丸、清肺丸等已经家喻户晓,成为许多家庭必备的儿童用药。何老主编《历代儿科医案集成》、《增订幼科类萃》,指导编写《何世英儿科医案》等书,发表论文三十余篇。现将其学术思想介绍如下。
1 开拓创新,走中西医结合之路
尽管中医、西医的理论体系不同,但其保障人类健康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何老认为,提高中医学术水平,除了要认真继承前人的宝贵经验外,还必须汲取现代医学及自然、社会科学知识。他指出,诊断明确,应急措施多,是西医之长;辨证施治,灵活性强,是中医的特点。何老曾举例说:“如急性肾炎患者临床症状刚刚消失,过去中医常认为病愈,但部分患者即使症状已经消除,而尿化验仍不正常,存在着临床症状再度出现,甚至发展成为‘慢性肾炎’的可能。又如肝炎患者,如属无黄疸型,单凭中医直观诊查,很难确诊。这不但是治疗,而且是关系到防病的重大问题。”另外,当某些疾病西医一时不能确诊,难以定出有效治疗方案,仅是采取对症疗法时,中医却往往可以通过辨证论治治愈疾病,从而走在西医最后诊断之前。中医和西医各有所长,将两者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就能提高临床疗效。以乙脑为例,从1973—1978年,何老所在单位共收治乙脑患者362例,在中西医结合以中药为主的治疗原则下,平均病死率仅为2.8%。
何老以中西医结合的观点深入阐释儿科病的病因、病机,常能自抒新见,并以此指导用药。根据《幼科发挥》中“小儿泄泻,大渴不止者,勿与汤水饮之,饮之则口愈渴而泄愈甚,宜生脾胃之津液,白术散主之”的论说和临床经验,何老指出,对婴幼儿消化不良,西医所云低渗性脱水与泄泻变证的伤阳相似,高渗性脱水与泄泻伤阴相似,而等渗性脱水即与泄泻阴阳两伤证相似,白术散有利于高渗、等渗脱水症的修复。考钱乙白术散药性略温,但何老根据临床所得,认为该方有扶助脾阳、补养脾阴的作用,这种生津护阴法如能防止体液的消耗和维持电解质平衡,可有利于减少胃肠道外的输液。对肾炎的辨证,何老提出要抓住水肿和血尿两大主症。病机上,水气潴留是静态,血尿排出是动态。治法上,利湿消肿是以动制静,清热止血是以静制动。两症并存时,重在治主症,特别是对顽固性肉眼血尿,要全力止血,不能辅以利水,以减少因动制静而影响了止血效果。他还通过对尿毒症病机的分析提出,利尿仅治其标,活血化瘀乃治其本。这一认识为进一步提高该病治疗效果作出了贡献。
何老在儿科的衷中参西方面进行了大量可喜的尝试。例如西医认为白喉患者多死于合并心肌炎引起的心衰,而何老指出,此相当于少阴病,故结合《温病条辨》中“温病误用升散,脉结代,甚则脉两至者,重与复脉,虽有他证,后治之”的理论将此病按轻重分为4度,分别予郑梅涧养阴清肺汤、吴瑭加减复脉汤(或养阴清肺汤去薄荷加人参)、四逆汤加人参、通脉四逆汤施治,挽救了不少患者。如1例重症肺炎患儿,发热紫绀,心音弱而低钝,两肺底有湿啰音,肝脾肿大,西医诊断为病毒性肺炎合并心力衰竭,因其舌淡润无苔,脉浮滑无力,眼睑及下肢微肿,尿少、腹胀,何老认为系气虚复感风寒,遂仿“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主之”,合三拗汤2剂证缓。另1例患者西医诊为肺炎合并心肌炎,虽有高热气急、肺部湿罗音、肝脾肿大等症,然因面苍便秘,阵寒阵热,遂诊为气虚风热留于少阳,予小剂小柴胡汤配青蒿,3剂而愈。
2 辨病与辨证相参,经方与时方并重
何老认为,西医擅长定性、定位诊断疾病,而中医则重视整体反应和动态变化。只有把中医的辨证与西医的辨病相结合,才能克服不打开“黑箱”的中医学术局限性,加深对疾病的微观认识,同时也弥补西医在疾病过程中对人体的整体反应及动态变化重视不够的缺陷。辨证与辨病相辅相成,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前者认识上的提高。对于某些疾病,可采用辨证、辨病相结合的方法。例如现代医学认为麻疹合并肺炎者约有以下5型:高热败血型、脑型、胃肠型、喘息型、心脏血管型。何老指出上述5型症状与中医疹毒内陷邪攻五脏,即入心、入肝、入脾、入肺、入肾,非常类似,这对指导用药、提高疗效有着重大的意义。何老治疗疑难杂证验案很多,都是结合现代医学,辨西医病而辨中医证,屡奏奇效。
一般认为,“经方”专指《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记载的方剂,而后世医家在精研张仲景学说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而创制的方剂谓之“时方”。“经方”、“时方”之争其来已久,何老认为学术流派越多,越有利于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如“经方”与“时方”之争推动了以急性热病为主的中医理论的发展和临床疗效的提高,当然也容易产生固守一隅的偏见。“经方”用之得当,效如桴鼓,这是历代医家的共识,但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按照温病辨证论治及应用“时方”才能取效。例如热病神昏一证,完全依照《伤寒论》“胃家实”对待是不妥当的。又如外感初期属温病者,仍然按照治疗伤寒的原则,坚持“一汗不解,可以再汗。再汗不解,可以三汗”及“下不厌迟”等论点,也是不合理的。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伤寒论》不可能概括万病,温病学说就是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伤寒与温病是外感病的两大类型,每一类型包括若干病种,而同一病种也可能在病程中出现不同的证型。两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其理论核心都是脏腑经络学说,《伤寒论》的一些方剂仍为温病学派所沿用。因此,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辨证应该密切地结合起来,根据具体病情灵活掌握,“经方”、“时方”统一运用。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说:“名医之病,首在门户之学。”何老强调,临证之际,是以保证疗效为宗旨,故需精心辨证,据证遣方用药,当摒弃伤寒、温病门户之见,打破“经方”、“时方”界限,有斯证即用斯方。他认为自己,既不是经方派,也不是时方派,而是综合派。
何老认为小儿病变不甚复杂,故喜用药简效捷的仲景方。如患儿周某,行心包剥脱术后,高热、巩膜黄染、鼻煽唇绀、遍体冷汗、纳呆、气急、痰黄而稠、便黏奇臭、脉滑疾数,肺部满布湿罗音,透视为左肺脓疡,左侧胸膜炎。何老诊断为正虚邪实的湿热结胸证,予竹叶石膏汤去半夏、大枣,增入瓜蒌、贝母、知母、茵陈蒿、灯芯草,1剂即热退气平。又如9个月的患儿徐某,水样便暴注下迫1周,且高热,会诊当日即泄泻20余次,肢厥,缓缓抽动,肤干尿少,血压 35/20mm Hg(1mm Hg≈0.133 kPa),舌淡,脉细无力。何老诊断为泻伤脾阳,发为慢惊风,予理中汤2剂,配合自拟磨积片,病遂去大半。再如患儿许某被诊为肾炎合并尿毒症而急诊入院,呼吸深促、面青唇紫、烦躁无尿。何老诊断为水气壅下凌土,急投猪苓汤加琥珀、三七等利水逐邪,开闭安神,9剂而愈。其他如将防己黄芪汤合防己茯苓汤治风湿性疾病,用栀子豉汤、麻杏石甘汤及小柴胡汤分别治流感初期、中期及伴见胃肠道症状者等,均无一不是对经方的妙取。
对时方的运用,何老也极有心得。如1岁患儿张某,高热咳喘,惊厥,经治未效。何老见其嗜睡,喘促痰鸣,颈项强直,无大便,舌红苔腻,脉弦滑数,投俞氏羚角钩藤汤冲服紫雪散,3剂后出院。再如患儿邢某因肺炎、先天性心脏病、慢性心力衰竭、佝偻病入院,经治两月而肺部罗音不消,何老诊断为脾虚肺弱,投六君子汤为主,1周后罗音全除。又如患儿吴某被诊为咽白喉,初治以养阴清肺汤体温反增,何老改用仙方活命饮损益,1剂即热退。又如用增液汤治患儿丁某风湿性心脏病,犀角地黄汤合失笑散治患儿池某过敏性紫斑等,均是妙用时方的佳案。
此外,何老还常将经方、时方合用以治顽疾,如麻杏石甘汤配增液汤为主方治愈麻疹并发肺炎之危症,用桃花汤加味合苏合香丸治愈中毒性痢疾,用白虎汤合银翘散配服安宫牛黄散将患乙脑的赵某由昏迷、抽搐中挽救过来等。何老所创制的许多验方,如肺闭宁、止泻2号、硬肿汤、疏表散等,也均系时方、经方合璧组成。
3 深谙小儿脏腑特性,擅长通里攻下
何老认为中医学对“小儿稚阴稚阳之体”的说法,反映在病理上,有变化快及正不胜邪的倾向。他指出,这种看法不能仅停留在认识阶段,而应当具有预见性和采取防止病机转化的适当措施。不能选方用药一味偏执,戕伐稚阴稚阳,以致变化丛生。何老治疗儿科疾病,紧紧地把握住小儿脏腑独特的生理和病理特点,他精辟地指出:“小儿肝常有余,极易木旺生风。久病伤阴,也能导致虚风内动。心火常炽,受邪易扰清窍。脾常不足,易虚易实,转化较速。肺尤娇嫩,更易邪乘火克。”这种论点对认识小儿复杂的疾病起到提纲挈领、执简驭繁的作用。
小儿急症往往病发突然而又极易骤变,《万氏秘传片玉心书》认为宜“察之既精,治之得理”,指出“外毒急攻,毋令入腹,表邪急解,毋令再传。余则缓而调理,常恐急而生变……”何老在治疗小儿急症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尤擅通过下法以挽危症。下法是中医治疗学的八法之一,早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就有“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的记载。《素问·至真要大论》曰:“留者攻之。”《素问·热论》曰:“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张仲景重视下法的临床应用,创立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等方剂,“釜底抽薪,急下存阴”。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治病“十居八九”用下法取效。《景岳全书·小儿则·总论》曰:“小儿之病非外感风寒,则内伤饮食,以至惊风吐泻,及寒热疳痫之类。”治疗当以袪邪为首要,通过泻下疏通,调理气机,从而扭转病情,达到化险为夷、邪去正安的目的。如刘某患胃炎,呕吐4日,3日不便,脉弦滑,苔白腻,上腹压痛,诊断为痰热结胸,予小陷胸汤(瓜蒌重用25 g)加焦栀子、竹茹、荷梗频服,一剂则便通呕平。9个月的高某患支气管肺炎月余,持续高热,投麻杏石甘汤反致烦躁气急,痰声嘶嘎,便秘,腹胀如鼓。诊断为痰热闭肺,大肠壅塞,认为势必通腑以减腹压,遂投一捻金散及肺闭宁,使痰热随大便畅下而症平。患新生儿肺炎及先天性巨结肠症的李某、高某也均以泄中有补的一捻金散治愈。又如李某因尿毒症进中西药而效果不显,何老便用自拟蟾蜍散(用巴豆14粒分塞两只蟾蜍口中焙干研末)吞服,取巴豆善逐水饮与蟾蜍解毒破瘀相合,疏通三焦之壅滞,尿量大增,此亦可看作釜底抽薪的活用。
吴又可认为“急症急攻”,治病常用下法,擅用大黄,明确指出“得大黄促之而下,实为开门祛贼之法。”对大黄的运用,何老已臻炉火纯青之地,前贤虽有“伤寒当先表后里”、“湿温禁下之过早”等戒,但他并未囿于“表不解不可攻里”之论,每遇外感发热,只要便秘,迳用大黄。如胡某患流感,高热半月,午后热甚,纳呆呕吐,神萎嗜睡,便秘1周,左侧小腹压痛,苔黄褐干,脉沉实,遂用生大黄配枳壳、青蒿、火麻仁、神曲等初服,二诊无效,并未疑惑药证不符,反断为系药轻病重所致,加大生大黄药量,加冲玄明粉。三诊时更增瓜蒌仁,终使便畅热退。非心有定见者难为也。患者王某咽痛数日伴高热烦躁不眠,三日不便,两侧扁桃体红肿且满布脓点,诊为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何老施治中参以生大黄、皂角子、晚蚕砂攻下泄之,2剂顿瘥。再如赵某患乙脑,处于深度昏迷,何老询知其大便黑褐如酱,恶臭,触按腹部有疼痛表情,舌红苔干黑有芒刺,属邪入肠腑、热结旁流,予小承气汤合桃仁、牡丹皮、赤芍、黄芩,煎汁冲紫雪丹鼻饲,终至起死回生。
此外,何老自拟的验方中有近半数均选用了泻下药,如大黄、玄明粉、槟榔、葶苈子、瓜蒌、枳壳、皂角子等。
4 脑病从五脏论治,注重活血化瘀
何老认为,神经、精神疾患统属于脑病。中医学对脑的理论阐释虽然不够系统,但从组织形态及功能方面早已认识到其重要性。《灵枢·海论》云:“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素问·五藏生成》曰:“诸髓者,皆属于脑。”中医的藏象学说把脑的功能分属于五脏而统归于心,认为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肾藏志。《素问·灵兰秘典论》记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特别强调心在精神、意识、思维及情感活动中的主宰作用。因此,中医对神志疾患无不以调神治心为主,根据具体证情,兼治其他脏腑。《医宗金鉴》云:“头为诸阳之首,位居至高,内涵脑髓,脑为元神之府,以统全身者也。”神志活动以脏腑精气作为物质基础,所以临床脑的疾患可以表现为五脏六腑的病症,从而形成脑病从五脏论治的原则。
何老善治脑病闻名于全国,他认为从血论治是治疗脑病的重要方法,其采用活血化瘀法治脑病更有独到之处。何老以活血化瘀法治疗的脑病有眩晕、脑震荡、癔病、脑梗死、神经性头痛等。分析其病证,大多有瘀血阻络之症。何老治疗瘀血证,首先分清实证还是虚中挟实证,后再辨其轻重,结合病位以不同的活血化瘀药治疗。如一头部外伤者,因初诊延误,病变已发展至周身,出现心悸、胸闷、双下肢指凹性水肿,舌质有瘀斑。治以峻方桃仁承气汤,也是治上取下之意。又一癔病患者,由大怒而气滞血瘀,元神不安,治以活血化瘀、安神开窍之法,予血府逐瘀汤。该患者病情较前者为轻,前者舌质有明显瘀斑,此则单见舌质黯。还有一高龄患者,气虚血滞,瘀阻脉络,发生偏瘫,属虚中夹实之候,又病在经络脑窍,故非单一治疗实证之逐瘀法所能获效,因气为血帅,只有益气行血方能化瘀通络。
内伤性头痛相当于西医的高血压、高黏血症、脑震荡后遗症、血管神经性头痛。其病因与遗传因素、精神、饮食、外伤及妇女经期有关。辨证分型有普通型、特殊型两大类,特殊型又分偏瘫型(痰浊阻络型)、定位型(瘀血型)和虚热型(气血亏虚型)。何老认为脑为诸阳之会,又为髓海,所谓火性炎上,巅顶之上惟风可到,故临床上肝阳上亢所化之风及虚风均可上扰头巅,而尤以肝阳上亢为多见,故将其列为普通型。在治疗中善用平肝潜阳之品,并治风先治血,搜风通络活血,何老虽主张引经药的应用,但对于川芎却强调不可多用,用量不过5 g。
何老治疗神经、精神疾患疑难验案很多,包括各型精神疾患、顽固性失眠、雷诺氏病、智力障碍等。
5 小结
何老一生忙于诊务,亲临一线,深知临床实践的需要就是最大的需要,他对中医的研究和运用并未固守前人之说,同时还广泛地汲取了西医的经验和成果。其审证遣药,既严绳墨,又富心裁,一向以辨证精确、药味简廉、疗效显著为世人所称道,成为学验俱丰、享誉津门的中医学家。
R249
A
1672-1519(2012)03-0213-04
天津市高等学校科技发展基金计划项目(20100202),天津市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项目(11026)。
何 山(1969-),男,西医临床学士,中医内科硕士,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中西结合临床和科研工作。
马佐英。
2011-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