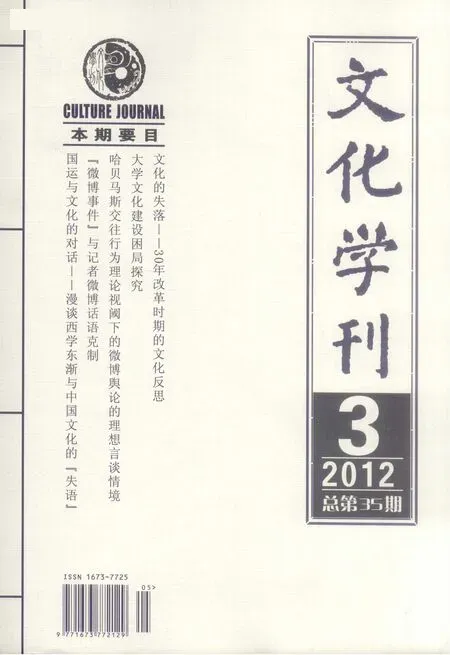陇南白马藏族的“目文化”造型符号研究
2012-05-15余永红
余永红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甘肃 成县 742500)
白马藏族是聚居于甘肃南部、四川北部地区的古老民族,由于该民族无民族文字,加之史料缺乏,因此目前学界对其族属问题还存在争议,其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氐族和藏族之争。由于地域因素的影响,因此白马藏族文化也存在一些地域性差异,四川北部地区的白马藏族受藏族文化的影响颇深,而陇南文县的白马藏族目前还延续和传承着较为原始古老的民俗文化,但从更为深远的民族历史来考察,氐羌民族的历史更为深远,藏族的族源中也有氐羌民族的因素,所以即使白马藏族的民族文化中包含藏族文化因素,也只是后来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而一些更为原始的、本体的、不变的民族文化符号,仍然传承了古老氐羌民族文化特征。所以陇南白马藏族的民俗文化至今依然体现出独特的地域性和原生态文化特征,其民族艺术也体现出原始艺术的综合性特征,是白马藏族民族文化的复合体,由此也决定了他们的美术文化也非纯艺术形式,而是包含在建筑、服饰、面具、刺绣、家具等民间美术类型中。白马藏族美术造型具有本民族独特的形式特征与文化含义,尤其以人物面部造型中的“纵目”、“三目”等“目文化”现象最为独特。
关于“纵目”、“三目”等民族文化符号,目前部分学者已有较多的研究,一般认为这应与西南地域氐羌族系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创世神话有密切联系,这些少数民族的神话虽然各不相同,但其中都普遍提及了 “独眼人”、“直眼人”等;同时《山海经》中也有“一目国”、“深目国”、“三目人”以及烛龙“直目”等奇异形象的描述。关于“三目”形象,《山海经》中有明确的记述,《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而后又云“形天与帝至此争神”[1],形天即为“黥刑”,也称“雕题”,“奇肱国”也是上古时期额上有“立目”造型符号的三目部族。关于“纵目”形象,从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青铜人面像”结合西南地域部分少数民族的傩面具造型来看,古文献所谓“纵目”或“直目”就是眼珠向前凸出的独特造型,所以称为“凸目”更为准确直观,三星堆的“纵目青铜人面像”正是南下西进的氐羌民族后裔蜀王蚕丛的“凸目(其目纵)”形象特征,也是蚕丛部族的图腾符号。
从生物和人类进化的科学角度来考察,这种奇异的“目”造型是不可能存在的,但神话传说中的人类始祖或部族领袖的这种奇异形象,却可以成为氏族的图腾符号,也可能来源于该部族巫傩仪式中的面具装饰[2],并且反应在氏族内部成员的身体装饰或服饰文化中。所以综合来看,这些奇异的“目文化”应与族群的图腾崇拜相关,这些模糊的“目”意象为后期民族文化中的“纵目”、“三目”等文化符号的形成奠定了前期文化基础,并最终演变完善成为后来以额上的“立目”和“凸出的双目”同时并存的“三目神”形象。有学者认为,《山海经》中的一目、三目、直目神话之所以都记载在“海经”中,是因为这些神话都是远古时期生活于西北地域的氐羌族群的神话,从目前民族学、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结果来看,发祥于西北地域的古氐羌族群,是西北乃至西南地域各少数民族的主要源头之一[3],随着这些族群的南下和西进,将其“目文化”也带入西南地域的民族群体中,从而在目前西南地域的彝族、羌族、白马藏族等民族中广泛流传,这些族群正是古代氐羌族群的遗裔,而这些奇异的“目”形象也成为了族群的标志[4],这也正说明古氐羌民族文化融入并深深影响着整个西部地区的各民族文化。

从考古学文化的地层和地域分布情况,结合民族学研究的结论,可以推论是西北地域的氐羌族群创造了辉煌的史前彩陶文化[5],这些彩陶文化的一些纹饰中,也向我们流露出一些与氐羌民族 “目文化”相关的视觉符号。《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有“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的描述[6],作为具有神话性质的历史文献,对氐人的描述显然与现实不符,但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氏族文化符号信息,“人面鱼身”形象也可能是氐人的氏族图腾符号或装饰习俗之一。甘青地区的史前彩陶纹饰中恰有类似的装饰图案,例如出土于甘谷县西坪村的“鲵鱼纹彩陶瓶”文饰,虽然整体造型似鲵,但其实是人格化的氏族图腾,正是“人面鱼身”图腾符号的体现。而且从其形象特征进一步分析,鲵本为4足,而图中鲵鱼只有像手一样的前两足,也与《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无足”的描述一致。再从头部造型分析,鲵鱼的整个头部造型其实就是人的面部造型特征,面部正中的一条竖线和两只格外大而凸出的眼睛,和现实鲵鱼也存在较大差异,可能正是“雕题”与“凸目”造型符号。整个面部下为张开的大嘴,形成张牙舞爪、神秘恐怖的“人面鱼身”的奇异形象,这正是氏族图腾崇拜的实物见证。这件彩陶器物虽然属于仰韶文化类型,但其出土地也是古代氐羌族群聚居地区,应是甘青地区马家窑彩陶文化的前身[7]。马家窑文化后期彩陶图案进一步向抽象化发展,但其中也流露出一些与“目文化”相关的图形符号,例如后期流行的圆圈纹,以及齐家文化、寺洼文化中流行的联体双口罐、联体双口杯、马鞍形双口大耳罐等造型格式,似乎都与氏族图腾“目文化”符号有着某种内在的关系。
作为远古时代氐羌族群中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的民族文化中依然保留了一些鲜明的“目文化”痕迹,虽然随着后来不断的民族融合这些符号有所变异,向装饰化方向发展,但作为主体和核心的符号并没有随着民族文化的融合而泯灭,至今仍然是该民族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图腾符号。白马藏族的这些“目文化”符号主要集中体现在傩面具造型中,宗教造像中也表现得较为突出,另外服饰图案中也有较为明显的痕迹。
一、傩面具中的“目文化”现象
陇南白马藏族每年春节都要跳民族傩舞“池哥昼”和“麻昼”,俗称“面具舞”,因为这种民族傩舞的装饰主要以面具为主,其面具也主要有“池哥昼”面具和“麻昼”面具,前者以代表祖先崇拜的人物面具为主,后者以代表图腾崇拜或自然崇拜的动物面具为主。目前陇南白马藏族各村寨的面具在造型和色彩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综合考察,其中又存在着鲜明突出的共性特征,这种共性特征就是面具造型中的“凸目”和“三目”等“目文化”造型符号特征。

“池哥昼”的角色一般由四个“池哥”、两个“池母”和三个“知玛”组成,“知玛”俗称“猴子”,是逗笑的丑角,只在面部用锅墨进行涂抹和描画,无面具;“池哥”和“池母”是主体。“池母”面具柳眉凤眼,和善慈祥,造型和色彩相对写实,无凸目和立目。“池哥”也称“池哥神”,面具类似于传统戏剧中的净角脸谱,呲牙咧嘴,面目狰狞,以强烈的色彩、怪异的造型凸显出白马文化的神秘,而额头上的纵目以及强烈外凸的双目形成的“三目”形象,则是其典型的民族文化符号,体现了白马藏族源自远古时代氐羌族群“目文化”鲜明的祖先崇拜意识,而崇拜对象就是其民族先祖三目神,也即全体白马人敬拜的祖先“白马老爷。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池哥”面具的额头上都有纵目,第一位“池哥”的纵目较为具体,眼睛造型完整,其他几个“池哥”面具的纵目痕迹依然存在,但明显图案化了。对于“纵目”现象,著名学者赵逵夫先生认为这里的“纵目”正与形天神话有内在的渊源关系,源于古老氐族的雕题遗俗,白马人崇拜的“三目神”其实就是氐族“雕题”遗俗的反映[8],额头上的一只纵目就是雕题遗俗符号。而这种额头正中有“纵目”的“三目神”崇拜也主要流行于甘肃、四川、陕南一带,这些地域正是古代氐杨活动的范围[9]。

除了额上的“纵目”以外,白马藏族“池哥”面具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凸目”,即双目明显突出眼眶以外,体积感格外强烈。目前陇南文县石鸡坝乡堡子坪保存的两件晚清时期的“池哥”面具是整个陇南白马藏族中制作年代最早的面具,虽然雕刻手法粗犷,色彩已剥落,但凸出的双目依然是其最显著特征,而且此面具无额上的纵目,同样类型的古面具在四川南坪地区也有流传,说明“凸目”造型在白马藏族傩面具中也具有悠久历史,同样成为重要的民族文化符号。关于“凸目”的形象问题,《山海经·海外西经》中也有描述:“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10],根据赵逵夫先生考证,“奇肱国”乃为“奇股国”,即独脚人之国,这正好与古体象形文字武都之“武”相合,古体“武”字就是一个形象的独脚人造型,这正是“武都”地名的由来[11],而武都自古就是氐人聚居繁衍之地,所以这里的人不仅为“三目”,而且眼睛“有阴有阳”,郭璞云:“阴在上,阳在下”[12],即额上的立目为阴,下面的双目为阳,阴下陷,阳凸出,这正好与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池哥面具的三目情况相吻合。
这个解释虽然较为圆满,但还存在两个疑问:其一是双目凸出的强烈程度究竟如何?其二是只有凸出的双目而无额上纵目的造型又作如何解释?所以笔者同时以为,《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关于“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文字中[13],同样存在“凸目”形象的有关线索。多数人在此只注意到了形天 “操干戚以舞”的不屈精神,而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造型符号信息“以乳为目”,这也正是其后的民族文化中“凸目”氏族符号的来源之一[14]。形天被砍去了脑袋,面部的三目皆不复存在,但突出的双乳又成为形天独特的双目,后来的氐人为了纪念这位氏族英雄,随名之以 “形天”,并以“凸目”造型符号来纪念其以乳为目、战斗不息的精神。“凸目”标志着形天精神不灭,并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所以形天“凸目”造型也成为氐人图腾意义上的造型符号,体现出鲜明的祖先崇拜意识。

陇南白马藏族 “麻昼”傩舞的角色由两“池哥”、两个“池母”、两个“笑面小鬼”和六个神兽动物构成,但从其角色构成来看,神兽动物是“麻昼”的主体,面具造型也别具特色。从面具内容方面来看神兽动物主要以十二生肖为主,但其中有狮子面具,可见“麻昼”中的神兽并非全为十二生肖,而代表的内容却与十二生肖完全相同,所以“麻昼”中的神兽应是古老的动物图腾崇拜与“十二神兽”、“十二生肖”融合的结果[15],也是民族文化演变与融合的结果。“麻昼”的六个动物面具中,除猪面具以外,其它动物面具都不同程度地突出了“凸目”形象特征,显然是用民族文化中的“目文化”符号对动物面具进行了意象化改造,使其具有人格神的形象特征和精神意味,不仅体现了古老的动物图腾崇拜意识,也融合了白马人的祖先崇拜因素。其中尤以狮子和鸡面具的“凸目”特征更为明显,在陇南白马藏族“麻昼”的6个动物面具中,鸡的造型最为独特,不仅双目格外突出,而且额头上有纵目,这种鲜明的“目文化”也正是他们的祖先“池哥神”面具的造型符号特征。在白马藏族的标志性服饰“沙嘎帽”中,就已体现了对白雄鸡的崇拜,说明白马人已将鸡作为民族的图腾来崇拜,所以使鸡面具包含了更为深厚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除此以外,三目神面具也流行于西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中,这也正反映了其共同的族源以及相同的氏族图腾符号。川滇一带的彝族就有与白马藏族相似的面具,罗婺支系的许多村寨,都有一对由每户人家轮流供奉的始祖面具,其显著特点是凸目、阔嘴、露齿[16],形象特征与陇南白马藏族的池哥面具十分相似,可见这种特殊的“目文化”面具,是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原始符号之一,体现了共同的祖先崇拜意义。
二、服饰图案中的“目文化”痕迹

白马藏族的民族服饰也有本民族独特的个性特征,在结构、装饰、类型等方面完全不同于藏族服饰,服饰的装饰图案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寓意。部分研究者对其图案的形式以及代表的含义已有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该民族服饰中一种最普通但最有代表性的女性服装百折衣背部图形:背部的正中间为一倒三角形的图形,是左右对称结构的分界线,在肩胛部位,用传统刺绣手法装饰两个圆形图案,在整体装饰以抽象的几何形图为主的服装上,显得异常醒目。目前较为一致的解释是圆形团花图案代表月亮,而带圆圈的“米”字图案代表太阳,但目前学术界对这种图案所代表的含义还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多认为这种图案只体现了白马人的自然崇拜意识。但笔者以为,这种图案出现在白马人最具民族特色和代表性的传统服饰中,而且格式相对固定,代代流传,所以并非单纯的以“日月”为主的自然崇拜,其中必然蕴涵着更为本体的民族文化涵义,应具有祖先崇拜的文化寓意。有学者指出,华夏民族共同信仰的最高自然神“天帝”最初也来源于祖先崇拜,而自然崇拜是后来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果,因为在古老的甲骨文中“天”字的象形文字就是完整的人形[17]。所以在民族文化中祖先崇拜比自然崇拜更早,也更本体。笔者以为,日月崇拜只是就圆形图案而言,未从背部整体图案的结构形式综合分析。从整体结构和传达的寓意综合考察,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服饰图案,仍然是古老的雕题遗俗与“以乳为目”之“凸目”形象在白马藏族服饰中的承传与发展,是白马藏族的先祖“三目神”的意象化造型:中间细长的倒三角形显然是 “立目”图形的变异,而左右对称的两个圆形则属于“凸目”,这样解释比单纯的日月崇拜更符合民族文化的本体含义。有些百褶衣在中间的倒三角形中又添加一个圆形图案,从而使中间的立目造型更加具体。从圆形和“米”字图案的造型特征来看,具有日月的象形特征,但这种象形性质是在“凸目”、“三目”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是祖先崇拜向自然崇拜的过渡。
“雕题”习俗也称为“文身”,本身就是一种图腾崇拜形式,原始先民将部族的图腾符号雕刻在身体上,以达到崇拜祖先与保护自身安全的目的。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服饰文化的发达,有些氏族部落则根据本部族的图腾形象来装饰和设计服饰,《山海经》中记述的各种诡异人物造型,虽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也间接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各氏族部落的装饰习俗以及服饰文化[18]。例如“人面鱼身”的氐族部落,也可能是以鱼皮包裹身体以为服饰的民族;“人面鸟身”者,是用鸟的皮毛来装饰身体以为服饰的民族……这种与氏族图腾相关的“文身”习俗以及服饰文化,后来随着农耕文明的发达而逐渐演变为服饰图案。白马藏族服饰图案中的这种独特“目文化”符号,在远古的史前时期亦有可能是部族内部的一种傩面具装饰或纹身习俗,以纪念其部族领袖“形天断首”的英勇事迹。我国的少数民族服饰,无论是色彩、样式还是图案中,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其先民们图腾崇拜的遗迹,承载着各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层的文化意识[19],风格迥异的各民族服饰图案,都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在后来的民族融和中,服饰文化也相互融合,服饰图案逐渐向抽象化发展,但只要我们仔细分析,这些抽象图案中依然隐含着一些原始图腾符号的造型因素。
三、宗教造像中的“目文化”遗留
关于古代氐羌民族宗教造像中的 “目文化”现象,在四川地区古代宗教造像中早已有之:“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磈垒如蚕,金色,头上额中有纵目”[20],这种三目神宗教造像至今依然流行于西北、西南地域的民间宗教美术造像中。陇南白马藏族宗教造像的古迹几乎没有遗存,目前的一些宗教造像主要为现代作品,由白马藏族或汉族的民间画师所制作,具有较为鲜明的“目文化”痕迹。白马藏族的绘画艺术主要以民族宗教绘画为主,多为庙宇壁画和卷轴画,主要有白马老爷、山神、家神等造像,这些神灵也正是白马藏族的祖先神或由祖先神演变而来。这些宗教造像最显著的形象特征也是“纵目”和“凸目”,和傩面具体现出相同的文化含义,只是表现形式以具象造型为主。在白马藏族的宗教绘画中,除部分神灵额头正中明显的 “纵目”以外,对所有神灵的“凸目”也进行了极度的夸张,这些神灵造像眉宫深陷,鼻梁突起,如铜铃般大而圆的眼球格外突出,产生了强烈的立体感。从整个人物造型的基本结构特征分析,反映了白马藏族美术文化的传统延续和共性特征,人物的面部造型与“池哥昼”面具具有相似的符号特征,“凸目”仍是主要的象形符号。
四、余论
总之,这种源自古代氐羌民族文化中奇特的“目文化”符号,在整个西部地域的众多民族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除了独具特色的傩面具以外,有人考证,在西藏、不丹以及巴郎山麓的嘉绒人(古属人后裔),至今尚承袭着“纵目”遗制[21]。同时这种“目文化”符号也广泛流传于陇南地域的汉民族文化艺术中,陇南地域的汉民从更为远古的族源来考察,也与氐羌族群有密切关系,他们的宗教文化中也保留了氐羌民族的宗教文化因素,例如广泛流传于陇南地域的“羊皮扇鼓”傩舞,和他们敬拜的宗教神灵及其造像等。目前陇南汉民敬仰的地方神中,也有三目神“二郎神”和“马王爷”等,二郎神传说为氐族的狩猎神[22],而马王爷也似乎与氐羌民族的游牧文化关系更为密切。陇南民间宗教绘画中马王爷的造像双目圆睁,额上有纵目,威武彪悍,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人物形象特征。由此可知,陇南汉民信仰的三目神“二郎神”和“马王爷”造像的“凸目”与“三目”特征,与远古时代氐羌民族的“目文化”也密切相关,与白马藏族祖先崇拜中的“三目神”同出一源,反映出氐羌民族“目文化”与白马藏族“三目神”的渊源关系,以及对陇南地域宗教美术文化的重要影响。历史记载固然是我们研究白马藏族及其文化的主要依据,但美术造型作为一种视觉文化符号,也包含有民族历史文化基因的传承,在历史文献资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通过美术造型符号解读和探寻民族文化,也是一条可行和可靠的途径。以“凸目”、“三目”等造型构成的“目文化”符号,形成了一条隐约但较为连续的视觉文化链条,同样为我们研究白马藏族历史、文化和艺术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1][6][10][12][13]山海经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5.
[2]郭发明.关于纵目人的传说[J].文史杂志,1987,(1).
[3]段丽波,龚卿.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溯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4).
[4]鹿忆鹿.眼睛的神话从彝族的一目神话、直目神话谈起[J].民族艺术,2002,(3).
[5]李振翼.从地域分布上看马家窑诸文化的族属[J].西藏研究,1996,(3).
[7]张强禄.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J].考古,2002,(1).
[8][11][20]赵逵夫.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氐族地望及“武都”地名的由来[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4).
[9]赵逵夫.从《二郎爷赶山》的传说说到白马人的来源与其民俗文化的价值[J].西北民族研究,2009,(4).
[14]余永红.白马藏族美术文化中的“凸目”现象再探析[J],装饰,2010,(2)
[15]余永红.陇南白马藏族傩面具及装饰的符号特征与文化含义[J].民族艺术研究,2010,(3)
[16][21]黄永林.三星堆青铜直目人面像的历史文化意义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718.
[17]陈筱芳.天神信仰与皇帝[J].社会科学研究,2007,(4).
[18]俞艳庭、李梅.神人以和:上古图腾服饰的审美特征[J].学术论坛,2010,(10).
[19]吴锡标、陈莹静.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图腾崇拜遗存[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22]孙功达.氐族是古代羌族、三苗和东夷族融合的结果[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