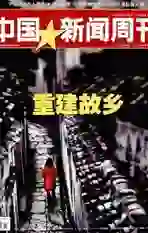匠心王澍
2012-05-14滑璇
滑璇
不鼓励拆迁、不愿意在老房子上“修旧如新”、不喜欢地标性建筑、几乎不做商业项目。王澍始终对潮流保持警惕与拒绝,这使得他备受争议,也更让他独树一帜
中国建筑评论家史建曾为5家中国建筑设计事务所在纽约策划了一个展览。在这个专为专业机构举办的展览中,有一家却叫“业余建筑工作室”。其他建筑师都滔滔不绝地讲解自己的作品,业余工作室的建筑师王澍却不慌不忙铺开一幅李公麟的山水画,对老外讲起了画中的空间布局。
他的讲解让外国建筑师大跌眼镜。他们开始理解,中国传统山水画不仅是在描摹景物,更是一种洞悉世界的角度,甚至展现着某种含有哲学意味的世界观。
从学生时代起,王澍就想把中国山水画的思维方式移植到建筑领域,经过十几年的摸索,终于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建筑思想。这种建筑思想在他49岁时获得了世界级的承认,2012年2月,他获得了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公民。
不鼓励拆迁、不愿意在老房子上“修旧如新”、不喜欢地标性建筑、几乎不做商业项目。在乡村快速城市化、建筑设计产业化的中国,他始终与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使他备受争议,也更让他独树一帜。
“很奇怪,当你真正走上一条独创的道路时,你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无竞争的市场。很多项目摆在面前等着你挑选。”获奖后,王澍这样评价自己的成功,“当一些人重新考虑要不要走我这条道路时,我已经骑着一匹快马绝尘而去,只留下一团烟尘。”
人要过有信念的生活
位于杭州转塘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是王澍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按照传统观念,这里应该没有什么设计,因为50%的土地没有任何建筑,全部是水渠、田地、草木丛生的小山,房子仅仅是环境中的次要因素。但迈进这里,顿感青瓦白墙问流露出书院般的古雅气息。而远离一步,房屋又与环境融为一体,如天作之合。
象山校区工程被分成两期,分阶段完成。王澍回忆,绘制二期的图纸前,脑子里整天都像在“过电影”,各个细节变成一个个分镜头,这样过了三个月电影,他最终只用4个小时就把整幅草图一气呵成。画图时,他也没有借助任何电脑软件,而是按照中国传统绘画方法手工作业,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他自称这套工作流程是“胸有成竹法”。
时不时冒出一些顽念的王澍还故意在校园里造了一幅“画”。一天,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站在3号楼数米高的门洞前往外看,突然说:“咦,这不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么?”
王澍带着孩童恶作剧被发现般的惊喜答:“你发现了?”
当各种学校、写字楼、公寓打着“人性化”的幌子建造奢华时,象山校区却反其道而行,不仅成本低廉——只及普通大学校园造价的一半——就连电梯、空调这样的现代化“必需品”也被限制使用,每栋楼里只有一小块地方设有空调,以供人们需要时使用。
“人要过一种有理念、有信念的生活。”王澍解释。
建筑界中有人认为,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和王澍的象山校区是城市建筑的两个极端,分别代表了现代与传统两种发展方向。然而,普利兹克奖的评审辞中却写道:王澍的作品已然超越了中国城市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应当面向未来”的争论,它唤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
对此,有一个让王澍津津乐道的故事:一位老奶奶4次来到他设计的宁波博物馆,不为看展览,只为寻找曾经的“家”的影子。
宁波博物馆所在地,原有30个小村子,然而随着附近一处被称为“小曼哈顿”的商业区建设,这些村落陆续都被拆毁。王澍在设计和建造宁波博物馆时,有意识地使用了许多这些老村落拆毁后收集到的旧材料,并刻意把它们呈现出来,拼砌成后来颇负盛名的“瓦爿墙”。
,
这使得对许多人来说,宁波博物馆成了一座回忆之城,倾注了王澍心目中“对时间的诗意体会”。博物馆最初建成阶段,他有时也会来到这里,看着那些曾在这里居住过的人们,扶老携幼地前来,对着博物馆指指点点:那一块跟我家原来的墙一个样。
近十年来,王澍无数次感慨自己身处的这个古老国度已被拆得面目全非、丧失了记忆,他不敢想象,照这个速度拆下去,未来的中国什么样?
“再过10年,我们恐怕就没脸说自己生活在中国了。真正存在于生活中的实物都不在了,你凭什么说自己还在中国?”王澍说,“如果生活里真实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活着的老师就已经死光了。”
他并不认可那些封存在博物馆玻璃罩子里的“传统”,那些只是传统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传统一定是活着的”,他说,“而且一旦被切断就很难再承续。”
建筑师首先要是个哲人
这种对传统的向往,或许可以追溯得更久。
王澍的童年正好赶上文革。别的孩子都跑出去“停课闹革命”,只有他,借着母亲是图书管理员的便利,翻遍了几乎所有被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这让他比别的孩子早熟很多,并逐渐产生对同龄人的疏离感。
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读大二时,他就公开宣称“没人可以教我了”;大三时拒绝画商业效果图,还带着同学到教研室谈判。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有几分得意:“关于自由表达,那可是这所学校7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开禁。”
别人睡午觉,他练毛笔字;别人在教室上课,他去图书馆自习;别人研究后现代主义建筑,他四处寻觅后现代主义电影、后现代主义文学。
他还追着沈从文《湘行散记》的脚步走了3个月,但旅行中既不给房子照相、也不搞土地测量,没有一点建筑师的样子。20多年过去了,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做青浪滩的小村,村小的老师就着夜色专程来拜会这位传说中的大学生。“聊得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那里没灯,一个人吹着口琴一路踏歌而来。”
上了研究生,同学们狂读西学时,王澍却写出一篇《当代中国建筑学危机》,强烈批判中国建筑界100年来始终没能形成一股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风气。仅批判社会大环境,他觉得难以到位,就拿大师们下手,从梁思成到自己的导师齐康,业内有几分名气人物几乎都让他数落个遍。
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硕士论文命名:《死屋手记》。答辩前,还特意在教室里挂了自己创作的巨幅黑白抽象作品。论文虽全票通过,却因其言行“狂妄”,学校未授予其硕士学位。但雪藏在东南大学阅览室的论文副本,没过几年就被学弟学妹们翻烂了。有人说它像个寓言,前瞻了中国建筑界未来的20年。
20年后,王澍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并依然保持了学生时代的“另类”。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的学生,要从锯木、挖土、砌墙学起,五年本科学习的重要目标是逐步掌握成为一名工匠的能力。象山校区15号楼的天井里有一堵矩形的墙,每年都是上一拨学生砌完,下一拨学生再推倒重砌。
大一新生刚入学,就要亲手设计并制作一个1:2大小的木凳。那些在家里连倒开水都不会的学生,到了这里照样要拿起
锉刀锯条。有的孩子上课时把手上划的全是小口,依然兴致不减。上学期末,好几个学生拿着自己打造的1:1大小的木凳,兴奋地找到木工课老师陆文宇(王澍的夫人):陆老师陆老师,你快过来坐坐。陆文字往上一坐,“不错,没倒”。
在王澍看来,这并不是以培养工匠的标准来培养建筑师,相反,正如作曲家需对器乐音色和演奏技巧娴熟掌握后方能谱出名曲,能够对建筑材料和建造方法信手拈来,正是成为一名优秀建筑师的基础。少了这两方面的知识,再好的创意也会在实践过程中大打折扣。
为了开阔视野,王澍还经常邀请外国建筑专家来学校上课,专家与主题每年不同。比如2011—2012学年,生土研究方面的国际权威、法国卡代研究中心派出两名研究人员带着一整套实验设备来到象山,为研究生讲授“土壤的手工鉴定方法”,著名的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也送出师资,与本科生探讨气候对建筑营造的影响。
学生们眼中的王澍式教学,多靠一语点拨、当头棒喝帮他们“大彻大悟”,而非你讲我听的填鸭式灌输。
杭州市规划局规划处处长章建明是王澍博士生中的开山弟子,读书时经常跟随“师父”出门会友,绘画、书法、音律、茶道,聚会主题无所不包。一次,他从竹笛的音色中感受出一种远近亲疏的差异感,并将这种感受告诉了王澍。没想不久后,在一次评图讨论时,王澍指引他:还记得上次你对竹子的体会吗?做建筑就要把这种特质和它的品格表现出来。
王澍是在力图恢复一种“想象中的”传统建筑教学,因为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建筑教育”。而在他看来,一个建筑师首先要有某种一以贯之的思想,然后不断用建筑去表达。所以,成为好的建筑师之前,首先应当成为一个“哲人”。
重拾活着的传统
传承传统不只靠设计,还要靠工艺,尤其是用旧砖瓦建造瓦爿墙的工艺技法。
宁波博物馆正式开工前,王澍带着工匠做了一面几百平方米的样墙。可是,现代工匠哪能掌握几十年没人用过的老手艺?刚开始,工匠总按自己的想法揣测王澍的意图,改了又改,还是不对路子。工匠急了:“王老师,你到底想让我们怎么做啊?就做成我们农村家里那样行不行?”“嗳,我就是想要你们做成那样。”
一次,他几天没来工地,一来就看见工匠在墙上像铺瓷砖一样,将瓦片整齐地砌起一大片,“这个不对,你们得拆!”工人一听要大面积返工,眼泪都快出来了。王澍想了想:“这个必须拆,但不用全拆,拆到我能容忍的最大限度吧。”最后,一半的“瓷砖墙”被作为样本保留下来,每天立在那里,以最直观的方式告诉工匠,造成这样不行。
除了宁波博物馆,象山校区也大量运用了瓦片墙工艺。一期、二期加起来,光回收来的旧砖瓦就超过700万片。这些旧材料的价格最早只有新材料的1/10,后来涨到一半,现在大概比新材料还要贵了。不过,近两年市面上的旧材料越来越少,王澍夫妇觉得是好事,“至少说明现在比原来拆得少了呀。”
面对工程中难以避免的建筑拆迁或异地保护,王澍深感无奈。他不无讽刺地把“保护性拆迁”形容为“中国人的创造性”。“故宫会不会也在某一天被整体保护性拆迁?”得奖后在一次公开场合,他尖刻地说:“那里实在是北京城里最好的地段,商机无限。”
王澍设计的房子也不全是旧货,他也会对现代建筑材料重新解读,比如把浇注混凝土时用的竹板放在瓦片下做支撑,或者,混凝土房顶上还覆着旧瓦片,瓦在这里没有任何实际功用,只是一种对传统的演绎。
仔细欣赏过王澍的作品,会发现它完全是一种?昆搭,新旧材料一起使用,起到的效果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不过你别把他想成一个天才,他在自我摸索的过程中也走过不少弯路。”对王澍研究了多年的史建,把他的成功归结为厚积薄发,“他真正做建筑之前,就已经把东西方的建筑理论参透了,所以一出手就是设计理念非常成熟的东西。”
保持内心的宁静
王澍说:“标准化生产的建筑就像资本主义,是以异化的人作为前提进行设计。”
研究生毕业后,同学们纷纷进入京沪大型建筑设计院,融入城市扩张的浪潮。王澍却回到杭州。“北京、上海没有我心目中的中国,而杭州有。”他曾这样解释理由。
刚到杭州,家徒四壁,铺着一张草席,睡在水泥地板上。婚后,他在50平方米的家中探索、演练着一些不甚成熟的想法,比如,用宋代《营造法式》中的榫卯结构自制画桌,在阳台上构造出一个“亭子”…一天夜里,他鬼使神差地琢磨出一套房子一样的木制灯具,八个不尽相同的外罩套着八个尺寸相同的内壳。木工被这个诡异的想法搞昏了头,他只好一点一点手把手地教。当木灯以不同角度安装妥当并放入灯泡时,魔幻般的光线把所有工匠惊得目瞪口呆。
“等我把钱挣够了,就像你这么去做”“等我拿到副教授,就像你这样生活”……昔日同窗这样说,但王澍不以为然,“在那条路上走得太久,沾染了一身习气,就回不了头了。”
为了不沾染那种“习气”,王澍每年只接一两个项目,并将创意和质量的重要性放在数量之上。谈及此次获奖,他说,他并不指望会对中国建筑界带来任何变革或影响,但或许大家可以意识到:“在这种状态下仍然可以思考,仍然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
年近半百的王澍,年轻时的狂傲渐渐变成了淡定、接受与宽容。一次,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恺看到王澍的作品被人肆意篡改,气得在电话里大叫:“你怎么能允许他们这么做?他们知不知道它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是什么位置?竟然就这样把它拆掉一块!”王澍只淡淡地回了一句:这就是中国,这就是现实。
生活中的王澍不用电脑不上网,甚至很少使用手机。他认为那些事物对生活无益,他要保持内心的宁静。
十几次巴黎之行,他每次只去一个地方——圣日尔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一泡就是半天,那是几十年前海明威、萨特静静思考的地方。他说,在那个朴素的街角,他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王澍觉得,这种气息就叫“传统”,“它能让一些东西从过去活到今天,并且一直感染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