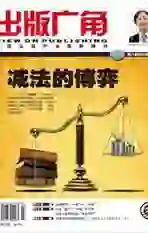流传坊间的诗歌思想史
2012-04-29刘波
林贤治以心贴心、灵魂靠近灵魂的方式,娓娓道出那些诗人的前程往事,解析那些耳熟能详的诗歌经典,这也是本书能够让人读得下去,并读出一种文字之美和思想之力的缘由。
怎样将一本新诗史论著作写得好看,在这个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年代,肯定是有难度的,甚至还会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与尴尬。因为在当下,诗歌本身就是极其小众化的语言艺术,更别提诗歌研究著作了。曾经有个说法,现在的诗歌读者比诗人还少,而诗人也大都被认为属于自娱自乐型的,他们因为圈子化,边缘化,几近被人遗忘。诗歌偶尔为大众所关注,还是以小丑的面目示人:不是以“梨花体”的恶搞让人不耻,就是以“羊羔体”的喧嚣遭人诟病,这到底是诗人有错,还是怪罪读者?我们一时还真难说清楚。或许是时代病了,社会病了,这才有了诗歌之病。
其实,话说回来,诗歌没有病,它只是因其严肃和高贵,渐渐让趋于功利化的社会所难于接纳。如果说绝大多数人都被这个物质化的社会所俘虏,所挟持,那么,只有诗人才是当下时代的“钉子户”。因为他们的天才和敏感,才让句子变得生动,让语言显出活力;因为他们的执著和坚守,才有了与时代对抗的乡愁意绪;只有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主义,才会让这个世界不至于滑向工具理性的无趣和冷漠。诗人或许没有能力做得更多,不能让经济发展,也不能使政治进步,但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美的参照,一种为寻求真相而不懈探索的动力和精神。这正是诗人存在的价值。在我看来,诗人于当下时代,尤其必要。
之所以道出这些言辞和感想,并非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自说自话。在林贤治先生的《中国新诗五十年》里,这些现象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当然,他的言说更精彩,更给人一种力量感。他以论述的方式写诗歌史,这种结构并非其首创,但重要的是,他论的姿态与众不同。当你看多了专业诗歌研究者的长篇大论,再来读林贤治的这本书,确有一种新异之感:鲜活的场面,生动的细节,富有哲思的表达,并留给我们更多想象的空间。他剔除了那些包裹在文本表层的漂亮装饰,而直接进入到了诗歌的内核里,这包括对50年来经典诗歌的推介和评价,也包括对诗人们的理解与期待。
由1949年以来这50年的诗歌,我们也可从中看出一个国家在文化精神上的流变过程,这正是林贤治在本书里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由诗到思,再由思到史,他将一种语言艺术引向思想之境,并以此显出诗歌精神的大气、厚重与瓷实。朱学勤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追问道:20世纪那特殊的年代里,何以有些“民间思想者”后来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而青年诗人朵渔也化用此句,发出召唤:当此时代,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的意思很明确:诗人应该有所担当,而不仅仅是在语言上小打小闹,同时也应该在思想上为我们提供新的价值观。《中国新诗五十年》虽为论诗,但更多的笔墨还是放在这50年新诗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性上,这包括诗歌文本的语言、节奏和艺术美感,更包括诗人的担当、道义与伦理责任。
与纯粹的诗歌理论和评论著作不一样的是,《中国新诗五十年》并没有什么高头讲章式的宏大理论,所以并非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学术专著,它有着鲜明的个性,甚至也有着“一个人的诗歌史”之性情和意趣。当然,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是本书渗透着作者独立的立场和自由主义的文学观,这是一个思想者寻求正义感的投射,也是半个世纪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精神缩影。
这本关于诗歌的书,其实早就在坊间被很多人议论,但一直无缘见到。如今看到它的面世,通读之,确有一种惊喜之感,这并非虚言和过誉之辞。林贤治以心贴心、灵魂靠近灵魂的方式,娓娓道出那些诗人的前程往事,解析那些耳熟能详的诗歌经典,这也是本书能够让人读得下去,并读出一种文字之美和思想之力的缘由。